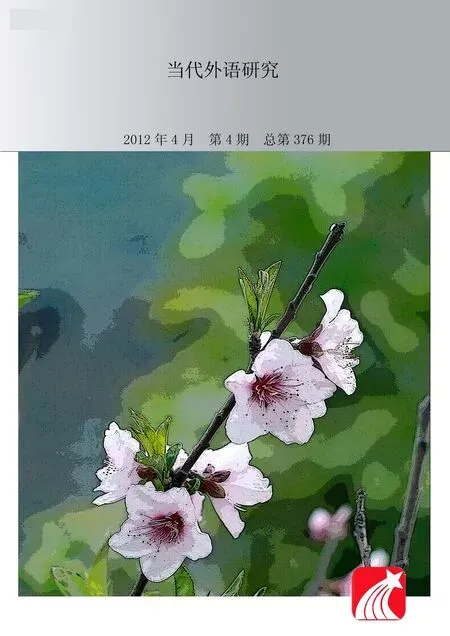作为“思想贸易”原动力的翻译
——斯达尔夫人的翻译思想
朱 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211106)
译者是再创造的能人。通过翻译,他(她)们在两种文学体系之间穿行,如同一座桥梁,把二者联接起来。在《比较文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目的》一文中,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吕迪格提出:“比较文学关注各国文学媒介……,尤其是那些由于宗教和政治原因被迫出走的作家们的活动,这些作家常常无意之间起到一种媒介作用”(转引自谢天振1999:6)。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l 1766~1817)就是这样一个典型。通过译介的方式,斯达尔夫人及其追随者促成了不同文学体系之间的交流。当浪漫主义文学在北欧取得了非凡成就时,法国仍然在新古典主义的泥淖中挣扎。高扬理性和歌颂王权的宫廷文学限制了创作,也桎梏了思想,文学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斯达尔夫人认为,浪漫主义,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浪漫派,是更新南部(法国和意大利)古典文学的力量源泉;更新的手段就是翻译(西蒙2002:276)。她把翻译视为文学变革的动力,主张通过翻译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贸易”。虽然没有发表卷帙浩繁的译作,斯达尔夫人对翻译却有独到的见解,集中体现在《翻译的精神》(Del’espritdestraductions)一文中。
1. 斯达尔夫人及其代表作
Madame de Sta⊇l原名Anne Louise Germaine Necker。父亲为银行家,在路易十六时代任法国财长,母亲是恪守传统的贵妇。Anne出身名门,从小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在母亲主持的沙龙里耳濡目染。20岁那年,她嫁给了瑞典驻法大使Baron Erik de Sta⊇l-Holstein,成为斯达尔夫人。由于年龄和性格差异,这段婚姻没有给Anne带来幸福。婚后不久,她就投身创作。《苔尔芬》(1802)和《柯莉娜》(1807)两部小说塑造了热情奔放的女性形象,描述了她们不幸的爱情和生活经历,受到读者欢迎。
斯达尔夫人在理论上也展现出过人之处。1788年,她发表对卢梭的评论,在文学界引起轰动。1789年,浪漫主义运动顺势而起。斯达尔夫人积极参与,和自由人士聚会并交流思想,先后完成了《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1800)和《论德国与德国人的习俗》(1810)两部作品。前者评论了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深入考察了宗教、风俗、法律三者和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奠定了西方文艺社会学的基础。后者对德国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具体而客观的论述,同时还穿插了英法、英德间的比较。这部作品一方面让德国人看到了一种不受民族感情色彩影响的客观评价,另一方面又使法国人通过比较了解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被视为比较文学的经典(管新福2008)。歌德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推翻了横亘在德国与法国之间的那道墙,穿越了莱茵河,随后又跨越了英吉利海峡,邻人终于了解我们,为我们的影响敞开了大门”(白壁德2002:14)。
斯达尔夫人发现,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与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即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北方文学擅长描写真实的自然、自由的心情以及带有浪漫气质的忧郁,能够激发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与之相比,南方文明程度较高,但理性的增长却造成人性压抑和社会专制,限制了文学发展。经过对比,民族和文学间的差异显现出来,给文学发展带来了生机,增添了创作题材。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民族文学的发展需要相互关联、作用、和学习;经由翻译,软弱静止的民族文学可以从生机勃勃的民族文学那里获得一剂能量,继而焕发青春。斯达尔夫人对欧洲文学的南北划分和渊源关系的追溯,标志着“影响研究”的开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她形成了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和真理的思想,导致了和统治阶层的冲突。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斯达尔夫人的足迹遍布整个欧洲。这种生活不仅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者,也让“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民族的交流工具和思考客体成为她的主要活动”(Simon 1996:62),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起到一种媒介作用。在异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下,斯达尔夫人的作品为法国文学界输入了一种新的翻译感受力(translational sensibility),成为翻译方面不容忽视的“隐形书写”(费小平2005:144);通过翻译,把北部浪漫主义的活力引入南部僵化的文学机制,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文学生命力的跨国流动。
2. 翻译的本质——思想贸易
特殊的经历让斯达尔夫人对翻译形成了不同一般的见解。在《翻译的精神》中,她开篇就赞扬翻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能满足于自己国家的作品和文学传统;文学翻译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输到另一种语言中”(de Sta⊇l 1821/2006:241)。她把翻译看成是“思想贸易”,并且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论证了这种贸易。
回顾人类文明史,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翻译才跨越国境,流传到世界各地,最终得以世代相传。翻译把古希腊文学珍品从拉丁语中拯救出来。与此同时,民族语言也借助翻译获得了新生。斯达尔夫人以意大利为例,讨论了翻译在文学发展中的纵向转换功能。文艺复兴前,拉丁语威慑台伯河两岸。在意大利,很多学者和诗人,比如弗拉卡斯托罗(Fracastoro)、波利希安(Politian)、桑那扎罗(Sannazaro)等,在创作上都沿袭着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和贺拉斯(Horace)的风格。对科学文献而言,使用拉丁语影响不大,因为它们拥有相对固定的文体,无需通过不断变换的风格展现其魅力。但是,这种做法却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文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由于无法读懂拉丁文,古典著作的“盛誉”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和拉丁文相比,人们在生活和创作中更青睐母语。为了让古典作品得到传承,同时也为了滋养母语,对拉丁文献和作品的翻译势在必行。
翻译把饱享盛誉的古代语言和文化带入了羽翼未丰的民族语言之中。通过不断丰富的表达方法,翻译促进了民族语言的裂变;通过把古代经典引入本土体系,翻译开创了民族文学新的空间。和纵向的传承相比,斯达尔夫人更看重翻译在民族文学间的横向联结,并且和歌德、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诺瓦利斯(Novalis)共同论证了促进民族文学发展的贸易模式。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文学必须经常通过对峙、对话和交流来更新自身;文学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只有自由而生机勃勃的民族文化才能生产出最成功的文学来。斯达尔夫人提倡中世纪的转换概念,认为生命力能从一个民族“旅行”到另一个民族,而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精髓已转移到德国并在那里定居。她推崇德国文学,并且不遗余力地把德国作家介绍给富有修养的法国同胞。
在西方,文学民族性的讨论可以上溯到18世纪狂飙运动时期的德国。17世纪末,长期内战让德国陷入了割据分裂和民族国家认同衰退的状态。“文学之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呼吁重视民间诗歌、歌谣、传说和神话,根据国民信仰和趣味,以传统作品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诗风。在其影响下,以歌德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开始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力争在创作中再现民族精神。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和洪堡(Wilhem von Humboldt)特别强调民族语言对于塑造民族性的重要性,提出语言即世界观,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民族性的基础。赫尔德和歌德在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时,并没有走向封闭而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之间平等而相互交流)的理念。在他们的推动下,不同民族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译入德语,德语也因此成为世界文学的媒介,正如勒弗菲尔(Lefevere 1992:24)所言:“那些理解和学习德语的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市场中,世界各国都可以在这里兜售货物。”
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下,斯达尔夫人形成了利用外国文学资源、振兴民族文学的思想。她发现,由施莱格尔(Schlegel)翻译的莎剧,精确而感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德国文学,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当莎剧在剧院上演时,德国观众已不再把它当作英国作品;莎士比亚也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和席勒(Schiller)一样成为自己的同胞”(de Sta⊇l 1821/2006:243)。翻译帮助各个民族更加丰富起来,翻译意味着扩大。和诗歌相比,戏剧的影响力更为突出。当人们把翻译当作创造,而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就可以把其他民族文学的活力变为己有。英国文学在德国的影响证明了翻译的这种创造功能。参照莎剧在德国的成功,斯达尔夫人建议意大利人从法国戏剧中汲取营养。经过翻译,配上意大利演奏模式,拉辛(Racine)作品《阿达莉》(Athalie)在米兰歌剧院可以像原作在巴黎演出时一样产生轰动效应。
作为转述性质的话语,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疆界的交流,也是最具建构力的创造活动。翻译让人类思想跨越时空和疆界而日趋完善。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斯达尔夫人(1986:7)体现出辨证思维:“首先,我并不是说今人的思维能力超过古人,而是说各类思想的总和是与时俱增的;其次,我所指的根本不是某些思想家对不切实际所作的幻想,而是指在各个国家和各个阶级文化的连绵不断的发展”。翻译的本质在于思想的越界和传播,恰如鲁迅先生所言,翻译是打通“运输精神粮食的航道”,它可以拓展文学的思想和表现能力,可以“去聋哑而发新声”。翻译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形式到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转换的背后存在着社会文化的参数和意识形态的航标。
3. 文学和政治变革的动力
在思想贸易的基础上,斯达尔夫人进一步提出,翻译是文学和政治变革的动力(motors of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hange)。这一观点和她的流亡经历关系密切。大革命初期,巴黎陷入动荡。伴随父亲在政坛的起伏,斯达尔夫人出走布鲁塞尔。1793年,由于和当局者意见相左,她被迫到伦敦避难,后随丈夫来到荷兰。雾月政变后,她重归巴黎。1799年,拿破仑攫取政权后,对外推行侵略战争,对内限制思想自由。当言论受限、沙龙被封、朋友失散、作品遭禁,斯达尔夫人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在革命后变成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慑于其特殊身份,拿破仑没有把她投入监狱,但却把巴黎及周边设为她不得逾越的禁区。
1802年,斯达尔夫人回到日内瓦附近的科特派(Coppet)故居,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活。在施莱格尔的陪同下,她先后到过英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当她“不得不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这样就使她那永远活跃的、爱分析的头脑有机会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加以比较”(勃兰兑斯1991:106)。这种特殊经历拓宽了斯达尔夫人的视野,使她有机会突破民族和疆域的界限,对各国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对比,形成了通过翻译推动变革的观点。
在历史上,法国人一度认为本民族是完美的、是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不需要再到北部(德国)野蛮民族中去寻找值得学习的东西。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认为,法国文明比其他国家更加活跃,更具感染性,是欧洲文明画卷的集中表现。他把北方思想的译介看成是“蓬头垢面的野人对文静稳重的民族的入侵”,而译者是用“粗糙原始的野性交换可口的拉丁风味”(Simon 2002:127)。这种自我陶醉的、骄气逼人的心态正是斯达尔夫人感到痛心和希望纠正的。流亡和旅行让斯达尔夫人得以和法国文化传统保持距离。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民族之间要互相借鉴,通过翻译,打破传统和疆界的束缚,实现交流和变革。她(1981:325)坦言:“谁要是剥夺本来可以互相借鉴的智慧,谁就要犯错误。任何人,不管多么高明,都无法猜到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活、呼吸着另一方空气的人脑子里发展着什么;不管在哪个国家,都要对外国思想采取欢迎态度”。
通过浪漫主义思想,斯达尔夫人批判了法国人对古典主义的眷恋和文化优越感,主张从德国等外部文化中引入新鲜血液,并以此打破法语和法国文化的自足性。她想告诫自己的同胞:明察自身的劣势,翻译和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对本族文化的发展格外重要。
借助外来文化和思想,翻译打乱了现存的分类和等级制度,从而开始了陌生化、规范变革、意识形态批评和机制变化的过程。作为实用主义的运动家,斯达尔夫人形成了整套的对峙伦理学(ethics of confrontation),把对峙看作驱动力和构成力。自然法则在道德生活中重现,在那里,内力抵制外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压制内力的永不完结的互动,成为衡量人之真正伟大的尺度(Szmurlo 1991,转引自Simon 2002:126)。翻译从来不以毫无争议的方式进行交流,因为这个过程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代之以本土化的、可以被接受的表述。译者与外来文化建立一种共性,在理解的基础上谋求合作,修正、发展、甚至颠覆传统的观念和习俗。在斯达尔夫人位于科特派的家里,经常聚集着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把大量时间用来讨论和实践翻译。这是一个流动的组合,一个排外和孤立的小组。它积极地与压迫性的政府作斗争,影响遍及整个欧洲。
4. 克服硬化的直译
斯达尔夫人强调翻译的必要性。人不可能学会所有的语言。即便一个人精通外语,翻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够带来“新的颜色、非凡的道理和陌生的美”(Simon 2002:128)。17世纪以来,复古之风在法国盛极一时,不仅表现在大量翻译古典作品,而且围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古今之争”。“有的译者厚古薄今,讲究字随句摹,推崇准确;有的译者则恰恰相反,厚今薄古,任意发挥”(谭载喜2006:87),强调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达布朗考特(d’Ablancourt)是后者的代表。他通晓拉丁语和希腊语,主张翻译在于迎合当代读者。不管原作风格如何,只要译文能够迎合读者口味,就可以不惜代价地任意发挥,而不必顾及原文。
达布朗考特的译笔练达典雅,既隽永俏丽,又通俗易懂,翻译的《编年史》家喻户晓,一版再版。其译法不仅成为仿效的对象,甚至成为法国式翻译的代名词。对此,一些批评家不以为然。梅纳日(Ménage)将这种翻译比为“不忠的美女”(les belles infidels),暗含了对翻译和女性的双重贬抑,引发了后世旷日持久的争论。在翻译中,斯达尔夫人反对“为译文批上华丽的外衣”。在她看来,翻译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采用“法国的方式”——过度修饰,美化译文。这种做法固然能取悦读者,提高译本的接受程度,但对文学发展却毫无益处。译者如果一味迁就读者,就无法从原文中吸取到营养,更谈不上创新,导致译文千篇一律,失去了原文的风格。翻译并不是通过现存的策略合法化而赋予源文学以价值;译者“应该挑战译语规范,通过翻译来促进译语及其文化体系的发展与变革”(Simon 2002:128)。
斯达尔夫人把陈规陋矩视为民族文学衰落的标志,将其比喻为血管的“硬化”(sclerosis)。同时,她指出消除这种硬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长期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南部地区,诗人和文学家坚持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形象。在北欧,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已趋于平庸。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变。斯达尔夫人建议意大利人把目光转向阿尔卑斯山以北,借鉴英、德等国诗歌在创作上的变化,为读者带来全新的作品。“译者一定要摆脱传统方法的桎梏,它们就好比‘官场套话’,让文学和日常语言失去了自然和活力”(de Sta⊇l 1821/2006:243)。翻译不是为了抄袭,而是要了解;不是为了模仿,而是要创新。翻译让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相互交融,相互借鉴;通过吸收新鲜的文化因子,民族文学能够实现自新。
为了把其他民族的活力变为己有,消除日久生成的硬化,斯达尔夫人提倡直译。同时,她也反对硬译。她以荷马译作为例,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荷马听起来不能像现代诗人,他也不能说德语。译者的出路在于忽略文本的时空悖论,创造一个虚幻的译本时空,为相应的读者服务。在荷马译作中,德国人福斯(Voss)的译文被认为是最忠实的。为了在德语中复制古希腊六步格(hexameter),他甚至采用了逐字对译法。这种译文通过音节数量的对等,从形式上唤醒了人们对古希腊的“记忆”,却给译语套上了“枷锁”,丢失了原作的精神。通过对比,斯达尔夫人发现蒙蒂(Monti)对荷马精神的“演绎”更为准确。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她用了一个比喻:“在译诗时,译者不能借助一幅‘圆规’来把握每一处尺寸,而应当把原文精神引入译文,让它在译文中复活”(同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译者要设法实现与原作精神上的契合。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斯达尔夫人提倡直译,这种直译有别于硬译,是灵活的直译,目标直指原作精神。通过翻译,原作生命被带进了译文的崭新领域,译文也在与原作相遇的过程中得到更新。对译者来说,原作是作者本人思想的触点,是他要塑造的形象的来源;译者的价值在于通过翻译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5. 结语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翻译是一种转换,既是从能指到所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在这个流动过程中,人类思想的精髓得到传输。翻译意味着文本具有一种普遍的可读性,能把所指从能指中分离出来,使文本获得继续生存。翻译不仅使读者的数量增加,而且成为发明创造的学校。作为一种越界,翻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是要把两种语言/文化对立起来,而是让二者相互映照、相互强化、相互认同。翻译在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穿梭往返,其目的在于互惠。斯达尔夫人把翻译视为思想贸易的本质因素,通过翻译,揭示了变化中的文学和文化关系。翻译总是在边界上嬉戏,对边界或造成威胁,或予以肯定。当边界概念日益淡化,文化差异取而代之,正日益变为共有,并转化为文化认同。在斯达尔夫人看来,翻译是一种批判和介入的活动。通过促进某些文学价值,通过在新的环境内相互作用,通过变革,翻译产生文化效益。伴随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斯达尔夫人以交流和互惠为特色的翻译思想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
de Sta⊇l, Germaine. 1821. On the spirit of translation [A]. In Robinson, D. (ed.). 2006.WesternTranslationTheory:FromHerodotustoNietzsche[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41-44.
Lefevere, A. 1992.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Simon, S. 1996.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Simon, S. 2002. Germaine de Sta⊇l and Gayatri Spivak: Culture brokers [A]. In Tymoczko, M. & Gentzler, E. (eds.).TranslationandPower[C].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22-41.
勃兰兑斯.1991.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费小平.2005.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管新福.2008.斯达尔夫人的比较文学观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89-93.
欧文·白壁德.2002.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学宜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达尔夫人.1981.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斯达尔夫人.1986.论文学(徐继曾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谭载喜.2006.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谢天振.1999.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雪莉·西蒙.2002.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和加亚特里·斯皮瓦:文化掮客[A].陈永国.2005.翻译与后现代性[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7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