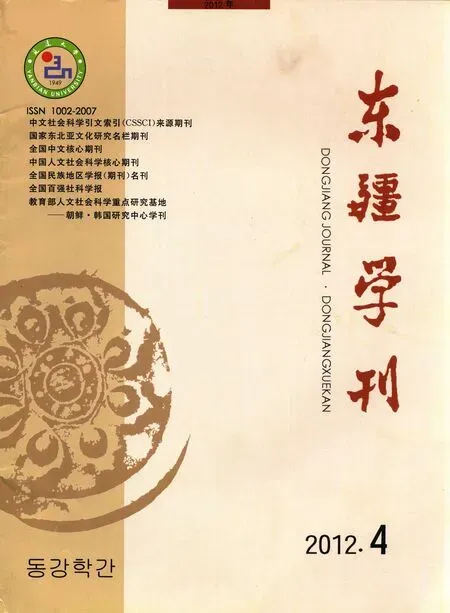“利他”的文化渊源及其概念界定
周 纯
“利他”,作为一种人类美德的体现,一直是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焦点。早在该词语被创造出来之前,诸多学者就对“利他”的内容做过相关阐述,比如康德所提倡的责任论,“尽自己之所能对人做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1](47)。这里的利人之说,究其本质而言,与“利他”的含义十分接近。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针对利己 (egolism)的概念 ,结合拉丁语中“外在的”(alter)词源,创造出了““利他”(altruism)”一词,这也是公认的“利他”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的产生。孔德认为,“‘利他’是一种为他人而生活的愿望或倾向”[2](566-567),是一种与利己相对应的倾向,“利他”主义所强调的是他人的利益,提倡那种为了增进他人的福利而牺牲自我利益的奉献精神。
但早在“利他”概念被明确创造出来之前,不管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探讨中,还是在宗教信仰的具体教义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对于“利他”概念的思考与探索。此时所探讨的“利他”,一般被冠之以诸多其他的名义 ,如“仁”、“兼爱”、“爱”、“慈悲”等,大都体现了“利他”的本质所在,即超脱于个体自身利益之外,强调对于他人的关心和考虑,为增进他人的利益和幸福而行动,并且此时所推崇的“利他”,大多是一种纯粹性的无私“利他”。此阶段所研究的“利他”性与文化的道德要求、宗教的教义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对于个体和教众在思想和行为层面的要求,有时甚至成为一种被宣扬的理想状态。一般而言,这一阶段中有关“利他”的阐述,被视为“利他”的思想文化渊源,具体主要表现为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两大方面。
一、哲学思想中的“利他”主义
在二十世纪之前,“利他”性研究更多地被冠之以“善意”、“友好”、“美德”等指称而发散开来,“利他”与道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顾早期的文化起源,无论是在西方先贤的道德哲学论著中,还是在中国儒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的讨论中,关于人类“利他”性的思考都无处不在。在西方的道德哲学论述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康德“责任论”的观点。康德将人的利人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帮助他人,即为己利人,虽然其行为也是符合责任的要求;另一类则是单纯从责任出发,完全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去帮助别人,即无私利人。“在康德看来,只有出于职责的无私行为才可以称为责任”[3](12-20)。
此处可以看出,虽然在康德的笔下并没有直接出现“利他”这一概念,但是这种“利人”、帮助他人的叙述,完全等同于“利他”的概念,并且其对于为己利人和无私利人的划分与现代“利他”科学研究中对于“利他”的类别划分不谋而合,都是在共同强调“利他”行为的“利他”动机与利己动机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分类。康德对于无私利人的推崇,更直接地体现在其对于促进他人幸福的阐述之中。“我应该努力提高他人的幸福,并不是从他人幸福的实现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论是通过直接爱好,还是间接理性得来的满足,仅仅是因为,一个排斥他人幸福的准则,在同一意愿中,就不能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1](95)进一步而言,在康德的义务哲学中,所谓的“利他”必须是,也只能是出于无私的责任所产生的帮助他人的态度与行为。那些为了个人的利益,哪怕是内心的情绪满足这样的隐性利益,也是不符合其所推崇的“利他”概念的,也就是所谓的绝对“利他”主义的观点。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对于“利他”的界定也是十分丰富的。孔子所提倡的“仁”的概念无疑就是“利他”,“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197),仁者爱人,“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5](110)。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所提倡的“仁”与康德的“义务责任”一样,强调的都是要去除自己的私利,不能从自身的利益满足出发去利人,而是要从他人利益的角度去帮助他人,甚至是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进他人的利益,“舍生求仁”。“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要人们除掉一些自私自利的心计,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6](88-89)此外,墨子的诸多著述中也涉及到对“利他”的界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其兼爱非攻的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7](76)所有人应该“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7](85)。与孔子的无私“利他”思想一样,墨子也认为“利他”就是那种出于对他人的关爱而做出的帮助他人的行为,将他人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将他人的问题当做自身的问题,尽己所能来帮助他人。与孔墨强调“利他”必须是不为己的无私“利他”观点不同的是老子所提出的“道”的观点。在老子的思想中,道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他所推崇的“利他”是一种在实现途径中不考虑自身利益去帮助别人,但在最终结果上却对自己有利的形式,即不为己的“利他”最终有利于己。“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8](11)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利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自身的发展,从其对于圣人的叙述中就可见一斑,“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8](162)
在中西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利他”一直处于讨论与关注的中心位置。“利他”是要帮助他人,提高他人的利益,增进他人的幸福感,克制只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幸福的极端利己欲望。对于“利他”内涵的这种界定,无论是在中国的儒家、墨家和道家,还是在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哲学,都表现出一致性。其主要的分歧在于“利他”行为的动机内容。一种是强调只有动机“利他”的“利他”行为才是社会所要大力提倡的,是道德伦理的中心内容,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利他”是不值得,也不应该被广泛讨论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包括中国的儒墨和西方的康德哲学;另一种则不反对出于利己的“利他”行为,认为“利他”和利己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区别,并应该把二者切断开来,“利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个体自身上来,同意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道家的老子。
此阶段中,虽然“利他”的概念没有被创造出来,没有在传统文化的著述中直接出现“利他”这一指称,但是有关“利他”的讨论源源不断。此时对于“利他”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楚,是一种比较含糊的,在总体层面上展开的泛泛阐述。“利他”的代名词也是多种多样,如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康德的“责任”等等。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虽然在结果上都体现为“利他”的形式,但是却依然区别很大。社会所要提倡的“利他”必须是无私“利他”,是排除了自身利益,单纯为了增进他人利益的“利他”。这种界定带有非常浓重的道德伦理的教化色彩,与其所来源的思想文化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联系。虽然此时对于“利他”概念的界定并没有一个统一清楚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文字阐述,但是已经开始涉及到“利他”概念中的核心问题,即“利他”行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利己的动机所产生的“利他”行为与“利他”动机所产生的“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利他”分析在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积淀,为当前“利他”概念的清楚界定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来源。
二、宗教信仰中的“利他”性要求
“利他”与宗教之间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些宗教思想的论述中就有直接涉及到“利他”的部分,包括教化信仰者去从事“利他”的行为,培养“利他”的态度,增进“利他”的动机等等。不为自己而为他人,甚至为他人牺牲自己成为许多宗教的信条之一,较具代表性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和东方的大乘佛教。
在基督教思想中,“利他”的概念讨论是直接通过对与“爱”(charity)的理念的表述展开的。此词最早出现在“新约”中,希腊语为agape,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最高、最纯粹的爱,即圣爱,用来表示上帝对人的爱;另一是指信徒之间的兄弟之爱”。[9](80-85)这两种类型的爱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密不可分的,上帝对人的爱要求他的信徒去彼此相爱,彼此“利他”,只有这种信徒之间的兄弟之爱,才可以体现出信徒本身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教教义的接受与诚服。“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兄弟。”[10](237)此处的“爱”这一理念,就其指向对象而言,就是增进他人的利益,提高他人的幸福,为了他人而奉献乃至牺牲自己。兄弟之爱就等同于“利他”的概念。
在《简明基督教全书》中,爱的词条解释是:“charity(爱),代表舍己,以他人为中心的爱”[11](245)。这种以他人为指向对象的“利他”就暗含着无私“利他”的指涉。也就是说,基督教中所提倡的“爱”,所提倡的“利他”,是一种从他人的角度出发,为了他人的幸福与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态度与行动,它排除了增进自身利益的功利目的,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因此,基督教中所指涉的“利他”,和儒家、墨家以及康德观点中的“利他”一样,强调的是超越自身利益之外,出于对他人利益和幸福的关心形成的有利于他人的态度与行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教义中的“利他”与传统文化中的“利他”完全相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亦即上帝的存在,上帝对所有人的爱是个体无私“利他”的终极来源。
在东方社会中,对“利他”阐述比较多的是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慈悲”、“利他”的思想,它也被称作“自利”、“利他”。对于此概念的解释,在《佛学小词典》中有非常清楚的体现,“上求菩提,自利也;下化众生,‘利他’也;声闻缘觉之行,唯自利;诸佛菩萨之行,兼利也”。[12](42-44)此处的自利并不等同于目前所说的利己,而是强调个体自身的一种解脱,一种脱离自身的凡夫俗子之身、修炼成菩萨的结果。佛教所强调的终极目标在于个体的修炼,可以说自利是这一目标的典型体现。自大乘佛教传播以来 ,“利他”开始进入佛教教义之中,并得到极为广泛的推崇,“利他”成为自利最主要的途径,即只有在尘世间普罗大众,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帮助他人,做出各种“利他”行为,才是教徒修炼为菩萨的终极途径。
佛教推崇普度众生,强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帮助他人,造福大众,不关心可能得到的回报。大乘佛教中指涉的“利他”是一种普世性的、不求回报的助人行为,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个体自身的解脱,关注的是个体的行动与心灵信仰之间的关系。“当你行救济时,没有救济的对象,也不是为了想要救济的悲愿,只是随顺众生的需要、需求,随缘救济众生;纵然度尽众生皆出苦海,也是众生的自救自度,不会以为自己对于众生做了救济工作。”[13]大乘佛教中“自利”“利他”的“利他”,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助人行为,而是特指那种在自利基础上的“利他”,即不仅要帮助人,而且不能抱着从主体想帮助人的心态去帮助人,而是要脱离、超脱本人的思考角度,从他人的需求出发,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去增进他人的幸福,要在自己的心态解脱的基础上去做“利他”行为。 此处的“自利”“利他”,虽然冠之以“自利”的名号,但其指涉的内容与儒家、墨家所提到的“无私”“利他”更加相似,只不过一个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思考,一个是从宗教信仰中个体的超脱心灵角度去探讨而已。
从“利他”的角度看,基督教与大乘佛教都强调“利他”必须指向他人的利益,强调一种不求他人回报、不期待任何外在奖赏的“利他”,“利他”是起源于个体信仰体系的。基督教认为,“利他”起源于上帝之爱和兄弟之爱的互动,只有关爱他人才能体现个体对于上帝之爱的回应,才能使个体在彼岸生活中赎清原罪。大乘佛教则认为,“利他”的产生是基于个体与其自身的超脱肉体的心灵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帮助他人,才能使自己在尘世中的修炼达致脱俗状态,才能实现彼岸世界中的佛陀、菩萨的境界。彼岸世界和个体信仰的增进是“利他”的根本出发点,它体现了宗教本身的特点对于“利他”的影响作用;从“利他”的对象范围看,基督教和大乘佛教都强调,“利他”是针对所有人的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是普适性的。无论是基督教中的“兄弟之爱”,还是大乘佛教中的“普度众生”,此处所推崇的“利他”是一种无差序的、普遍平等性的、帮助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它脱离了世俗色彩,这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差序式”“利他”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而言之,宗教中所界定的“利他”由超脱个体本身的力量所推动,一般表现为信仰的力量,是指向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没有任何等级差别的增进他人利益和幸福且不求回报的态度和行动。此处的“利他”,并非目的,而是充当了个体宗教信仰中终极价值目的的一种手段,具有极端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总而言之,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利他”性阐述,揭示了“利他”概念最本质的要求,强调的是崇高、纯粹、无私、不求回报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讨论内容的集中也限制了从其他角度对于“利他”的理解,并且此时的“利他”讨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非常松散含糊的讨论,没有形成对“利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确界定,只是一些宽泛的观点、观念,是一些涉及到“利他”内容的引导性描述。但是这种空缺在现代科学领域中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尤其是在孔德创造“利他”一词之后,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对“利他”进行了极为详实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理论观点,也逐渐形成了各种对于“利他”概念的清晰界定。
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利他”概念的界定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在提出“利他”时强调一种利己主义对立面的概念,将“利他”界定为“一种真诚地并形成习惯的做好事的意愿,或者是为他人生活与存在的行为倾向”,[14](40)强调的是增进他人的幸福和利益,甚至可以以牺牲自身为代价。从这个定义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德所提的“利他”,是一个态度与行为的统一体。他最大的贡献之处在于使得“利他”这一概念终于脱离了宽泛的思想讨论,获得了独立的概念定义。其开始使用“‘利他’—— 利己”这一对立的模式概念来解释人类的各种行为。继孔德之后,包括涂尔干、韦伯等人在内的诸多社会学大师在其论述中也或多或少地提到“利他”,比如涂尔干提出的“‘利他’主义自杀”等。之后最引人注意的应该是索罗金对于“创造性‘利他’”的研究,他将“利他”定义为“一种为他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增进和维持利益的行动,是由爱和移情所塑造出来的,并且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可能需要个体为他人无偿地牺牲自己的全部”[14](44)。这一界定更多地强调“利他”的具体行为表现,以及个体为“利他”行动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在社会生物学领域中,为了理清这种表面上看来完全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现象,诸多学者针对“利他”这一问题,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讨论与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尔逊和特里弗斯对于“利他”行为的界定。威尔逊认为,“当一个个体以牺牲自己的适应来增加、促进和提高另一个个体的适应时,那就是‘利他’主义行为”。[15](125)其中衡量个体适应的标准,是指其所留存的“后代的存活量”,包括数量与质量两方面,即后代的人数与其个人的发展程度。他将“利他”主义行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有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即“‘利他’者期望社会为自己或其亲属获得报酬”[15](141),其帮助他人的行为是一种个体有意识的利益权衡之后的行动决策,是在个体选择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受到文化进化的影响,被称为软核(soft-core)型的“利他”;另一种则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即“‘利他’主义的冲动可能是非理智的,单方面为了别人,贡献者无意要求同样的回报,也不为了得到报酬而有意识地做什么”[15](141),这种类型的“利他”一般不太容易受到社会奖励或者惩罚的影响,被称为硬核(hard-core)型的“利他”。
此外,在社会生物学领域比较重要的还有特里弗斯对于“利他”行为的界定,他认为“‘利他’行为是那种有利于与个体关系并不十分亲密的其他生物体的行动,且这种行动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不利于行动主体的后果,此处的有利与不利的程度是以对生物总体适应性的贡献度来衡量的”[16](35)。特里弗斯与威尔逊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利他”行动所指向的对象应该是一个与行动主体关系并不密切的他人,而非与个体分享血缘关系的亲友。当个体去救一个落水的男孩时,如果这个男孩与个体关系并不密切,则个体的营救行为可以被称为“利他”行为;但是当这个男孩是个体的儿子时,这种行为就不一定符合“利他”行为的界定,很有可能只是个体为了延续其基因而做出的投资行为。这种排除亲缘关系的“利他”行为的界定,究其本源而言,是为了特里弗斯所提出的互惠“利他”模型而服务的,不过也引发了一些学者关于“‘利他’行为指向对象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何处”的讨论。
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利他”做出了概念的界定,马格鲁伊斯(Margolis)认为,“利他”行为是指那种“个体出于考虑其行动对他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放弃去做那些对其本身有益的行为”[17](29);在研究囚徒困境的社会博弈理论中,李班德(Liebrand)将“利他”主义行动者界定为那些“在进行行动决策时,更加看重他人的需要和利益,而非自己所需要付出的代价”[17](29);西蒙认为,“如果为了另一个人的财富或权力而牺牲了自己的财富或权力,那么行为就是‘利他’主义的,如果寻求最大化财富或权力,则行为就是自私的”[18](4);贝克尔则将“利他”界定为“一个人因其他人的效用增进而感到高兴,或者是从对他人所做的财务或劳务无偿支出中获得满足”[19](337-342)。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对于“利他”的定义非常强调该行为对行动主体所带来的后果,强调“利他”行为对其接受者所产生的利益增加,并且没有将个体可能从“利他”行为中获得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这一条件排除在定义之外。这是由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经济人”假设的大前提下,经济学家对于“利他”的研究更多的是作为利己的补充和调整而展开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贝克尔将“利他”也纳入到人类的偏好之中,将“利他”与利己结合起来,共同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出发点。
中国的经济学家基本沿袭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利他”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明确细化了“利他”概念的分类。如叶航将“利他”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20](22-23)三种类型;杨春学则将“利他”分为两大部分,即“具有亲缘关系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和非亲缘关系者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21](82);胡石清、乌家培则在叶航的分类基础上增添了一个新的类别,“从广度上分,‘利他’行为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 惠‘利他’、纯粹‘利他’以及强互惠‘利他’”[22](4);张旭坤则使用了四个衡量维度来给“利他”行为进行分类,“一是纯度,是纯粹‘利他’还是有利己动机;二是程度,是倾囊相助,还是有所保留;三是广度,是普度众生,还是只施惠于特定人群;四是频度,是经常为之,还是偶尔为之”[23](14)。基本上说,这些不同的分类还是沿袭了威尔逊关于“软核和硬核‘利他’”的大方向,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化了,经济学学者们主要围绕着论述“软核型‘利他’”,即期待对方或社会回报的“互惠‘利他’”展开的。
另外一个对“利他”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学科就是社会心理学。与社会生物学、经济学中对于“利他”行为结果的强调不同,社会心理学家更加强调“利他”的动机问题,强调“利他”行为主体本身的自觉自愿性。比较公认的一个对于“利他”的界定来自于 Bar-Tal,“利他”主义的行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必须对他人有益,必须是个体自愿进行的,必须是个体有意识地开展的,增进他人利益必须是该行为的目的,且个体在做出行动时并不期待任何外在的奖赏和回报”[17](30)。由上可知,经济学对于“利他”的界定更倾向于强调行动带给行动主体和行动对象的后果,包括利益的增加或减少,而社会心理学的界定则更为强调行动背后的动机,强调行动主体的自觉自愿性和不求回报的动机,因此,索伯(E.sober)将“利他”分为两大类型,即“进化主义的‘利他’”(evolutionary altruism)和“本土主义的‘利他’”(vernacular altruism),前者强调“利他”行动的客观结果,后者则着重于“利他”行动的主观动机。简而言之,在社会心理学研究视野下的“利他”,一般被界定为不仅要在实际结果上有利于行动对象,而且这种有利必须是行动主体本身所自觉自愿产生的,并且不是因为期待行动对象或者外在的社会所给予的回报而去从事这种行为。此处的“利他”界定,基本上把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中所关注的互惠型的“利他”排除在“利他”的概念界定之外,更加类似于前者所提出的纯粹性的“利他”的分类。
除了上面涉及到的几个主要讨论“利他”的学科之外,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也存在各种对于“利他”的探讨与研究。比较重要的有克里斯滕·门罗(Kristen Renwick Monroe)在《“利他”的本质:对于普遍人性的理解》一书中对于“利他”所做的界定,即“‘利他’是那种自愿去帮助他人的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极有可能导致行动者本身利益的损害和牺牲”[24](6)。在这个定义中,门罗强调“‘利他’一定要涉及到具体的行动,行动的目的必须是改善他人的处境,行动的动机比行动的结果更为重要,行动一定存在可能给行动主体带来利益损害的不利结果,且‘利他’行动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可言,不是由于期待回报与奖赏而产生的”[24](6-7)。这个界定类似于无私纯粹“利他”的概念,不过门罗提出了一个“准‘利他’行为”的概念,指那些符合一部分“利他”概念描述特点的行动。同时,门罗将人类的所有行为视为一个连续统的存在,一端是极端的利己,即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另一端则是其所界定的“利他”,而准“利他”行为则是处于二者之间,从利己这一端持续不断地向“利他”的方向进行过渡与转化。这种连续统概念的提出,避免了将利己与“利他”绝对对立起来的二元分割,有助于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了解与分析人类社会中现有的“利他”现象。
与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教义对于“利他”的阐述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赋予了“利他”清晰的概念界定,使其从宽泛的哲学思辨和道德教化中独立出来,有了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当前对于“利他”概念的许多界定更多地着眼在对于“利他”行为的描述方面,倾向于从行动特征的角度去界定“利他”。现有的概念界定基本上都同意一点,即“利他”一定是有助于除个体之外的其他生物体的利益、幸福和福利的增进和改善,并且都存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如果一种行动可以被称为“利他”的,则其必定对他人有利,同样,一种“利他”态度必然是同意、赞同或者认可这种有利于他人的行动的观点和看法。
四、小结
虽然“利他”在哲学思想、宗教教义与社科研究中的具体分析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对“利他”的宽泛讨论,体现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对于“利他”的具体要求,提倡的是一种近乎理想型的“利他”行为,无私的纯粹性“利他”是这种文化渊源的主要内容;但在近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利他”的概念得到了非常清楚的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开始逐渐清晰化。虽然在社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学科对于“利他”的概念界定也有诸多差异,尤其是在“利他”概念外延界定的问题上,“利他”性是否需要“利他”动机和行为二者并存的讨论成为各学科分歧的焦点,但是从所有学科中“利他”概念界定的共同内容角度而言,现有的“利他”概念界定与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的内容仍然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只不过前者将后者对于纯粹无私“利他”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并且依据学科不同将这种纯粹“利他”放在了整体“利他”概念的不同位置之中。总而言之,“利他”概念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在狭义的概念界定中,只有那种在起因上不追求个人利益回报,不期待未来可能获得的奖赏,一心只是为了增加他人利益,并且是主体自觉自愿、有意识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与态度才可以被称为“利他”;而在广义的层次中,只要一种行动和态度在客观的结果中有助于他人福利的改善和利益的增加,就符合“利他”的概念的界定。最终,无论是哪种层次中的“利他”概念,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与秩序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研究“利他”概念界定的最终意义所在。
[1][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丽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Comte,I.Auguste.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2vols.).London:Longmans,Green&Co.1875.
[3]王海明:《“利他”主义重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 3期。
[4]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5]朱熹:《孟子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6]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7]施明译注,《墨子》,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年。
[8]沙少海,徐子宏译注 ,《老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9]刘林海:《从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济贫观念的变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6期,总第 210期。
[10][美 ]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约翰福音》,基督教内部资料,2003年。
[11][美 ]泰勒:《简明基督教全书》,李云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林君希:《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思想述评》,《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4年第 3期 ,总第 65期。
[13]圣严法师:《慈悲——心灵环保的最高原则》,《龙泉佛学》,2006年第 3期。
[14]Elvira del Pozo,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ltruism:the case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Michig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2,Vol.16.
[15][美 ]威尔逊,Wilson,E.:《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阳河清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Robert L.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Vol.46,No.1.
[17]Jane Allyn Piliavin and Hong-Wen Charng,A Review ofRecentTheory and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0,Vol.16.
[18][美 ]赫伯特· 西蒙:《西蒙选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美 ]加里· S·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20]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家》,2005年第 3期。
[21]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经济研究》,2001年第 4期。
[22]胡石清,乌家培:《从“利他”性到社会理性——“利他”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综合观点》,《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 6期。
[23]张旭昆:《试析“利他”行为的不同类型及其原因》,《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 4期。
[24]Kristen Renwick Monroe,The heart of altruism:perceptionsof a common human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