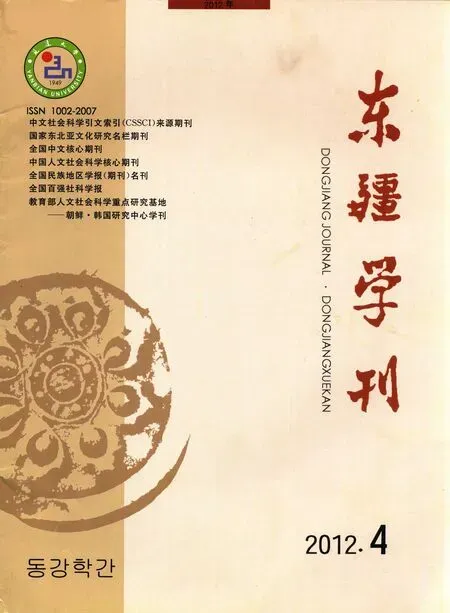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
金柄珉,崔 一
狭义的“东亚文学”是指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文学。中韩日三国同属于“儒教文化圈”或“汉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之间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从“儒教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等范畴界定就能够看出,在言及东亚文化交流关系时,人们往往把中国视为“发信者”,而将韩国和日本视为“受信者”。自然,这种观点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笔者在此要着重阐明的不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而是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为此,首先要界定“东亚文学”的概念。界定“东亚文学”的概念范畴,必须明确以下几点:首先,东亚文学是东方乃至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主要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一部以儒释道文化为精神支柱的东亚精神文明的记录。其次,东亚文学的长足发展得益于该地域各国文学特有的传统及其互动。这既是东亚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最后,东亚文学的互动包括直接对话和潜在对话这两种方式。直接对话包括通过人际交往和文献交流所进行的实质性的对话以及思想、价值观的相互影响等精神层面的对话。潜在对话源于地理(地域的相邻性、自然环境)、人文(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价值观)语境的相通性,潜在对话可以通过对相同题材和主题的比较等互文性的分析加以阐明。
研究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不仅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在广义上它也是谋求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有益实践。在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面临着被资本这一“洪水猛兽”吞噬的危险,因此,研究东亚文学的互动和生成,有助于发现东亚的文化价值,确立东亚文化的新关系,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如黄俊杰曾提出,东亚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从“结果到过程”、“从中心到边缘”视觉转换的观点。[1](167~168)
鉴于东亚文学的上述特性,就其研究的方法论,可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摆脱一味地关注结果的研究范式,转而细致地考察和解读东亚文学互动的过程。以汉字作为共同文字是东亚各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人们在对待东亚文学时就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观点——“中国文学是东亚文学之‘本’,其他文学都是‘表’”。 其实,中国文学也是由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也是在与周边诸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东亚文化的多元互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凭借对结果的研究显然无法探明新的规律和特性。例如,鲁迅、郭沫若的文学与日本,胡适、闻一多的文学与美国,这些都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冲突和融合的产物。“自我”的觉醒和完善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实现的。“自我”的觉醒是认识“他者”的前提,而“自我”与“他者”的接触与交流又是引发“自我”觉醒的要因。总而言之,考察东亚各国文学间的互动关系,相比起只单纯考察其结果、追踪和探明其过程更为有效。
其次,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向。一般来说,从中心向边缘的辐射是文化交流的普遍现象。但是,文化交流在多数情况下又是双向的,纯粹单向性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文化的输出难免要伴随着输入,同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引发“误读”现象,而“误读”本身既是一种变异,也是一种再创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逆向思维,从边缘发现中心的本源价值和潜在价值。例如,儒家和佛教思想在日本的变异,尤其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之间的结合。《源氏物语》的主人公源氏的形象就是典型个案。再如,“程朱理学”传入朝鲜之后,李(退溪)对其加以全新的阐释。朝鲜“北学派”文人洪大容来到中国接触到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天文思想,从而进一步阐发了独特的天文思想。从中心向边缘的视角转换,有利于更好地解读东亚文化的合力与张力,这种“去中心主义”的视角还有利于确立“和而不同”的价值观,进而阐明多元共存这一东亚文化的重要特征。
通过这种方法论的转换,我们可以重新解读东亚文学及文化,阐释其互动与生成的过程,以崭新的视角发现新规律。互动意味着对话与交流;生成意味着“嫁接”与创新。互动是过程,而生成是结果。环顾东亚发展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互动,东亚文学与文化才得以更加光辉灿烂,才得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才得以实现更具普世性的文化价值。
在下面,笔者将从异国体验叙事、文本传播、潜在对话三个方面考察东亚文学的互动与生成现象。
一、异国体验叙事
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的体验的产物。不管它是劳动体验,还是宗教体验,都是源于人的生活体验,因此,文学创作可概括为“生活体验(或者经验)→体验的升华→象征化”,体验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文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异国体验在文学研究中备受瞩目。
异国体验是人通过空间的移动获得的有关他国文化的经验,同时又是通过“域外视角”反观自我的过程,即“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的过程。在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异国体验文学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文化对话、融合、共存和创造。异国体验文学是一种通过域外视角对本土(local)的反观,因此,异国体验可谓是通过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转换形成有关自我与世界全新认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诞生了杰出的文学作品。
第一,韩国人的中国体验叙事。
近代以前,根据中国之行的目的,韩国的中国体验可分为留学体验、求道体验和使行体验。
留学体验是指以求学为目的的异国体验。代表人物有统一新罗时期的崔致远、崔彦伟、崔承佑,即所谓“三崔”。求道体验是指以宗教活动为目的的异国体验。慧超、元晓、金乔觉等就是为求法而来到中国的新罗僧人。使行体验是指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出使明朝的朝鲜朝使臣所留下的“朝天录”作品以及出使清朝的朝鲜朝使臣所留下的“燕行录”作品就是使行体验的代表作。
近代以后,韩国人的异国体验主要有以谋生为目的的移民、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出现的强制移民以及由知识分子对近代化的渴望而引发的求道体验。其中,求道体验的源头是由朝鲜朝末期“西势东渐”的趋势促发的“开化思想”,即韩国文人对“域外”文化的强烈渴求。随着日帝殖民统治的开始,许多韩国人为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和学问纷纷奔赴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还有众多独立运动家们在中国开展了抗日独立斗争。这类异国体验极大地拓宽了韩国文学的文化地理学空间,创作出了大量宝贵的异国体验叙事作品。金泽荣、申柽、申采浩、姜敬爱、安寿吉、朱耀燮、李陆史、尹东柱等人的文学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第二,日本人的中国体验叙事。
在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体验包括“遣唐使”的使行体验、宋代日本派往中国的贸易使节团的中国体验,以及为了学习传入中国的佛教而来到中国的“留学僧”们的求道体验等。通过这类体验,日本文学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体验叙事作品,还促成了中国文学向日本的传播,从而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例如,“唐传奇”通过日本人的中国体验传入日本,从而形成了日本的“汉文传奇”。“汉文传奇”之后朝着“口语体”的方向演变,同时吸收“和歌”等日本“韵文文学”的诸因素,成为日本古典小说形式——“物语”的重要因素。
第三,中国人和韩国人的日本体验叙事。
在东亚,最早实现近代化的日本一跃登上东亚文化强国的地位。渴望实现近代化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将日本视为“黄种人的引路人”,于是,通过移民、流亡、留学等途径获得的日本体验成为韩国人和中国人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媒介。日本体验对韩国和中国近代文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日本体验是最主要的源泉之一。王国维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之后,深深折服于被称为“新学”的西方学问。于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参加工作,一方面还到日本语学校进行学习,直至 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修习英语和数学。虽然迫于疾病,他数月后最终结束学业回到祖国,但却在留学期间阅读完费尔班克斯、杰文斯、海甫定、康德等人的著作。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还广泛阅读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学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并逐渐转向文学,逐渐具备犀利的批判意识。郭沫若在留学日本九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歌并发表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以此为契机,他结识了在日本大坂留学的剧作家田汉以及担任《时事新报》文艺副刊编辑的美学家宗白华,他们三人联手出版了广泛探讨近代文明的《三叶集》。不久之后,郭沫若联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被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火炬的文学团体“创造社”。
近代初期,日本是韩国人接受近代文化的最重要的窗口。就韩国近代文学而言,多数作家曾经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虽然西方文学在日本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对韩国近代文学理论、思潮、批评的建构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崔南善的“新体诗”、李人的“新小说”、李光洙的近代文学批评、金东仁的唯美主义文学、“普罗”文学等都受到日本体验的巨大影响。
总而言之,东亚各国文人在体验异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文学的文化内涵,拓宽自己的文化视域。通过这一过程,东亚文学得以演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比较视域,进而拥有了在“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他者”与“他者”之间复杂的力学关系中准确把握自我坐标的智慧。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能够通过东亚各国的异国体验发现东亚文学多元共存的本质。具体而言,通过互动造就的文化接受与创造、崭新的文化视域与文化自省、文明建构的参与意识等是东亚文学多元共存的特性。归根结底,东亚文学通过文学的象征化展示了东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二、文本的传播
文本的传播是文化互动的主要媒介和途径,因此,有学者借用“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中国、韩国、日本之间以书籍为途径的文化传播称为“书籍之路”。东亚是印刷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书籍的印刷和流通十分活跃。加之东亚各国之间的使节互访和贸易等人际交往极为活跃,书籍的传播较之其它地区更为有利。
文本因其有形性,在传播过程中较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同时,文本的传播通常不是单向模式,而是双向乃至多向模式,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出现变异和再创造。
众所周知,瞿佑 (1341~ 1427)的《剪灯新话》给予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以巨大影响。不仅如此,浅井了意(1612~ 1651)的《伽婢子》也是在《剪灯新话》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是应该说,《金鳌新话》对《伽婢子》的影响比《剪灯新话》的影响更为直接。以此类推,《雨月物语》也应该是在《金鳌新话》的影响下创作完成的。
金万重的《九云梦》的蓝本是《太平广记》。而《九云梦》传入中国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部分因素又掺入到其中,翻案成为白话小说《九云楼》。后来,《九云楼》重又传入朝鲜,以《九云记》为题得到传播。[2](42)
清代文人王士祯与朝鲜“北学派”文人之间的文本交流也是典型的个案。王士祯的《带经堂集》传入朝鲜大约是在 18世纪 50年代,20多年后,开始受到“北学派”文人的普遍关注。“北学派”文人洪大容燕行时结识“古杭三才”——严诚、陆飞、潘庭筠,并从他们手中得到王士祯的诗话集《感旧录》,带到朝鲜后被“北学派”文人广为传阅。“北学派”文人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的诗集传入清朝后通过不同途径得到刊行,并受到当时清代著名文人纪昀、翁方纲、李调元等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海东四家”。“北学派”文人的诗文能够在清代文坛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其中,“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祯文学的创造性接受与阐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等人的诗集以及《三国志》、《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从中国传入朝鲜,又经过朝鲜传入日本。
近代以来,日本在东亚最早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大量翻译和翻案的西方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品、朝鲜“新体诗”和“新小说”的模本。同时,日本作家的许多作品也对中国文人和韩国文人产生了诸多影响。例如,厨川白村(1880~ 1923)的文论著作《苦闷的象征》是在作者去世后的 1924年 2月由作者的亲友付梓出版的。同年9月,鲁迅就开始着手翻译此书,并于同年12月出版中文版。其实,《苦闷的象征》在日本的反响甚微,被鲁迅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却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苦闷的象征》的思想源自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其主旨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3](17)。鲁迅为厨川白村强烈的批判精神所倾倒,相信这种强烈的精神力量能够给中国人萎靡的精神带来强烈冲击。因此,鲁迅陆续创作出表现自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苦闷与苦恼以及强烈批判的《野草》、《故事新编》等作品。
总而言之,文本的传播能够引发作者对相同题材与主题的文学思考,使得处于不同时空的作家们在自身所处的语境中对其做出不同的解读。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可能引发“误读”,文本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多新的意义。
三、“潜在的文化对话”
钱钟书先生曾经以一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1)道破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类似性。我们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中不难找出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或形象,这正是人类普遍价值的表现。这种处于两个或多个不同时空的文学作品探索同一主题的文化对话可称之为“潜在的文化对话”。
首先,安藤昌益(1703~ 1762)与朴趾源(1737~1805)之间的潜在对话值得关注。安藤昌益的《法世物语》与朴趾源的《虎叱》虽然形成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度,但两者间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类似性。两者都假借动物的形象和口吻批判封建制度与文化,在艺术形式和文字等方面展示了伟大的变革精神。
在《法世物语》中,鸟、兽、虫、鱼这四种动物聚在一起讽刺和批判人类社会的弊病。在“鸟”一章中,鸟向秃鹫询问人与动物的区别,秃鹫回答道:“人间‘法世’比起动物界显得更加昏暗、残暴。”[5](8~9)在“兽”一章中 ,狗批判道:所谓的“儒士”,“产生偏气,并写下许多‘偏心’、‘偏知’的荒唐文字来。”[5](8~9)
在《虎叱》中,老虎痛斥所谓的君子北郭先生,借此揭露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道:“计虎之食人,不若人之相食之多也”[5](321)。老虎还讥讽封建儒士的虚伪和堕落道:“儒乎臭矣”,“儒者谀也”。[6]
《法世物语》和《虎叱》都采用了拟人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摆脱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主张“以文为戏”,从而在语言和文字上实现了一大革新。
安藤昌益指出:“文,文道器也,器践束而得器内味道,则器无用也,器假用也,文又然也。诵文字得意,则无用也,文假用也。”[5](17)他还认为,一切书写文章的技巧都是“混述”。朴趾源也反对“文以载道”,主张“以文为戏”。在《虎叱》中,朴趾源借用老虎之口指出,北郭先生校正万卷书籍皆为“校书”,而非“著书”。
从语言风格上看,安藤昌益的文体更接近日本的汉文,与正统汉文语法有较大的出入。朴趾源也一直肯定朝鲜语,他虽然也使用汉文创作,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体,被喻为“燕岩体”①燕岩为朴趾源的号。。朴趾源经常在文中使用朝鲜专有的官职名称和地名,还引用朝鲜语中特有的谚语和俗语等,从而强化了文学的通俗性。例如:“医无自药,巫不己舞”(《秽德先生传》),就是直译朝鲜谚语“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巫婆不能为自己跳大神”,再如“诵如冰瓢”(《两班传》),就是直译了表现话语流畅的朝鲜谚语“犹如冰面上推瓢”。朴趾源还破格使用了汉字的音和意,突出了文体表现的民族特色。文体和文字使用上的不拘一格,无疑是朴趾源积极摆脱旧有封建文化传统的结果。
安藤昌益与朴趾源生卒年仅仅相差20年左右,两者的对话堪称同时代人的潜在对话。百余年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与朴趾源之间再度展开了跨时空的潜在对话。鲁迅一贯批判封建礼教以及被旧价值观束缚的国民性,主张文体改革。通过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与朴趾源的《虎叱》、《广文传》、《朴氏夫人传》,我们不难发现两位时代先行者之间潜在的文化对话。面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新旧文化的剧烈冲突,两位时代先行者表现出相似的立场和态度:坚决拥护新文化,坚决抵制和志在颠覆旧文化。这也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两位作家虽然相隔百余年,但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儒教文化弊病的激烈抨击却如出一辙。[6](231)
总之,阐明文学创作中的潜在对话,能够发现和确认各国、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与生成关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一个特定的文本总是要想象地或象征地解决某一真正的矛盾;一个文本既是一种行为又是象征性的。”[7](205)鲁迅与朴趾源的小说也是如此。它们既是想象的或象征的文本,也是为解决社会矛盾而采取的“行为”。同时,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同(或相似)文化语境下话语的连贯性,即两位作者的近代志向及其精神史的延续性。而且,朴趾源小说的主题意识和人物形象又是鲁迅小说主题意识和人物形象的雏形,并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塔尼亚·弗朗哥·卡瓦利亚尔指出:“伟大作品的范本不必早于伟大作品,相反,最伟大作品创造了它的先行者。”[8](187)通过朴趾源与鲁迅之间的潜在对话,我们可以重新确认朴趾源小说文化精神的先驱性,进而确认鲁迅小说文化精神的集大成意义。另外,安藤昌益、朴趾源和鲁迅之间的潜在对话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1]黄俊杰:《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跨文化对话》,第二十八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2]丁奎福,《韩中文学交流之本然双向互动关系—— <九云梦>与 <九云记>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 1期。
[3][日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4]钱钟书 ,《〈淡艺灵〉序》 ,中华书局 ,1984年。
[5][日 ]安藤昌益 ,郑 18,第 8— 9页。 转引自赵东一《安藤昌益与朴趾源比较研究序论》。 (赵东一,《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4期。
[6][朝 ]朴趾源 ,《虎叱》,《热河日记· 关内程史》,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美 ]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转引自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8][哥 ]塔尼亚·弗郎哥·卡瓦利亚尔,《拉美的文化对话或文化误读》。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播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