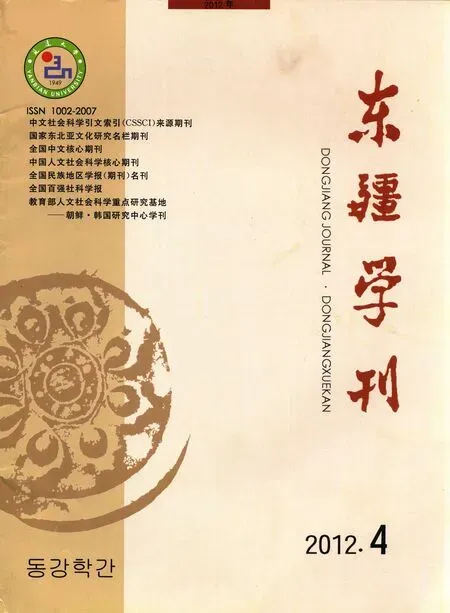第二人称叙事的不确定性与普拉斯诗学艺术的构建
李文萍
人称是叙事学的一个经典话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而很少关注第二人称。理论上开始研究第二人称叙述始于 1965年布莱斯·莫里塞特在《当代文学中的“你叙事”》中提出的“作为一种新文类的‘你’叙事”[1](1-24),此后热奈特的“第二人称叙述”[2](344)术语为从叙事学研究第二人称叙述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受述者和读者,即相对于叙述者和作者主体“我”的客体“你”。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詹姆斯·费伦、布赖恩·理查德森、尤里·马戈林和彼得· J.拉比诺维茨等学者使第二人称叙述研究得以延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们开始从意识形态、修辞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历史叙事、读者反应批评等不同视角研究第二人称叙述。诗人尤其重视对人称代词的选择以及使用。正如John Berryman所说:“一个代词可能看起来是件小事,但是她重要,他重要,它重要,他们都重要。”[3](165)这里显然没有提到第二人称“你”。但是第二人称“你”因其含义具有开放性而被更多地用于战后美国的诗中,又由于其所表达的不确定性而受到普拉斯的青睐。
《爸爸》是普拉斯最出名的并被广泛收录、评论的一首诗,对其主题思想评论者各执己见。《爸爸》反映了女孩对已逝父亲爱恨交织的情感,它也被解读为普拉斯对父亲过世和丈夫不忠的一种发泄。肖小军认为:“普拉斯选择女儿‘我’这一女性代表来承担叙述者的角色,而使男性代表‘爸爸’处于一个非常被动且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失语状态,是为了凸显叛逆后的女性霸权意识”[4](69)。还有评论者从自白的角度分析诗歌的自传性色彩。目前,很少有评论者从第二人称“你”的视角关注这首诗。诗歌中“我”出现 26次,“你”出现23次。这种使用频率使读者不能忽视第二人称对诗歌意义的构建作用。在数量上,“我”的主体性特征略强,同时“我”通常出现在行首,“你”在行末,顺序的前后也体现了诗歌的主体和客体。这两个人称代词的变换使用使全诗充满了创作与理解上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现代和后现代诗学的重要特征。
诗人对人称代词的选择反映了诗歌叙事的视角以及传播的策略。第二人称叙事不利于传播,但是它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爸爸》中所展示的,其控制、从属、监禁、复仇及逃避相关的矛盾主题与第二人称叙事直接相关。诗中的第二人称“你”是诗人构建艺术、再现普遍生活的一种方式。本文将在修辞性叙事理论的框架下研究诗歌的第二人称叙述问题,重点分析第二人称叙述“你”“是”什么,对叙事交流“做”了什么。通过分析由第二人称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来解读普拉斯诗歌艺术的独特性,以期纠正“普拉斯的诗歌只是个人叙事”的认知误读,在更广阔的话语层面上理解她的诗歌,探寻其诗学话语形成的根源。
不确定性是《爸爸》这首诗的中心,第二人称增强了这种不确定性。叙述者“我”与爸爸“你”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诗人一开始便虚构出了“你”这个叙述接受者,“你”存在于叙事文本内,与叙述者互相依存,是叙述者的听众。“你”在文本中的存在意义就是通过构建一种叙述者“我”和人物“你”之间的虚拟对话而直接昭示诗歌创作的虚构过程。[5](47)“你”与“我”形成一种心灵对话,建立情感的认同,从而缩短了诗人、虚构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诗人同虚构人物直接交流,而读者会不自觉地以“你”的角色进入诗歌文本中,从叙事学角度实现了“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一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作为书写者的“我”将爸爸称为“你”,就是有意识地将爸爸视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可以和“我”对话的人。第二人称“你”更多带有二人对话性质的话语,直接把二人置于在场的叙述主体“我”的关照之下。
叙述者与爸爸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诗中的叙述者是由爸爸来界定的;反过来,爸爸又是被叙述者创造出来并由其赋予生命的。叙述者以灵巧的语言、变换的形式构建爸爸形象。爸爸是叙述者的倾听者,同时如果叙述者对他没有渴望和对抗的愿望,他就不会说话。爸爸只有在叙述者唤起他的灵魂并赋予他权利时才存在。诗歌对于修辞、比喻、转义的依赖,反复重复的爸爸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提醒读者:诗歌是构建的,“你”最终也是文本中的。叙述者对第二人称和修辞比喻的依赖,把诗人和诗歌中的人物区分开来。诗人在诗歌中被剥夺权利,但作为叙述者,她在诗中的作用不会因为诗歌形式而受限制。相反,她驾驭修辞的能力、包括第二人称的能力,把她自己从隐含在第二人称所表现的屈从于其他人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第二人称以互动的方式把“你”这个真实存在改变成虚拟的存在,既保留“你”的真实社会属性和身体存在,同时又给予“你”虚幻的身份和空间,真实与幻象相交错,给予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普拉斯的诗歌经常被理解为诗人的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表达,然而她的诗歌所表现的绝不是诗人简单原始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活动,而是经过了诗人对之进行的提炼,使之审美化,使之服从于一定的艺术范式。作为一种形式建构,诗中的爸爸形象虽然与诗人的父亲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诗歌本身是艺术再现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叙述者描述爸爸,在不断变换的人物中,爸爸成为真实的人,不再是具有威胁性的和神秘性的人,叙述者意识到真实的、活着的爸爸是不可再现的。相反,爸爸只能存在于叙事者的艺术想象之中。
第二人称确定叙述者和爸爸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对立的。普拉斯的《爸爸》把读者置于一场拔河赛中,通过使用“我”与“你”视角之间的动态张力,不仅扩展了诗中爸爸的内涵,同时也延伸了父权意识的概念。普拉斯结合个人的情感体验并将它扩展。从第一节起,“你”通过“我”的视角被引入。普拉斯确立了专制的“你”和与之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我”之间令人窒息的关系。诗中的“爸爸”被赋予多重角色。“爸爸”通过“我”的镜头不断被调焦成为一个容器 (“black shoe”)、有不祥预感的神 (“a bag full of God”)、种族灭绝的压迫者 (“I thought every German was you”)、教师 (“ You stand at the blackboard” )、恶魔 (“no less a devil for that”),最后是一个不死的、寄生的怪物 (“The vampire who said he was you” )。作为爸爸的“你”似乎无所不在,既是一个权威形象,又与神话视域中的邪恶力量为伍。“你”的形象来源众多,令人难以辨认 (“So I never could tell where you/Put your foot,your root”)。“你”说不同的语言,因此与“你”的直接交流更是不可能。
作品通过第二人称设定的虚构情境加强了作为叙述者的“我”与爸爸“你”之间的张力,即尽管叙述者反复试图要杀死他,但爸爸仍然存在。诗中模棱两可的的第二人称暗含着叙述者对爸爸既渴求又憎恨的矛盾心理。如果诗中第二人称被剔除,把“爸爸,我不得不杀了‘你’”改成“爸爸,我不得不杀了‘他’”,虽然原有的强制感仍然会被保留,但由“你”所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将会丢失,因此亲切性也随之消失。叙述者的爸爸离世已久。第二人称的叙事结构表达了叙事者与之对话的愿望,并且显示叙述者尽管声称杀了他,但还是在爸爸的情感掌控之中。尽管他已死,但她必须杀死他,或者把他的最新化身杀死。这一事实加深了诗中的根本矛盾。在某种程度上,爸爸对于叙述者来说仍然活着。然而当作为爸爸的“他”被以第二人称“你”的方式呈现,并用现在时态来展示时,死去的爸爸就成了对话的参与者,普拉斯也因此从艺术的角度否定了他的死亡。
《爸爸》是对话的序曲。作为一首抒情诗,虽然它不是一个对话,而是一个单独的声音的言说,一种祈祷、符咒,最终是一种单独的回应,但它不仅肯定了叙述者的想象力,还有她的孤独。在诗中,反感和渴望、怀旧之情和诙谐的改编诗文的交错源于这种双重性。叙述者似乎相信失去的父亲难以接近,然而她继续尝试以艺术的方式构建他。正如“爸爸”不断复活,又不断被杀死。“爸爸,我不得不杀了你”,“我过去时常祈祷能找回你”,“我从不会对你谈起”,“我想每个德国人都是你”,这些重复出现的句式使叙事者“我”和宾语“你”——“爸爸”之间的对立、依存关系凸显。此处的这种句式强调了叙述者“我”的相对稳定。然而,诗中的“你”的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叙述主体“我”没有避讳我对你“爸爸”的内心想象,从没有生命的物体黑鞋子、充满上帝的袋子,到现实的纳粹、超现实的吸血恶魔,这些都是叙述者虚构的形象,反映了“你”在诗人跳跃式的想象中不断变化。因为我的介入,“你”的内心世界得以在我的关照下呈现。并且,我的介入也在进一步模糊虚构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关系,亦在模糊故事内外的界限。你和“我”在同一首诗中又在不同的时空之中,你是“我”所处时空之外的另一个存在。通过反复尝试把自己置于与父亲的关系中,叙述者表达了要接近爸爸的愿望。
普拉斯的第二人称表达了叙述者悲伤、矛盾的心理。对于那个死去的人“爸爸”,叙述者希望复活他、斥责他、接近他并且放弃他。第二人称的使用效果,与其说是叙述者迫使爸爸回到生活中来,毋宁说是迫使她忘记死去的爸爸。叙述者渴望爸爸并想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使得叙述者可以回到过去与他为伍。20岁时她曾经试图自杀,她也曾把他当作偶像,但后来她意识到她未来的幸福在于自己必须从他那里解脱出来。叙述者意识到爸爸只是一个纳粹标记、一个残暴的人、一个魔鬼,这些迫使她丢弃他。无论是父亲、丈夫还是法西斯分子,他们都代表男性,在男权社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虐待女人的身体,践踏女人的心灵,侵扰女人的情感空间。但是普拉斯在《爸爸》中却以一种强势话语来建构属于女性的权利体系,而在强势话语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她无助的客体意识形象。
第二人称叙事有助于构建叙述者与读者之间近距离的对话关系。“你”对于叙述者来说是被叙述的对象,而对读者而言则可理解为第一人称。读你的故事,似乎就是读者在审视与阅读自我,让真实的自我去体验你的经历与意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与你的角色“在阅读中完成互换,融为一体”[6](74)。 诗中的“你”和“我”相互界定。普拉斯的“我”通过“你”的视角来界定自我,反过来又界定与之相对的“你”。“我”相对稳定,但也不断变化,尝试以适当的形式来刻画我的压迫者—— 你。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你”无法界定。“你”无法被压倒、抚慰或战胜。“你”不能评价“我”或者运用身体的和心理的力量来控制我。你的力量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只能评价和控制自身。“你”因为“我”作为施动者只能间接运用权力,而不会形成一个与“我”相抗衡的“你”。
《爸爸》精心构建的语言和意象否定了这首诗是即兴创作的观点。这首诗的作者被归为“自白”派别,因此诗中的人物具有原型的轮廓,但绝不是自传的节选。第二人称多出现在战后美国的诗中,尤其是所谓的自白派和语言派诗歌中,表达与他者的矛盾关系,对他者参与现场的愿望和诗歌叙事者的根本的孤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一位诗人采取自白的姿态,即便诗歌展示了虚构的主人公在虚构的读者面前,她邀请她的读者成为“不仅仅是对话者,而且是权威者”,并且要求他们参与到评价、惩罚、原谅、安慰和调解中来。很明显,矛盾的角色确认读者的力量。否定的回应,把真正的读者认同为诗的真正的听者。诗人,在允许听者听时,也赋予那个听者以权力,诗人明显地远离读者掩盖了她对读者的依赖。自白是她艺术创作中修辞的选择。
诗歌是虚构文本。而读者之所以“明知其假而宁信其真”,并非仅仅由于文本摹仿了生活,给读者制造了“真实生活的幻觉”,而是由于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一种先定的契约:读者允诺作者有权在文本中设置一个“可能的世界”或“不可能的世界”[7](94),“而读者阅读文本的前提条件是默许作者的‘所设’(包括实设和虚设),而不以现实生活作为判断的标准检验文本的真伪”[8](67)。第二人称叙事,使诗人与真实的自我既能同步又能保持距离。诗中的声音是叙述者的,不过,态度、意图和技巧却是隐含作者的。叙述者可以被赋予发声和视觉能力,但只是传声筒,不具有其他人格性质。诗人采用第二人称叙事使读者仿佛看见孤独的诗人坐在桌前与想象中的读者对话。
第二人称“你”是普拉斯借以与读者沟通的叙事策略。通过此策略,普拉斯使读者可以把自身映射到诗中,从而在诗与读者之间创造一种无言对话。由于性别、背景和思想的不同,每位读者会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我”和“你”身上,从他们自身体验中去定义这两个概念。“我”没有对方不能确定自我身份,通过第二人称“你”的叙事策略方能与读者产生思想碰撞。诗人创作的首要原则是要建构一个审美化的、艺术的诗人形象。普拉斯选择与己相关的生活素材,其目的并非是对具体行为或事件作出回应,而是把它转换成诗性的语言,表达一种超越时空的普世关怀。普拉斯诗歌中众多的他者形象突显出公众话语与诗性语言之间的伦理张力,让读者在体验诗歌美学内涵的同时,关注艺术以外的世界。
[1]Brace Morrissette. Narrative You’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2(1965).
[2]Irene Kacandes: Narrative Apostrophe:Reading,Rhetoric,Resistance in Michel Butor’s La Modification and Julio Cortazar’s‘ Graffiti’.Style,28 No.3(1994Fall).
[3]Carol Frost.Self- Pity.After Confession:Poetry as Autobiography.edited by Katherine Sontag and David Graham.Minneapolis.Minneapolis,Minn:Graywolf,2001.
[4]肖小军:《论女性创作中的客体意识——普拉斯名作〈爸爸〉话语分析》,《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 3期。
[5]翟杨莉:《一种未完成的叙事状态的魅力——析〈扶桑〉叙事当中的第二人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期。
[6]刘亚律:《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 6期。
[7]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三联书店 ,1994年。
[8]曹禧修:《修辞学:文学批评新思维》,《东疆学刊》,2002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