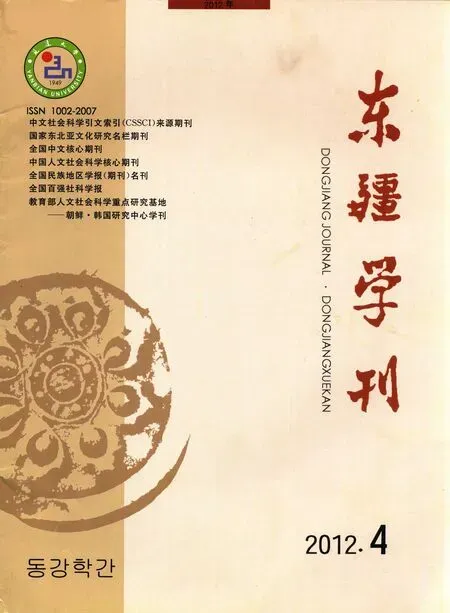《女奴生平》中的观视与权力
史鹏路
《女奴生平》(Incidents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是非裔美国妇女文学与19世纪美国历史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采用笔名琳达·布伦特(Linda Brent),以自己在奴隶制中的亲身经历为材料写就自传《女奴生平》。这部自传讲述了雅各布斯为挣脱沦为奴隶主的玩物、世代为奴的命运,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与男主人弗林特医生斗智斗勇,藏在昏暗、狭促的阁楼中长达 7年,最终一家人获得自由的故事。书中不仅记录了奴隶们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指出奴隶制同样侵蚀并扭曲了白人奴隶主、女主人及其后代的人性。作者身为女奴母亲,更是将关注点投置于女性,记述了自己以及其他女奴所遭受的种族、性别的双重迫害。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女奴还要忍受来自白人奴隶主的性侵犯、女主人出于妒忌而施与的迫害、以及儿女被卖、骨肉分离的精神痛楚。这些叙述涉及到此前典型的男性自传奴隶叙事(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道格拉斯自传》)所未能观照到的盲区,即黑人女奴在奴隶制当中所遭受的性虐待。哈丽雅特勇敢揭露的这一事实,是许多人不愿面对的,这成为这部作品被忽视了一个多世纪的原因之一。
《女奴生平》自问世以来,公众与学界就从未停止过对作者身份以及书中所述事件真实性的质疑。在自传中,作者坦言了自己与白人邻居塞缪尔·崔德威尔·索耶(Samuel Tredwell Sawyer,后成为国会议员)发生关系并生下两个孩子的事实。但碍于社会传统道德舆论的压力,并为了保护事件所涉及的人物,她以笔名进行叙述,且“隐去了地名,并为人物取了假名”,因为她认为“保密处理是友好体贴的做法”[1](2)。在自传出版时,封面上只印有编辑丽迪亚·玛利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的名字。因此,批评家们认为《女奴生平》是白人废奴主义者假借奴隶之口杜撰而成的作品。琼·费根·耶林(Jean Fagan Yellin)于 1981年在 《美国 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53(Nov 1981): 479-486)上发表文章《由她本人撰写: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奴隶叙事》(“Written by Herself:Harriet Jacobs’s Slave Narrative”)。 在文章中 ,耶林严谨缜密的调查结果证实了琳达·布伦特确有其人,那便是哈丽雅特·雅各布斯,且自传中所述人物及事件也均出自作者的真实经历。自此,《女奴生平》成为美国历史、妇女研究以及非洲裔美国文学研究一部重要作品,并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多种外语版本。
毫无疑问,这部自传具有浓烈的政治诉求。而细读文本则会发现,作品与其社会语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申丹指出“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的方法,该方法可有效地揭示表面文本背后的潜藏文本[2](1~7)。在这部自传中,这一策略可被运用于梳理文本突出的艺术特点与当下科学技术、文化、社会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此来揭示文本所处社会语境当中的性别成规与权力关系。
一、权力的眼睛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而言,可谓是一所大监狱。在种族主义社会中,权力之眼无时无刻不在为贯彻压迫制度行使着监督之职。雅各布斯一生致力于逃脱身陷奴役的命运,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最终仍需通过自囚7年的方式来抵抗迫害,以身陷真正的监狱来摆脱奴隶命运。雅各布斯所代表的奴隶们的悲惨生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景监视机制的产物。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18世纪盛行的残暴酷刑作为一种公共景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19世纪,虽然对肉体的惩戒尚未完全消失,但“惩罚的重心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剥夺财富和权利”。[3](16)19世纪的美国社会正是福柯所指的“全景敞视监狱”,为了按照一定的规范去驯化肉体,通过无止境的监控把有色人种禁锢在特定的位置,对他们进行肉体以及精神上的改造。
在雅各布斯的叙述中,她无时无刻不处在“权力的眼睛”的监视下。男主人弗林特医生及其妻子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就是监视者。白皮肤、男性、奴隶主,这些特质决定了弗林特医生对奴隶具有绝对的掌控,这其中包括对黑人女奴任意的性侵犯。黑人女奴被物化为白人奴隶主的审美对象与欲望工具。作为一名女奴,“如果上帝赋予了她美貌,这其实是对她最大的诅咒。白种女人靠此博得仰慕,而对女奴而言这只是罪恶的催化剂”[1](27)。“注视”行为成为奴隶主的“天赋之权”,让他们在女奴当中挑选泄欲对象。而“当时在所谓的真正的女性概念的影响下,中产阶级妇女节欲自禁,使白人男性更有理由以女奴习惯于男奴的性欲无度为借口,随心所欲的侵犯女奴”[4](84)。据雅各布斯记述:“据我所知,我的主人是十一个奴隶的父亲。但是妈妈们胆敢说出谁是她们孩子的父亲吗?”[1](32)根据当时的法律,女奴的孩子要跟随母亲的身份成为奴隶。这就意味着,男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女奴进行性侵害而不负任何责任,而女奴为奴隶主生育的后代则成为了主人的奴隶库存中的一份子,任其买卖。女奴所忍受的这些残酷的肉体以及精神痛楚,即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所指“她们所遭受的肮脏罪行不堪入耳”[1](5)。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曾做出评论:“正是对日日笼罩着她的生活以及每一位黑人女奴的生活的性剥削给予了详实而痛苦的细节描述,雅各布斯的故事得以获得重要地位。”[5](12)在自传中,弗林特医生通过严密的盯梢监控来实施这一“日日笼罩着她的生活”的性剥削。雅各布斯写道:“主人每次见到我,都会提醒我,我是属于他的,并对天地起誓,他终会逼我屈就。在一天孜孜不倦的劳作之后,我若是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的脚步就尾随而来。如果我跪在妈妈的坟前,他的黑影甚至也会在那儿将我笼罩。”[1](27)在这组“看”与“被看”的关系当中,遭到性剥削的女奴们,是被审视的对象,是奴隶主欲望的载体。受置于“被监控”地位的雅各布斯,是“凝视”行为下的被监管的囚徒。她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因此导致了后续的反抗,即偷情和藏匿。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论述道,“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6](11)在奴 隶制中 ,黑人女性不仅成为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他者”,也成为白人女性的“他者”,即她们遭到了性属以及肤色的双重压迫。奴隶主的妻子们对奴隶制当中“秘而不宣”的罪恶了如指掌。虽然有一些夫人慈悲宽容,但这个邪恶的制度却扭曲了大多数人的是非感。妒火中烧时,她们成为残害女奴的帮凶与刽子手。弗林特医生的妻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雅各布斯写道:“在我出生前,弗林特太太就掌握了她丈夫性格当中的弱点。她可能曾运用过这个认识来劝告和保护那些年轻天真的奴隶们,但她对她们毫无同情。她们是她长久猜疑和憎恨的目标。她以不懈的警觉监视着她的丈夫。”[1](29)除了对丈夫采取严密盯梢,弗林特太太还要对有姿色的女奴监控调查,对可能对她构成威胁的女奴严防死守,并对已经为其丈夫生下混血后代的女奴们实施迫害。弗林特医生觊觎雅各布斯的美貌,女主人出于嫉妒,伪善地安排她睡在隔壁,实则为了监视她。雅各布斯写道:“她很多个夜晚都在监视我。有时我醒来,发觉她正俯视着我。其他时间,她会在我耳边轻声呢喃,装成她的丈夫在对我讲话,并去听我会怎样回答。”[1](31)紧接着,雅各布斯便呼吁读者调动感官与想象力来体会这种经历的恐怖:“你可以想象,远比我描述得生动,在死寂一片的夜里醒来,发觉一个妒忌的女人正俯视着你,这多么令人厌恶。这种经历太恐怖了,我害怕它会带来更加骇人的后果。”[1](31)在这场权力关系当中,处于“被看”地位的雅各布斯是弱势、无助的,“被监控”这一经验于她而言是一种恐怖的经历。而弗林特夫妇则如处在圆形监狱的望塔的看守一般行使着监视权力。同时,奴隶主夫人虽对奴隶握有生杀大权,但在内战前,受到父系社会对理想白人女性的规范与塑造,“南方女士是白种蓄奴男性想象的产物,他们指望在她身上使他们的特殊的种族与性属制度合理化”[7](1)。因此,她们不仅是视觉主体,是权力的化身,同时也是被其他视觉主体塑造的结果,是白人男性的“他者”。在“全景敞视监狱”式社会中,监视效应在每一个被训练和惩罚的对象身上发挥效应。这一权力规训巩固了种族歧视及性别成规等社会微观机制。
二、产生“真理”的话语
社会规范对有色人种的驯化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和媒体宣传进行的。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紧密相关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3](32)。权力与知识是同盟关系,统治阶级依靠生产“真理”而获得权力、构建观念、规训肉体。
在种族歧视的美国,宗教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话语的范式。白人依靠宗教来愚化黑奴,望其内心获得慰籍,消除他们的反抗精神,巩固自己对有色人种的统治。在《女奴生平》中,白人牧师为奴隶们做出如下布道:
你们这些奴隶,好好听着!注意我的话。你们是逆反的罪人。你们的内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是魔鬼在诱惑你。如果你不从邪恶的路上迷途知返,上帝会生你的气,且决计要惩罚你。你们这些住在镇子上的奴隶,得要主人看着才干活。忠诚地侍奉你的主人,这会让在天上的父感到愉悦。可你们不。你们闲散懒惰,躲避劳动。上帝看着你呢。你说谎时,上帝在听着。你们不全身心地敬仰他,反而躲在某处,饕餮你主人的食物,与邪恶的算命师一起丢咖啡渣,或是与老巫婆算牌。也许主人不会发现你们,但上帝在看着你,也势必惩罚你……你一定远离罪恶的道路,成为忠诚的奴仆。要对你的男女主人和小主人惟命是从。如果你违抗了现世的主人,也就是侵犯了你天上的主人。[1](59-60)
雅各布斯深知这是白人的愚民政策。她指出,黑人并非生而智力低下,而是这个制度以残酷的鞭刑和进监服刑等暴力手段禁止奴隶学习。奴隶主将黑奴视为与牛马无异的劳动力,进行奴隶贸易,拆散他们的家庭。为了使这些罪行合理化,奴隶主声称黑人生而感情迟钝,道德低下。对此污蔑,雅各布斯申辩道:“有些可怜的人们已在鞭刑之下被严重摧残。因此他们会偷溜出去,为主人留下对其妻女的自由使用权。你认为这就能证明黑人是劣等人种吗?如果你生为奴隶,作为奴隶被养大,祖先世世代代也是奴隶,你会怎么做呢?我承认,黑人是劣而次之的。但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的?是白人强加给他的蒙昧生活;是那将人性从他身上抽离的拷打的皮鞭;是南方凶猛的猎犬,是同样残忍地执行着《逃亡奴隶法》的北方的追捕者们,是他们让黑人变成这样的。”[1](39-40)
媒体也是产生“话语”、强化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雅各布斯亲身经历了各种不公正,而媒体对肤色分界线的深化令她震撼。19世纪美国科技不断发展,技术条件的成熟推动了报纸的发展。“到了1800年,大多数大港口和商业中心都有了自己的报纸。当时报纸是大多数居民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文字材料,它们充当了主要的教育工具。”[8](27)在南北战争期间,新闻界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充当喉舌,对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废奴主义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是加里森在 1831年 1月 1日发行的《解放者报》……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是惟一一家始终维护宪法赋予南部权益的北部日报。”[8](28)雅各布斯对媒体的立场有着敏感的评判。作品第二十五章中曾提到《纽约先驱报》是一份“系统地诋毁有色人种的报纸”,也犀利地指出尊敬的默里夫人 (Hon.Miss Murray)对美国奴隶状况的描述是乐观的美化。[1](106)作品还谴责被假象蒙蔽了双眼,宣传奴隶制是“一个美好的‘家长制’,奴隶们并不想获得自由”的学者们[1](64)。雅各布斯对媒体的扭曲宣导非常不满,但同时她也认识到媒体对社会以及观念的巨大影响。因此,她逃到北方后,便积极投身废奴主义事业,与弟弟合办废奴主义图书室,努力借助传媒工具推进解放奴隶事业。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雅各布斯在受过教育及启蒙之后,对掌握一种有效的沟通语言有着迫切的需要。雅各布斯从媒体中看到的对黑人的扭曲宣传对她构成了视听冲击。在这些视听冲击当中,她的“自我意识”得以构建,而这个“自我意识”是被分割成“看”与“被看”两者的。也就是说,她的种族意识已不单单指被描述当中的自我,而更是认识到自己的族群是被书写的,并通过媒体作为一种景观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自我意识”的构建是与她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密不可分的。这时,雅各布斯既是“画中人”,也是“赏画人”。这就意味着,雅各布斯的“自我意识”兼具了“看”与“被看”的两种角度。换言之,她的“自我意识”不仅是看自己的族群如何被媒体呈现的问题,而是观看作为景观与早已被“注视”的自我的问题。
三、反抗权力:自动遁形与旁观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奴隶制度是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因此,奴隶以及有色人种的各种权益都得不到保护。他们是社会体制的边缘族群,是被法制体系无视的族群。雅各布斯控诉道:“一个女奴不论是黑得像炭,还是和女主人一样白皙,都没有一条法律范围是保护她不受侮辱,暴力甚至是死亡的侵害的,而这些都是由化作人身的撒旦造成的。”[1](26)而弱者的英雄主义,则如雅各布斯一般通过长达 7年的藏匿而达成的。关于藏匿生涯初始之际的情况,雅各布斯回忆道:
这个顶楼小屋只有九英尺长,七英尺宽。最高的地方三英尺高……到了早上,听到噪音我才知道天亮了,因为在我的小洞穴里,白天和黑夜完全是一样的……我没法直立,但我在洞里爬来爬去做运动。一天我的头撞到了个东西,我发现居然是个手钻……这样我成功地凿了一个一英寸长,一英寸宽的洞……早上,我出去找我的孩子。但我看到的在街上的第一个人是弗林特医生。我对此有种迷信的恐惧,认为这是不详的征兆。几张熟悉的面孔经过了。最终,我听到了孩子们欢乐的笑声,两个甜美的小脸正看着我,仿佛知道我就在那儿,知道他们给我带来了欢乐似的。[1](96-97)
正是在这个长2.74米、宽2.13米、最高处仅有 0.91米的空气稀薄且一片漆黑的阁楼中,雅各布斯藏匿了7年之久。这便是为了逃避权力体系的“监视”而自动消失遁形成为囚徒的例证。她在狭促的阁楼中日日望着自己的孩子,虽无法将母爱付诸实践,但这种囚禁对她而言,却是比奴隶制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在白人至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不得不自动磨灭自我的主体性。这部作品将读者引入那个狭小的庇护所,使他们理解到作者的英勇。为免受迫害而将躲藏作为反抗手法的作品如安·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在社会的镜子中看不到自我而消解自我的作品如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和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这些作品与《女奴生平》一样,使读者通过这些消失遁形的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他们所处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看到谁?看不到谁?谁有权处在威势赫赫的体制内部?”[9](3)通过对《女奴生平》的考察,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得到了回答,更使我们从中看到奴隶制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权力博弈,视觉政体后的性别成规以及不同利益集团利用媒体而选择呈现出的景观。而观视行为,作为贯穿《女奴生平》全文的艺术特色,是与作者长时间处于“被看”地位并时刻保持“旁观者”的中立视角这一经验不可分割的。
在自传中,如上述视觉与权力关系和性别成规的交织还有很多。而将“被看”视为无力的,“看”视为权力的象征,这种观点是对视觉性理论的大幅简化。实际上,雅各布斯也是一个旁观者,也常处在“观看”的辩证逻辑中。逃亡北方后,雅各布斯为一户白人家庭做保姆以维持生计。在陪同太太出游就餐时,她被一名黑人服务人员喝令不准同白人坐在一起。在另一个用餐场合中,她再次受到服务人员的种族歧视,而此时,其他有色人种保姆的态度却非常耐人寻味。她写道:“四下张望,我看到其他和我一样的,仅仅比我的肤色浅了一些的保姆们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仿佛我的存在是一种污染。”这些保姆已经将压迫着自己的制度内化,并靠这套是非观参与对自己以及同胞的压迫。这正如黑人女活动家宝莉·穆蕾所说:“压迫制度,从受害者的默认中获得了很大的力量,这些受害者已经接受了主流文化对于他们自己的形象刻画,而且被一种无助感所麻痹。”[10](102~105)雅各布斯不囿于“被观看”的位置,在被人审视的同时也保持中立的旁观视角,对自己的同胞甘受奴役的行为发出批判。
四、结语
《女奴生平》为读者勾画了一部监狱式规训社会图景。为了维护各种权力机制,社会以一整套高效有序的惩罚系统和规训力量来监视着社会每一个阶级的活动。白人蓄奴者以及奴隶制拥护者在法律的庇护下动用监狱、酷刑、猎犬等暴力机关来管制黑奴,并对他们实施剥削。他们是监狱式社会中望塔里的看守人。然而,任何统治与被统治都不是单一的对立抗衡,二者之间势必达成某种共识或认可。现代社会将真理与惩罚结合起来,围绕权力产生出一套知识话语。在此,宗教和媒体等便起到了从意识形态上驯化肉体,从被压迫阶级处获得认可的作用。处于社会底层的雅各布斯为逃出强大的权力网络而自行监禁 7年,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弱者只能以消解自我这种消极方式对抗强权的例证。她在藏匿期间通过窥探孔观察到的人和事,以强大的视觉观感带领读者体验到奴隶制社会的种种罪恶。不论是具有隐喻的权力观视,亦或是雅各布斯直观的窥视与旁观,观看行为这一要素贯穿自传始终。雅各布斯通过编织诸多“看”与“被看”,忠实却又不失艺术感染力地描述了监狱式规训社会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性别成规。
[1]Jacobs,Harriet.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2001.
[2]申丹:《整体细读与经典短篇重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
[3][法 ]米歇尔·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4]鲍小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5]Gates,Henry Louis,Jr.ed.The Classic Slave N arratives.New York:Penguin Group,1987.
[6][法 ]西蒙娜· 德· 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7]Chemishanova,Polina Petrova.“Representing the Plantation Mistress in AntebellumLiterature”.<http://firstsearch.oclc.org/WebZ/FSQUERY?format= BI:next= html/records.html:bad= html/records.html:numrecs=10:sessionid=fsapp8-42322-gejxwje0-i27nsn:entitypagenum=4:0:searchtype=advanced> (5 July,2010)。
[8]周礼:《19世纪美国报纸的社会影响》,《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年第 2期。
[9][英 ]伊雷特· 罗戈夫:《视觉文化研究》,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周春:《抵抗表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形象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9月第 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