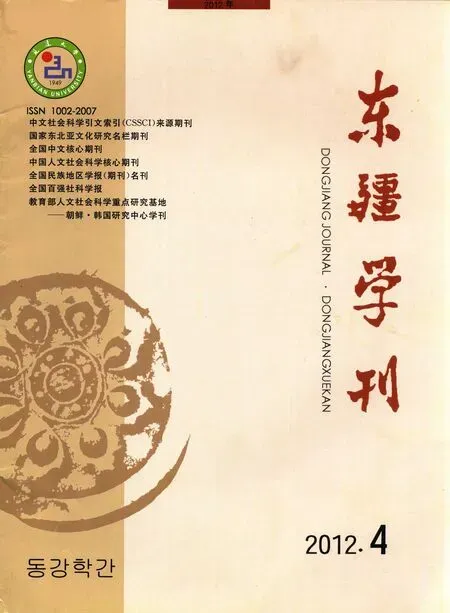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阈中的《污染海域》
宿久高,杨晓辉
《污染海域》是日本当代推理小说作家西村京太郎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71年。作品发表之际,日本先后发生了“水俣病”、“森永奶粉事件”、“萨利德迈安眠药事件”等多起公害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为了应对和消除这些公害事件对日本国家和社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日本政府积极采取对策,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大气污染防治令”(1968)和“噪音防治法”(1968)等一系列法规,并认定“疼痛病”、熊本与新泻的“水俣病”等为公害病。这一系列举措,为日本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指明了方向[1](8)。
《污染海域》讲述的是一起公害污染、公害杀人事件。小说以律师中原收到一封来自17岁自杀少女梅津由佳的来信拉开序幕。该少女——主人公梅津由佳是新太阳化工厂的一名工人,工厂位于伊豆半岛的锦浦。由佳因长时间在废气弥漫的环境中工作,患了哮喘病,痛苦至极。她认为这与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关,因而要求公司补偿,可公司的回答却是:如果住院就开除。中原律师虽然能干、正直、善良,但为了生计,也不得不以代理能赚钱的诉讼案件为先。所以,由佳的信就被搁置起来。直到某一天,中原从报纸上得知由佳从游船上投海自杀,良心受到谴责,才奔赴现场调查这起事件。在调查过程中,他遇到了质朴的高中教师吉川,这是一位领着一群高中生投身于家乡环保事业的教师。同时,他还遇到了“公害调查团”的团长、公害“专家”——吉川的老师冬木教授等人。冬木等人出于私利、竟然无视公害事实,公然断言该地域没有污染。作者以中原出于正义,着手调查少女投海自杀事件为主线,揭示了海洋污染给民众带来的身心伤害,凸显了“利己主义”等精神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危害这一主题。
生态文学研究者鲁枢元曾将生态学分为“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并将梁漱溟指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人的复杂性与其提出的生态学三分法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相对应。他认为:就现实的人的存在而言,人既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其观点强调了精神生态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和研究价值。[2](146-147)笔者认为,该作品对人类精神生态的积极探索,使得小说成为了一部充分展示作者生态智慧的作品。小说的题目《污染海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生态观及对现代社会的深度思考。
一、人与自然的对话
“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及对自然的理解,对我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3](28)。早在日本古代,人与自然的对话已悄然开始。那时的人类尚未意识到自我,对自然抱有依偎和敬畏之情。随着历史的推移,特别是到了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工业立国思想浸润着人们的心灵,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抬头。自然成了被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和平等对话关系被彻底摧毁,处于矛盾与对立之中。诚然,大自然是脆弱的,但只要不过分施压,它仍然富有弹力和韧性[4](93)。正是因为人类的施压超过了自然的承受力,大自然才对人类的胜利进行报复。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描写的正是日本战后在经济复兴、工业发展过程中破坏自然、破坏环境,导致大量公害事件发生,从而招致严重后果的过程。
上世纪 50年代,日本在四日市建起了全国第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城,工厂废水排入伊势湾,使得海水变臭,大气浑浊。仅几年光景,整座城市便黄烟弥漫,上空几百米厚度的烟雾中漂浮着多种有毒气体和有毒的重金属粉尘[5](31)。1961年,四日市哮喘病大发作,市民在病痛的折磨中艰难度日,几年后,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痛苦而自杀[1](8)。上世纪 6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继50年代后又迎来了以出口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个高速增长期,增长速度维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平。70年代,石油制品的消费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然而,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农业、林业和渔业为代价的。梭罗曾经慨叹道:“感谢上帝,人类现在还飞不起来,所以还不能像蹂躏地球一样去蹂躏天空。”[4](99)但是,一百年后,梭罗的感慨不仅在美国,在大洋彼岸的东瀛也变成了现实,蓝天、大地、海洋无不充满了人类破坏的痕迹。《污染海域》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污染海域》发表于1971年9月,正值日本四日市哮喘病患者剧增之时。小说中的锦浦海域,曾是一个海天一色的小渔港。自从这里建了化工厂以后,昔日美丽的自然、这片纯净的海域和清新的空气被化学工业吞噬殆尽,人们终日为污浊的海水和空气所困绕。片片褐色的油污漂浮在海面,臭气熏天;座座烟囱吐出的毒烟形成厚厚的天幕,令人窒息。“残缺不全的大自然,成了一首被抽掉了某些更令人兴奋的乐章的交响乐,一本失去了很多章节的书。”[4](91)工业霸权摧毁了原有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与侵占,招致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冬木教授前一天还断言,锦浦海域没有污染,而遇害后被扔入大海的他,尸体上却沾满了油污。冬木的死被断定为他杀,是因为他死后,胃里灌满了伪造的干净盐水,而尸体上却沾满了海里漂浮的废油。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另一方面,高中教师吉川带领着高中生“专家”,建起了“锦浦高中公害研究所”,三年如一日,奔走于山间、海边,做着亲近自然、拯救自然的努力。小镇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足迹。鲤鱼旗下,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风向;用温度计测气温,用手表记时间。手里的温度计各式各样,女学生拿的,还有可爱的人偶形温度计。鲤鱼旗也好,温度计也罢,都是他们走进深山、靠近大海、与自然对话的工具。他们用最柔和的方式感悟自然,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最质朴的对话。
二、人与人的对话
当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话关系也被无情摧毁。梅津由佳在与厂方交涉无果的绝望中最终投海自杀。律师中原正弘出于自责和义愤,毅然挺身投入到案件调查之中。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中原意识到公害调查和诉讼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持久战。人与人的关系,因利益的不同而处于相互排斥甚至尖锐对立的状态。
主人公梅津由佳因工厂不承认自己患病是公害所致,而住院治疗又要被开除,于是在绝望中走向绝路。她在投海自杀之前,曾试图与企业管理层对话,期望通过对话唤起对生命的共鸣,寻求一种生命关怀。但企业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又怎能愿意开辟对话的空间!律师中原几度去找新太阳化工厂的管理人员,甚至去找企业老板佐伯大造讨说法,希望通过对话,唤回理性,为那些控诉无门的渔民开拓可能的生存空间,但也是无果而终。
受害的渔民在对话无果的情况下,竟也采取了默许公害的态度。查明公害产生的原因,超出一般渔民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如要渔民举出因果关系的证据,实属不易;若通过科学检验方法取证,势必拖延诉讼,而且也无力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而受害人若等得到赔偿后再行医治,恐怕早已处于绝境之中。这一点,从中原的叹息中也可窥见一斑。
受害的渔民为了生存,抑或为了眼前利益,只好选择了自欺欺人和欺骗他人的妥协方式。与其等待漫长的公诉,还不如在谎言的世界里实现人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换来企业捐赠的市立医院,换来高中的若干现代化教学设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将污染的海产品卖给不知情的市民而换来维持生计的钞票。
利己主义的魔咒已经将人与人的对话推向了不可实现的境地。原为师生关系的冬木教授与高中教师吉川之间竟然展开了师生对决。受雇于新太阳化工厂的冬木,率领“调查团”,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所谓的公害调查,并发表了“中间报告”,向当地民众宣布该地域没有公害。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背弃了道德良知和责任。但冬木遭害前,与自己的学生吉川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富有良知和值得庆幸的。冬木在弥留之际,终于被眼前这个领着一群天真的高中生,进行空气和海水污染检验的吉川所感动,他读完了吉川和高中生们记录的公害日志后,在最后一页写道:“惭愧。我竟然不如这些高中生。吉川君,你是对的。”[6](206)
冬木与吉川通过对话达到了生命共识,只是这种共识来得太迟,冬木在被企业利用后还是难逃被杀害的厄运。
三、人与自我的对话
人类精神生态的健康是当今自然生态健康的前提,而健康的人类精神生态需要汲取自然生态中的健康营养[7](88)。在被人类异化的自然面前,人类的精神生态也无法保持平衡,这其中包含人与自我对话的建构失衡。在工业立国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渔民变身为工人,农村人口急剧流向城市,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人自身原本包含精神与物质、肉体与心灵两个方面。作为完整的人,应该兼顾两者[8](11)。但现代人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往往看重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追求,精神受到了污染。这也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由和谐走向冲突的根源所在。
在《污染海域》中,主人公中原由佳自杀前,人们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受害者的苦痛和公害的危险。观念的改变源于由佳之死。律师中原在赴锦浦调查公害事件的途中,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司机的偏颇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原曾有过的想法不谋而合:企业进驻后,贫穷的小镇摇身变成繁华的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有了酒吧,有了脱衣舞剧场,就连近处的艺妓,只要招呼,都会踊跃而至。那些整日喊“公害、公害”的家伙,真是烦死人。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里有钱赚?但由佳的死令他幡然醒悟,开始自我反思,并从灵魂深处进行自我批判,进而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公害事件的调查中去。出租车司机的偏颇言论,非但未让中原动怒,反而使他深刻反思自己此前的态度和行为。
锦浦的工厂、医院均是新太阳化工厂老板佐伯大造出资建造的,整个小镇都置于他的权利和金钱桎梏之下。物欲堵塞了人的心灵渠道,科技文明腐蚀了人的健康心态。在这个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小镇,人的精神空间也被侵蚀殆尽。
镇里的公害事实一目了然,但在这位学者专家的“专业考证”下,锦浦摇身变成了一座活力四射、人们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现代化小镇。物质欲望的膨胀远远超过了自我精神欲求,“在自然生态系统蒙受严重损伤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在随之恶化[9](36)。”
比利时生态学教授 P.迪维诺 (Paul Duvigneaud)早在 70年代初在他的《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正式提出了“精神污染”这一概念[9](21)。这种精神污染具体体现在自我和道德感的丧失。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条,自然万物中的一名思考者,在敌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是无法寻回原初意义的人的善良本性的。而三年来凭借一己之力和非凡见识,率领一群高中生,从事公害调查的高中物理教师吉川的行为,如同黑暗中的一抹曙光,让有良知的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了生的希望。吉川憧憬的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他与冬木的斗争,可称为“竹枪战术”:一方是由所谓专家学者指挥的调查团,配备精良,一方是高中教师率领的学生团,工具简单、粗陋;一方是直升机、发烟筒、二氧化硫自动检测装置,一方是自行车、鲤鱼旗、学校化学实验室、宣传册等。势不均力不敌、几乎赤手空拳的吉川,在几近挫败之时也没有退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认为,大众幸福 (the general happiness)是唯一有价值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10](59)。“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以行动者的共同利益作为道德和行为的基础优于仅仅以行动者的个人利益作为道德和行动的基础[10](37)。”吉川的行为不是为了满足自我欲望,他是通过自我反省、发现,并将大众幸福和大家的共同利益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前提而付诸行动的。人类认识自我,是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自身行为的盲目性和愚昧性,真正主宰自己。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人类才能实现与自我的对话,进而超越自我,走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未来。
四、结语
与自然为友,天长地久。生态文学表层上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求其深层研究意义,是探讨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对于生态文学而言,也许自然环境只是外在的物态,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11](378)。所以,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深入分析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作品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这不仅能使我们清晰地了解上个世纪 70年代日本社会的生态环境和精神意识状态,而且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对话,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1][日 ]佐岛群巳:《学校中的环境教育》,东京:国土社,1992年。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德 ]汉斯· 萨克塞著:《生态哲学》,文韬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年。
[4][美 ]唐纳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5]张庸:《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环境导报》,2003第 22期。
[6][日 ]西村京太郎:《污染海域》,东京:德间书店,1987年。
[7]钟燕:《生态批评视野中的 <海风下>:一个“蓝色批评”个案分析》,《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
[8]吴先伍:《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冲突的观念论根源》,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9]鲁枢元.《生态解困:期待一场精神革命》,《绿叶》,2007年第 3期。
[10]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陈真.《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鲁枢元.《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