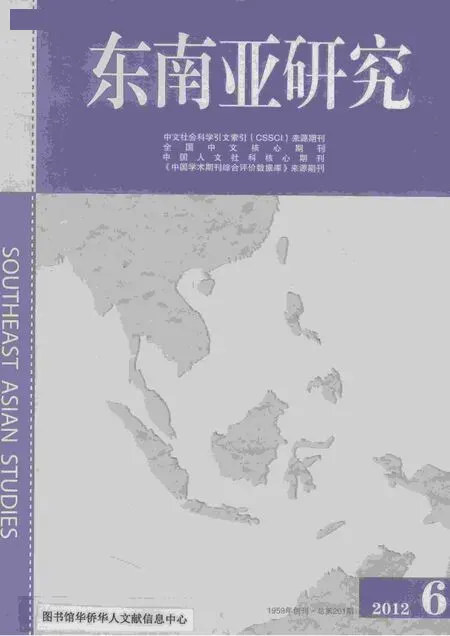从女性文学形象看当代越南妇女生存现状
黄以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51042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越南女作家们创作的短篇小说日渐成熟并在文坛上占有相当的分量,她们的作品以及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并得到评论界的如潮好评,这可从女作家们的一系列作品一再获得各种奖项得到明证,同时这也证明了其作品的受欢迎并非偶然。这些作品展示的女性形象显现着人们熟知的身边女性的朦胧倩影。女作家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其独特之处,越南本土的文学评论界对这些女性形象做过基于文本意义层面的传统的文学批评,然而,对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社会意义,特别是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少有涉及。本文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着重考察20世纪末在越南当代文坛上广受欢迎的女作家阮氏秋惠、武氏好、依斑的获奖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集中探讨具有典型性的女性文学形象的深层寓意,试图说明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并非虚构的想象,并以此为据评析当代越南女性的地位,揭示越南女性的整体生存本相。
一 女性形象范式
范式 (paradigm)意指可被看作是典范的样式。本文所取之“女性形象范式”,是文学共同体对作家的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女性人物的总体关照,是人们心目中的女性总体形象——她们有着外形与内质上的共同点,是具有共性的经典范例。
综合阮氏秋惠、武氏好、依斑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种典型性的女性形象范式。
(一)传统贤良型
这是最典型和“曝光率”最高的一类人物,年龄层次涵盖老中青。从她们身上可以反观越南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原型,她们集“女子气质”于一身,顺从、纯洁、隐忍、包容、自我牺牲、自我否定……她们以家庭、丈夫/恋人、子女为中心,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可以说是失落了自我的群体。阮氏秋惠《金色秋天》中的“外婆/奶奶”,依斑《一生的三分之一》中的“我”,武氏好《贞女魂》中的无名氏“她”以及《笑林幸存者》中的“阿草姑娘”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一生的三分之一》中的“我”在农村生活、学习和成长,家乡有她年少的身影和生活乐趣,还有“他”——首都某文科大学的学生 (后来成为诗人)——她的初恋,她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能与“他”齐头并进,她进城谋生,后来虽然与另一个人成了家,但丈夫年轻有为,是她生命的另一部分。之后,她有了两个天仙般的孩子——她生命中的第三部分。除此以外,她自己呢,什么也没有。家庭生活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暴风骤雨,“他”是她唯一的心灵安慰。分开多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却以“砰”的关门声拒绝了“他”,没有一句话,因为,她要维护她历尽艰辛换来的宁静温馨的家庭。故事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没有情节,没有矛盾冲突的描写,基本以回忆检视“我”走过的人生历程,更多的是“我”对“他”(在故事中以第二人称出现)的一种自语式的倾诉。人物“我”温顺、贤惠的性格在这种自语式的倾诉中显露。
《笑林幸存者》以两条主线讲述主人公的故事: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阿草姑娘善良,隐忍,包容。她的生命如小草般渺小,她的遭遇令人扼腕。在战争年代,她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祖国为了民族扛起枪杆子投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她与四个姐妹驻守在隐于长山山脉的某一军需库中,美军的落叶剂与山林瘴气夺走了姐妹们的灵气,她们染上了“狂笑症”,军需库所在的那一片林区,因此得名“笑林”。在美军的一次偷袭中,为了保护正患伤寒的阿草,姐妹们拖着虚弱的身躯与敌军在密林中周旋,全部牺牲了。阿草成了幸存者,牺牲了青春年华与如花容颜的幸存者。然而,相对于那四个姐妹,她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阿草回到校园中,回到恋人身边。阿草枯槁的容颜使男友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了不让男友怜悯自己,为了男友真正的幸福,阿草姑娘自编自导了一出自己“移情别恋”的戏,“决绝地”离开了男友。两条主线勾勒出一个典型的传统越南妇女形象:隐忍、自我牺牲,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性命,为男友的幸福而舍弃自己的幸福。
《贞女魂》用神话故事的叙述语气讲述了古代一个家庭祖孙三代女性“一辈子供奉当兵的丈夫”的命运悲剧。祖父一去不返,父亲两鬓花白始返家。到了第三代,女儿与小伙儿青梅竹马,一个如初绽的玫瑰,一个似腼腆的处子。他为皇命出征,她芳心暗许。经过17年的漫长等待,“她”终于等回来她的郎君——有着如钢铁般冷峭目光和显赫战功的将领。新婚之夜,她惊觉自己忠贞不渝翘首以待了17年的腼腆小伙已变成一台杀人机器,并且,永远失去了“笑”的功能,“她”用青春乃至一生等回来的只有男人冰冷残酷的心。“她”看到的是无数的冤魂、丈夫沾满殷红的血的双手,丈夫已然忘记了人除了征战、杀戮,还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做:微笑。新婚的幸福荡然无存。也就在新婚之夜,丈夫出走,她从此落下害怕见人的病根,孤独终老。“她”死后,灵魂幻化成含羞草,一如作品名《贞女魂》所预示。故事在一组风与花、草的对话中以童话的形式结束。作品充满灵异、神鬼之气,仙界与人间的景象穿梭出现,成为维系人物关系、揭示作品主题的纽带。
(二)独立冷静型
这种类型的女性浑身散发出现代妇女自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气息,她们敢于独立承担人生。她们中的大部分成功投身到父权社会中,与男性并肩战斗在时代的舞台上。不可思议的是,伴随着她们的成功,可能是婚姻与情感的逝去,使她们成为婚姻与情感最为脆弱的群体。往往,在她们成功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作为后方的家庭中,男性坚实可靠的肩膀要么无迹可寻,要么不可靠。面对这一空白,她们惟有藏匿起难以与外人倾诉的内心苦闷。为此,她们也曾有过为诱惑所迷惑、倾心的刹那,但最终仍能保持理智与清醒。无比讽刺也无比恼人的是,许多时候,在她们貌似清醒的面纱下面,是饱受“本我”与“自我”、个人情感生活与社会责任相纠缠这一双面人生煎熬的无边苦痛。这一类型的代表有阮氏秋惠《楼梯》中的“阿珍”、《故人》中的“我”,依斑《闪电过后是风暴》中的“她”、《抱窝鸡》中的“我”、《有魔力的女人》中的“女人”等。
《楼梯》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女白领阿珍。作品通过对阿珍每天必经楼梯时的心理活动描写,以及一段偶尔发生的阿珍与某男看似“无厘头”的对话,揭示在都市拼搏和生活的人们的生活场景和心路历程。每一次的拾级而上,阿珍都会在心里想象并描绘将会出现在楼梯尽头的画面,而结果多是令她意想不到的景象:有惊喜,有失望,更重要又更吸引阿珍的是它的神秘感。与此同时,阿珍发现,当到了楼梯尽头,所有的貌似“真实”的东西会在一瞬间被撕去面具,那种“期盼”的心理亦会在一瞬间被粉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那么的神秘与不真实。阿珍的心理活动似乎预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生活就像爬楼梯,人们不知道楼梯的尽头有什么,它令人向往;而一旦到了尽头,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故事情节被淡化,人物心理活动得到彰显,人物形象由此展现在读者眼前:一个喜欢思索而又对一切感到迷惘的现代都市女性。
《闪电过后是风暴》描写了一个喜欢自问、在平淡生活与乏味的机关工作中漂浮的女人。她潜意识里填塞了对平淡、索然无味的现实生活 (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牺牲自我等)的不满,她认为现实生活消磨了女人的天性 (每次她轻哼小曲都会遭到来自丈夫、婆婆的冷嘲),剥夺了女人的智慧。一次公干中发生的暧昧让她“明白”她需要激情来点缀日趋“亲情化”的夫妻感情生活。但是,面对丈夫时发自心底的内疚感让她没有逾越雷池。然而,空虚的感情世界常常让她迷恋那种甜蜜的感觉,以至于她常自问:“为什么我想把头靠在他的肩头?”她无法给自己找出合理和正确的答案。经过一个多月的内心挣扎,在丈夫的悉心照料下,她终于平复心态,认为那“甜蜜之感”是现代人类普遍需要的一种“非常温柔”的情感——一种非亲情、爱情、友情的“第四种”感情——边缘感情。最终她战胜了自己,在风暴即将到来之时与“他”成了好朋友。
(三)现代魔女型
所谓“魔女”,相对“贤良”而言,是“传统贤良型”女性形象的反面,是脱序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说,对这一类型人物的塑造,是女作家们对女性在情感婚姻生活中以被动为荣、以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的颠覆。但是,她们挑战自我、挑战旧观念、挑战男性对女性固有的审美观等的种种行为有悖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准则,最终,她们或孑然一身,或为此付出生命。她们都是疏离传统的女性。典型的有依斑《致母亲瓯姬的信》中的“女儿”、 《情人》中的“她”,阮氏秋惠《后天堂》中的“我”和“女儿”、 《未婚少妇》中的“阿媚”,武氏好《地狱之舞》中的“垂珠”、《救赎之海》中的“妻子”和“女人”等。
《写给母亲瓯姬的信》(以下简称《信》)讲述了未婚怀孕的女儿“我”的故事。“我”在医院做“人流”时遭到来自母亲、病友及医护人员的厌弃、歧视和唾骂。别人的眼光引发了“我”对爱情的怀疑。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我”终于将压在心底的苦闷与不解,以家书的形式向母亲乃至社会宣泄、质问。 《信》流露出来的感情真挚,叙述及描写颇为直白,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但它的质问有着震撼人心的穿透力,更直指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
《后天堂》讲述一对母女异常相似的命运遭遇及她们对爱情差之千里的态度。“我”——作品中的母亲——24岁那年爱上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把“我”带进了天堂。六个月短暂的欢愉之后,“他”抛弃了“我”,将“我”推进了万丈深渊,之后,伴随着“我”一生的是对男人的怀疑、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和“我”视如包袱的女儿。“我”漠视女儿的存在,只抚养她而极少关心她,她只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在男人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和适当的距离。“我”沉迷于一种世人眼中堕落的生活方式 (沉湎于舞场,周旋于男人间)之中,日子在百无聊赖中流逝,“我”以为一切会渐被遗忘在这种生活惯性中。直至女儿16岁生日那天,一切又突然涌现在眼前。透过女儿的日记,“我”从梦中惊醒,女儿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正在步“我”的后尘,经历着一场所谓“天堂——后天堂/地狱”的洗炼,女儿却全然不知。心力交瘁之下,“我”变成孤魂,游荡在女儿与被其视若“天堂”的男人之间。故事幽怨,充满悲剧气息。
《未婚少妇》中的阿媚姑娘为了摆脱贫穷落后乏味的农村生活,追求未来的幸福,不顾身患绝症的姐姐的劝告,主动搭上亲姐夫,在城里姐姐家中双宿双栖。姐姐身心不堪重创,带着年幼的儿子避住到乡下。一年后,阿媚在医院待产,此时,在乡下,她的姐姐也撒手人寰。当她产后回到姐姐家中,迎接她的只有姐夫留下的信和空荡冷冰的屋子……故事没有具体详细的人物外貌与行为描写,但有着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故事中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借助人物语言不断铺开去,直至故事的高潮——阿媚在精神上被彻底抛弃。其间,人物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也暴露殆尽,各种传统与现代的观念的交锋也得到充分的展现。
二 形象范式对现实的反映
文化批评理论认为,一切形象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根据社会和审美惯例创造的……是在动态的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中被生产出来的。”[1]形象的生产过程“取决于它们所引发的广泛的文化意义和它们被看时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语境”[2]。那么,毋容置疑,“形象是一种生产和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方法。”[3]由此可见,基于生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形象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文学形象是意识形态表象系统的一员,女性形象作为主体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也当属此表象系统中的一员,其主体的建构不可能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越南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范式的产生凸显了越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现状——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主体的期待或者建构?
巴赫金 (M.Bakhtin)的“镜像”理论认为,在“镜像”中,“我” (即“个体”——笔者注)无法认识整体的自我,镜像中的自我认识始终渗透着他人的虚假意识,“我”必须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借助于他人的视角才能构成对自我的完整认识[4]。该理论阐释了一种源自“他人眼中之我”、“我眼中之我”的“我与我的关系”,是主体自我认识的关键所在。要深刻认识自己,“我”必须通过他人对我的反应、态度、观照和评价等等,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到自我在人群中的真实存在状态,以避免在自我认识中被动地渗入他人的虚假意识。把“镜像”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我与我的关系”体现在作品主人公的“自我认识”上[5]。基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我们认为女性形象范式具有“镜像”的功能。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对生活的高度凝炼。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现实中的女性可以借助那些沉淀下来的历史中的女性系列形象见出自我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女性形象范式”(在这里,其实质是一组镜像)是女作家们凭借一定的想象理解、描述、规范并再现她们所看见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以此折射女性在社会中存在的状态;另一方面,生活中的女性通过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体验,摒弃虚假,从而完整、真正地认识自我、反观自我,实现自我意识的重新定位。
倘若我们把这些女性每天的生活情景加以浓缩,可以得出带有共性的女性生活场景:安稳、普通、富足、风平浪静的城市家庭生活场景。她们每天穿梭来往于办公室与家之间,但往往家才是她们生活的中心:下厨、洗濯、照顾家人;偶尔遭遇一下浪漫、呢喃。不管是“传统贤良型”、“独立冷静型”还是“现代魔女型”的女性人物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琐屑、日复一日、平庸无比的生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刻意描写“独立冷静型”女性人物如何在危机四伏、尔虞我诈的政界、商场拼搏,相反,不惜笔墨地描写她们平淡无奇的家庭和情感生活。试想,面对色彩缤纷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种生活随处潜伏着引发危机的导火索,稍有不慎,便极易导致夫妻间或是心灵、或是身体、又甚或两者皆有的背叛 (如《情人》、《闪电过后是风暴》等短篇中的人物)。倘若是未婚女性,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做出逾越雷池的另一种背叛也不是不可能 (如《后天堂》、《致母亲鸥姬的信》等故事中的人物)。对这种生活场景的描写,作者的意图何在?是否旨在肯定女性对生活、事业与家庭的一种态度:此三者被同时置于一杆天平之上?然而,显而易见,这是极难维持的一种平衡。
保持家庭与事业的平衡是现代社会对职业妇女的共同期望,甚至,妇女自身也是这样奢望着。但这恰恰让妇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并最终导致了这个神话的破灭。如上文所述,“独立冷静型”女性的工作场景不是女作家青睐的描写对象,似乎她们在有意规避这样的描写。设想,如果女作家着力描写女性的工作场景及其工作表现、成就等并建构起女性自我形象,这种叙述是否有违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审美惯例?女作家的作品能否得到认同并获奖呢?我们不得不对此表示怀疑。
有着极强穿透力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中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个体,一系列女性形象范式的出现,使越南社会意识形态仍然以封建制度的产物父权制占主导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明晰。男权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人们对所谓的“女子气质”非常熟稔,女子必须具备的“工、容、言、行”已成为世人眼中的一面超大型镜子,规范着女性的一切行为、道德、言语和处事,同时,也是女性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我、调整自身脱轨行为 (如“现代魔女型”人物的行为)的标准。另一个问题是,职业女性 (社会角色)与家庭妇女 (家庭角色)的这一双重身份带来的角色冲突,社会对“双肩挑”女性的“女子气质”近乎苛刻的要求,使女性心力交瘁、身心俱疲,迫不得已选择“回归”家庭。那么,她们的事业呢?
三 常态下的不合理
结构主义批评曾提出一种假设:任何故事的形成都离不开规矩和想象。长久以来,这一假设一方面影响了文学文本消费者——读者的再创造力,另一方面,亦多少削弱了文学文本生产者——作者的艺术才华和创造力。当读者面对按照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惯例塑造出来的形象,他们会怎样解读它?
先看几组简单的统计数据。
第一组数字:据越南统计总局的统计,截至2010年,越南总人口约为8700万,其中,女性人数约4400万,约占总人口的51%[6]。
第二组数字:据越南国会的统计,从第四届国会开始,女性国会代表人数所占百分比分别为32%(1971—1976),27% (1976—1981),22%(1981—1987),18% (1987—1992),18.5%(1992—1997),26.2% (1997—2002),27.3%(2002—2007),25% (2007—2011),24.4%(2011—2016)。虽然,女性国会代表人数略有波动,但总体而言代表的层次和质量均较前有大的提高[7]。
第三组数字:越南女性国会代表的比例在亚太地区位居第二,在世界国会联盟135个国家中位居第九[8]。可以说,越南女性的政治地位及参政意识都较高、较强,反映了越南在解放妇女、争取性别平等事业中取得的可喜成绩。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这个国家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尺度,而妇女的参政议政程度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妇女参政的广度与深度如实反映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从1930年越南共产党成立初始在“政治论纲”中明确越南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妇女解放,到1986年越南经济社会步入革新开放时颁布的《婚姻家庭法》 (修订案)、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各次大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制订的培养、选拔女干部的规划,再到近期的《性别平等法》的出台,说明一直以来越南党和国家在解放妇女、争取性别平等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
但问题并不能就此而止步。上面三组数字之间形成一个反差:在妇女人口占总人口数51%的越南,女性的参政议政比例相当低,人数非常少。也就是说,妇女参政的广度与深度仍不尽如人意。那么,该如何评价越南妇女的社会地位?比照一下女作家作品中的系列女性形象范式,我们发现一些常态下的不合理现象。
(一)不合理现象之一:湮没的星星
越南女性既善于经营家庭,也擅长经商,而且,有着相当强的经济独立意识;涉足政界的女性虽占比例不高,但在政坛的位置也可说是举足轻重(越南现有一名女国家副主席)。她们如同夜空中的星星,在男权社会的苍穹下熠熠生辉,格外明亮。
然而,在越南当代文学文本、特别是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文本中,绝少有驰骋政坛、叱咤商场的成功女性人物形象得以具体地再现,她们几乎销声匿迹,而为家庭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等属于“女子气质”的美德则被无限放大。另一方面,重男轻女的观点仍使女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被支配、被领导的位置,女性自身 (包括女作家们)浸染于这种意识当中并无时不受其暗示直至对它默许,以致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被迫认同既定的传统角色,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自我生命本体的主人翁。因此,笔者认为,在越南,成功女性仍占少数而且未能代表越南妇女群体。相反,平庸、平凡、默默无闻,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的人物形象,才是现实生活中越南女性的生存本相,是她们的缩影。她们仍以爱情、婚姻、家庭为己任,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冠于女性头上的“女子气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已浸透她们的骨髓,以至于她们“甘心”沉迷于日常生活的琐碎。
(二)不合理现象之二:美女的缺席
再看三种形象范式,我们捕捉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女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回避”在作品中再现外形外貌俱佳的美女佳人,她们的作品遭遇美女集体缺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美女”永远是市场意识形态的中心,但不论“美女”、“丑女”还是“庸女”,其实质,仍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其身份是“她者”客体。视觉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不论在何种文化中,凝视均发生在主体(注视者/观察者)与客体 (被注视者/被观察者)之间。“注视绝不只是去看,它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心理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注视者是优越于被注视的对象。”[9]在这种不平等而且多元、多层次的关系中,女性更多的是客体而非主体。约翰·伯格(John Berger)早在1972年就指出,女性同时成为观看者与被看者的这种关系,不仅决定了大部分的男女关系,也决定了女性与自己的关系,女性不但成为自己所观看的影像,亦“把自己变作对象”——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10]。亦即,在女性与自己的关系中,女性以双重身份出现:一个是作为被观察者的女性,一个是作为冷静的观察者的男性。由此,可以断定,女性并非只以自己的视角去观看 (不管是看自己还是看别人),她同时也站在男性的立场上用男性的视角去观看。可见长久以来,由于社会文化原因,女性作为审视和观察者的自我其实是以男性的视角在自我观看,印证了形象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引发的广泛的文化意义和它们被看时 (体现在文学文本中则是被阅读、被阐释时——笔者注)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语境。因此,女作家们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时候,为了不让她们成为“景观”,对笔下人物的外形外貌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笔地描写她们的内质——某种内在的魅力,那种“有魔力的女人”(依斑作品之一)坚持以女性真正自我的角度去观察、审视、体验并体现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她们的作品隐藏着张扬女性潜在能力的强烈的观点:请你关注我的其他方面,包括我的学问知识、我的生命经验、我的内心感受、我的社会角色,等等。美女的缺席无疑成为一种反讽,它直指这样一个事实: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并非男性心理期待的对象,它摧毁了男性心中的天使神像并向世人宣布:姐妹们不愿意亦不再永远是被凝视的对象与客体。
四 潜文本的寓意
富有文化反思和批判力的文学,总是实现着它特有的对现存文化的“解构”和“重建”[11]。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形象的意义都是多元的,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将之概述为表面意义和隐含意义。“形象的表面意义和它字面的、描述的意义相关。……隐含意义依赖这一形象的文化历史语境和观赏者对那些环境的体验和认识。”[12]
出现在本文论述过程中的多个设问到这里也许已有答案。越南女作家凭借一系列的文学文本,通过对现实中女性群体的集体生存本相的再塑造,为我们展示了具有典型性特点的女性形象范式,她们代表着众多的越南女性,是越南女性生活的常态。然而,亦正是这些常态揭开了隐匿在深处的某些寓意。其一,妇女的生活场景仍以家庭为中心,视家庭为平凡生活的立足点。其二,在政坛、商界占一席之地的女性形象/人物未能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其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女作家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可见,这些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并非虚构,而是对现实的本真复原。女性借助形象范式重新认识自我,并以此为诉求,摆脱男性视阈窥视下的客体身份。
文学话语作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二度加工,自然会渗入更多的虚构和想象成分[13],但在女作家的文学文本中,虚构和想象成分却被排除在外。那么,女作家们何故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来塑造、建构这些女性形象范式,而弃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成功人士不顾,使她们在作品中缺席?是否这是女作家叙述策略的选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叙述策略的选择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14]。在东方社会,“女性面临着强大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其在父权制文化之内的位置令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女性的创作,始终笼罩在一种悲剧性的惨淡前景之中。”[15]然而,在德里达 (J.Derrid)看来,缺席的能指,即“未说的话”和“未写的文”,能够和“已说的话”一样重要[16]。对于意识形态批判而言,如果在各种互文性的含蓄参照中得到表征,沉默的话语与缺席的话语也可能产生出各种强大的政治影响——这就是笔者从女性形象范式背后读出的无声话语:越南妇女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与解放,她们仍未彻底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注 释】
[1][2][3][11][15]余虹、杨恒达、杨慧林主编《问题》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2页、第54页、第52页、第7页、第50-51页。
[4][5]秦勇:《论巴赫金的“镜像”理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越南统计总局网站,http://www.gso.gov.vn/default.aspx?tabid=387&idmid=3&ItemID=12874
[7][8]越南国会网站,http://www.na.gov.vn/htx/Vietnamese/C1454/?cateid=1456
[9]《文化研究》第十辑编者话《阿尔都塞及其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2543,2004年3月18日。
[10]参见黄以亭《背负传统的反叛——从“叙述声音”说开去》,《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3期。
[12]〈英〉约翰·伯格著,戴行钺译《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13]孟登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问题》,《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14]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6页。
[16]〈美〉艾伦·卢克著,吴冠军译《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