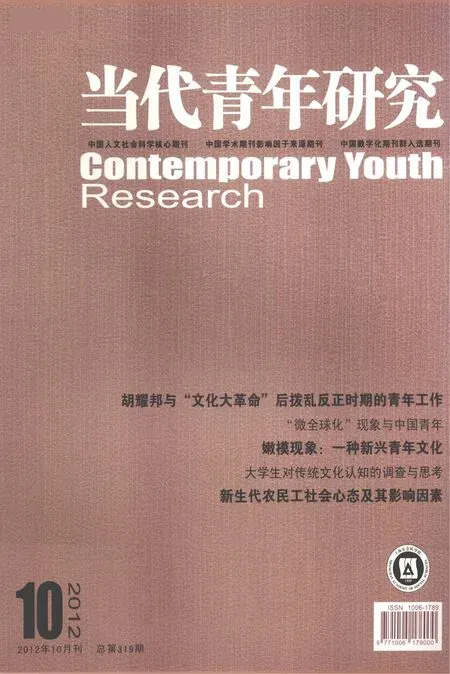“微全球化”现象与中国青年
孙嘉明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微全球化”现象与中国青年
孙嘉明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由于计算机网络等通讯媒体的广泛使用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突破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以个体为核心的全球性的社会交往模式。“微全球化”研究是一种基于微观视野的全球化研究,其一般模式和共同特点是把个人层面上涉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作为其研究的切入点,并进而把握某种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微全球化”现象泛见于与青年群体相关的各种活动和事件中,对青年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微全球化;跨国交往;跨文化互动;全球社会化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特别是年轻人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周游世界,或参与到国际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中。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全球化洪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这是由于人类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由跨越国界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状态中,这也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很显然,这一时代的重要的现实基础即是人们早已熟知的所谓网络时代或曰网络社会,由于计算机网络等通讯媒体的广泛使用,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流通的全球化,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再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突破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以个体为核心的全球性的社会交往模式,从而使得各种文明、文化通过互动和大众传媒而进行频繁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么一个客观存在的全球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与全球化之间正形成着某种相互作用,或更具体的说,个人与虚拟全球社会这一现实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频繁和密切的互动,这种互动的过程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个体的成长,激发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提供了展示个体智慧的机会;而这种互动的结果则是作为众多个体的集合体得到全面发展,生存的社会情景得以改观。这种个人与全球化现实之间关系的现象则可概括为“微全球化”现象。
一、“微全球化”概念
全球化研究可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全球化的宏观研究,也称“巨全球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体制、机构、公司和制度性的跨国界活动。早期的全球化研究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来进行,之后则基本上是以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经济系统、文化变迁等宏观视角,以城市、区域、跨国公司作为分析单位来进行研究。[1-3]全球化的微观研究,亦称微全球化研究是基于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的全球化研究。它主要以个人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个人如何受全球化的影响,个人如何参与全球化的实践,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进而影响到本地社会为基本研究内容。具体来说,全球化的微观研究就是对诸如对个人层面的跨国界流动、跨文化互动,包括海外留学、境外旅游、跨国婚姻、外企求职、虚拟全球社交网络等现象的研究和分析。
国内外学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早已有之,然而“微全球化”的研究则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柯林斯所发表的题为“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一文强调了对于微观领域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重要的宏观体制变革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基于连续的重复的微观情景之变化,以及伴随着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和随之产生的对于社会存在的认识。[4]所有宏观层面的变化,诸如社会模式、机构和组织等,都可以看成是微观层面的抽象和总结。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则是微观情景的序列,而这些分布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宏观层面的总和将构成所有可能的社会学数据。
克诺尔·塞蒂纳和布洛格也曾提到全球“微结构”的概念。“全球微结构体现在活动主体尽管在地理上有着遥远的距离,然而却相互关联着和互动着。[5]米瑞姆·仪埃雷兹和埃弗拉特·盖缇在其《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模式: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到全球文化的宏观层面》一文中也提到社会文化变迁是从人们行为变化开始,从个人层面上讲,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进而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从而使得文化的宏观层面实体得以改观。[6]萨斯基亚·萨森进一步提到“微情景”和“微交换”的概念。她指出那些全球化城市中的活动主体实际上并未活动于不切实际的全球舞台,而是生活在某种日常生活中全球形态的“微空间”里。[7]笔者曾在《Global Connections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化的微观研究理论,并认为它关注于个人的全球连接,这种连接把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对于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影响和机制。[8]
上述的这些观点和概念构建和形成了“微全球化”概念的基本雏型:“微全球化”研究是一种基于微观视野的全球化研究,是把个人层面上涉及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作为其研究的切入点,并进而把握某种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行为、交往、关系的一般模式和共同特征。总体上讲,这种研究与“巨全球化”或宏观全球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微而巨”的全球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常用的是归纳法、抽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和逻辑判断法等。国内学者对于“微全球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也零星泛见于一些文章中。比如对于跨国界交往以及海外关系的研究。[9]跨国关系网的形成和建立及其功能是“微全球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由于跨国界关系网历来被认为是一种“稀有资本”,建立个人的“海外关系”其意义并不在于“关系”本身,而在于这种“关系”可能对本地社会所能带来的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微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也体现在华侨华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比如《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跨国婚姻》、[10]《中国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11]《大学生网络素养与全球意识现状研究》、[12]《中外合资企业青年人才流动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13]以及《从全球化视角看人的生存方式的当代转向》[14]等,这些研究都反映了中国青年的“微全球化”现象,也都是“微全球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之,“微全球化”现象意味着人们超越国界、跨文化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它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认识和加强人与人之间跨国界沟通和互动及其对本地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正待开发。
二、中国青年的 “微全球化”现象
多方位、多层面的跨国界交往以及全球互联网系统已经伸展到了地球上的各大主要地区。那些跨越国界的学生、研究者、情侣、游客、商人以及资本投资者穿梭来往于不同国家的城市之间,相聚在一起交流互动;全球无数的网络社交者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虚拟沟通交流等。这些现象形成了今天这种“微全球化”的基本现象和态势。中国青年的“微全球化”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概括:
(一)“出国热”与“海归潮”
“出国热”与“海归潮”是微全球化研究中的一大课题,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上升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青年人的出国热始终未减。《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9日报道,从1978年到2010年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留学输出国之一。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10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了28.47万人,比2009年增加5.54万人,增长率为24.2%。据人民网消息,美国教育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人数高达127628人,与上一年相比激增了30%。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今高速增长的留学大军中,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低龄留学人员占有不小的比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目前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占了我国总留学人数的22.6%。[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家有关留学政策的调整,出国留学迅猛发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泛见于报端和杂志,比如在《中国出国留学研究述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16]中,研究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出国留学学习内容和历史使命的演变,将中国百年留学史上的留学生划分为五个阶段:怀有富国强兵梦想的第一代,抱有革命救国志向的第二代,执著于科技救国的第三代,负有建设祖国使命的第四代,勃发创业热情的第五代。[17]诚然,当今出国留学与一百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众多普通人的选择之一。出国留学呈现出几大趋势可以概括为:(1)人数持续增多,大学生留学人数稳定增长,中学生人数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自费留学生数量占了留学生总量的90%以上。(3)赴美留学依然是众多留学生的首选,同时北欧等国家日益受到关注。(4)留学专业选择多元化,凸显理性回归。(5)留学归国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回归创业呼声日益高涨。(6)留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并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16]
出国留学不断增长的态势其实本质上反映了青年人参与“微全球化”进程的愿望以及置身于跨文化的情景的实践。一方面,出国留学对于青年人的成长以及开拓视野,提高自身素养和能力有很大的益处;另一方面,他们学成回国后对祖国的发展建设也不无益处。
与“出国热”相对应的是“海归潮”。海归回国对国家建设无异会带来诸多有利之处。这不仅仅是在于他们学到了一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科技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经历过“微全球化”的过程,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以及与其留学国的人脉关系。目前,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业人员中,留学回国人员有1.6万,其中硕士以上学位的达1.2万人,占77.4%。另据报道,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都是留学回国人员。[18]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载体的留学人员创业园取得了丰硕成果。到2009年底,全国己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148个,入园企业超过6000多家,吸引了留学人员约15000人,技工贸总收入327亿元。[19]仅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就有2家留学人员企业落户,而留学人才创办的企业已经成为各地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亮点。
国家开明的政策也为海归的回国创造了条件:从片面强调“回国服务”向全面鼓励“为国服务”转变,即不再以是否举家搬迁回国、放弃外国永久居留权和外国国籍为标准来要求留学人员,而是允许其在保留外国永久居留权和外国国籍的情况下,鼓励其以定期应聘来华工作或在海外开展对华合作等多种灵活形式为国服务。这种政策上的转变使得海归人员在华工作的同时,可继续保留其“微全球化”的某些优势,从而在本职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跨国移民
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中外经济文化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跨国移民潮也随之兴起并持续增长。其原因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有关,但也和民众个人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解放、个人的自由度的扩大相联系。30余年来,中国移民数量大增,至今已达5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青年。[20]中国流向海外移民大约可分为四大类:(1)留学移民;(2)技术与投资移民;(3)家族移民;(4)非正常渠道移民。第二、第三类移民中也有一部分是留学移民,即他们曾经是留学生,回归后又回流国外。留学移民与非正常渠道移民几乎全部是青年。以2003年的数据为参照,国际移民(移出)在全国的分布及人数是:福建省90余万人,浙江省90余万人,广东省60余万人,上海市20余万人,北京市约20万人。以上5省市已达近300万人。黑龙江、新疆、山东、云南等大多数省、市都有几万乃至十几万人。合计移出人数应不少于390万人。[20]
移居海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越来越引起重视,这不仅仅是由于移民数量的增加,而且还与华侨、华人对祖籍国和居住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关。显然,由于海外华侨和华人在世界上的人数众多,因此对这一群体和现象加以研究,正确看待和分析与之有关的各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21]
移居海外是个人在永久居住地和文化适应性,以及个人人生处境上的一种选择,但也体现了“微全球化”的一种过程,即对异域文化适应和调适的过程。从总体上讲也反映了某种社会关系的迁移和扩散。移民们在居住地与自己祖国的关系其实并非由于移居海外而终止,而是恰恰得到了更深层的发展。
(三)跨文化婚姻
跨文化婚姻是一个全球性民间互动现象。它涉及到男女双方、中介人、律师、代理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介团体等多个方面,通常也包含了婚姻双方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对于全球文化的交流、认同以及制度化机制的形成和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不断频繁,跨国婚姻已不再变得神秘。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也逐渐开放。跨国婚姻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形态悄然出现,很多中国女性以嫁给外国人为荣,追求异国婚恋成为一种时尚。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 193件,1997年已达50 773件,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据估算,中国人的跨国婚姻占到了全体婚姻的5%,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40多万外国人和中国青年男女结缘。[22]
与此同时,青年人对跨国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北京青年为例,在被调查者当中,有41.7%的人认为“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或能得到幸福,他(她)们就愿意尝试跨国婚姻”,只有23.1%的人认为“自己不想走跨国婚姻这条路”。男女对跨国婚姻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持赞同态度的人分别为41.9%和41.1%。[23]
跨国婚姻现象显然与全球化的发展有直接关联。以中韩跨国婚姻为例,由于经贸合作增加以及人员交流频繁,文化认同的机会增多,再加上韩剧热播的影响,以及国际婚介所的推动等,中韩跨国婚姻近10年来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和韩国人结婚的事例还非常少,中国人对韩国也知之甚少。当时有少许的中韩国际婚宴,基本都是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因为语言相通,交流起来比较方便。1992年中韩建交后,两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中韩国际婚姻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中韩国际婚姻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增长,截止到2010年中韩国际婚姻的多文化家庭在韩国家庭中已经占到了1%。[24]
中日跨国婚姻则体现了“微全球化”中的困惑,同时暴露了青年人在异国文化的适应性上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问题。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中日跨国婚姻增长迅速。1970年仅有475件,到1990年已增加到4 322件,增长了约9.1倍。在日本跨国婚姻总数中所占比率由1970年的8.6%,增加到1990年的16.9%。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跨国婚姻又迈上了新台阶,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日跨国婚姻从4 322件增加到10 762件,增长了约2.5倍。近年来,中日跨国婚姻数量激增,问题也纷纷浮出水面。中日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日跨国婚姻问题频发,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暴力愈演愈烈,恶性犯罪案件层出不穷。[25]
青年人的跨国婚姻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个人在人生重大事件上的选择度的增强。年轻人选择外国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必然在生活习惯、人生态度和文化适应等方面会有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而这种适应的过程是在“微全球化”情景中进行的,需要备加细心设计。
(四)境外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际旅游新兴客源输出国。仅以1994—2003年为例,中国累计出境人数近一亿人次,年均增长13.87%。中国在2003年以出境总人数2022万人次,超过1700万人次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旅游客源国。[26]
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旅游对中国人来说仅是一个梦。当时只有少数有海外关系的公民能够申领护照,并以“探亲”的方式走出国门。1988年,泰国成为中国出境旅游的第一个目的地国家,此后中国的出境旅游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呈现迅速发展的势态。据国家旅游局介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跨越。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分析,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位旅游接待大国和第四位客源输出国。
显然境外旅游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享受和经历“微全球化”的条件,有机会到异国他乡接触异域文化,与异地朋友交流,与国外的风土人情互动。然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境外旅游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协调的现象。比如有报道说,中国人不仅嗓门大,而且不分场合。在国内的饭馆、餐厅吃饭,讲究的恐怕就是热闹,这种风俗习惯在自己家中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一到了国外就显得格格不入。在饭桌旁说上两个笑话,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拍起桌子来,引得外国人纷纷投去惊异的目光。[27]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良莠不齐,大多数的人行为规范、遵守礼仪,能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但也不乏在境外丢人现眼者。虽然这些人只是作为个人参与境外旅游,但在外国人眼中,你就是中国人的象征。总之,人们随旅行社到海外旅游,那里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道德规范可能与自己熟悉的完全不同,因此必须逐渐地适应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特有的文化习俗,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处事方法。广而言之,这也是一种“全球社会化”的过程。
(五)外企就业与海外劳务
随着国家事业、企业单位就业的日趋饱和,以及越来越多的拥有先进管理经验和发展前景的外资企业入驻中国,外资企业日益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首选项。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4500万人。而据2010年上海外资企业就业市场供需状况调查,八成半的外企青睐于应届毕业生作为人才储备。[28]
然而机遇总是与挑战共存。在享受外企带来的较为丰厚的薪水、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的同时,在外企就业的员工也一直受到如何应对外企所带来的跨文化障碍的困扰。其根本原因也就是这种“微全球化”的情景所至。外企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其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要使他们在一起工作,必须实现跨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外企或一般意义上的跨国企业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经营,参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市场上的竞争,还必须和当地的顾客、竞争者、供货商和股东实现跨文化的沟通,否则的话就无法实现协作,无法保持企业运行的高效率,无法有效地取得资源,无法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从目前情况看,外企或合资企业大多高度关注跨文化沟通问题,普遍重视管理人才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本地优秀中青年人才送到所在国去培训等方式,增进相互理解,构建相互信任。
无论是外企就业和海外劳务,都存在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对个人而言,这也就是一种“微全球化”经历。如果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价值观不加以理解和领会,则会造成双方交流的误解。因此,进入外企就业或海外就职的青年,必须对这种“微全球化”的经历要有所准备,这样才能尽快地适应新环境。
(六)互联网的虚拟交往
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12月,中国网民总量达4.57亿,其中,30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量的58.2%。[29]可见网络已成为青少年生活中必不可分的部分,并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网络青年亚文化。调查显示:48.7%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为“2小时以上”,其中有3.5%的人为每天“6小时以上”。换句话说,接近一半的大学生把生命1/12以上的时间花在了网络上,而有3.5%的人把生命的1/4以上献给了网络。调查还发现,大学宿舍的平均可上网率是66.49%,大学生个人电脑拥有率是60.31%。因此,大学生想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又想了解异域他人的情况,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网络。[30]
显然,互联网构成的“微全球化”情景也让青年人进入了前所未见的虚拟全球平台。它有效地缩短了全球间的人与人的有形距离,转变了人际间的沟通模式乃至生活方式,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在这种跨国界互动、跨文化交流的“微全球化”情景中,人们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全球视野与全球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青年人在信息科技方面的应用能力和网络素养的提升都是培养全球意识的重要条件。
尽管互联网提供的是一种虚拟的交往,但由于它满足了“微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因此它是一种“微全球化”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包括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交往将如何对个人的现实交往产生影响、论证虚拟社交网站的使用对青年人社会资本有怎样的提升作用,以及虚拟交往对维持现有人际关系和拓展人际圈的意义等。[31]
三、“微全球化”的研究对策及其思考
综上所述,“微全球化”现象泛见于与青年群体相关的各种活动和事件中。因此,对“微全球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特别从其起因、条件、过程、影响等出发,对青年与全球化进程,以全球为基础的社会化过程,青年人的全球意识产生及其教育,“微全球化”进程与青年素质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微全球化”与社会维稳和安定,全球文化与伦理传播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微全球化”现象与本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微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观察指标与测量,“微全球化”模型等进行探讨和研究成为今后的主要课题。其中,与青年研究相关的主要课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微全球化”与青年的全球社会化
青年的“全球社会化”,是指青年如何参与全球化进程与融入全球社会的过程,具体来说,即青年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接触、交往、互动,享用和吸收异域文化的特质,并与自己的本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过程。它属于社会学中通常讲的社会化的范畴。
个人社会化从本地转向全球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过程。传统上讲,社会化是一个过程,即由老一辈,或年长者向年轻人传授已有的文化传统,使得社会的文化能稳定或延续下去。同时,社会化可以通过同代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而发生。比如在学校、社区、工作场所,通过面对面的交往而产生。显然,传统的社会化更多的是在一个比较接近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互动可以跨越地域甚至跨越国界,社会关系的形成也突破了以往的有赖于地理上的接近等传统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社区”这一概念早已超出其地理意义,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能够且已经频繁地一起参与互动。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由于世界各地的人际交往的频率急剧地增加和程度不断地提高,从而增加了人们跨国界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formative)。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化概念早已无法解释当今跨国界的交往和跨文化互动。“全球社会化”概念取而代之成为必然。
在个人的“全球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个人参与更多的跨国活动,拓展全球视野、发展全球交往,使个人更具有全球意识。如此个人全球意识以及全球互动对本地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深远地影响。从不少案例可以看到,有留学海外经验的人会具有更强的全球意识和相对更高的文明行为。比如曾在国外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会更为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等。这种现象泛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种普遍共识是:有过出国经验的,也许更懂得文明办事、按章守法;有着海外经历的人,会更有参照意识,也更懂得祖国意味着什么。
“全球社会化”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框架。因此对于人们的“全球社会化”过程及其效应以及对本地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需要更进一步地探索。
(二)微全球化与青年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人们在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必然代替地域性的交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2]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肯定了人的发展是受到社会的物质存在所制约的,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等等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反映。从这一角度出发,全球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本质在于其活动主体的全球性的相互交往与互动。而人类发展与全球化的世界是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全球化必将推动人类整体的发展。
“微全球化”关注于人的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其原因是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全球化本身也是由人所推动的;而发展的结果又直接影响到社会中的人。就以青年群体而言,无论是从社会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还是文化观念都可以看到社会发展对青年的影响之深刻。在现实社会中,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通讯网络的出现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已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因此必将对青年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微全球化”所关注的跨国界互动和跨文化交往带来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人层面上的改观或物质形态上的变化,其蕴含着更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跨国界互动和交往可能或者已经带来了新的社会或文化层面的结果。总之,“以人为本”的跨国行动和全球互动是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文化、经济、社会现象,它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社会关系和地理空间上的综合关系。
“微全球化”研究还尚在雏形阶段,这一概念本身就有创新意义。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把个人放在全球系统中加以研究,强调和突出体现了全球范围内人的活动以及人们的多层面多样性的社会互动关系,而这正是社会学家可能建立的新范式以及观察的新视角。
[1]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4(2):5-17.
[2]文军.全球化概念的社会学考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发展研究,2000(6):22-57.
[3]王黎芳.社会学视野中的全球化[J].学习与实践,2006(4):88.
[4]Collins,R.,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5):985.
[5]Knorr Cetina,K.and U.Bruegger,Global microstructures:the virtual societies of financial market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2(4):18.
[6]Erez,M.and E.Gati,A Dynamic,Multi-Level Model of Culture:From the Micro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Macro Level of a Global Culture.[J].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4.(4):583-598.
[7]Sassen,S.,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M].New York:W.W.Norton.2007:193.
[8]Sun,J.,Global Connectivity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A Micro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Shanghai,[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2008.
[9]孙嘉明、杨雄.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国界交往现象——试论“海外关系”对本土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J].社会科学,2007(6):140-151.
[10]李丽嫒.从跨文化视角分析中美跨国婚姻[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1]刘莉莎.中国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2]方琼.大学生网络素养与全球意识现状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为例[D].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
[13]胡近、刘志刚.中外合资企业青年人才流动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1(6):20.
[14]贾英健.从全球化视角看人的生存方式的当代转向[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12-14.
[15]刘秀英.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已占我国留学总人数的22.6%[J].少年儿童研究,2012(2):59.
[16]苏一凡、胡庆亮、张晓冰.中国出国留学研究述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高教探索,2011(3):149.
[17]王辉耀.海归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47.
[18]人事部.人事部关于印发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人发(2000)63号][G],2000.
[19]杨诚.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的政策与法律探讨[J].太平洋学报,2009(1):54.
[20]郭玉聪.中国青年的国际迁移态势及主要迁移原因[J].中国青年研究,2006(5):20.
[21]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4):8.
[22]中国跨国婚姻日趋增多[N].参考消息,2006-10-11.
[23]纪秋发.北京青年的婚姻观一项实证调查分析[J].青年研究,1995(7):22.
[24]肖丽艳.中韩跨国婚姻增加的原因研究[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75.
[25]师艳荣.中日跨国婚姻问题分析[J].理论与现代化,2009(4):88.
[26]王军、彭涛.亚洲第一客源国的现实[N].瞪望新闻周刊,2004-10-4(40).
[27]曹刚.中国人的海外旅游陋习[J].华人时刊,2003(1):54.
[28]鲁强、廖华英.大学生外企就业的跨文化障碍分析[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30)(4):380.
[29]李春玲等.新时代的新主题:2007-2010年青年研究综述[J].青年研究,2011(3):89.
[30]浦颖娟、孙艳、征鹏.大学生与网络青年亚文化关系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9(4):44.
[31]刘静、杨伯椒、校内网使用与大学生的互联网社会资本[J].青年研究,2010(4):89.
[3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
责任编辑 裘晓兰
The Phenomenon of"Micro-globalization"with the Youth in China
Sun Jiam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Fudan University)
Due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computer networks and other high tech communications,as well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people's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 has undergone a revolutionary change,that is,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untries and generate the individual-based global social interaction mode.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n the youth in China with such social phenomenon,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micro-globalization".The study of"micro-globalization"is a study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microscopic vision,with its focus on the personal level involving cross-border and cross-cultural behavior,to put changes of contacts and relationships as the entry point of its research and then grasp a general pattern and a common feature of certain behavior of cross-border as well as cross-cultural exchanges.From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the individua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the study,stressing on the global system and highlighting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worldwide multidimensional activities,may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and observe a new perspective.
Micro-globalization;Transnational Exchanges;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Global Socialization
D432.7
A
1006-1789(2012)10-0011-08
2012-07-10
孙嘉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城市文明、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