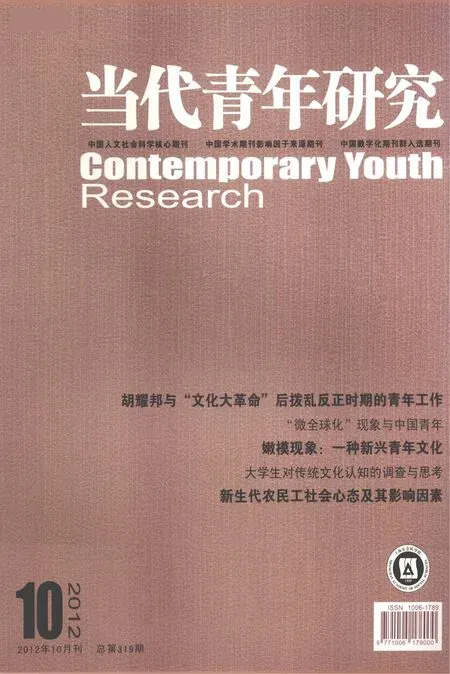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陈启懋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胡耀邦与“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的青年工作
陈启懋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胡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特殊的年代,对青年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的估价,青年工作拨乱反正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各种严重的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对当时的共青团组织怎样工作和团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与作风等,都有相关的系统论述。这是我党青年工作的一个典范。青年是社会变革中一支最敏感、最活跃也是很重要的力量,今天我们重温胡耀邦同志当时的指导思想,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耀邦;青年;工作;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各级团委机关陷于停顿,团干部受到迫害,团刊、团报等各种青少年读物被封禁,团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停止工作。“四人帮”还妄想把各地的共青团组织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受到广大团员、团干部的抵制。199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毅然决定终止“文化大革命”,从而开始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使广大人民得以摆脱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使广大青年看到了前途,有了希望。“文化大革命”后党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大量问题,进行了艰巨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青年问题成堆,青年工作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文化大革命”后不久,胡耀邦就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不久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工作非常忙,但仍十分关心青年,关心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作了系统的深入的指导,对青年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深切关怀青年,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领导了平反数量巨大的冤假错案、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承担着党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时刻把青年教育事业挂在心上,满腔热忱地指导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
1978年,胡耀邦接受党中央的委托,指导筹备和召开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不仅出席团“十大”筹委会,还多次同大家一起研究团中央工作报告的主题、内容和新的团中央委员人选、团中央的领导班子,特别提出要注意选拔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优秀青年参加团的“十大”和中央委员会。1978年10月28日,在共青团“十大”闭幕后的新老团干部见面会上他又鼓励新的团干部不怕困难、会干实事、带头学习、不断前进。[1]以后他虽然公务繁忙,但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团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总是经常挤出时间来参加。如1979年初“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一些青年问题凸显,有些矛盾很尖锐,影响了大局的稳定。同年2月,胡耀邦在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团的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作风,面对青年,到青年中去解决问题,在实际中找办法。[2]1982年,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十分关注团的“十一大”的召开,并亲自出席团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发表了以“你们一定胜过我们”为主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团的干部一定要了解,你们的身上肩负着双重任务:第一重任务,你们要带领、团结和教育团员青年,站在四个现代化的前列英勇奋斗。还有一重任务,就是你们要准备接替老一辈,把我们党和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3]
胡耀邦经常同一些青年保持通信联系,满腔热情地回答他们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1978年初,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当时许多青年感到困惑的问题,希望耀邦同志予以解答。胡耀邦为此写了一封热情的复信(《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结合自己的体会回答了来信提出的问题。他在复信中写道:“有些青年同志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青年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老实说,青年缺乏经验,缺乏锻炼,盲目性很大。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成熟起来。”[4]
胡耀邦对青年深切的感情与他的经历有关。他16岁(1931年)就担任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局书记,18岁(1933年)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19岁(193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来又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52年起任团中央书记14年之久。他自己就说过:“我对青年抱有特殊的亲近感。这当然不仅是因为我同其他年长者一样,都是由青年过来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一生中,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长达二十年。”(1983年11月26日在日本各界青年集会上的演说)[5]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以历史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青年,深知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对日本青年的演讲中他说:“长期经验,使我相信一个真理,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未来主宰者。”[6]胡耀邦的心始终和青年、青年工作连在一起,他对青年教育事业念念不忘。
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代青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少青年被煽动起来造反,做了一些错事、坏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青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游荡,沾染了不良习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引起社会的动荡,其中大多与青年有关,“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时间里党内外对青年的评价产生了分歧。有些同志认为那一代青年是“走下坡路的一代”,有些认为是“荒废的一代”,也有些认为那一代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怀疑的一代”,众说纷纭。这是当时青年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胡耀邦十分重视如何正确评估、看待“文化大革命”后这一代青年的问题。在与团干部的谈话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时候都要肯定青年的主流、青年的大多数。针对一个同志认为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新中国土地上生长的第三代、第四代走下坡路的观点,他明确指出:“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这种看法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作具体分析。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青年大致上总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走下坡路,甚至走到泥坑里去了。但这只是极少数。一种情况是在十字路口徘徊,迷迷糊糊不知往哪里走好。这种人比第一种人多一点,在‘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煽动下,就更多一点。‘四人帮’被打倒了,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鼓舞下,这种人大大减少了。另一种是充满朝气、奋发有为的人,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种人也到处有,在那些用血和泪为人民、为我们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人们当中,不多数是青年吗?这种青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少数。”[7]1980年2月12日,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他也特别谈到了如何看待青年的问题。他指出,“有同志说,青年是好的;有同志说,青年是坏的。我觉得两种看法都太绝对。我们党历来讲青年绝大部分是好的,也有少数不好的。”[8]在20世纪80年代初伦理学界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讲到了怎样看青年的问题。他说:“有人对大学生的估计是‘三信危机’,这里有个看问题的标准问题。现在要求振兴中华、要求改革是青年主流,这是对青年估计问题。”[9]
第二,强调对青年要一分为二。胡耀邦指出:“青年人很可爱,他们本质上很纯洁,很有朝气,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是人在青年时期,一般来说,却比较幼稚,容易上当。”[10]“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天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他们弱点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东西,鼓励他们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11]
第三,重视“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业荒废的问题,但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青年的学业问题。他说:“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从8岁到18岁的青少年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那时,他们本来都应该在小学和中学里好好学习,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学业基本上荒废了。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打砸抢有理’和‘交白卷光荣’,毒害了我们整整一代青年。连国外许多朋友都清楚,在这场大破坏中,受害最大和最深的就是这一代青年。现在他们一般是20岁以上到30岁左右的青壮年,大部分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小部分还在学校学习。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现不错,思想上受毒害较深的只是少数。无论如何,他们所受的思想上的毒害还比较容易消除,但要弥补他们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损失,那就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都担负着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有的已经成了家,还要操劳家务。我们希望科协的同志协同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同志用心研究这个问题,希望一切厂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的同志们,也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看看采取什么最有效最便利最切实的办法,在继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技术,使他们真正成为适合四个现代化需要的一代新人……现在有两亿一千万青少年在中小学校学习,他们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备队。他们今天上课堂,明天就要上战场。现在课堂上的功夫如何,同今后战场上的战果有密切关系。我们要想得远一点。”另一方面,他不同意把青年说成是“荒废了的一代”。他强调指出:“这几十年国家总的来说是处在大变化、大动乱、大发展的时期。痛苦的经历,只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对它重新加以认识和体会,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不好的东西也可能变成很好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二十几岁的人,三十几岁的人,四十岁左右的人,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化、政治局面的大变化,两方面的经验都有,这很难得啊。什么是正确的,是错误的,错误的应该怎么防止,正确的应该怎么发扬,这种经验是买不到的,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第四,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弱点并注意帮助青年克服自身的弱点。1980年他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1982年,在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青年人中有两个带普遍性的弱点,一个叫抓不紧自己,一个叫瞧不起群众。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看不起。自古以来,就有很多长者、贤者向青年人打这个招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讲这个事情的。毛主席几十年来也经常向青年人打招呼。但许多人往往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回头来想自己,觉得年轻的时候耽误了、懈怠了,经常吃这种‘后悔药’,就是后悔当年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青年人有股闯劲,什么都不怕,敢说,敢干,这是好的。但是,一定要防止对自己抓不紧,对别人瞧不起。”[12]
胡耀邦这一系列判断和分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引导青年向前看,做新长征的突击手
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委托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时,就提出了“新长征”的口号。那一年的十月中旬,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号召科学院的青年技术人员要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思想。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长征”,这个新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新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13]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压力造成的沉闷气氛下,这个报告有如石破天惊,在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尽管“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仍在肆意横行,但“新长征”的口号却冲破种种封锁,开始在青年中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极左思潮毒害,同时也饱受摧残、历经曲折、多少有点迷惘的青年,胡耀邦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引导青年向前看,让他们在建设国家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锻炼成长。1978年5月,胡耀邦受北京东城区团委邀请参加纪念“五四”59周年的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曾任团中央书记的王照华同志对此作了十分生动的回忆:耀邦面对与会者热切的目光、激动的神情,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开口就说:“我们这些做过团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老人,今天来参加你们这个会,主要是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刚才听说你们说要欢迎我们,说的不对。我们老了,或者说,我们正在变老,我们没有资格再做青年团的工作了,我们这生再也没有这个希望了。因此,你们不应该欢迎我们,而是应该欢送我们。”说者很动情,话语间充满着对团的工作留恋之情。听者动容,报以热烈掌声,掌声中充满着对胡耀邦等“老团干”的感激之情。接着耀邦说:“我们党现在把新时期的总任务叫做新的长征。什么是新的长征呢?新的长征叫作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是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四个现化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的长征的雄心壮志就是毛主席讲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新的长征我看应该是‘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最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老的长征中有好样的,也有窝囊废;有英雄,也有逃兵。新的长征中有没有逃兵呀?有没有窝囊废呀?这是摆在你们面前应该考虑的问题。现在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我们怎么进行长征,我们是大摇大摆、两手空空地进行长征呢,还是要有新准备,有新武装参加长征?我们进行老的长征,至少有两大武器,一个是步枪,一个是手榴弹。步枪加手榴弹,拿着这两个武器参加长征。进行新的长征靠什么?进行新的长征可不像逛颐和园,也不像逛香山。预祝新时期的共青团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勇的突击队,预祝新时期的青年一代个个都成为进行新长征的新英雄。”[14]
新长征的号召在广大青年中传播,得到热烈响应。不久后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以“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为题[15]。“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成为青年中的响亮口号。
四、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团干部和青年
在拨乱反正期间,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青年,除了个别一贯搞“打砸抢”,有血债、民愤的犯罪分子外,对一般受害上当、做过些错事的青年,都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治好创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978年春夏之交解放军报社一个同志访问胡耀邦。耀邦同志说:“我们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跟着起来造反的,绝大多数是受林彪、‘四人帮’的煽动而受骗上当的好同志,许多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在群众中划分这个派那个派搞批判,容易扩大打击面,伤害一些本来是可以争取和教育好的同志,这样做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多做团结工作,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6]
胡耀邦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团中央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冲击,胡耀邦和其他团中央领导同志“靠边”挨斗。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道义被指定临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和机关的“斗批改”。他多次组织对胡耀邦的批斗。但“文化大革命”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仍分配他当兰州市的市长,后来又让他担任甘肃省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人对此不解,问胡耀邦为何如此处理。胡耀邦解释说;“他批判我50年代的讲话时,说我只讲以生产为中心,不讲阶级斗争是修正主义。我当时就是那样讲的,他也没有造我的谣呀!批得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后来我只是批评他,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做了那么多错事,你还尽讲他们的好话,这是错误的。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工人出身,是个好同志。错误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犯的。”[17]就是对这位军代表,胡耀邦后来也分配他到国家体委当了副主任。有人问,这个人犯了那么多错误,为什么还让他当体委副主任,胡耀邦回答:“还要给他出路嘛。”[18]“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机关不少人在那种特殊条件下造过他的反,批判过他,或搞过他的“专案”。“文化大革命”后有的去看他,甚至有事求他,他都不计前嫌热情待之。一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干部去他家,他热情接待,他的孩子却因为这位同志在运动中揭发批斗过父亲而态度冷淡。孩子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还对揭发过自己的人这样热情。胡耀邦不仅当面让孩子叫叔叔,事后还对孩子们讲他身边工作的人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造反派把他们当成“走资派”的知情人,千方百计地从知情人身上挖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他风趣地说道:“保皇派不好当啊。”[19]团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青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中受到审查,一时过不了关,他写信向胡耀邦同志“求救”。胡耀邦把信批转给团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尽力做好这个青年的转化工作。这个批示加快了这个青年解脱的进程。这充分体现了他宽以待人的胸怀。[20]胡耀邦正确对待、处理团中央机关犯错误的干部,为全团树立了榜样。
1983年开始整党后提出要清查“三种人”(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胡耀邦对此十分重视,强调要注意那些比较年轻,有文化,造反起家,而且隐藏下来的,甚至已经钻进领导班子或者第三梯队,正在受到信任和重用的人,这种人对党的危害很大,要坚决清除。但同时又提出要注意把犯严重错误的、说过错话的、办过错事的三种情况与“三种人”区别开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那股潮流来了,谁挡得住啊!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不过轻重、大小不同就是了。当时处于各级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就难以不犯错误,我们要慎重区别这些错误是不是属于‘三种人’性质的。”[21]“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是个重灾区,有两个书记处书记被迫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但团中央未划一个“三种人”。
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青年和青年干部,使一大批青年和青年干部放下了包袱,轻装前进,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
1978年冬、1979春,正当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化大革命”中积累起来的青年问题突然爆发。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要求回城,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受到影响也要求回城,形成了一股“返城风”,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卧轨、阻拦交通等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政治集会、论坛和组织,如北京的“西单墙”、上海人民广场的“民主论坛”等。一些年轻人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表他们的政见,提出他们的诉求。其中有不少意见值得执政党重视研究和反思,但也有一些过激甚至极端言论。这样,如何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就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重要任务。胡耀邦在中央集体的支持下,为正确、妥善处理青年诉求和群体事件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胡耀邦强调要正确看待青年的诉求和群体事件。当时有些同志把青年闹事看得非常严重,一些人甚至藉此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他指出,青年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他把这些有错误思想的人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并指出其主要表现是:一是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是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是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22]胡耀邦在这里既肯定了青年的主流,指出上访者的诉求绝大部分是合理的,要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指出少数青年中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基本原则,这与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其次,胡耀邦强调对青年群体事件要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要切实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对一些极端言论和行为不要怕,要多做工作,正面教育,以理服人。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23]1989年3月26日胡耀邦逝世前不久,在与张黎群、陈沂谈青少年教育问题时还强调:“周恩来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我们必须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青年人上上街,说说怪话,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善于引导和教育,而不能压制和禁锢。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是被学生推翻的。毛主席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这句话还是对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么一个先进的党,决不能把青少年当敌人对待。当然,‘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也是年轻人,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问题不在青年身上。青年中也有害群之马,那是极个别的,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啊。”[24]
再次,胡耀邦强调处理群体事件一定要深入第一线面向青年做工作。他曾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教育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听这些同志的汇报,进行指导。他在1979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书记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团市委干部深入到人民广场“民主论坛”的青年和要求回乡的知青中直接做工作的经验,要求各团省市委都这样做。[25]他还主张搞一些讨论会、讲座,请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报告,并吸收那些“民主墙”的青年参加,讨论民主问题。他还亲自找一些青年中的代表人物谈话。
第四,热情鼓励青年参加农村、边疆建设,妥善处理知青回城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中央和省市团委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部分城市青年到农村、边疆垦荒。这既是建设新农村、支援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部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这些青年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为加强农业第一线、巩固边防作出了贡献。其中出现了大量先进人物,如邢燕子、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鱼珊玲,等等,以及先进集体如北京青年的黑龙江垦荒队、上海青年在江西德安建立的共青社、温州青年在大陈岛建立的志愿垦荒队,等等。尽管在安置工作中有不少缺点,但其方向是正确的。胡耀邦一贯热情支持、鼓励这些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的青年。1978年9月,江西共青垦殖场的团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在听取共青垦殖场代表的汇报后,欣然命笔题写“共青垦殖场”。1984年12月12日,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再临共青城。他漫步街头,留下一路欢声笑语。他登高俯瞰,凭栏远眺,与人攀谈,与老垦荒队员合影,并根据他们的要求,欣然命笔,题名“共青城”。1985年10月15日共青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时,胡耀邦又给共青垦殖场的新老建设者们发来了热情洋溢和寄予殷切希望的贺信,信中说:“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26]对“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胡耀邦总的是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建设祖国的边疆和新农村。当然,他也指出对安置工作中的缺点要努力加以克服,有些确有实际困难的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在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遭到大破坏、城镇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既不为大多数青年和他们的家长欢迎,也不为大多数农村欢迎。“文化大革命”后近一千万知青要求回城。党中央经过研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中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做法早有看法。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27]1979年5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28]胡耀邦在这里讲的“一举两害”,显然是指既不利于青年又不利于国家,“一举两得”是指既要有利于青年个人的发展,又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解决“上山下乡”知青问题也作了指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知青返城问题终于大体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部分“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了城市,也有一部分已在当地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的青年留了下来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奋斗。
六、高度重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大批知青返城后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突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胡耀邦高度重视这个问题。1979年6月他对他儿子胡德平说:我今年下半年就抓两件事,一是抓轻工生产;二是抓75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29]一段时间里他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作为他的工作重点之一,采取了不少措施。
第一,他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就业问题。当时在报刊宣传上,仍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30]
第二,他把青年就业问题与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重新分配、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等问题联系起来,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进行研究、思考,从而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31]
第三,他重视抓安排青年就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如湖南省湘潭市红旗和先锋两个知青综合场的经验、北京广开门路特别是发展服务业安排青年就业的经验。他还亲自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
第四,他强调要教育青年在就业问题上摆脱过时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观念。1983年8月30日上午,在会见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胡耀邦作了题为《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还说什么,当干部光彩,没当干部就不光彩;上了大学光彩,没上大学就不光彩,等等。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并且不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有些是非好坏就分不清楚,就会阻碍我们更好地前进。他说,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作了贡献的都是光彩的。那些在困难危险的环境下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们最光彩。那些同犯罪分子拚搏,克服技术困难、材料困难,自力更生打开局面,作出成绩的同志们最光彩。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最不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织律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们必须把陈腐的观念清除掉,代之以正确的观念。[32]
青年就业问题是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参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积极性较高,与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密切有关的。
七、重视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部分青少年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段时间里失去上学的机会,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加以“四人帮”制造派性、挑动武斗、鼓动打砸抢,沾染了不良习气。其中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恶习未改,经常聚集街头、拉帮结伙,耍流氓,打群架,在工作单位则不遵守劳动纪律、“磨洋工”,影响了社会风尚,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青年问题。
胡耀邦十分重视对青年的道德教育。在他指导下写成的团“十大”报告中把“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发扬而斗争”列为新时期共青团的四大任务之一。要求各级团委把培养青少年的良好道德风尚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作好调查,抓好典型,主动配合有关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在党委领导下,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关心和教育青少年的热潮,争取全国城乡首先是大中城市青少年的道德风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33]胡耀邦把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作为对团的一个基本要求。“十大”后他立即与韩英、胡启立等团中央领导人商量,提议为了迎接1979年,开展一个“发扬雷锋精神,维护社会公德”的活动,以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首先在北京、上海开展,再推广到全国。为了推广这个活动,他建议召开一个学雷锋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他还强调培养好的道德风尚要从具体问题抓起。如在工厂开展爱厂如家、美化环境的活动,从1979年3月开始,选择一些工厂种花、种草、种树,大搞环境卫生。针对有的同志认为环境卫生不是工厂主要任务,劳动纪律、思想教育才是主要的。胡耀邦指出,教育青年爱厂如家,美化环境,花也种得很好,草也种得很好,这样从大事着眼,从小事着手,就可以用小事带动大事,用具体事带动大事,移风易俗,振奋精神。[34]
胡耀邦还特别关注青年的文化生活,认为这是与培养青年良好道德风尚密切有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分析有的地方发生青年打群架的各种原因,指出没有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感慨地说,我们要关心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对全体人民的关心。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了解,对青年劳动者精力之旺盛不了解,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35]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并于1983年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对青少年发扬良好道德风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9年6月15日,胡耀邦亲自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十二省市青少年道德教育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对十二个市搞青少年道德风尚竞赛表示热烈的支持。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少年道德教育要先从少年抓起,以少年带动青年,再带动成年。要真刀真枪地干,要一干到底。切忌讲空话、弄虚作假。要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让他们自己组织竞赛委员会,自己当家作主,大人给他们当顾问,不要包办代替。[36]
八、拨乱反正时期青年团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这一时期胡耀邦在多次团的干部会议上,对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第一,新时期团的工作要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为纲。团的“十大”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当时党中央已在讨论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根据中央的思想,确定团的“十大”的主题是动员青年“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这就点明了新时期团的工作要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理论的影响,一部分团干部在传达贯彻团的“十大”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混乱思想。他们在讨论中提出,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斗争到底还是不是纲?学马列还是不是青年团的根本任务?阶级教育是不是青年的主课?毛泽东思想还要不要高举?……针对这些混乱思想和迷惘,胡耀邦在1979年2月23日的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新时期团的工作就是要以搞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四个现代化就是搞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高举,就是搞马列主义。[37]胡耀邦还提出在四个现代化中团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四化”英勇奋斗的积极作用;二是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三是维护安定团结的积极作用;四是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的积极作用。[38]这就为新时期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二,强调团组织对青年要善于引导。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工作“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要好好地爱护青年,很好地培养他们。除极少数违法犯罪的害群之马外,要保护绝大多数青年。第二,还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对青年不要一味捧场。我们要像培育鲜花似地爱护他们,可是不能无原则地吹捧他们,不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和低级情趣。在对待青年的问题上,我们的工作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39]他认为,教育青年的办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他说,“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他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他还说过,压制的办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他又说,“四人帮”对青年人施行镇压的办法、收买的办法。我们要回到引导的办法上来。[40]
第三,强调团的工作“要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广大青少年,面向各种类型的基层”,团的干部“要敢闯、敢干”,“到群众里面去闯,到基层去闯,到上山下乡的知青里面去闯,到民主墙去闯”。碰到困难不是眼睛向上,总是希望上面给我什么法宝,党委给我什么法宝,而是要眼睛向下,从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寄托在群众,寄托在基层。[41]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积累的青年问题成堆、矛盾尖锐,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共青团组织刚刚恢复。一些团干部有畏难情绪。胡耀邦的指示鼓舞广大青年干部勇于面对实际,到青年群众中,在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下解决问题。
第四,指出团的工作任务、方针要有稳定性,不要经常翻新。现阶段就是搞四个现代化,搞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工作方法要“万紫千红,‘不尽长江滚滚来’”[42]。这也就是要善于根据青年人的特点搞些独立活动。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抓在实处。要大处着眼,小事着手,有些事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不是小事。如何搞法?要一个一个搞。这里搞一个,那里搞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地搞。来它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43]
综上所述,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时期青年工作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后青年一代的估价、拨乱反正时期青年工作的任务和基本方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各种青年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中受骗上当犯有错误的团干部和青年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部分青年中的思想混乱迷惘和“三信危机”问题、知青回城问题、部分青年中的不良道德风气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业荒废问题、青年就业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共青团的工作方法、团干部应该具有的精神状态和作风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对共青团工作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指导,并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这一时期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做得较好,广大青年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胡耀邦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
笔者在1978年后曾奉命调回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在胡耀邦对青年工作思想的指导下参与了青年工作的拨乱反正。回顾那一段工作,重温胡耀邦同志这些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指导思想,备感亲切,同时也深深体味到这些重要思想的深远意义。毛主席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44]青年人比一般人更为敏感。一种社会思潮、一个社会问题,往往首先在青年中反映出来。正确引导青年,调动青年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积极性,是关系社会主义成败的大问题,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工作上碰到的一些重大波折,往往与青年问题的处理有关。因此今天重温胡耀邦青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1][7][8][10][38]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M](上卷).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11):332-334、309、366-367、435.
[2]怀念耀邦[M](第四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347.
[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65-66.
[4][40]郑先等.共青团卓越的领导人[M].怀念耀邦(第二集),香港凌天出版有限公司,1999:122-126.
[5][6][32]人民日报,1983-11-27.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M].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11):867、847-848.
[9]引自内部记录稿。“三信”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信心。
[11]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80-11-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人民出版社,1982(8):567.
[12]1982年在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M](下).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11):773、775.
[13][26]引自怀念耀邦[M](第一集).香港凌天出版有限公司,1999:163、339-340.
[14]他无限关怀北京青少年[M].怀念耀邦(第一集).香港凌天出版有限公司,1999:87-88.
[1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11).
[16]和谷岩.在耀邦同志家中作客[M].怀念耀邦(第二集).香港凌天出版有限公司,1999:385.
[17]最后的交谈[M].怀念耀邦(第一集).香港凌天出版有限公司,1999:290-291.
[18][35]陈利明.胡耀邦传[M](第二集).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10):322、49.
[19]正气常存天地间[M].怀念耀邦(第四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49.
[20]尊敬的导师 学习的楷模[M].怀念耀邦(第四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189.
[21]在江苏、河南、安徽三省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M].怀念耀邦(第四集).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10):963.
[22][23]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M].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979-1-18:61-62.
[24]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M](下卷).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11):1211.
[25]1979年2月23日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团中央印发的讲话记录稿。《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卷也载有此稿全文。
[27]胡耀邦思想年谱[M]:160.转引自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M].人民出版社,2011(1):164.
[2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833.
[29][30][31]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M].人民出版社,2011(1):125、168.
[33]韩英.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M].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978(11):26-28.
[34][43]胡耀邦在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新老团干见面会上的讲话,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M](上).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333、332.
[36]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编.胡耀邦的青少年教育思想[M].内部编印,2005(12):19-22.
[37]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M](上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3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上),1980-2-12、13:366-367.
[41][42]1979年2月23日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44]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M].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4):247.
特邀编辑 金志堃
Hu Yaobang and Youth Work in the Period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after the"Cultural Revolution"
Chen Qimao
(Shanghai Rim-Pacifi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Hu Yaobang ha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facing youth work in the special era after"cultural revolution"which include the valuation of youth after"cultural revolution",task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youth work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serious youth problems left over the"cultural revolution",how should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s work and what mental state and style should league cadres have.It is a good example of our party's youth work.Youth is the most sensitive,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in social change.Therefore,it still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ven today we revisit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u Yaobang.
Hu Yaobang;Youth;Work;Cultural Revolution
D430
A
1006-1789(2012)10-0001-10
2012-07-10
陈启懋,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