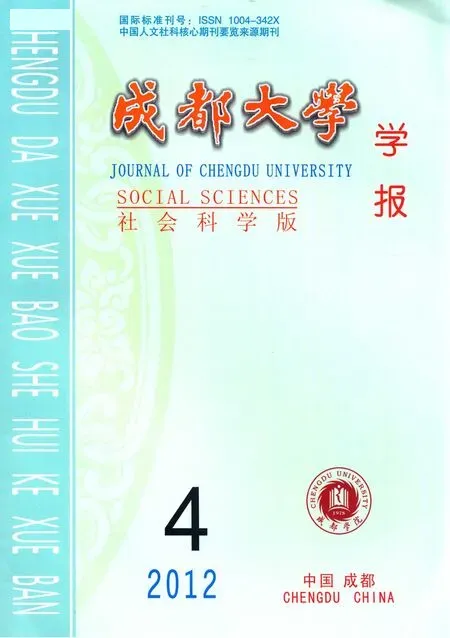移民文化浇铸川菜大系
——从成都旧方志看近代川菜的形成
张学君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四川成都610000)
移民文化浇铸川菜大系
——从成都旧方志看近代川菜的形成
张学君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四川成都610000)
川菜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大菜系,但古今川菜的差异很大。今日川菜形成于清代,是随着移民大潮引进的海椒等辛辣类调味品、发酵类调味品和酱菜类、泡菜类佐料,以及南北烹调技艺的交流、荟萃而逐步积累成型的。
古今川菜;成都旧志;川菜调料;酿造类调味品
川菜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古代川菜与近代川菜有很大的区别。古代与近代川菜的主要差异是制作菜肴所用调味品、饮食习俗和烹调技艺。清初随着移民入川浪潮而出现五方杂处的口味差异,随之带来了烹调技艺的交流与切磋。随大移民引进的海椒,与原有麻辣味调味品结合,成为川菜变革的基因;豆类等的发酵、加工技艺,促使酿造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优质豆瓣、辣酱、豆豉、酱油和保宁醋等调味品的诞生,冬菜、芽菜、榨菜等酱菜类佐料相继出现,迎来了传统川菜的变革。本文主要依据成都旧志中物产的记载,判断近代川菜诞生的历史时段。
一 古今川菜有别
巴蜀历史记载中的“尚滋味”、“好辛香”,是古代川菜的特征,与近代川菜的麻辣鲜香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是因为川菜古、近代所用原料有太大的差异。川菜所用基本原料,如猪、牛、羊、鸡、鸭、兔、鱼等肉类,韭、笋、芹、茄、瓜、藕、菠、蕹等蔬菜类,只有品种日益增多,没有质的差异。明以前,人们最多用这些原料做出熟香可口、有盐有味的菜品,即段成式所谓“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酉阳杂俎》);也即苏易简所谓“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而已。观宋代烹调美食家苏轼的菜式,不离鱼羹、烂肉,调料大致有食盐、葱、姜、酒之属。其《养老篇》也说:“软蒸饭、烂煮肉。温美汤,厚毡褥”,是老年人饮食生活要点①。流传至今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也属于这类烹炖类菜肴。姜、葱有辛香味,作为菜肴调料,是汉以来巴蜀饮食的一大特色。有人说:花椒、姜和茱萸,是中国最传统的三大辛味调料。
古人的五味,按烹调专家的研究,应当是咸、甜、酸、苦、鲜。咸味来自食盐,化学名称氯化钠,分布广袤,山海皆有之,早期人类已食用自然盐泉、盐岩,或取自湖、海卤水;早期甜味来自绿色世界,许多蔬菜瓜果带甜味,或者山崖蜂蜜,唐宋时期才有蔗糖的制作;酸味最早来自植物瓜果,或有机物发酵形成酸味,是醋的起源;苦味也来自植物类食物,例如苦瓜;上古饮食中重视鲜味,看“鲜”字的结构就知道,这是鱼、羊等肉类食品烹煮后产生的自然香味,所以鲜味是五味之一,如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而五味中的“鲜”为“辣”取代,成为川菜中的极品,应是辣椒类调味品传入巴蜀地区以后的事情。
近代川菜所具有的香辣、麻辣、酸辣等基本特性,是调味品变革的产物。笔者认为:催生近代川菜产生的主要因素是麻、辣类佐料、油料作物与酿造类调料的奇妙组合,包括海椒、花椒、胡椒、大蒜、圆葱、胡葱、胡荽(香菜)等调料,以及加工作料芸薹菜(油菜籽、菜油的来源)、胡麻(芝麻)的引进,揭开了川菜创新的序幕;豆麦类、蔬菜类盐渍发酵工艺的成熟,促使酿造业研制出豆瓣、豆豉、酱油、醋等优质调味品,以及腌菜、芽菜、冬菜、榨菜等酱菜类辅料的创制,才引起川菜的大变革,这一变革延续了二百余年才完成。
二 成都旧志中所见引进调料和酿造类调味品
上述调料和酿造类调味品的引进和创新,实际上与近代川菜变革和创新同步,清理新兴调料和调味品的出现过程,也就理顺了近代川菜的创造过程。
与一般历史文献相比,地方志文献则是记载地方风物的实录。明清两朝都重视地方志书的编修,从中发现与川菜革新相关的调料,应是可行的。从明代正德朝(1506~1521)开始,到万历朝(1573~1619),四川共计编修了四部《四川总志》,繁简各不相同,但均无土特产栏目,更不见调料、调味品的踪影。现存成都地区最早旧志,是天启《成都府志》。天启(1621~1625)是明熹宗的年号,时当明王朝末期,成都府在天启元年(1621)就刊印了这部有相当史料价值的府志;更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府志完成20年之后,巴蜀地区经历了长时期毁灭性战乱而没有让它化为灰烬,出奇地经由刻印本和传抄本两个载体幸存下来了。
晚明统治虽然已经腐败不堪,但商业贸易,特别是以走私活动为主要方式的海外贸易,却处在方兴未艾的状态,其间经由南洋传入了许多农副产品,特别是新兴调味品。在天启《成都府志》卷五“物产”一目中,笔者见到了可用于调味品的原料和蔬菜:用于酿造豆瓣的蚕豆(胡豆)、酿造豆豉的大豆(黄豆)、酿造麸醋的小麦均见于记载。见于记载的调料还有葱、韭、姜、蒜,但没有出现辣椒。没有出现辣椒的物产记载,至少说明成都府所辖地区还没有种植辣椒。
此后,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四川总志》、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四川通志》,都没有种植和食用辣椒的记载。康熙《成都府志》完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是明天启《成都府志》的续志,在卷二十一下“土产”一目中,见于记载的调料和蔬菜仅有盐、用于酿酒的酴醾花,以及巢菜,仍然没有辣椒的记载。在经历了明末清初30年毁灭性战乱之后,人烟稀少,土产绝迹,大量客籍移民尚未迁川,没有外来物产,特别缺乏制作调料的原料,也是自然之理。
迄今为止,辣椒见于成都地方志记载最早的,是嘉庆二十年(1815)的《成都县志》和同时完成的《华阳县志》。这两部县志,反映了清代盛期成都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在嘉庆《成都县志》卷六“物产”栏目中,笔者发现了海椒、花椒的记载,与近代川菜调味品相关的原料还有大小麦、芝麻、黄豆、胡豆、豌豆。嘉庆《华阳县志》卷四十二“物产”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记载辣椒甚详,首句标明引自《蔬谱》:“番椒丛生,白花,子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蔬谱》显然早于当时,故下句说:“今名海椒,一名辣子,有大小二种。”《蔬谱》尚称海椒为番椒,可见是清代康雍大移民时期从海外传入的;说它形状像“秃笔头,味辣色红”,可见最初只是试种、观赏,还特意介绍其性状颜色,连青辣椒阶段都忽略不计,证实人们尚未食用。到嘉庆二十年,“番椒”已正名为“海椒”,还有一个俗名“辣子”,可见已普遍栽种和食用;海椒品种也增加了,有大小二种。
四川客家文化的研究者提示:海椒的传入,是由岭南客家将原产于墨西哥的辣椒引入四川,四川客家人称其为“芥椒(gai jiao)”,并广泛栽种于巴蜀大地②。
值得注意的是,大麦、黄豆均成为酿造原料,说大麦“煮粥甚滑,磨面作酱,甚甘美”;豆类中的黑豆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豆“可作腐,榨油、造酱”;白豆也可“作酱、作腐”。介绍“刀豆”时,吃法除“煮食”外,还有“酱腌”;芝麻取油以后,渣滓就成为“芝麻酱”;萝卜“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见酱萝卜,豉油凉拌萝卜,糖、醋腌制的萝卜均已出现;菜瓜也可“作豉、腌葅”;香椿,“叶自发芽及嫩时皆香甘,生、熟盐腌皆可茹”。这些酱、豉、腐、腌制品的出现,表明川菜中调味品的制作种类、数量都在快速增加。
川菜中使用最广的菜油在《本草》中称“芸薹菜”,来自外域,又称“胡菜”,即油菜,“开小黄花,四瓣,子灰赤色,炒过榨油黄色,燃灯甚明;近人因有油利,种者亦广矣”。这是川菜创新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故近代川菜中煎、熬、炒、炸、酥等做法均需清油(以菜油为主,也用花生油)。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三食货志第三下“物产”记载的调料和调味品种类甚多,调料主要有:姜、花椒、海椒、茴香、葱、韭、大蒜、薤(火葱)、辣菜(芥菜)、芹菜、蒝荽(香菜)。从四川嘉庆年间种植和食用辣椒的地区来看,主要在成都平原,并快速扩散到川南、川西南和川、鄂、陕交界的大巴山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四川普遍食用辣椒,以至辣椒在巴蜀地区“山野遍种之”。20世纪初期,四川菜肴中辣椒成为重要调味品,在民间广泛食用,经典菜谱中也有了大量辣味菜肴的记载。清朝末年傅樵村《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各种菜肴达1328种之多,辣椒已经成为川菜中主要的作料之一。
三 新兴酿造行业研制出调味精品
清代四川经过百年左右的大规模移民,形成了东西南北各省客籍移民和谐共处的移民社会,也促成了各省移民饮食习俗的交流。近代川菜离不开优质调味品,而优质调味品的诞生,正是清代四川人共同努力创造、各展其长的结果。
不少学者知道清代历仕嘉、道、咸三朝的内阁大学士卓秉恬祖上是开酱园铺的,却很少有人知道卓氏是清初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迁川的客家移民,作酱的工艺也来自广东客家。卓氏“曾祖讳上隽,迁安岳县,又迁成都之华阳,遂占籍焉。”③三朝元老结束仕途生涯之后,卓家又在成都重操旧业,在棉花街“相府”门前开设了清代四川最有名的“广益号”酱园,所生产的酱油、酱菜、豆瓣久负盛名,至今还是川西地区著名特产的唐场豆腐乳、海会寺豆腐乳等,过去通称红糟豆腐乳,就是由“广益号”酱园做出名并流传四方的。“广益号”甜酱贡入皇宫,大受赞赏,故而以后的甜酱就有了“京酱”之称,至今川菜名菜“京酱肉丝”也就由此得名。长期以来,成都人对于“广益号”酱园的产品有着极好的口碑,正如一首清代的《竹枝词》所云:“开门七件事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五事都寻广益号,米柴另自有生涯。”④
无独有偶,正当卓氏“广益号”享誉成都的道光末年,另一家酱园“元利贞”号也在棉花街开张营业。这家酱园的发起者为江西抚州迁川移民胡叔樵,胡氏因仕途失意,面对卓氏酱园生意日益红火,他深受启发,于是邀约两位江西同乡凑集资本银一千两,在邻近“广益号”酱园的菜市场,开办了“元贞利”酱园。除生产酱油、豆瓣、醋外,这家酱园还酿制少量黄酒。经营数年,年年有盈余,到咸丰年间,资金积累到万余两白银。因两位合作者要回原籍,退股归本后,“元贞利”改名“太和号”,从棉花街迁到正府街,由胡氏独立经营。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太和号”的酱油生产规模已超过号称陈半城的“豫昌隆”酱园。仅酿制黄酒略少于陈半城,也达到600石糯米。资产总额达到10万两白银⑤。
再看潼川豆豉,也是移民文化的产物。清初,江西移民邱正顺的祖辈迁居四川潼川州(今三台县),凭祖传酿造工艺在南门外生产水豆豉出售,价廉物美、适销对路,获利丰厚。于是扩大经营规模,开办邱记“正顺号”酱园,以优质豆豉畅销四方,被潼川知州奉为独特方物,上贡清廷,名噪京师,潼川豆豉由此得名。后有冯、袁二姓,从“正顺号”聘得技师,相继开办“长发鸿”、“德裕丰”与“正顺号”竞争,潼川豆豉质量愈益提高。竹枝词说:“潼川豆豉保宁醋,荣隆二昌出麻布。”可见潼川豆豉和保宁醋都是清代四川调味上品⑥。
郫县豆瓣虽然成名稍晚,但它在川菜调料中的地位,却是极其重要。清嘉庆九年(1804),陈氏家族在郫县创办酱园,最初专门酿造酱油、麸醋,因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后由陈守信扩大经营规模,在南街开办“益丰和”酱园,常年酿造酱油、麸醋,按季节制作泡菜、酱菜等。每逢夏季鲜红海椒登市之时,便大量收购,宰细后加入食盐、面粉与胡豆瓣等原料,日晒夜露,自然发酵,形成色香味美的辣豆瓣。“郫县豆瓣”作为川菜佐料,使菜肴的色、香、味发生了重要变化,享誉中外,成为川菜主要佐料之一,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⑦。
关于郫县豆瓣的创制过程,有关研究者认为经历了福建汀州迁川陈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成功:经过原籍福建汀州、落业于川西郫县的客家人陈逸仙及数代的努力,终将盐渍红辣椒精酿制成了具有“川菜之魂”美名的饮誉海内外的郫县豆瓣,再加上湖广人有特别嗜好辛辣的天性,为以麻辣刺激为特点的川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辣椒的引进、种植和郫县豆瓣的诞生并与花椒配伍,最终孕育而成闻名遐迩的以麻辣为主味型的川菜大系列,使川菜荣居于中国四大名菜之中,由此引起川人由喜食姜蒜一类的低度辛辣的嗜味习惯向喜食以麻辣为主的高度辛辣嗜味习惯转变。四川客家虽有嗜麻辣味的习惯,但其程度远远低于湖广人,其咸味重于湖广人,这与广东省客家喜嗜咸味有着必然的联系⑧。
四川泡菜是近代川菜中的重要佐料,它是独特的腌制蔬菜,做法与一般腌菜或干菜不同,需要可以隔绝空气的泡菜坛。坛内是饱和盐水(老盐水最好),将稍加晾晒的蔬菜放入有坛舷的坛中,盖上坛盖,在坛舷内沿加水养护。
四川泡菜分为调料泡菜、下饭泡菜两类。像泡红辣椒、嫩姜、大蒜等一般多用作做菜的调料,即为调料菜,用老坛盐水泡,时间不定,具有泡菜香味最佳。在制作许多炒菜、烧菜、汤菜中,四川泡菜是重要调料,如鱼香肉丝、家常鱼、酸菜鱼等;下饭泡菜,泡青菜、萝卜、藠头等时令蔬菜,作为川味菜肴佐餐的风味小菜,因泡的时间短,又称跳水咸菜,食者喜爱。泡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等无机物,既能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又能预防动脉硬化等疾病。清代川南、川北民间还将泡菜坛作为陪嫁妆奁之一,足见泡菜在人民生活中所占地位。
除此而外,还有保宁醋、犀浦酱油、德阳窝油、中坝口茉酱油、白豆油、甜红酱油、资阳临江寺豆瓣、永川豆豉、夹江豆腐乳等,都为川菜创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调味品。川菜厨师利用众多各具特色的调味佳品,制作出目不暇接的新菜品,使川菜最终达到了与大江南北各地菜系媲美的高水平。
四 优质调味品造就特色川菜
成都物产丰富,崇尚滋味,是川菜文化的核心地区。清初开始,随移民浪潮不断引进调料和研制特色调味品,成为近代川菜诞生的重要催化剂。四川的饮食特色,源于调味品的独特。在清代贡院(明蜀王府)参加乡试的全省生员,进场必带的两件东西是“卓家酱菜、丁家烛”⑨,一是闭关考试的下饭菜,二是夜以继日的照明蜡烛。可见,作为佐餐菜肴,卓家的调味产品已经颇有名气了。
清代乾隆时期,罗江著名学者李调元将川菜制作技法归纳为腌、酥、煮、糟、熏、酱、蒸、风、焖、炒、醉、羹等38种,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川菜技艺的一个荟萃。同时代的袁枚,则详细阐述了川菜烹饪原料的时令、特性、调味、烹制方法、盛器组合、上菜顺序等。光绪年间,川西进士李实对川菜及其小吃佐料加以归纳,使川菜烹调技艺更加完善○10。其中,既有自古传承下来的古代精品,也有清代创新的特色川菜。
清干嘉时期的竹枝词反映了清代成都饮食文化的兴盛实况,兹列一首:秦椒、泡菜果然香,美味由来肉爨汤。延客官家嫌味劣,庖厨不及大生堂。
秦椒、泡菜都是川菜烹制调料,川菜的特色;汤也有浓郁、清淡各色,“爨汤肉”为人们所爱,“芙蓉豆腐是名汤”。“大生堂”是当时成都的著名餐厅,厨艺无出其右者。“玉芳”、“玉顺”也是当时成都的著名餐馆,公馆、衙门宴客一般都在这两家餐馆。“三山”餐馆是“苏州式”菜肴,已经被新开的“四大园”抢了生意。成都人请客不必自己操办,已有“包来筵席”,上门服务。
清代正宗川菜,其风味特色可以概括为:清鲜醇浓并重,以清鲜为上;广集民间风味,以麻、辣兼备见长;烹制方法多种多样,以干烧干煽、爆火煎炒驰名;选料范围极广,以禽畜鱼品蔬鲜为主;刀工技法特殊,贵在快、稳、精、巧,能雕出动人图案,能切出赏心悦目的菜肴花样,如凤尾、腰花、荔枝肉花等。川菜使用佐料十分讲究,如名产叙府芽菜、资中冬菜、涪陵榨菜、永川豆豉、郫县豆瓣、夹江豆腐乳、保宁醋等均为正宗川菜调味佳品。仅以主要佐料酱油而论,成都正宗川菜使用的老号名品就有犀浦酱油,德阳窝油、中坝口茉酱油,成都太和酱油、白豆油、甜红酱油等十余种。厨师依据不同菜肴的色香味要求,配备不同佐料,制作出色香味美、花团锦簇般的莱肴。川菜特别注重色、香、味、形,尤其强调口味,因此人们对川菜的评价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如大众化的川菜“回锅肉”,要求半肥瘦的二刀肉,先放锅内煮成八九分熟,再捞起来切成肥瘦相连的薄片,下锅爆火煎熬,直到肉出油,呈灯盏窝形状时,和少许豆豉、豆瓣、甜酱煵炒,煵出干香味,再加蒜苗合成起锅。回锅肉肥瘦匀称、软硬搭配、细嫩化渣、味道香美,是风味独特的大众化食品。
又如宫保鸡丁,传说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发明的一道颇具地方风味的糊辣鲜香的菜肴,因他官职上加太子少保衔,故其菜冠以“宫保”。宫保鸡丁选取鲜嫩鸡胸脯肉切丁,将干海椒剪短下油锅煎成棕红色取其红油香味,而后和鸡丁爆炒,加花椒、油酥花生米,调以糖醋合炒而成。宫保鸡丁热烫鲜嫩,糊辣又略带荔枝般的甜酸香味,成为脍炙人口的美味。
川菜名菜多达300余种,按其烹制方法不同,可分为凉菜、炒菜、蒸菜、烧菜、汤菜等数十种,凉菜一类,就有红油、麻辣、椒麻、姜汁、蒜泥、白油、芥末、麻酱、糖醋、怪味、酸辣、咸甜等十多种风味。即使汤菜一类,亦分清汤、奶汤、红汤、鱼汤、毛汤等,制作方法精细、考究,风味迥异。
川菜讲究配菜,按价格高低,配成高、中、低档全席。高级筵席,代表菜有干烧鱼翅,家常海参、红烧熊掌、清蒸江团、蟹黄凤尾、凉办麂肉、孔雀开屏、熊猫戏竹、开水白菜、鸡蒙葵菜、干贝菜心、烤酥方、樟茶鸭、鸡豆花、干烧野鹿筋、冰糖银耳羹、枸杞牛尾等等。这类席桌用料考究、制作精细,色香味俱美。普通筵席代表菜有粉蒸肉、咸烧白、甜烧白、烧什锦、烧杂烩、清蒸鸡鸭、清蒸肘子、酥肉汤,再配以韭黄肉丝、宫保肉丁、白油肝片等几样炒菜。这种席面,民间称之为“九大碗”,特点是就地取材、菜味鲜香、经济实惠。
清代正宗川菜的形成与菜品的丰富多彩,注重色、香、味的特色,都与调味精品的不断涌现有直接关系。此外,在研究近代川菜的形成过程中,还要看到,川菜制作技艺的日益精湛,许多厨艺创新者在不断推进川菜的改良。
此中,不能忘记迁川客家人对创新川菜的特殊贡献。客家虽然处于巴蜀文化的强势氛围中,但客家垦殖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天府之国得到传承,客家菜延续下来并为川菜增添了美味菜品。酿豆腐、麻圆等东江菜被客家引入四川后,还一直保持原有的风貌。今天宜宾的酿豆腐和广东的酿豆腐相近,成为川南宜宾的一道久负盛名的佳肴,深受川南人民的喜爱。在川西成都,客家酿豆腐被更名为“怀胎豆腐”一直根植于蓉城的席桌上。当今,深受川人喜爱的回锅肉、咸烧白、肉圆(丸)子分别脱胎于客家菜肴中的青蒜焖肉、梅干菜扣肉和肉丸。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名厨”之称的关正兴(约1825—1910年,又名关治平),在棉花街“相府”老宅旁开设了“正兴园”包席馆,创办人与主厨者关正兴,不仅菜肴精美,汤质绝佳,而且餐具十分讲究,其中不乏名窑产品,故而成为当时成都高档包席馆的代表。因他是满族人,官场人缘极好,又聘请了不少名厨主理,官绅、富豪家的宴席多由他承包,上门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正兴园”把从外地入川的的美食家、外籍官员的家厨技艺有意地加以发掘与继承,以山西票号商人为代表的山西面食技艺、以四川警察总监贺伦夔为代表的“贺派”京菜、以四川劝业道周善培为代表的“周派”苏菜,再加上荟萃了本城的满族名厨戚乐斋、贵宝书的满汉全席,汉族名厨周志诚、游炳全的拿手川菜,真正做到了海纳百川、博采众长、认真继承、勇于创新。
“正兴园”最具优势的服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包席餐饮,从价格白银二两五的田席、五两的海参全席、十二两的鱼翅全席,到十八两的燕菜全席加烧烤,来者不拒,为近代川菜“随行就市、贵贱皆宜”的市场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广阔的营运空间。在清末曾经三次承办真正的满汉全席,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正兴园”培养了蓝光鉴、周映南等一批技艺精湛的大师级名厨,成为了近代川菜特色真正形成的奠基者与领军者。1910年,关正兴病逝。1911年10月18日“正兴园”遭遇了一场大火。这年12月8日的成都兵变又再遭洗劫,雪上加霜,遂于1912年初关门歇业。“正兴园”在川菜行业的领军事业,后由其培养的川菜名厨蓝光鉴所开创的“荣乐园”所继承。
注:
①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45册213、323页,巴蜀书社1994年出版。
②张明生:《论四川客家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引自《四川客家网》,四川海外客家联谊会主办。
③民国《华阳县志》卷十四“人物第七之八”附录。
④《成都竹枝词》第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⑤侯松生辑录《百年酱园太和号》,载《四川商业志通讯》1987年1、2期合刊。
⑥《潼川豆豉》,《四川省商业志通讯》1985年第1期。
⑦郫县政协文史委整理《郫县豆瓣》,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⑧张明生:《论四川客家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和演变》,引自《四川客家网》,四川海外客家联谊会主办。
⑨《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10王大煜:《川菜史略》,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Immigration Culture Nurtured Sichuan Cuisine——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ichuan Cuisine Seen from Old Chengdu Records
Zhang Xuejun
(Sichuan Local History Editorial Board,Sichuan Chengdu 610000)
Sichuan cuisine is one of China's greatest distinctive styles of cooking,but the modern Sichuan cuisin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one.Today’s Sichuan cuisin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coming into being with the immigration tide that brought into Sichuan spicy condiments such as hot pepper and others,fermented condiments,preserved vegetables and pickles,as well as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northsouth cooking skills.
G127
A
1004-342(2012)04-41-05
2012-03-16
张学君(1945-),男,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