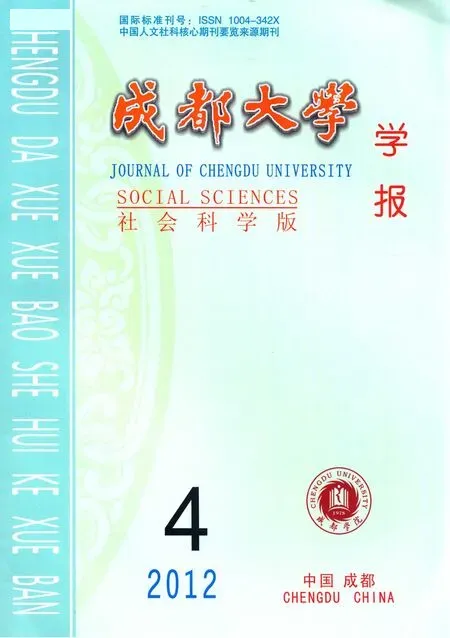《钟形罩》中女性意识的探讨
杨茜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钟形罩》中女性意识的探讨
杨茜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钟形罩》(The Bell Jar)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埃斯德·格林伍德的全优女生自杀未遂至逐渐康复的故事。本文通过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及文本细读方法,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审视文本所建立及推崇的意识形态权威,这种意识形态权威是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自我叙述建立起来,意在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定位。但由于文本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社会传统女性意识的阻碍,最终,女性权威依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男性权威的统治之下。
《钟形罩》;文本权威;女性个人化声音;意识形态权威
《钟形罩》(The Bell Jar)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63年以维多利亚·卢卡斯的笔名率先在英国出版,七年后问世美国。小说以普拉斯大学时代精神崩溃的经历为蓝本,详尽讲述了一个名为埃斯德·格林伍德的全优女生自杀未遂至逐渐康复的故事。长久以来,《钟形罩》因其自传性质而倍受评论家们的关注,普拉斯也被誉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殉道者。尽管有不同声音,但《钟形罩》作为女性文本的地位难以被撼动。1991年国内漓江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由朱世达先生所译的中文版《钟形罩》。译林也邀杨靖重译,并于2003年出版译本《钟形罩》。然而国内外对于此部小说的批评大都集中在心理分析及社会历史批评上。本文意在通过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及文本细读方法,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审视文本所建立及推崇的意识形态权威,这种意识形态权威是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自我叙述建立起来,意在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定位,但由于文本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社会传统女性意识的阻碍,因此其女性意识的虚弱性显而易见。
一
《钟形罩》是自身故事的叙述,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权威通过女性叙述者的叙述建立起来。那么,在考察文本权威之前,必然要对这一叙述进行分析。
首先,在叙述内容上,《钟形罩》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威有着强烈的冲击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对于女性来讲,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贝蒂·弗里丹在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给出如下数据:
截至本世纪5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降到了十几岁。有1400万个女孩子在17岁时就订婚了。读大学的女子与男子相比,其比例从1920年的47%下降到1958年的35%。一个世纪以前,女人们要奋斗才可能进大学,而当今的姑娘念大学却是为了找丈夫。到50年代中期,有60%的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或是她们害怕过多的教育将会成为结婚障碍。[1]P2
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角色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内,女性的自我价值更多体现在家庭与婚姻中。美国式的家庭主妇“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1]P4。而对于像埃斯德一样的女大学生,“几乎必须学习的一课就是:如果她想成为正常,幸福,具有适应性的女性,有一位事业上成功的丈夫,学习优秀的孩子,及一种正常、富于女性特征、适宜的、成功的性生活,她就不要对结婚和生孩子以外的任何事情有兴趣,特别是发生浓厚的兴趣”[1]P184。
但埃斯德处处与这些社会传统及要求背道而驰。她不愿成为像威拉德夫人那样以丈夫和孩子为生活中心的家庭主妇;她选择在暑假去纽约长见识而不是陪着自己的男朋友;她渴望性平等,热爱诗歌。在男友巴迪·威拉德求婚时,埃斯德回答说“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2]P86。诚然此时埃斯德可能是在婉言撒谎,但她对孩子问题的直言不讳——“孩子们让我恶心”[3]P96,已是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权威的直接挑战,而她的精神崩溃及自杀也正是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极端回应。
其次,在叙述形式上,《钟形罩》中的女性个人化声音也让人耳目一新。
苏珊·兰瑟在其《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曾以专章讨论女性个人化声音,并以《钟形罩》为例说明:“在政治进步和个人化声音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举例来说,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铃罐》(The Bell Jar)发表于1963年。当时的美国文学处于50年代保守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主流之中,J.D.塞林格(J.D.Saling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菲力浦·罗斯(Philip Ruth)这些男性叙述者占据着主导地位。《铃罐》一问世,立刻震撼了美国文坛”[4]P216。
个人化的女性叙事声音在普拉斯的时代属于常规叙事声音[4]P216,然而,普拉斯并非刻意采取这一常规形式。正如上文提到,《钟形罩》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性质的小说。普拉斯并未将自己的经历、感情与小说分开,以客观冷静的笔触来讲述故事。她曾提到“写这部小说(《钟形罩》)是为了把自己从过去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此篇小说的写作像自传的写作一样,采取个人化声音属理所当然,赋予这一常规声音进步政治意义的,是其在讲述非常规内容时所拒绝进行的妥协。
基于数字化方法的城市设计使用后评价研究——以天津市滨江道商业街为例 赵楠楠 侯 鑫 王 绚2018/05 106
同样是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苏珊·兰瑟开篇便提出:“女性个人型的叙事如果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讲故事建构自我形象诸方面超出了公认的女子气质行为准则,那么她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4]P21。所以,《禁戒》、《卡洛琳·莫当》、《埃格尼丝·格蕾》都在回顾性叙述中宣称以“教喻”为己任,建立社会认同的女性形象。叙述者不时直接指称读者,对读者进行安抚,逢迎[4]P204-20。在《钟形罩》中,叙述者虽然也是十几年后的“我”,且其身影时有出现,文中却没有出现直接的叙述者干预,也就是说,叙述者并未对人物行为进行任何判断或是批评。相反,她推断或惋惜的口吻反而体现了对人物的尊敬及同情。在第一次提到多琳时,普拉斯写到,“我想我那时的一个麻烦是认识了多琳”[2]P4。小说中主句所采用的现在时态暗示了叙述者的在场,而“想”(原文为“guess”)这个词的使用更体现了叙述者和人物的平等关系。在自身故事的叙述中,叙述者是经历过发生事件之后正在回顾往事的主人公,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她有权对以往的自我及往事进行判断。在这种判断中,叙述者和人物的价值观区别也越发明显。然而普拉斯的叙述者绕过了直接判断,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了“想”来表示一种推断。这正体现了叙述者对往事,同时也是对往事中的人物的尊敬。
再如,在小说第七章里出现的叙述者显形:
最后我决定,既然要找一位年已二十一岁却依然清清白白,还要有头脑的热血男儿难如登天,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贞节也抛到脑后,然后嫁给一个同样没有贞节的人。这样,当他开始叫我痛苦时,我也可以叫他尝尝痛苦的滋味。
在我十九岁那年,贞节是个大问题[2]P77。
引文的第二段出现了叙述者显形。这句话的前半句,即“在我十九岁那年”,确立了整句话的回顾性口吻,也就暗示了叙述者的在场,而后半句“贞节是个大问题”,则是叙述者在人物表达观点之后做出的回应。作为人物的埃斯德纠结在贞节一事上,作为叙述者的埃斯德再次绕开了判断,在与过往的痛苦拉开距离的同时,也在解释人物为什么会有如上想法。叙述者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人物的同情,更是在呼吁读者的理解及同情。
主人公埃斯德是个极其敏感的女大学生,心思细腻,情绪善变。个人化声音允许叙述者最大限度地暴露埃斯德的想法,追踪其心理变化。诚然,在全知型叙述中,作者也可通过自由间接话语等写作技巧进入人物内心,但却难以企及个人化声音的贴切与真实。所以这一拒绝妥协的女性个人化声音的采用,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也使得文本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权威更加明显和不受干扰。
二
那么,文本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权威又是什么呢?《钟形罩》在表面上成功地建立了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的文本权威。要定义这一文本权威很难,但毫无疑问,它是女性的权威。然而,这一女性权威足够真实吗?足够稳固吗?笔者认为未必。
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曾着重指出,“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5]PⅡ。故在分析某一叙述时,除了分析叙述者在讲述文本时所采用的策略(如笔者在第一部分所做),叙述者对于自身的讲述更是不可被忽视。
引文中出现的后三个“我”都是指处在叙述现在的叙述者,而非人物。此处叙述者便是在讲述自身了。而与“我”相伴,同样处在叙述现在的是“小玩意儿”、“唇膏”,以及“孩子”等传统女性符号。于是,叙述者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所建构的自身形象,是传统的母亲形象。她细心照料自己的孩子,屋子里有许多小玩意,似乎已然接受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小说中焦虑不安且反叛精神十足的埃斯德。虽然叙述者在此同样没有发表对往事或人物的任何评论,但她这一形象的出现已是对主人公埃斯德的价值观的背弃,足以威胁《钟形罩》表面上所建立起的女性文本权威。
继而颠覆这一文本权威的,是小说中唯一的纯虚构事件——女同性恋者琼·吉琳的自杀。《钟形罩》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几乎所有人物、情节都可以轻易地在普拉斯的生活中找到原型,唯独琼例外。小说中的琼与埃斯德是同乡,喜欢埃斯德的男朋友巴迪并曾与之约会,在埃斯德自杀未遂,几经周转进入私立医院疗养之后,她也精神失常,进入了同一所医院。然而,这一“过去的我的精华部分的光彩夺目的翻版”[2]P198却在埃斯德临近康复时自杀身亡。这细微之处实则意义深远。
《钟形罩》中一直困扰埃斯德的一个问题便是男女间的性不平等。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贞节十分看重,埃斯德的母亲还给她寄来《读者文摘》中的一篇文章,标题即是《捍卫贞操》。但对于男性,规则却十分不同。埃斯德那看上去十分纯洁的男友巴迪·威拉德,事实上却与一个女招待员有过私情。当埃斯德向身边的同学询问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根本没办法指责他们,除非你们有约在先,或者已经订婚了”[2]P67。这件事对埃斯德刺激很大,她无法再与巴迪继续交往下去。同时,她也想尽快摆脱自己的处子之身。在纽约时,她试图勾引威拉德夫人介绍给她的同声传译员;疗养期间,她更是与一位刚刚认识的大学老师发生关系。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权威所不能容忍的。
而小说中琼的出现以及自杀,正是普拉斯向这一意识形态权威的退让,甚至屈服。首先,琼女同性恋的身份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唐娜·佩恩在《性欲化妇女:美国战后的女同性恋者’妓女和对女子性行为的抑制》一文中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出现了“逐渐占据上风的一种观点”,即“将女同性恋者与妓女合而为一,以其作为女子性欲望’女子性无度’女子性行为放纵乃至女子性不正常及危险的象征”[6]P395。“妓女和女同性恋者变成了腐化和荒淫的象征,对照这两类女流,“正常的”异性恋妇女得以界定自己”[6]P392。
借助于琼,埃斯德也得以界定自己。正如小说中写到的,“有时候我真纳闷,不知琼是不是我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有时候又想,在我以后人生的每一次危机中,不知她会不会继续突然冒出来,提醒我,我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并且在我眼皮底下,经历她自己的与我的情形相似的危机”[2]P211。普拉斯之所以创造了一个与埃斯德并行的人物,正是为了在对比中圈定埃斯德的观点、想法,从而免除评论界或读者可能施加的批评。当琼向埃斯德表白的时候,埃斯德对琼的断然拒绝隐藏着更深刻的含义,即埃斯德要求的只是性平等,而不是性行为放纵。这一拒绝诚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以琼做为界定及在文本中出现这一拒绝的必要性却有待商榷。可以说,有关琼的这一情节是文本中一处不和谐的声音,代表着文本权威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权威所做出的友好姿态。小说结尾,普拉斯杀死琼,是为了在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威的对话中保全埃斯德。但这种保全,却是以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遵从及自身权威性的牺牲为前提。于是,《钟形罩》所谓的女性权威依然处于男性权威的统治之下,形同虚构。
三
《钟形罩》就以这种方式,表面上建立起了女性文本权威,却又在深层次上将这一权威自我瓦解。虚构的文本权威无疑会使文本对社会权威的抨击力度大为减弱。然而,笔者认为,即使搁置上述两点不论,假定《钟形罩》的女性文本权威已然建立,男性社会权威也不会受到真正威胁。
笔者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所引的一段引文指出了女性个人化声音的先天不足——“女性个人型的叙事如果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讲故事建构自我形象诸方面超出了公认的女子气质行为准则,那么她就面临着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4]P21。《钟形罩》即面临着这一危险。所谓女子气质准则,其实是关乎叙述可靠性的问题。“叙述者的智力或道德水平离一般的社会认可标准远时,会使叙述变成不可靠”,“由于小说的评价主要是价值观,因此道德上的差异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可靠叙述的标记”[4]P45。对于女性叙述者来说,道德上的差异则会导致其在“准则”遵守方面的差异。笔者在此同样无意深究《钟形罩》是否可靠叙述,只想从接受的角度,指出文本声音对文本意识形态权威权威性的负面影响。
《钟形罩》无论是故事本身,或是其拒绝采取妥协的女性个人化声音,虽然锐利、新颖,却都毫无疑问超出了“女子气质行为准则”。精神崩溃,自杀,一夜情,这些情节在当时的社会语境,甚至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中,都足以让读者立刻警惕起来,加之叙述声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这一点,以争取读者。故文本出现后,其影响范围可能很广,但文本权威在读者中的接受必然会受到限制。
《钟形罩》强烈的自传性质,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文本内记录与文本外事实是否相符合的问题。笔者并非要以自传叙述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文本,更无意将自传的叙述可靠性问题引入到所有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2]。只是,对于《钟形罩》这一文本来讲,文本内记录与文本外事实是否相符是在谈及对此文本及其意识形态权威的接受时所不可避免的。本文在开篇已经提到,《钟形罩》首先是在英国伦敦以笔名出版。普拉斯之所以采用笔名,并选择在英伦出版,一方面是出自对评论界的逃避,另一方面则是不愿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受到伤害。普拉斯曾写信给她弟弟,说道:“这本书永远不可在美国出版”[2]P249。尽管如此,《钟形罩》还是于1970年在美国公开发行,普拉斯本人也在死后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被不少女大学生当作偶像来崇拜。
随着普拉斯于1973年成为第一位在死后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美国国内对普拉斯的研究日兴,有关她的传记也逐渐出现。在多个版本的传记比较下,《钟形罩》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丑化,特别是对埃斯德男友巴迪·威拉德的丑化浮出水面。于是,知情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难免对文本叙述的客观性及可靠性产生怀疑或抵触情绪。小说里,埃斯德是现实中普拉斯的替身,而巴迪则是普拉斯当时的男朋友,狄克·诺顿的代表[7]P37。埃斯德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巴迪是父权制社会的中心。女性叙述者对巴迪的丑化即是对父权制社会的丑化;而当读者怀疑文本中对巴迪的描写时,无疑,文本所推崇建立的意识形态权威也受到了相应的怀疑。
上述两点分别限制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以及时隔多年后,文本权威在争取读者方面的效果。文本权威难以对读者产生权威性,也就意味着其对社会权威无法产生冲击。于是,对于普拉斯这一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而言,不仅女性文本权威是不可及的,男性社会权威也是不可及的。
[1]弗里丹,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女性的奥秘[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2]西尔维亚·普拉斯,杨靖译.钟形罩[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Plath,Sylvia.The Bell Jar.New York:Harper&Row,1971.
[4]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伊丽莎白·赖斯,杨德等译.美国性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7]安妮·史蒂文森,王增澄译.苦涩的名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I106
文章编号:1004-342(2012)04-76-04
2012-03-20
杨茜(1982-)女,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