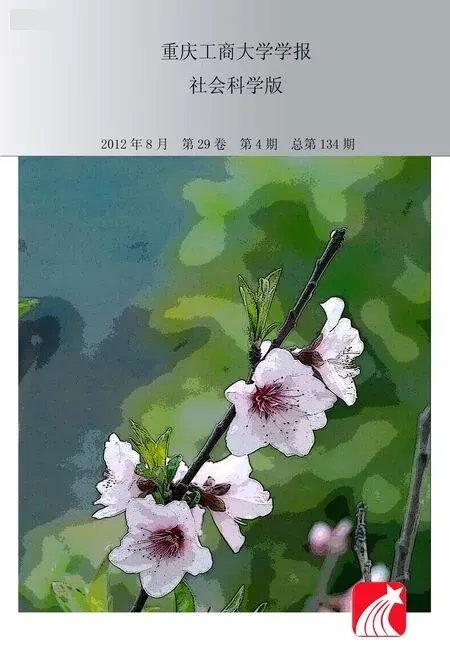政治文学论*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545007)
一、政治文学的含义及其哲学基础
尽管政治文学的存在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事实,然而此前学术界还只是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尚没有人把“政治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特质进行研究。作为一种专门术语,它还只是近些年来才在论文中偶尔出现。因而,“政治文学”的概念至今并不明晰。
照笔者看来,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说到底,其核心在于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1979年,我国曾经开展过关于“为文艺正名”的讨论,其实质是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1981年,周扬在一篇文章中说:“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和政治关系上表现为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等于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1],笔者认为“不等于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一语,还是不够准确。因为毕竟还有一些作品不跟政治关联,比如那些赞美自然风光,或者表现人生感悟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政治文学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一大部分。就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大部分来说,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弗莱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中所说的:“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每个文本都是一种政治幻想,它以矛盾的方式连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内部构成个人的那种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关系。”[2]而我们所说的“政治文学”,其实就是直接“连接”“特定的政治经济内部构成”的那种“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关系”的文学。
政治文学的哲学基础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和反映论。列宁说:“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趋向。”[3]毛泽东进一步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4]正因如此,人类生活中就必然充满矛盾。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也就出现各种利益群体、集团以及民族、阶级和国家。它们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成了政治。政治不但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利益集团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人类的生活就是如此,而反映生活(无论是直接反映还是间接反映)的文学作者并不能独身其外,必然有自己的态度,所以文学也就和政治发生了关联。“政治文学”也就应运而生。
二、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学
我国自《诗经》始,就形成了政治与文学相关的传统,唐宋八大家提出“文以载道”(这“道”虽不等于政治,但也包含政治)既是对之前我国文学的回眸,也是对之后我国文学的布控。而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方向文学)则是当时对于政治和文学关系的宣示。国外亦是如此。早在1885年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中,他就说:“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指政治倾向)的作家”[5]130-131。而“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5]130。而遵循列宁“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5]162原则的苏联文学,更是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说文学与政治相关,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学表现出政治思想的倾向性;二是文学参与政治斗争,直接为政治服务。就我国而言,前一种如《红楼梦》《西厢记》《围城》《家·春·秋》等等;后一种包括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如蒋光慈的小说,吴组缃的《山洪》(《鸭嘴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赵树理的小说以及《暴风骤雨》《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等等。因而,所谓的“政治文学”,实际上包含这两种:一种是表现出政治思想倾向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是直接地为某一政治集团、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前者称为政治倾向文学,后者称为政治斗争文学。这两种文学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治倾向文学主要从文学出发,体现文学的意义。
三、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的文化差异
所谓政治倾向文学,是指那些通过某些带有政治性的生活事件,表现出作者明确的政治思想意向的文学作品。上面说过,政治倾向文学在我国和西方都照样存在。不过,中、西方的政治倾向文学,又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
(一)发展路径的差异
上面说过,西方在公元前500多年就出现了“悲剧之父”和“喜剧之父”“有强烈倾向”[5]130的政治倾向文学。前者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所写的普罗米修斯和宙斯以及河神奥克阿诺斯、神使赫尔墨斯之间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反映了雅典工商民主派与土地贵族寡头派之间的矛盾;后者的《阿卡奈人》,反映的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冲突,指出“战争对政治煽动家有利,对人民有害”。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倾向,是站在大众的民主立场的。到了18、19、20世纪,许许多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都是政治倾向文学。18世纪后期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戏剧”[5]130的席勒的剧作《阴谋与爱情》,讲述的是贫民少女路易斯和贵族青年费迪南的爱情悲剧故事,展现了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真挚爱情和宫廷政治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显然,它的政治倾向仍然是反封建,也仍然是站在大众的民主立场的。而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1829-1848)、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雨果的《悲惨世界》(1862)等一大批作品,它们“有的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6]116,表现出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倾向,即使如巴尔扎克是站在“正统派”(“保皇党”)的立场上,也是把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而这之后,德国诗人海涅和毕希纳尔,他们的作品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而且“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6]169,即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资产阶级。
从发展历程看,到海涅为止,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从反封建专制的大众民主立场,到批判贵族,同情下层人民的资产阶级立场,再到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这过程中,反封建、批判资产阶级,同情下层人民是一脉相承的政治倾向,并无反复和倒退的情形。这是由西方反封建的彻底性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政治倾向文学的适时性和进步性。
而中国的政治倾向文学,从《诗经·国风》的反封建禁锢开始,继而有汉乐府《孔雀东南飞》的反对封建礼教。然而到了唐、宋时期,却有八大家“文以载道”的复古情结。在元朝,既有《窦娥冤》《西厢记》的反封建,又有《琵琶记》的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同是在清朝,既有反封建的《红楼梦》,又有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桐城派散文。直至20世纪初期,既有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高举反封建大旗的五四新文学,又有“学衡派”和“甲寅派”的复古。从中国政治倾向文学的发展看,反封建和维护封建的政治倾向总是反反复复,或者说我国的政治倾向文学总是在反对与维护封建思想之间徘徊。这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禁锢所造成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治倾向文学的犹豫状态,以及缺少对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适应性。
(二)文化立场的差异
有人说:“西方文学中从古希腊文学开始,一直到当下的‘现代主义’文学,始终贯穿着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这就是人道——或叫人道主义的主题,它显示着西方人独特的个性,也显示了西方文学‘以人为本’的厚重本色。”[7]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包括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6]116,所以西方的政治倾向文学,都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以人道主义来抨击封建专制,以人道主义来批判资产阶级金钱主义的不人道,以人道主义来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我们看西方的政治倾向文学,不但那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6]77,英国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通过描写贫穷的农家子女苔丝的一生的不幸遭遇,表明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6]97,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通过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的兴衰,反映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显然“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6]326的,就是那些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如乔治·桑的《华伦蒂纳》等小说,同样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6]79“反对束缚妇女个性解放”[6]79的。
中国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仁爱”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倾向文学作家用于评判社会的一把尺子。同时,他们还受到墨家“反对私幸政治与贵族政治,而赞同贤人政治”[8]的“兼爱”思想的影响。他们是以“仁爱”和“兼爱”思想为文化立场来反封建的,即以此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压迫,反对控制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我们看《窦娥冤》就是因为主者失去了“仁爱”和“兼爱”之心,才造成了窦娥的“冤”;《红楼梦》中封建思想害死了一个个丫环,从而证明着当时的社会缺乏“仁爱”和“兼爱”。只有到了鲁迅时代,反封建思想才脱离了“仁爱”和“兼爱”思想的禁锢,具有阶级反抗的意识。
我国古代这种“仁爱”“兼爱”思想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出发,以求生活的和谐稳定及对人民的同情,其对封建思想的谴责与批判,是以不推翻封建统治为前提的;而后者则是从封建阶级外部的立场出发,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和下层人民的权利,他们对人民的同情,对封建贵族的批判,是以推翻封建统治为前提的。两相比较,显然人道主义的反封建要比“仁爱”思想的反封建要来得彻底。这也反映出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中国古代政治倾向文学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由于西方政治倾向文学的适时性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总的来说,它的封建色彩并不浓厚,而“人本”和公平色彩浓烈;相反,由于中国政治倾向文学长期徘徊在反封建与复古之间,受“仁爱”“兼爱”思想影响,所以封建色彩和施舍、怜惜意味比较浓厚,即使一些以“反封建”著名的作品,也仍然流露出某种封建等级观念,散发出“仁爱”“兼爱”思想的施舍、怜惜气息,《红楼梦》就是如此,那种对丫环们的同情,不就有这样的意味吗?
四、我国和苏联政治斗争文学的创作思想分野
先要说明的是:所谓“政治斗争文学”,并非是说只要是描写了政治斗争就是,它要求不但要直接描写政治斗争,而且要直接站在斗争的一方,为其服务。从这一意义上说,巴黎公社文学是属于政治斗争文学的,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也是。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苏联和中国。比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等。我国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特别是工农兵文学更是如此。然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和我国的政治斗争文学又是有所不同的。
(一)生活式样,还是理想式样
苏联尊奉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世纪的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9]其中,“写真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指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生活,写出生活的发展及其趋势。依照这一要求,苏联的政治斗争小说,其故事情节都是生活式样的,即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按照作家的臆想去编造生活。正因如此,法捷耶夫的《毁灭》才会写出一支队伍在抗击白军时,以冲出包围圈时损失许多战士,队伍被击溃而告终。同时也因为如此,在最初构思时原本要把主人公美谛克写成自杀的,而在写作过程中,作家却感到主人公“在形象的发展中仿佛出现了自身的逻辑”,这主人公“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走”,终于在作品中“没有力量自杀”[10]373。
高尔基的《母亲》,所反映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这一革命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就是现实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过程,当然也预示了未来武装斗争的道路。还要提起的是,作品描写了众多的政治斗争如演讲、罢工的场面,这正是当时斗争的真实反映,所以有人指出这是“将时代的主要冲突作为情节的基础来描写的”。
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的写作更能说明问题。作品写“农民的和哥萨克的贫苦群众同一部分被击破的苏维埃军队,从古班向南方撤退,去同苏维埃主力军汇合”,“因为富裕的哥萨克们对同情苏维埃的贫农开始屠杀了。可是这些群众都很不愿意走,因此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事,不能保护他们。这些群众当时是混乱而无组织的;他们不愿意服从不久以前他们所选的长官。……这些撤退的人在行军里受尽了千辛万苦……使他们在行军完结的时候完全改变了:赤身露体的、光脚的、憔悴的、受饿的人们,都组织成了惊人的力量,这力量扫荡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这时就感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政权。这不是像无产阶级一样,是自觉地了解,而是一种本能的内心的感觉。”这样写革命的“铁流”,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对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郭如鶴,作者还特别指出,“是我从实际生活里取来的”,“我想写的是他在实际上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去写他。”他特别强调:“在文艺作品里首先要免除的是撒谎和粉饰现实。”[10]300-309
富曼诺夫在《夏伯阳》(即《恰巴耶夫》)的写作日记里,曾经这样说过:“我是如实地描写夏伯阳,连他的一些细节,一些过失以及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写出来呢,还是像通常写作时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说,虽然形象还鲜明,但是把许多方面都割弃掉呢?我更倾向于前者”[10]314。
事实已经很明显: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它遵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作品,都保持了生活的原本样式。
我国的政治斗争文学,其20世纪20 年代末到抗战之前的革命文学,在“学习苏联”的理念下,本意是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坚持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但大多数作品,如蒋光慈、巴金等人的革命小说以及好些人的抗战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到了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所产生的“工农兵文学”,就更是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大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1]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所体现的创作思想就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它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表现在:后者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而前者则是把所描写的生活理想化。在具体做法上,表现为按照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党的政策思想去设置人物,虚构情节,在所描写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现出斗争的曲折,另一方面表现出最终的胜利。在描写曲折时极力突出其艰难,使之“更理想”;而在表现胜利时突出其伟大,也是使其“更理想”。如反映土改斗争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写工作队进村怎样发动群众揭发地主的罪行,以后怎样发动群众,在发动过程中有遇到斗争的阻挠破坏,再后就是工作队怎样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即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通过大揭发,大斗争,终于斗垮了地主,分了田地,贫下中农当上了主人。其他反映抗日战争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则是描写抗日队伍怎样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日寇,怎样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怎样不怕牺牲铲除汉奸,最终消灭了鬼子。这些都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理想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情节模式,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如《铁流》的故事,相差甚远。
从生活本来面目出发,人物就是生活中存在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夏伯阳就是如此;而从理想化出发,人物就成了只有好坏之分,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的人物,中国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就是如此。
(二)类型性典型人物,还是融合型典型人物
直至如今,有两种典型理论:一种是恩格斯、黑格尔等人提出的共性与共性相融合的“融合论”,这一理论塑造出来的是“融合型”典型人物;另一种是巴尔扎克、别林斯基,和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等人主张的“类型论”。高尔基说:“把每个商人、贵族、农民身上最自然的特征分离出来,并概括在一个商人、贵族、农民的身上,这样就形成了‘文学的典型’。”[12]120这一理论塑造出来的是“类型性”典型人物。
苏联尊奉的是“类型论”。比如高尔基《母亲》中的巴维尔是作为先进工人的代表,母亲则是作为革命群众的代表;恰巴耶夫(夏伯阳)是英勇善战的将领的典型;《毁灭》中的莱奋生是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意志坚强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典型。这些人物都是某一类人物的代表,体现了他们的类型性。
我国的政治斗争文学中也有类型性典型人物,工农兵文学中的杨子荣(曲波,《林海雪原》),许云峰、江姐(杨益言、罗广斌,《红岩》)。这是作家们学习苏联作家创作经验的结果。但是作为最有影响、最为成功的典型形象,还是《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严志和以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朱老忠和严志和同是大革命时代的农民,其反抗精神是相同的,同时他们也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朱老忠身上体现出来的是慷慨悲歌的燕赵风骨,而严志和身上体现的却是私有制所造成的胆小和忍耐。朱老忠豪爽而坚定,严志和则软弱而本分。他们都是共性和个性相融合的“这一个”。而梁三老汉也是农民,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憨厚和朴实,又有旧时代留下的历史背负,因而表现出不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守旧。思想上的犹豫,行动上的徘徊是这一人物最大的特点。很明显,这依然是一个共性与共性融合的人物。
五、政治文学的美学意义及其审美缺陷
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阴谋与爱情》,说它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5]91,但是恩格斯却又称赞这部作品 ,说“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5]130,这并不是说他们两人的观点有什么矛盾,而是说,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看来,政治性应该受到肯定,同时又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同时,马克思还一再强调评价作品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这又表明他们坚持的是“内容重于形式”的审美原则。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内容是审美的重要方面。也因此,无论是政治倾向文学,还是政治斗争文学,都是看重内容的。这就为内容的审美提供了依据。实际上,好些非马列主义者,同样也是肯定内容的美学意义的。比如别林斯基,他说:“只有内容才是衡量一切诗人的真正标准”[13]297,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把“美”分为两种:内容的美(即“本质的美”,这种美与形式无关)和形式的美(这种美又与内容无关)[13]319。总之,除开那些形式主义者,其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是肯定内容的审美价值的。这样,含有政治意义的内容,自然也就成了审美的重要对象。那些具有反封建思想的政治倾向文学,那些歌颂人民革命斗争的政治斗争文学,自然也就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实际上,好些具有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具有审美的价值。所谓政治倾向文学,又包含两种:一是如同席勒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艺术创作的特点,而使作品的主人公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5]95的“传声筒”式的作品;二是如同巴尔扎克式“从现实生活而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描绘以及鲜明的性格刻画等,对社会做作深刻的反映”[5]94的,“见解”“隐蔽”[5]135的作品。前者主要具有内容上的审美价值,而后者则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无论是西方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还是我国的《红楼梦》《家·春·秋》《骆驼祥子》《围城》《雷雨》等等,它们所体现的进步的思想内容以及丰厚的文化气息,特别是人物形象的人文气息以及时代感、历史感,艺术上的含蓄隐藉,都耐人寻味,让人回味无穷。
至于政治斗争文学,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17年间的工农兵文学,其思想内容的先进性,同样也给人以美感。特别是作品中的那些鲜活、感人的英雄典型,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当然,无论是政治倾向文学,还是政治斗争文学,都存在审美缺陷。这是指那些作为“传声筒”的一部分政治倾向文学,由于直露,因而缺少了含蓄感和丰厚感,因而削弱了艺术魅力和美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朱立元.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9.
[2][美]弗莱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08.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281.
[5]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欧洲文学史(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宋纯花.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J].飞天,2010(2):64.
[8]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96.
[9]王凤.简明语文知识辞典[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89.
[10]宇清,信德.外国名作家谈写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4.
[12]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学理论学习资料(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