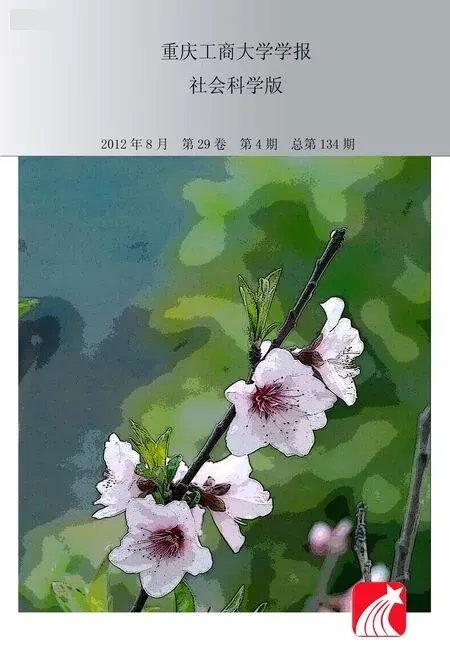凯尔森宪法保障思想的逻辑
——兼评施密特及中国的政治宪法学*
骆正言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公共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0038)
奥地利著名法学家凯尔森,以其纯粹法学、规范等级结构、基本规范思想,在中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影响了几代中国法律人。如果将当代中国人的宪法学思维比作一座大厦,其基石和框架都是由凯尔森建构的。凯尔森的思想,一开始凭借法学理论、宪法理论教材得以传播,后来,随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的翻译,[1]越来越多地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但稍嫌遗憾的是,作为奥地利宪法法院之父的凯尔森,其宪法法院的关键性思想并没有在国内得到精深的研讨。相反的,当年与凯尔森展开激烈论战的另一位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的宪法保障思想,却得到了高度的重视。[2]所以今天重温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思想,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凯尔森的了解,也可以恰当地回应当代施密特的追随者对规范主义的责难,达到准确认识、妥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鉴于此,本人希望以这篇短文,近距离审视凯尔森有关司法型宪法保障制度的论证策略,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一场“意义永不消逝”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经过了魏玛共和国的短暂繁荣之后,德国经济在战争赔款、外债沉重的压力下,渐渐步入低谷,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环境愈加恶化,德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崩溃又引出了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党派分裂、内阁垮台、议会解体不断上演,德国慢慢从共和制走向专制体制。[3]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是极力推行威权体制,为威权体制寻找理论资源;另一种则试图修正传统议会民主制度,为议会民主寻求新出路。在法学界这种分歧就体现在宪法保障的问题上,1929年德国召开了全国宪法学学者大会,针对政治转型与宪法保障的矛盾,学者们提出两种宪法保障制度,一个类型是政治保障型,即由总统来保障宪法实施,另一个类型是司法保障型,即由法院来保障宪法实施。这两大类型又发展成四派观点,主要以施密特、凯尔森、特里普、莱布霍茨为代表。
第一派是施密特的观点。施密特认为,宪法不是普通法,是政治法,宪法的争议本质上是政治争议,只有掌握政治的主权者才有权判断宪法是否被违反,所以“宪法的守护者”理应由总统担当。[4]第二派凯尔森依据纯粹法学的公法理论,以法律规范等级结构为理论框架,提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的宪法裁判制度,主张应该由司法机关掌管宪法的保障任务。他认为,“宪法作为上位规范,禁止作为下位规范的法律予以侵犯。因此,建立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宪法裁判制度——是宪法保障的必然要求。”他还说:“宪法保障制度,就是为防止出现违反宪法的法律而设计的种种措施。”按照凯尔森的观点,即便是政治争议,也可转化为个人主张在法律层面上如何看待的问题,最终也不过是法律争议。[5]第三派代表特里普(Heinrich Triepel)只在很小程度上肯定宪法的可裁判性。他反对凯尔森的对宪法争议采取形式逻辑的思考方式,说宪法虽是规制国家活动的产物,但不能规制国家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宪法表面上是“法”,实际上是“政治”,宪法争议是政治的争议,宪法裁判是对政治问题的裁判,所以本质上宪法与裁判是天生的对立物。[6]第四派人物是后来的宪法法院的法官,叫做格拉德·莱布霍茨(Gelhart Leibholz)。莱布霍茨的说法很隐晦,他说,宪法本身包含了不可扬弃的内在矛盾,即政治的因素和法律的因素的对立,宪法的目的就是想把政治的因素纳入到法律之中,以法律的手段来处理政治问题,将那些难以非政治化的、不能脱离政治领域的事情以法律予以规范。政治的因素是变动不居的、充满活力的。法律的因素是经久不变的、老成守旧的。政治要活动、要创造,法律要预测、要防御。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的对立,就像民主与法治的对立,自然与伦理的对立一样。[7]从这些语言分析,莱布霍茨的意思似乎是,在宪法裁判问题上,不是讨论要不要宪法裁判的问题,而是要讨论怎样掌握分寸,既不损害宪法的法律性,也不过多掣肘政治活动的主动性。
不难发现,这四人之中,对以司法手段审查违宪的问题,明确持反对意见只有施密特和特里普,凯尔森极力提倡,莱布霍茨折中。我们要考虑的是凯尔森怎样论证自己的看法,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宪法为什么需要守护?第二,为什么要说司法机关是天生的宪法守护者?这两方面加起来,才能圆满地证明以司法手段审查违宪的合理性。下面先说第一点。
二、宪法需要守护
要证明宪法需要守护,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先得肯定宪法的最高性。第二是说明要想维持宪法的最高性,违宪行为必须受到制止。关于第一点,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宪法被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任何下位法都不得违反。最早提出这种想法的人有英国的柯克,法国的西耶斯,德国的普芬道夫,美国的汉米尔顿等。[8]但是,魏玛时期德国学者并不总是这么看,比如施密特、安序兹都认为,国会所颁布的法律具有民主的正当性,自然而然地行使保护基本权利的功能,国会的立法者被视为基本权利的真正阐释者。[9]而且直到如今,英国除了欧洲人权公约具有高级法的性质之外,本国还没有成文宪法,更谈不上宪法的最高性了。
凯尔森是魏玛时期宪法最高性的倡导者,也是二战后德国基本法最高性的拥护者。他从法律规范的位阶理论(Stufenbau der Rechtsordnung)出发论证宪法的最高性,他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宪法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沿着塔尖往下,依次是法律、行政法规、法院的判决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等。[注]凯尔森将法院的判决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列入法律规范的体系之中,他的理由是,如同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规是法律的具体化一样,法院判决、行政行为正是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化。宪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宪法决定了下位法的制定程序、内容设置,法律在这两个方面都必须符合宪法。[10]另外,某些国家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更为严格的修改程序,也是宪法最高性的体现。凯尔森经过分析各国宪法现象,将宪法分为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形式意义的宪法指的是某个宪法文本,实质意义的宪法指的是调整法律规范的创制过程的那些规则。实质意义的宪法不具有这种最高性,它的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与普通法相同。形式宪法与普通法相区分,具有比普通法更严格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它的最高性是宪法本身规定了的。[11]。通过规范等级理论和修改程序上的差异,宪法获得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最高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保持这种最高性?当法律规范和国家行为损害了这种最高性时,是否应该施加制裁?
这是凯尔森试图证明的第二点。他说,只有违宪现象得到制裁,才能保证宪法的最高性。如果违宪现象频发,违宪者安然无恙,宪法的权威怎么保证?任何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制裁就没有效力,正如西方法谚所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这是凯尔森一再强调的。对于宪法也是一样,对违宪现象置若罔闻的宪法,只是一些原则、纲要、倡导、指南、道德,而不是法律。他说:
“缺乏保障的宪法,对违宪立法无能为力的宪法,是没有约束力的。……违宪的行政命令,特别是违宪的法律,依然发生效力。宪法,从真正的法律观点来看,事实上与缺乏强制力的个人愿望是一样的。……没有宪法的司法审查,法律体系中可能存在两个内容相反的规范。为了避免这种不一致性,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12]
凯尔森说得当然不错,仍有疑问的是,“政治性”的宪法争议能够以法律方法予以判断吗?如果违不违反宪法不能以法律手段进行裁判,我们也不能真正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前文施密特一派就主张,宪法具有政治性,不适合做法律上的判断。对此,凯尔森认为,宪法不仅具有政治性,同样也具有法律性。规范审查或合宪性审查,即是将下位规范的立法过程涵摄于上位法的授权规范之中,看看有无不合宪的现象,这可以使用传统的涵摄方法——三段论逻辑——予以审查。立法程序违宪与否可以判断,立法内容的违宪判断也是可以做到的。凯尔森拿美国宪法的条文为例加以说明,他说:
“(美国宪法规定)议会不能通过任何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在这种消极的方式下,不仅是法律的内容,而且还有这一法律秩序的所有其他规范的内容,包括司法的和行政的决定,都可以由宪法所决定。然而,宪法也可以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他可以就如美国的宪法那样,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享有:有发生罪案的州或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该地区应事先已有法律规定……’宪法的这一规定就决定了未来关于刑事诉讼法律的内容。”[13]
在“议会不得通过……的法律”“被告有权享有……陪审团迅速和公开的审理”一类的宪法条款面前,审查机关以涵摄式的演绎逻辑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违宪,也是不难做到的。所以凯尔森认为施密特对涵摄的理解过分狭隘,视法律之合宪性裁判为与构成要件事实之涵摄无关,乃大错误。[14]后来事实证明,凯氏的设想是可行的,二战之后,违宪判断的法律化伴随着宪法审查制度在战后的广泛推行,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行。
论述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凯尔森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宪法的最高性,另一方面主张违宪行为应该受到制裁。下面讨论由哪个机构承担违宪判断的任务。
三、司法机关是天生的宪法守护者
在1929年的大讨论之后,施密特和凯尔森在30年代先后发表了《宪法的守护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和《谁是宪法的守护者》(“Wer soll 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 sein?”)两篇重要的著作,提出了各自对宪法保障机构的不同设想。施密特借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康斯坦(B. Constant)倡导的元首的中立及调和权,意图提高总统地位,达到集中权力、稳定社会的目的。[15]魏玛时期的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任免文武官员,掌握国防军队,宣布紧急状态,大体上取得了以前皇帝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共和国总统由国民直接选举,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当国会与政府发生信任危机时,总统还可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虽然他也算政府的一个成员。[16]由于这种直接的民意基础,施密特将总统定为最合适的宪法守护人。针对建议采取美国式司法审查体制的学者,他提出两条反对理由:(1)德意志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不能建成美国式的司法国家;(2)美国司法审查主要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手段,保护私人财产及自由免于国家干预,但在其他领域未必具有作用,其判决亦非广受尊重,甚至招致危机。[17]
凯尔森当然也认识到施密特揭示的问题,他提出三点作为反驳。首先他认为,德国法律传统虽与美国不同,未被赋予违宪审查权的普通司法机关,本质上仍然具有形式上的审查权,这是法律演化的必然结果。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机关(法院)对于公布的法律具有初步的、形式上的审查权,即审查该法律是否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以及是否为宪法授权的合格立法机关所通过。[18]但是,凯尔森也不赞成采用美国式的分散审查模式,建议特设一个机关,如宪法法院,来审查违宪现象。他说:“这种解决方法(即美国模式)的弊端在于下列事实,即不同的法律适用机关可能对立法的合宪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而一个机关可能会适用立法,因为它认为立法合宪,而另一个机关却基于其所宣称的违宪性而拒绝适用。对立法是否合宪——即宪法是否受到侵犯——的问题缺乏统一决定,乃是对宪法权威的极大威胁。”[19]
其次,凯尔森认为违宪审查不适合由总统承担。在凯尔森看来,总统不适合作为宪法的守护人,首先是由权力分立原则所决定的。他说,权力分立的意义,不在于权力属性的划分,而在于反对集权。[20]德国通过限制、分割君主的权力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其结果,先是法院获得了独立于君主的权力,紧接着国会也摆脱了君主的控制,绝对君主制渐渐式微,个人权利保障更为切实了。凯尔森说,在君主制中,君主掌握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能,实行立宪君主制或者民主制后,君主的三项权能被分割了,分别由国会、君主和法院掌管了。所以,立法、行政、司法的区分不是逻辑发展的结果。在逻辑上,这三种国家权力是不需要划分的,三权分立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反对集权的结果。事实是,国会、君主、法院不是分别掌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能,而是共同执掌这三个部分。[21]的确,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是源于人们对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不信任,而由法院来分享这个权力,达到审核、制衡的作用。凯尔森也说:“司法权已经成为立法和行政权的一种重要制衡力量,这种制衡是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过程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22]所以,那种在共和国中一味提升类似于君主的总统的统治权的观点,那种将违宪审查控制立法的权限交给总统,是集权主义的标志。
第三,凯尔森主张宪法法院担任护宪者,还有一个条件,即宪法法院由民众直接选举。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议会、总统由选举产生,法官则由行政机关提起、立法机关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则不同,他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撤销法律,这种权力与立法具有相同的性质,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立法,与立法机关的主动的“积极”立法相对应。在凯尔森看来,宪法法院之所以能行使这种应该保留给国会的立法功能,正是因为宪法法院的成员应由国会选举,与其他法官由行政部门任命不同。[23]
由此三点可知,凯尔森的主张建立司法型宪法保障制度的理由是:它是法律理论的自然发展,是权力制约的必然要求和民主选举的直接结果。讨论到这里,凯尔森有关宪法法院的基本思想,已经基本清晰了。说起来也很简单,凯氏的想法,就是通过民选的宪法法院制衡立法和行政部门,最终达到更多维护宪法崇高地位和基本人权保护的目的。这些思想在国内也并不陌生,可是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思潮,让人深感凯尔森思想仍需大力弘扬。
四、中国不该成为宪政体制的特区
这就是目前愈演愈烈的“施密特热”,施密特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诸多课题,在法学上也形成一个独立的派别——政治宪法学,与目前已经颇有影响力的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形成了鼎足之势。大致说来,该派别有三个核心观念,第一,宪法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规范文本及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研究一个国家的现实政治状况。政治宪法学者这样描述现实政治:“我国三十年的法制改革是伴随着原先的党政一体化或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这个改革目前并没有完成。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作为宪法性的绝对力量在中国的法制运作中依然扮演着主动性的地位,所以,依法治国、法律之治的背后存在着强有力的政治。”[24]第二,宪法解释不应该拘泥于西方理论和判例,应该更多考虑本国宪法文本、制宪背景、现实状况。政治宪法学者将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本权利。[25]第三,宪法的保障,不是理想化的设计,应该按照各国实情,选取国家权力中最有实力的主体,使之成为宪法守护人。政治宪法学主张:“司法是否适合担当基本权利的守护者的问题,便变成了司法是否适合担当制度变迁的最终决策者。更明确的说,能指望法院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担当者吗?……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人大至上是中国宪法的基本法,如果我们还尊重中国的根本法的话,那么形式上以个案出现的基本权利保障事件就只能取决于社会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互动和合作,最终取决于政治决断。”[26]这三个论点基本上构成政治宪法学的骨架,也是政治宪法学与施密特思想的相似所在。为了不至于跑题,本文姑且不做独立的评论,而是站在凯尔森的立场来审视这三个论点。
首先第一点,政治宪法学主张研究实然的政治运作,而不是当为的宪法规范。在凯尔森那里,这种对实然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属于法社会学的范畴,它对于研究宪法如何制定、如何修改、如何实施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以宪法社会学替代宪法的规范研究,前者只能取得辅助地位。凯尔森说:“我们的理论关注的不是现实怎么样(What is),而是现实应该怎么样(what ought to be)。……如果这种理论(社会学或现实主义法律理论)可能的话,他也仍然不会是唯一的法律‘科学’,就像它的许多鼓吹者相信的那样。”[27]
第二点,政治宪法学主张宪法的解释,应该关注本国宪法文本、本国制宪背景,而不是拿西方价值观来解读本国宪法。这一点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文本之间存在矛盾、制宪思想错综复杂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作为解释的基础,就至关重要。凯尔森虽然始终强调法学的纯粹性,但是他仍然坚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念。[28]在凯尔森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法律观念,但他站到了自由、民主的一边。中国历史也是一样,它有集权的侧面,也不乏民主的侧面,传统思想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重视本国实际,不能只看那些另类的、褊狭的观念,也应该提炼传统价值的精华用以指导宪法的解释,这才是宪法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点,政治宪法学主张,只有在一个国家内部有实力保障宪法的机关,才有资格保障宪法,其他勿论。这一点,在施密特那里也同样可以清楚见得,魏玛共和国元首,继承了君主立宪时期的最高权力,又有着直接的民选基础,由他来护宪守宪,再适合不过了。问题在于,如凯尔森之言,宪法本身就是为了防范权力的过分集中,由掌握至上权力的机构、个人掌管护宪责任,怎么能保证这些机构和个人不会违宪,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恃强凌弱,而不是扶弱抑强了。当然话说回来,中国司法机构也缺乏西方社会法官那样的崇高声誉和广泛信任,由它们掌管违宪审查这个关涉根本的权利,也不见得让人放心。[29]只是有一点相信可以获得认同,即权力不能过分集中,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更进一步,中国不应该成为自由、民主、分权为特征的宪政体制的特区,这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可以看出来。
文章论述至此,不难发现,政治宪法学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学术流派,要想在新中国法学史上雁过留声,不好好回应上述的质疑,不好好研读凯尔森对施密特的责难,是无法做得到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恰恰是施密特那么热,凯尔森那么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11][13][20][21][22][23]汉斯·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2-143,143, 313,313,312,298.
[2]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M]. 李君韬,苏慧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浪漫派[M].刘小枫,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刘小枫.施密特与政治法学[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46-152.
[4][5][6][7]酒井吉荣,大林文敏.比较宪法学[M].东京:评论社,1999:268-269.
[8]Christia Star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M].杨子慧,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121-12.
[9]Christia Star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M].杨子慧,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167.
[10]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M].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221.
[12]Hans Kelsen, La garantie juridictionnelle de la constituion[M]. Revue de Droit Public 1928, 197f.; also see Michel Troper, “The guardian of the Constituion” Hans Kelsen’s Evaluation of a Legal Concept, in Hans Kelsen and Carl Schmitt[M]. eds. by Dan Diner/ Michael Stolleis, Bleicher Verlag1999:86.
[14][15][17]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70,270, 269.
[16]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M].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272.
[19]汉斯·凯尔森. 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的比较研究[J]. 张千帆,译.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
[24]高全喜.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EB/OL]. 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www.lawinnovation.com/html/fxpd/4204281164.shtml. 2011-6-02.
[25][26]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J].中外法学,2008(4).
[27]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M]. Translated by Anders Wedberg,Transaction Publisher2006:162.
[28]Yzhak Englard. Nazi Criticism Against the Normativist Theory of Hans Kelsen-Its Intellectual Basis and Post-Modern Tendencies[Z]. in Hans Kelsen and Carl Schmitt, eds. 1999:134.
[29]王伟.宪法司法化问题及其现实主义观照[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