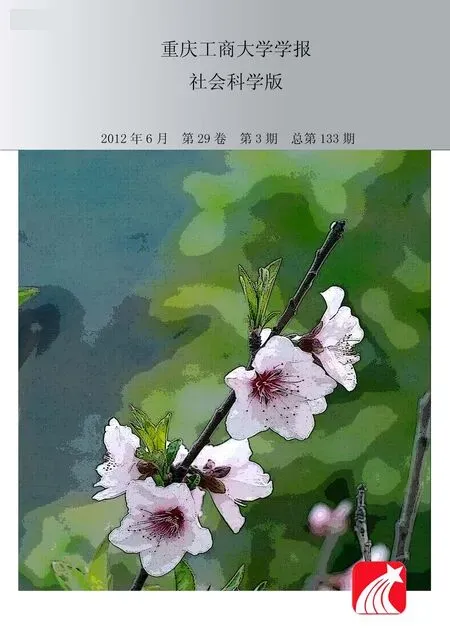屈辱和忽视:一种女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民长记》《撒慕尔纪下》的父权制思想诠释和反思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兰州 730030)
《旧约圣经》曾多次提到女性,首先是上主取了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从而使女人受男人的支配,女人变成附庸者。既然女人屈从男性,男人因直接受上主创造,其行为代表着正确和正当,而女性则往往与教唆、污浊、淫乱相关联,这似乎意味着女性所能给他人带来的仅仅是道德秩序的混乱。这种男性主义的视阈对女性的解读,让人们感到汗颜。今天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感到愤恨,情绪极其激动,基于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理念,她们集中火力,抨击《圣经》是一本男性对女性的宣言书,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同样需要一部像《圣经》一样能够挑战男性的宣告书,以此来解构和消解男性至上主义思想,以及作为占主导地位支配女性,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父权制和作为支撑父权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文章展开对女性遭遇和处境的分析,论证女性经验的被遗忘,揭示男性构建知识普遍性的虚假性,女性获得解放必须改变男性构建的社会结构,人的解放最终取决于女性的解放。
一、肉身存在与命名缺失
《旧约圣经》有关片段在语言表达上以男性阳刚之气贬低女性,这就暗含着一种男性至上主义的思想,由于父权思想的作祟,因而流露出对女性个体和身体存在的忽视,这种忽视对女性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她被挨打,尽管挨打让肉体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会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得以恢复。可是,一旦妇女遭到忽视,心灵受到创伤,这种心理创伤是很难弥补的,她的命运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女性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被他人的忽视,而传统认识论、科学知识、宗教知识等恰恰则把女性给遗忘和忽视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中论述的,“至于女人则是不算人的人,只能做些后勤补给的工作,被看成是二流市民,一起被摆放到市场之外的家庭领域之中。近代思想即认为只有健康的成年男子才是人,那么儿童就是人之前的存在,老人则是人之后的存在,至于女性,只有位于人之外。”[1]13这就是说,女性在人类发展史上不仅受屈辱,而且被严重的忽视,社会则不再把女性当做真正意义上的人来尊重和对待。与此同时,也就忽视男性对女人的、与生俱来的特权这一事实。
女性被严重的忽视,不被尊重而受屈辱,实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化的结果。首先,社会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合理化,通过社会过程,从家庭教育开始,经过学校、教堂等教育、宗教与文艺的熏陶。再次,男性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对女性剥削,并且依靠暴力占有女性,宰制和压迫男性。[2]54最后,男性依靠对文化、知识的控制,以此实施对女性思想、表达、认知的干扰、限制和扭曲,从而把父权制的种种思想和观点内化为女性的价值观,使女性认同男性为他们所设置的身份,女性丧失了自己成为自己的所是,相反,女性成为男性所是的所是。就此而言,笔者想通过对《旧约圣经》的《民长记》第19章“利未人至伯利恒迎其妾”的分析,进一步诠释这样一个问题。“利未人至伯利恒迎其妾”一章中提到的“其妾”就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者,就从“其妾”的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妾”一词使用了泛称的指义,这显示女人的身份是隐匿的,不该显现,因此女人缺乏一个具体的命名,没有“姓”名,这种无名就界定了女人的地位和处境。那女人的存在对两个男性而言,仅仅是一种符号的存在,只有在两个男性语言言说中得以显现和露放,而其妾本人并没有使用语言,言说自己的生存境遇,她似乎没有存在过,她的存留完全由两个男性的主观意愿所决定了,她自己完全不能为自己做主,似乎她不再是人,反而是一种财产。可以说,主体的缺场开启了她的悲惨命运。
二、屈辱的女性主义形而上学
《圣经·民长记》的“基比亚匪类之恶行”一节中,无视女子的人格和尊严,把妇女当成性欲的工具,也看作是抵御和保护男性遭受损害的工具,这种对妇女的人权无视和忽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我们看到,房主和那人为了维持男权主义,宁愿牺牲女性换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种男权主义让人感到厌恶和愤怒。当匪徒叫喊要与那人交合时,房主急忙阻拦,认为这是一件丑事,答应如果强盗不与那人交合,他承诺将自己的女儿与那人的妾交给强盗,并说“任凭你们玷污她们”。房主的这番话渲染了一个男权至上者的思想观念,为了维护男性的尊严,不惜让强盗玷污两名妇女,并从房主的言语表达中,透露出对妇女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同样,房主也把妇女作为一种财产和工具看待,当自己遇到危险,就把她们作为保护自己的庇护伞。房主对是非观念的评价建立在男性的偏见和主观臆断上,一方面,他在没有征得那人和妾的同意就承诺把自己女儿和其妾交给匪徒,其表现相当主观独断;另一方面,他从有利于男性自身出发确定价值判断的尺度和标准。他把匪徒要与那人交合看作是丑事,却把自己的女儿和那人的妾交给匪徒看作是正常之事,让那些匪徒对她们任意玷污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不是一件丑事,房主的这种道德价值观念值得人怀疑,而妾的丈夫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和贞节却把其妾“拉出门交给他们”,其妾终夜受尽匪徒的凌辱。后来,那人借此向他们的族人宣称,匪徒是在向他们挑衅,侮辱了他和他们族人,是对族人男性尊严和人格的冒犯,于是,主张通过一场战争来捍卫他们男人的尊严。而对女子的忽视,表现在那人不是把女子当作人看待,而是当作财产看待,谁动了族人的财产,族人们应该起来保卫,并通过战争,使族人的权力和生存的疆域得到拓展。可以说,这件事构成了满足男人实施残暴行为和征服他人野心的合法途径,与此同时,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构成人类文化的顽冥不化的权力结构。
谁来保护这些柔弱的女子呢?捍卫她的尊严和人格呢?是房主抑或丈夫,还是族人呢?都不是,其妾的遭遇恰恰证明父权制和男权主义思想观念的不正当和不合法性。房主和其丈夫不但不去救妇女,反而把她们送给匪徒,这就是说,房主和丈夫与那些强盗一起,合谋陷害了那女子,他们共同构成那女子受害的合谋者。那女子虽然一直在场,她却总是表现为沉默,其柔弱的身体却被几个男人挟持玷污,这不仅对女子的身体,而且对女子的精神造成极大伤害。
女子在场的沉默,主体的自我意识的不凸显,身份的模糊,自身消退,其身遭受强暴。在笔者看来,促使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的在场,它控制了整个场面,它使女性感到窒息和眩晕,虽然匪徒玷污了其妾的肉体,但是,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玷污了其妾的脆弱心灵和纯洁的精神,这一切唯有女子才是亲身的唯一见证者,父权制意识形态使她丧失人格和尊严,它所塑造的观念毁掉了女子的脆弱生命,而男人是那种观念的执行者,可以说,那些男人是一群缺乏情感和信念的存在者,一群忘记了存在本身的流浪者。海德格尔说,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忘记存在的历史,换言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一部忘记女性,女性受屈辱的历史,进一步讲,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是一部女性受屈辱的历史。正是女性使得男性作为存在者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做出了成就,女性的被遮蔽就是男性的开显,当男性在开显中攫取真理时,开始使用拥有真理的权力宰制产生真理的源头,真理也就变成残害女性的帮凶。当男性没有女性在场,女性仍然是不在场的在场者,男性无法论证自身的身份和性别,尽管男性觉得自己强大,拥有整个世界,但是女性是男性存在之为存在的理由,没有女性的存在,男性无法成为男性,男性也就无法确证自己的性别身份,因为存在本身证明着存在者的存在。因此,男性需要女性,女性同样需要男性,双方相互平等相处,才能使对方很好的开显自己,从而产生的知识,形成的真理不再对人本身存在构成威胁和宰制。
三、沉重肉身的伦理维度
父权制和男权主义思想导致忽视女性的心理感受与女性的经验和体验,而仅仅重视男性的心理感受和亲身体验,比如,当匪徒要与那人交合,房主就极力劝阻,认为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但却放任女子被匪徒的任意玷污,房主关注和重视男性心理体验和感受的同时,故意忽视女性所遭受玷污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在“基比亚匪类之恶行”中,妾的丈夫的一系列活动,证明了他没有关心过其妾,也没有因为妾在匪徒那里受到伤害而担忧过,一种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然而妇女扑倒在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证明遭受了极大伤害,已经生命垂危,丈夫不仅没有立即想办法救妾,反而说,“起来,我们走吧!”这种冰冷的话,令女子锥心刺骨,更伤透了女子的心。当女子不回答那人,那人就把女子驮在驴上回家。这个“驮”字准确的描述了那人的心理状态,妾被忽视,正因为被忽视,就把她当作一件东西,或者一些财产。女子就在被男人的忽视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旧约圣经》没有详细描述女子被玷污时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的感觉,而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并且也没有交代女子是如何死的,死之前又是怎样痛苦的等等情形,这体现了《旧约圣经》言语上的男权主义至上性,并以此悬置伦理道德,为男性争夺权力做了铺垫。
那女人被忽视,不仅是对她的经验的忽视,也是对她肉身本身存在和生命的忽视,由于“女人的经验将持续被排除在文化史之外。只有痛苦方能暗示女人经验的特殊性——那种被排除在对世界的集体描述之外的特殊经验。”[3]36因此,在父权制或者男性社会里,悬置了女性的内在特有经验,并把这种经验排除在男性建构的历史文化之外,那么,男性所建构起来的人类文明和文化、人类的知识和科学、伦理道德就不再具有普遍性,它们仅仅是一种体现男性独特的经验的一种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一种呈现男性世界观,显示了男性对世界图景的规划。如果按照康德的知识论,那么知识的构成仅仅是关涉男性的经验,女性因为被视为非理性,她的特殊经验被悬置,这样产生的知识相应地以真理之名宰制女性,女性在无声无息之中被耗尽了一生的生命,男性从而获得了权力和统治,并以知识和科学的普遍性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们把用自己经验得到的知识作为人类的普遍知识和科学,通过权力实施自己的阴谋,从而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利益。正如马克思对国家的分析获得的结论一样,国家把特殊的利益说成是普遍人的利益,同样,男性把根据自己经验制作的知识说成是人的普遍知识,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男性对女性的宰制。
其实,我们看到,男性的经验是不完整的,“这不仅因为被压迫者总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也由于被压迫者的知识乃是从对压迫的反抗中诞生的——女人的知识来自她们对男人的反抗,以及她们企图以新的知识取代男人生产出来控制与宰制她们的扭曲知识。女性主义的立场是一项成就——它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活图像,乃是从形成女人社会经验的活动观点出发,而非男人的统治性别经验中随手可得的偏见与谬见。”[4]210-211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回到像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面对性别事实本身,悬置外在的权力,直接洞察女性和男性意识事实本身,从而开显出两性的平等和自由。因为女性与男性原初就是自由自在的交往和相处,并不存在谁对谁的统治、压迫和宰制,只是后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建构所确定的社会结构模式,把一种违背自然的、不正当性的事情变为合法和合理的事情,从此女性遭到不平等的对待,并把这种不平等内化为一种习惯,一种把非自然的自然化,女性在男性主义文化背景下接受一种男性赋予女性身份认同观念,女性对这种身份认同的接受意味着不幸的到来。至此,只有重新返回性别的原初现象,当女性对自己原有的意识结构的反思,重建女性的意识结构时,就会与男性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从而促使女性变革现实,改变自身处境的意识的确立,即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就像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先有无产阶级意识一样。
在《圣经》的《撒慕尔记下》的第10章“戴维干罪”中,我们看到,戴维凭借自己的权力,就占有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而赫人乌利亚上前线打仗,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在强大王权压迫下,被接到王宫。这个“接”字恰恰掩饰了戴维强权对乌利亚妻子的“威逼利诱”的罪恶,也掩饰了权力对女人的宰制,从而把一种不愿意转换为愿意,把一种内心的反抗化解为平和的接受。从文字表达中显示,似乎乌利亚的妻子愿意并情愿来到王宫,接受戴维的玷污,这只能使男性主义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乌利亚的妻听到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这证明乌利亚的妻子是非常爱乌利亚的,妻子这样爱乌利亚,她不会背叛乌利亚的,之所以妻子与戴维交合,后怀孕,其原因在于妻子面对强大的政治权力,处于生存本能的自保,她只有被动服从戴维。从一般意义上讲,普通的男人在没有经过女人同意,强行与女人交合,那就是强暴,是犯罪,而一旦被一个男性国王强暴,其事却变得正当而不受任何制裁和惩罚,这种人定法对自然法的违背,意味着人的堕落,需要上主的拯救,这便构成圣经的救恩渊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戴维的强大权力吞噬了女人痛苦、羞辱、绝望、神情木然的心理和身体感觉,把女人转换为男人性欲的玩偶,这种对妇女心理情感忽视,只有女性主义者以女性的眼光才能透视出男性这种“盲点”,才能认清男性对女性的宰制和压迫,看清楚女性存在的悲惨境遇。实际上,基督教时期的意识形态便是:“凡是肉体控制、灵魂侍候之处,家庭关系就是颠倒的。女人控制男人的家庭,情况还要糟糕。然而,那种男人下令、女人服从的家庭关系却是正确的。因此,那种由灵魂控制、肉体侍候的人都是正确的。”[5]84正因如此,那人的妾和乌利亚的妻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都是男性的附属物,男性是支配者,女性是附庸者。由于“附庸者对自己的了解反而不如对支配者的了解。如果你的命运要靠适应及取悦支配者来决定,你自会全神贯注在支配者身上。因此,附庸者不觉得了解自我有何用处,其他的限制更加强了这种倾向。人只有经由行动及互动,才能了解自己。附庸者自己行动及与别人活动范围均极其有限,以致无法实际评估自己的能力及问题。不幸的是,了解自我的难处还不止于此。附庸者会相信支配者制造的谎言,对自己的认识因此更加混淆,这委实可悲。”[6]102-103因此,女性更需要主体和自我意识,像男性那样思考自己处境,与他者互动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现有的男性社会结构和男女心态,为解放自身创造条件。
四、结语
在父权制和男权主义思想观念的支配下,男性对女性的操纵和控制,使得女性处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当女性意识到自身存在与男性的存在身份上具有同等重要和平等时;当女性的公民身份认同、女性意识、女性平等和自由思想产生时,意味着女性开始了二次重生。女性通过斗争,争取把自己从忽视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使男性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女性的承认和认可才体现出来,这样,男性开始转化视角,包容女性,这时女性有机会同男性谈论平等和自由等问题。在18世纪,西方有些国家的妇女通过争取政治承认,开始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1792年,沃尔斯通莱芙特的《女性权利的辩护》作为第一本阐述女性主义的著作出版,标志着妇女开始有了话语权,因为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中规定,“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从根本上剥夺了妇女在公共场合说话的权利。埃莱娜·西苏认为,女性不能沉默,“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阳具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不是那种保留在象征符号里并由象征符号来保留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沉默的地位。妇女应该冲出沉默的罗纲。他们不应该受骗上当去接受一块其实只是边缘地带或闺房后宫的活动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7]87当妇女通过自己肉体思考,在与现实的斗争中获得女人应该享有的权利。
其实,当我们看到“女性比男性更接近存在”“女人比男人更是人”[8]196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加入到女性主义运动之中,开始思考和反对造成男性对女性压制、支配和剥削的缘由。在霍克海默看来,由于传统哲学认为女性不成熟和缺乏责任感,因此认定男性是完美的存在,女性则是受挫的男人,这就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理想主义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9]9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是男性的,即有利可图的生产率,过分的自信、效率和竞争”,[10]136它统治着女性,压制和剥削着女性,因此,女性需要一种女性的世界观、价值观,重新审视和打量这个世界,以此唤起女性创造社会生活的知觉。如果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宣布资产阶级死亡的号角,那么麦克因斯的《男性的终结》则宣告了父权制和男性主义时代的终结。温德尔认为,“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必须在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5]136从而重新书写一部女性的“新的百科全书”。[11]146这激发了女性主义对性别正义的思考。
无论怎样,女性受压迫、被支配和剥削的处境与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当把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来对待时,也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当把男女之间的关系看做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定。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了人的本质。从这个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个关系的性质中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12]80这就意味着,男人不能再把女人当玩偶、工具、物、财产来看待。人是目的,男人要把妇女当作人,当做另一个自己看待。这样,妇女才有可能从被忽视状态之中解放出来。一旦妇女从忽视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自主、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与男性共同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享有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权利时,女性与男性所构建的社会就是一种自由、和谐与平等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显现性别正义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上野千鹤子.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M].刘静贞,洪金珠,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7.
[2] 洪谦德.女性主义[M].台北:一桥出版社,2003:54.
[3]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Feminist Thought. Desire,Power,and Academic Discoure[M]. Blackwell Publishers,1994:36.
[4] Pamelan Aibbott and Claire Wallac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M]. Routledge,1990.
[5]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北京:三联书店,1995:84,3.
[6] 密勒.支配舆附庸[A].顾燕翎,郑至慧.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C].女书文化,1999.
[7]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顾燕翎,郑至慧.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C].女书文化,1999.
[8]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9] 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0]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1] 弗里克,霍恩斯比.女性主义哲学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