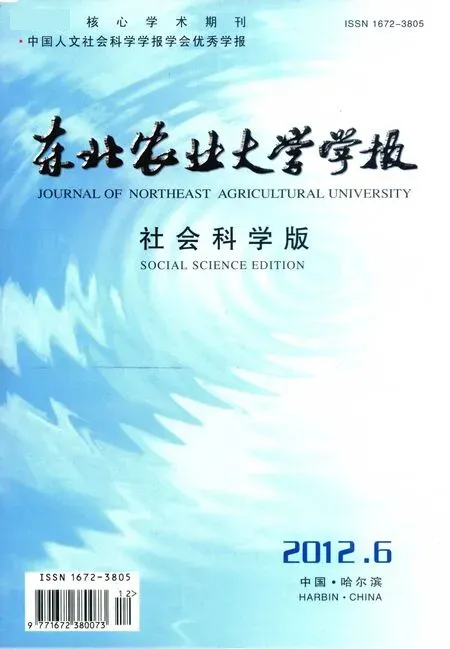中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跨文化视角解读《喜福会》
杨亚丽 杨 帆
(1.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以四位华裔母亲与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素材,描绘了华裔女性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对身份的认同和寻求的心路历程。“喜福会”是个麻将馆的名称,最初由四位母亲之一吴夙愿在桂林发起,移民美国后,四位母亲在异国的土地上再次组成“喜福会”,创造了一块中国文化的生息之地。小说也是以“喜福会”为线索,讲述了四位母亲和四位女儿的故事。
一、中美文化的冲突与差异
中美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但两种文化没有好坏与强弱、进步与落后之分。
(一)中国的高背景文化与美国的低背景文化的差异
爱德华·豪尔把世界文化分为高低两大类文化类型。高背景文化中大部分信息隐含在沟通接触的过程中,对话者通过语言、手势、空间等语境和相互间的默契来传递信息。而低背景文化是指信息的表达比较直接明确,语言是沟通中大部分信息的载体,在低背景文化中,社会内部差异大,交流需要详细的背景信息。
吴夙愿带着高价买下的一只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象征美好愿望的天鹅来到美国,在入境时被移民官强行夺走,只剩下了一片天鹅羽毛,吴夙愿一直珍藏着这片羽毛,自己去世后,由丈夫将它转赠给女儿。吴夙愿本是国民党军官夫人,在中国内战期间,由于身患重病,放弃了希望,抛弃了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她保存的这片天鹅羽毛就是她的希望,提醒她永远不要再放弃希望。女儿在母亲死后,了解了母亲的过去,体会了天鹅羽毛的含义,终于带着这片羽毛,回到了中国,代替母亲与双胞胎姐姐团圆。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片天鹅羽毛的真正含义,而这片羽毛在美国这样的低背景文化中是很难被理解的。
(二)中国的情感型文化与美国的工具型文化差异
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是以情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交往中,人们相互依存、相互满足,包括情感在内的各种需求,情感关系较为持久、牢固和稳定,而且情感固定在一个圈子里,很少变化;美国文化中的友谊观一般是属于工具型的,友谊是人们在交往时作为达到某一目标或获取某种利益所建立起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型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关系往往短暂、不牢固、不稳定。
《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喜欢聚会,互相了解彼此的过去和现在,她们的友谊固定在华人的小圈子里,稳定而持久,即使在其中一人(吴夙愿)去世后这种友谊仍在继续,生前好友帮助她完成夙愿,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女儿,并促成精美回国与姐姐团聚,这种友谊是典型的以情感为中心的中国式友谊。
而丽娜和哈罗德的婚姻关系却是美国式的工具型文化的体现,夫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友情,丽娜和哈罗德的婚姻生活是各自所需,各自付款,财产上“井水不犯河水”。这种貌似平等、自由、独立的美国家庭生活方式,就是美国工具型文化的一种体现,这种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时必然产生碰撞。母亲的来访,成为这种关系破裂的导火索,随着茶几倒地,花瓶破碎,他们的AA制生活也结束了。
(三)中国的团体主义文化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差异
传统的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团体的力量,在团体内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家庭是最重要的团体,家庭中家长与子女相互依存。这种关系一方面意味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子女要努力奋斗,“光宗耀祖”,实现父母的理想;而美国文化重视个人奋斗,美国人宁愿在成功的路上孤军奋战,独享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母亲琳达就是希望在女儿的成功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女儿薇弗莱练棋时,母亲站在身后充当保护和同盟,女儿赢棋是母亲最大的骄傲,她不但每天认真地擦拭女儿的奖杯,而且在街上拉着女儿的手,逢人就炫耀女儿的成就。这种做法让女儿极为反感,在大街上就对母亲大喊“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啥不学下棋呢?”母女之间,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具有团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人喜欢聚会,特别是节假日或空闲时间多与亲朋好友一起度过;美国人认为玩和休闲是自己挣来的,空闲时间是宝贵的,应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四)中国的垂直文化与美国的水平文化差异
Harry C.Triandis在对世界文化分类中,把文化分为垂直文化和水平文化。垂直文化以等级制度为基础,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处在等级制度顶端的人自然就该支配和统治处在等级制度底端的人。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就是明显的垂直文化;而水平文化的基础是人人平等,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和张扬,追求平等,属于水平文化。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孝悌是最基本的,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有悖祖训;而在美国文化中,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吴夙愿为了让女儿精美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不惜免费为钢琴老师做保姆,以换取每周一次的钢琴课,而在美国文化教育下长大的女儿精美对此并不领情,在她看来,母亲的做法侵犯了她的权利,因此她大声呼喊:“……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甚至说出了“我希望我没有出世,希望我已经死了,就跟桂林的那对双胞胎一样!”为反抗母亲逼迫她学琴,精美故意在表演会上弹得一团糟,让母亲下不了台。
(五)中国的间接文化与美国的直接文化的差异
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以谦虚、含蓄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往往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会轻易炫耀自己的成就;而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个人成就与自由,乐于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赞扬和感谢,也愿意展示自己的成就。在薇弗莱带男友理奇来家吃饭时,薇弗莱反复叮嘱理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可当琳达妈妈把她最拿手的梅干菜蒸肉端上桌的时候,故作谦虚地说:“哎,这菜太淡了,没什么味,真让人难以下咽。”薇弗莱知道这是在暗示他们赶快来尝尝,然后称赞她的菜烧得如何美味,但是还没等大家来得及这样做,理奇就接着琳达妈妈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然后在这道美味佳肴上倒上了一层黑乎乎的酱油,琳达妈妈顿时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在场的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处理这尴尬的局面。而理奇却对此毫不知情,仍觉得自己和未来的丈母娘相处得很好,因为他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二、中美文化的融合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充斥了《喜福会》,然而中美文化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随着女儿们长大成人和经历了挫折后,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华裔女儿们对处于弱势的本族文化从开始的一味排斥转而表现出好奇和兴趣,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她们以英语语境来讲述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文化的接纳以及他们的文化寻根情结。吴精美最后决定回上海与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相认,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向讨厌母亲拿她来“炫耀”自我的薇弗莱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抗争的愚蠢;她和理奇婚后准备到中国度蜜月,他们希望母亲琳达同他们一起去:“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飞向东方……”平常把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的露丝在婚姻危机时接受了母亲的建议,采取积极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在离婚大战中赢回自我,对即将离婚的丈夫特德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而特德在露丝的怒吼中看到了露丝的个性,找到了他们婚姻的基础,使即将走向灭亡的婚姻得到挽救。露丝破裂婚姻的复合恰恰是中美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合的最好范例和象征;丽娜则由否认到佩服的母亲未卜先知、未雨绸缪。小说的最后,女儿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中国苦难”中找回了人生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
固守中国文化的母亲们也逐渐走出华人的小圈子,接受了美国文化,她们开始参加每周一次的教会活动。琳达从开始反对理奇到后来耐心地教他吃螃蟹,对白人女婿的接受,实际上也是母亲们接受西方文化,对中美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包容。
两代人走向沟通与理解,中美文化的最终融合最后体现在女儿精美了解了母亲的过去,理解了母亲的苦心和伟大的母爱,代替母亲回中国与失散的双胞胎姐姐团聚:“我终于看到了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啊,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吴精美的中国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亲的中国姐姐,显然象征了她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认同,正如母亲吴夙愿所说:“万物起于东方:日从东方起,风从东方来。”
三、作者跨文化交际思想的表达
《喜福会》中,谭恩美通过母女两代人的关系、女儿们与白人社会的关系,力图探索美国华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问题。《喜福会》不仅反映了华人在美国的生存与奋斗的心态轨迹,还力图塑造新的华人形象。谭恩美通过描述四个华裔女儿在独特文化背景下的成长历程表达出自己应对多元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对跨文化交际给予一种新的诠释:尽管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碰撞与冲突,人与人之间尽管有隔阂、误解和矛盾,只要有爱,就能相互包容、共存。小说通过母女之间从误解、冲突到沟通、理解的描写,展现了中美文化在不断撞击过程中走向融合,表达了作者对中美文化最终走向和谐共存的信念。
[1] Samovar Larry.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New York:Clark Baxter,2001:80.
[2] Lusting Mw,J.Koester.Intercultural Competenc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M].New York: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112.
[3] Larry A.Samovar& Richard E.Porter.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7:287.
[4] 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61-16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