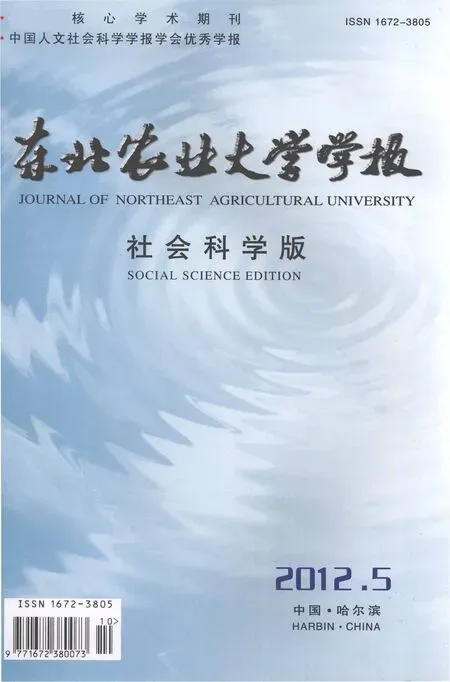从《宠儿》与《紫色》看黑人女性的身份重建
蔡 玥
(黑龙江科技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托妮·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是黑人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人物,肩负着民族与种族的双重使命。她们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多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悲惨生活,黑人女性的成长历程,黑人文化传统的传承等主题。作为莫里森和沃克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宠儿》与《紫色》分别以两位作家不同的视角描绘了黑人女性塞丝和西丽从身份缺失到自我认知与觉醒,再到自我救赎与身份重建的成长历程。尽管过程不同,但最终要实现黑人女性自我身份重建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一、黑人女性身份的缺失
在叙述黑人女性的身份缺失状态时,莫里森和沃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黑人女性的最终命运却惊人相似,即都失去了人的独立身份。
1.塞丝——奴隶制统治下,黑人女性的自我迷失
莫里森将《宠儿》的故事背景置于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1865—1900年),讲述南北战争后底层黑奴的苦难生活。尽管当时奴隶制已经废除,但其影响依然深远,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奴隶性仍然存在,她们所受的创伤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抚平,反而是历历在目。至1874年,奴隶制已经废除整整10年,然而黑人仍然身处社会的最底层,白人的压榨和迫害让他们无法看到命运的改变和希望。在保罗·D的记忆中,大多数黑奴“眩晕、饥饿、疲倦或者被掠夺到了如此地步,让他们重新唤起记忆或者说出任何事情都是个奇迹”,他们都“像他一样,他们躺在山洞里,与猫头鹰争食;像他一样,他们偷猪食吃;他们把身子埋进泥浆,跳到井里,躲开管理员、刽子手、退役兵、山民、武装队和寻欢作乐的人们”。黑人女奴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没有任何权力,只能极端地选择死亡。塞丝从“甜蜜之家”农庄成功逃亡,但奴隶主“学校老师”随即带人追来,为了不使子女重蹈自己奴隶的命运,塞丝锯断了一岁多女儿的喉咙,毅然决定以死亡终结她们成为黑奴的可能。弑婴行为实质上是黑人女性对奴隶制的惧怕和无能为力,她们以死亡这种极端的方式阻止奴隶制向下一代传递。莫里森对奴隶制的血泪控诉真实地还原了黑人女性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其在奴隶制影响下作为独立的人的身份缺失。
2.西丽——性别和阶级歧视下,黑人女性的失语和隐形
在《紫色》中,沃克侧重揭示黑人族群的内部矛盾,即在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失语和隐形状态。沃克笔下的黑人女性身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多重压迫,她们是黑人族群中最悲惨的阶层,完全丧失了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完整。
女主人公西丽长期忍受着父权制的摧残:她14岁即被继父奸污,还被威胁不得对“上帝”以外的其他人说,其两个孩子也先后被继父送人。对此,她不敢反抗,默默承受着继父的欺辱和奴役;她没有自己的意识,只能沉默并隐形。除此之外,西丽还长期遭受着自己丈夫的歧视和虐待:20岁时,西丽被继父卖给了某某先生(阿尔伯特),但是她的生活没有因此好转,反而更加艰难。在某某先生眼中,西丽仅仅是劳力和发泄工具。她被自己的丈夫奴役和压榨,却仍然无声地面对一切。西丽帮助妹妹逃跑,自己却屈从于无爱的婚姻中。只要能够生存,西丽可以忍受种种虐待和不幸,她的精神已变得麻木。即使有人鼓励她反抗,但她仍选择沉默和服从。西丽面对压榨和迫害的顺从与沉默,也预示着她的自我重建之路必将漫长而艰辛,她需要认识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二、黑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觉醒
1.塞丝的母性与母爱
在白人奴隶主眼中,黑人奴隶只是他们的所有物而已,黑人女奴更如牲畜一样。“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兽性十足,他们强行按倒塞丝,吸走了她哺养婴儿的奶水,疯狂地践踏她养儿育女的神圣母性,因此也激发了塞丝身为人的意识——保护自己儿女不重蹈覆辙的强烈母爱。
塞丝的母亲在贩奴船上多次被白人水手轮奸,她将和白人所生的孩子扔掉,只留下了和黑人所生的女儿塞丝。“婴儿的心每跳一下,他就退后一步,直到最后心跳彻底停息……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塞丝在逃亡途中锯断了年仅一岁多女儿的喉咙,因为在她眼中死亡比成为奴隶更加安全。两代黑人女性面对未来的抉择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极端的弑婴行为也使她们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奴隶制统治下,黑人女性只有在决定自己孩子的生死时才有真正的身为人的权力,她们默默地、无奈地、却又极其勇敢地想要去除白人强加的所有印记。她们满腔的母爱和强烈的母性在弑婴事件中得到了极度的抒发,这也正是黑人女性身为独立的人而具有的合理身份。
保罗·D认为塞丝的爱“太浓了”,而塞丝的回应则是“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学校老师’没抓走他们。”塞丝被动悲惨的命运和她在选择儿女命运时的主动出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通过极端、悲怆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声音,赢得了孩子的命运,迈出了黑人女性自我重建的重要一步。
2.西丽的同性之爱
沃克笔下黑人女性的同性之爱往往超越肉体和情欲,她们彼此吸引,互相扶持,勇敢地表现爱与忠诚;她们的精神和人格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和压迫。同性之爱已经成为黑人女性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
在西丽的意识中,男性的权威和女性的从属都是必然要接受的,她麻木地忍受着一切痛苦和悲伤,只写信给上帝来诉说苦闷。西丽与莎格的同性之爱为她麻木的生活注入活力,激发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莎格的出现证明了西丽爱的能力:她尝试着欣赏和享受自己的身体,体会到了爱的欢愉和满足。莎格的引导让西丽了解到了自己的懦弱和自卑,感受到了自己的麻木和无知,意识到了自己身为人的价值,“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逐步实现了精神、情感、经济的独立。她摆脱了“上帝”的精神束缚,在给妹妹耐蒂的信中写道“我不再给上帝写信了……我一直向他祈祷、给他写信的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和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鄙”。西丽曾过度沉迷于莎格的关爱,没有莎格,她的生活空虚而失落,然而正是莎格的再次出走让西丽完全掌控了自己,实现了情感的独立;在莎格的帮助下,西丽开办裤子工厂,并且有了不错的收入,她还获得了生父的遗产,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
三、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和身份重建
在对塞丝和西丽自我救赎与身份重建的描述中,莫里森和沃克都强调黑人民族的集体力量。
谈及《宠儿》的创作,莫里森一再表示反思过去、认识过去的重要意义:未来的幸福和平静必然要与过去发生某种联系,而要处理好现在和将来就必须要跨越难以启齿的过去这道屏障。“宠儿”即代表了塞丝的过去,代表了黑人女性比死亡还痛苦的艰难境况——她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再做奴隶,她们能够承受死亡之苦却对终身为奴的命运无能为力。“宠儿”的阴魂不散破坏了平静的生活,塞丝的精神和身体因此备受折磨;她内心的苦痛不可言说,而要实现自我重塑,就必须要正视现实,只有治愈了内心的伤痛才能真正地走向新生。最终塞丝最宠爱的女儿丹芙向黑人社区寻求帮助,以一首招魂曲驱除了阴魂。丹芙自我意识的觉醒帮助了塞丝的新生和重建,同时整个黑人社区也摒弃了嫌恶和歧视,在“集体行动”中增强了整个黑人民族的自我意识。
沃克认为,在充斥着性别和阶级歧视的世界里,黑人女性的成长和觉醒离不开她们彼此的友爱和团结。姐妹情谊是《紫色》中西丽成长与独立的关键性内容。在黑人族群内部,黑人女性不仅没有得到男性同胞的帮助和扶持,还要忍受来自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和虐待。面对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压迫,姐妹情谊成为了黑人女性争取自我救赎与身份重建的精神保证。情人兼好友的莎格启发了西丽人性的复苏,儿媳索菲亚和妹妹耐蒂激励了西丽女性意识的觉醒。姐妹情谊使西丽的生命更加完整、健康。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友爱的姐妹情谊还迫使黑人男性必须更新观念,摒弃性别和阶级歧视,共同构建平等和谐的黑人民族。相互理解与和睦相处基础上重建的两性关系也标志着黑人民族意识发展的新阶段,达成了两性和谐与内部团结才能最终实现种族的平等和独立。
[1] Morrison,Toni.Beloved[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3-15,35-38.
[2] 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5-30.
[3] 艾丽斯·沃克.紫色[M].陶洁,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25-28,50-57.
[4] 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230-235.
[5] 刘戈.革命的牵牛花——艾丽斯·沃克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5.
[6] 薛小惠.《紫色》中黑人女同性恋主义剖析[J].外语教学,2007(5):78-80.
[7] 高晓慧,宋宝梅,胡家英.论艾丽斯·沃克的生态妇女主义观——以《父亲的微笑之光》为例[J].学术交流,2011(7):18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