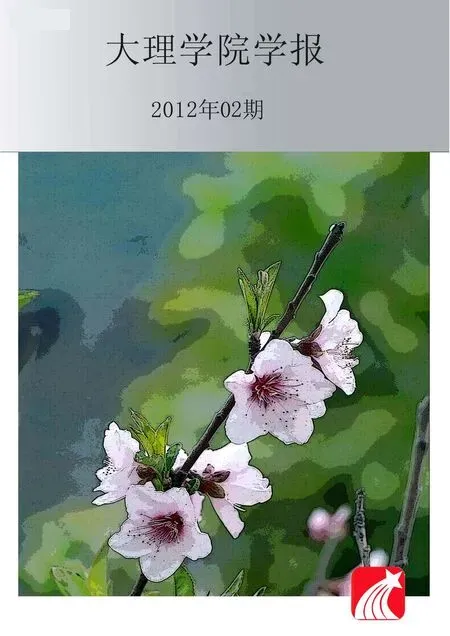愿为云南文学鼓与呼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愿为云南文学鼓与呼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纳张元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一书辨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与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在于表达作家的感情,情感是人的生命喷发的突破口,只有作家找到了表达自己思考的生命形式以及表达的感情形式,才可能构成文学作品审美的基本因素。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的文化基因是融化在其血液和生命之中,而不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感情的世界不讨论是否正确,只讨论是否真实和是否强烈。
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基因;生命形式;感情表达
纳张元是彝族作家,又担任了大理学院文学院院长,从事写作教学和理论批评,是一个创作和理论“双肩挑”的全面之才。差不多是在十多年前,他从大理白族自治州来复旦大学访学进修,那时他还是一位青年教师,生气勃勃,发表过不少小说。当时我正在主持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初稿,在研究生的课堂上逐章讨论,纳张元认真投入讨论,特别就非汉民族文学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为此在文学史后记里写到这本教程的缺点时,特别提到这是一本不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这本教程里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从此以后,如何完整体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特点,如何整合一部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民族现状的文学史,一直是我心中的目标。可以说,这个念头就是当年纳张元给予我的。
纳张元回到大理以后,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我们时有书信往来,能感受到他不断的进步。这期间我两次去昆明开会讲学,都曾想过要顺便去看看他,其中有一次已经购买了飞机票,纳张元也已经在大理机场等候我飞过去了,结果还是阴错阳差没有去成,留下了遗憾。这种遗憾也转换为思念,转换为祝福,关注着这个青年人的成长。最近纳张元来信并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文学批评集书稿《民族性与地域性》〔2〕,嘱我为之写一篇短序。我当然很乐意,便利用春节休假读完了书稿,想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问题,试谈一些自己的感受。
纳张元是一位自觉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探索民族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也大声疾呼,推动少数民族的创作。他身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彝族作家,又处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性潮流之中,现代文明发展(包括全球化趋势)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可能性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他纠结于心的问题。这是他在主要论文里一再涉及到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纳张元思路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不迷信也不过分渲染少数民族的许多行将淘汰的文化传统,敢于直面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生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他从重新解释长期被误解和歪曲的鲁迅的话着手,指出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流行观念是不准确的,并且一再辨析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他自己被困扰的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民族如何在与世界契合而又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比之主流作家的处境更艰难,他们一方面要表现本民族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不可避免被全球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本族生存的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的人文叙述来达到对民族特性的恪守与民族身份的认同”〔3〕。这里他用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主流作家”两个似乎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少数民族作家不是主流的作家而是边缘的作家。这是纳张元把自己感受到的身份认同的困境普及化了,普及到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上。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一定很准确,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很清楚,他想说明的是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这两个概念的文化内涵之不同。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处于中华文化体系的边缘,其处境似乎是“更艰难”。他想说的意思是,汉族作家在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面前,面临了汉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大趋势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他们与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传统之间也存在着另外一层意义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冲击中,是属于弱势文化中的弱势文化,它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表达的比较尖锐、也是经常性地折磨着作家创作情绪的,往往就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传统、全球化的强势与少数民族弱势等等,还有汉民族主流文化的因素穿插在其间,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般还是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汉民族(主要是沿海城市)比他们先走一步的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带来的困惑,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西方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还是间接的威胁,但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终究还是会发生的,甚至以激烈的形态出现。纳张元是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将会面临一次新的更为鲜血淋漓的突变和飞跃,所以他一再紧张地呼吁,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固守传统的过时的文化因素,而是应该有严厉的自省态度来清理自身文化中不合时代的落后因素,要做好接受全球化时代更大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冲突和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裂变的关键时刻,也是有可能获得凤凰涅槃似的新的腾飞和发展〔4〕。
这就不能不讨论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长期统治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关系。因为在封建皇朝时代,汉民族文化一直以强势文化压迫、统治以及所谓“教化”少数民族,他们一直把少数民族文化视为未开化的“野蛮”文化,他们用儒家文明提升边缘地区的自然文化,这种强势文化沁透少数民族地区也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流文化中,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以此来约束、压抑甚至遮蔽了边缘的原始自然的文化因素。因此,似乎很难说有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化,它本身也包含了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主流因素,如果我们把汉民族儒家文化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文化从少数民族原始自然文化中剥离开去,也许会把许多文化现象看得更加透彻些。某些在时代进程被淘汰被冲击的传统文化因素,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健康部分,倒可能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封建教化。我渴望看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现文化冲突时有更加复杂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描绘。
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创作,究竟是一种本能的感情抒发,还是对民族文化的思考?纳张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和学者,他肩负着沉重的民族责任感,孜孜不倦地探索文学创作如何表现今天这个激变中的时代的文化现象,企图以形象的画面来保留某些本民族行将消亡的文化痕迹。这个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愿望,但是我还是要进一步提出问题: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在于表达作家的感情,情感是人的生命喷发的突破口,优秀的文学创作,可能表达了作家对民族文化处境的严肃思考,但这种思考结果本身不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只有作家找到了表达自己思考的生命形式以及表达的感情形式,才可能构成文学作品审美的基本因素。因此,时代与文化的问题不是作家思考的对象而是感受的内涵,生活中发生的故事你感受到了没有?有没有激发起你生命投射的激情?如何表达你的这种生命的感受,这才是考量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的文化基因是融化在其血液之中、生命之中,而不是外在于生命的东西,当他发现自身的文化基因在时代变异中丧失的时候,如果他感受到透彻心肺的疼痛那他就能表达痛惜文化流失的感情,如果他没有痛苦反而感到一身轻松,那他就能表达自身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感情,感情的世界不讨论是否正确,只讨论是否真实和是否强烈,这就是为什么老舍的《正红旗下》〔5〕、张承志的《心灵史》〔6〕和阿来的《尘埃落定》〔7〕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为什么杨丽萍《云南映象》能够呈现如此有生命力的肢体语言,因为这些文字和舞蹈里包孕了作家和舞者们鲜活的生命感受、鲜血奔流和脉搏跳动,以及他们感情世界里的大悲痛大欢喜大绝望,这不是什么文化因素的拼接和替代,而是发自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竭尽全力的呼喊。
纳张元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起一个有趣现象,1999年他在复旦大学进修时,我曾经为他举办过一次作品研讨会,在那个会上,“那些文学博士在发言中纷纷劝我:要回到你的民族中去,用你民族童年时代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后来,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著名作家格非曾有过一个下午的长谈,他却对我说:走出你的民族,忘记你的民族,你和你的作品属于全人类。我知道他们在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同一个问题,但相互沟通的连接点在哪里?至今我也没把这个问题想透。”其实这两种意见是一致的,张新颖教授他们的意思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不要总是思考自己民族文化的出路,要寻找生命中的个人记忆,要表达那种联系着你的生命因素的民族性,也就是表达你生命真正要表现的东西;而格非的意思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要总是去想自己对民族的责任和负担,直接表达你生命深处最想表达的感情,这样的东西是属于人类的。其实格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真正从你心底里流出来的,必定是与你的民族记忆相关的,所以不必要去特意地表现。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我们自然不要倡导作家刻意去写所谓的民族风情,但也不必要刻意去写有关民族未来出路的大叙事,两者都不是文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拉拉扯扯,我说了一些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想法,供纳张元和读者们作进一步探索的参考。其实纳张元是一位很成熟的作家、学者和教师,他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但长期生活在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云南大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更主要的是,他的多种身份使他有条件把各个岗位的工作结合起来:用创作实践经验来证明理论探索,用科研成果来充实教学实践,还可以利用高校教学体制来提高和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纳张元的这本论文集就是体现了他在创作、研究和教学等方面三位一体的独有成果。这本论文集的内容共分五辑,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二辑:觅迹寻踪。这辑收入纳张元的两类文章,一类是他对宾川鱼泡江沿岸彝族创世纪史诗《天地人》〔8〕的研究,对白族民间歌谣的研究,以及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追根溯源地探索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源头;另一类是探索大理学院教学制度如何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特点。我特别看重这两类的文章,因为追寻文化的源泉、经典的历史、歌谣的民间性等等,是确立一门文学学科最重要的基础工作;而把学术研究落实在教学体制之中,通过教育来保存文学经典,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文学发展途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当年孔子修订民歌,没有后人把诗经列为儒家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就根本不可能保存两千年以前的民间歌谣和文化经典。因此,我觉得纳张元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是全面展开、富有成效的。这本论文集可以成为一个见证。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纳张元.民族性与地域性〔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纳张元.信念坚守与梦想超越〔DB/OL〕.(2011-02-23)〔2011-04-20〕.http://www.cssn.cn/news/146261.htm.
〔4〕纳张元.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3辑〔M〕.昆明:民族出版社,2009.
〔5〕老舍.茶馆·正红旗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6〕张承志.心灵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7〕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纳张元.来自苍茫天地间的隔世之音:对宾川渔泡江沿岸彝族创世史诗“天地人”的一种解读〔DB/OL〕.(2009-12-23)〔2011-04-20〕.http://222.210.17.136/mzwz/news/8/ z_8_24388.html.
(责任编辑 党红梅)
Hailing for Yunnan Literature
CHEN Sihe
(Chinese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by NA Zhangyuan dialec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Minority writers,due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ir own,hav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raditional Han Chinese.The vitality of literary expression lies in the writer's emotion,and emotion is a breakthrough of the eruption of human life.Only by finding a writer's own form to express their thinking and feeling may it constitute the basic elements of aesthetic literary works.The cultural gene of a nation has been melted in the blood and life of a minority writer,rather than something external.In the world of feelings,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nsity of feelings rather than its correctness are discussed.
minority writer;cultural gene;life form;feeling expression
I207.9
A
1672-2345(2012)02-0001-04
2011-12-01
陈思和,教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院校教学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