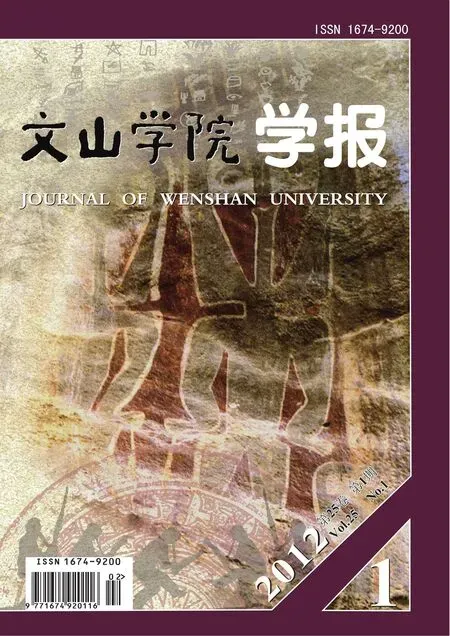中长时段视野下的边疆史研究
方 铁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是法国当代史学的主流,并对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兴趣,尤以总体史观和三维历史时间观的影响最大。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为真正的历史学,赋史料以生命,并使之成为真正历史学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1951年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出版。他提出“分析的历史哲学”,而与此前的“思辩的历史哲学”相对立,并在历史哲学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沃尔什认为历史学家的思维方法可称为综合方法,即“对一个事件,要追溯它和其他事件的内在联系,并从而为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 沃尔什对综合方法的定义,概括了总体史观的基本内核。[1](P224)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获得长足发展,在70年代达至鼎盛。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发展了总体史观并提出包括三种时间观念的长时段理论。他强调历史时间有不同的类别,大致可划分为结构(Structure)、局势(conjoncture)和事件(event)。这三种社会历史时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按照结构、局势和事件的顺序排列,并提出事件不过是“尘埃”,只有结构和局势的结合才能对历史给出最终解释。在其主要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应用长时段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叙述。[2](P244)在 20 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著作便产生于这一时期。
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我国学者做了如下归纳 :[3](P142)布罗代尔主张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这三种时段在历史运动中所处的层次、位置和作用各不相同。所谓长时段,指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等。长时段研究的是历史的结构,他称之为“几乎不动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历史对人与社会的制约最为显著。所谓中时段,是指时限较长时段短的某些历史因素,如人口增长、流通分析与国民产值等,中时段的时间约为数十年,可以用“态势”、“局势”和“周期”来叙述。短时段处于历史运动的表层,主要研究事件、现象和人物短期的活动。
长时段理论的提出,是历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将历史发展过程分解为不同的时段,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注重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给人们以积极的启示。同时应指出,布罗代尔关于三种时段重要性位置的排列有失偏颇。关于事件、现象和人物等短时段问题的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与前提,进行中长时段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复原基本史实及相关剖析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也认为,结构、局势和事件的排列顺序,是“该书(按: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2](P244)长时段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忽略了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在他的理论中明显被忽视;在叙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过分强调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的一面。
在我国史学界,中国边疆史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包括民族史、地区史在内的专门史,以及历史地理学中的人文历史地理,较早研究中国边疆史方面的问题,并取得受到推崇的成绩。与断代史相比,边疆专门史较注重历史的横向联系与纵向发展,注意历史过程的动态改变及其线索,关注边疆与内地、边疆与邻邦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边疆专门史还注意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边疆专门史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研究缺少全国或总体上的视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尽如人意等。中国历史地理学,大致有研究地理学中与历史相关部分的学科,以及探讨历史学中与地理有关部分的学科两种定位,或者说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4](P2)因此,历史地理学兼采历史学与地理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并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有所侧重。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特点,是擅长从整体观、发展观、运动观与比较观的角度考察历史。由于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地理学均较重视贯通时段的研究,亦较注意研究对象与相关领域及相关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致使在中国边疆史的某些领域,研究者较多采用源自长时段理论的中长时段研究方法,相关的研究也较明显地体现出总体史观。
近年尝试用中长时段方法探讨中国边疆史,大致可列举以下的研究为代表:
其一,边疆观念史与边疆治理史。前者主要指历代治理边疆的观念、思想与方略,后者大致包括历代治边的政策、措施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历代治边虽各有特点,但诸如“内华夏外夷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与“欲绥远者必先安近”等治边的思想或方略,历代在边疆置郡县、开通道、移民及屯田等举措,以及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都经历了上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而非某一王朝所独有。
如传统治边观。早在先秦时期,诸侯国政治家便提出“五服”说或“九服”说。①对《禹贡》的“五服”说以及《周礼》之“九服”说,历代方家的理解大体一致,即认为其言提出以王畿为国家的中心,统治由近及远推向四方,对不同地区的管理及这些地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亦由近及远而逐渐削弱。两汉接受先秦“五服”说或“九服”说的内核,同时总结汉代治边的经验,进而形成“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的思想,尤以班固所言最具代表性。②班固认为华夏与夷狄有山谷或大漠隔绝,不可随意扰乱。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面兽心”,其章服、习俗、饮食、言语异于华夏;夷狄之地取之不可耕,夷狄之民臣而不可牧,封建王朝应区分诸夏与夷狄的界限,做到内外有别;进而提出对夷狄应施治有度,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与夷狄交往应“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若夷狄慕义贡献,王朝须待之以礼,有争端则“使曲在彼”。若能如此,可羁縻夷狄而不绝,最终达致强国安边的目的。汉代以降,“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成为大多数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体系的核心。治边方面的下述思想或方略,便大致是从“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发展而来:“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5](卷一九三P6067)“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6](卷三○P678)朝廷对四夷应怀之以德,服之以威,“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7](卷七)“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8](卷三七七)可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思想在古代影响之深远。
又如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历朝治边大都有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情形。秦汉时便有重北轻南的倾向,以后逐渐形成重要的治边传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於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9](卷三〇P831)唐代房玄龄亦言 :“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10](卷九P486)两宋重北轻南的倾向更为明显,王象之云:“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11](卷一)《元史·地理一》总结历代边患说:“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12](卷五八P1345)明朝治边仍以北方为重点,重视防守漠北的蒙元后裔鞑靼及瓦剌诸部。朱元璋立国后分封二十四子,将之遣往各地协助统治,其中不少镇守北疆。在诸统一王朝中,仅有元清两朝的重北轻南倾向不甚显明,主要是因北部草原为元朝的发源地与根据地;清朝通过联姻与蒙古诸部交往密切,一定程度缓解了来自北部草原的压力。
重北轻南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历朝治边。历代驻兵、屯田的重点多在北方,经营南部边疆的规模相对要小得多。在历朝的正史与奏疏中,对北部边疆的治策探讨较多,针对南部边疆的则明显减少,一些重要的治边方略,便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总结而来。如东汉班固说:“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13](卷四〇下P1374)唐凉州都督李大亮总结朝廷对突厥的政策,认为内地与边疆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不可摇根本以厚枝叶。③唐朝实行“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的治策,亦主要是来自应对北方夷狄的经验。④由于防守的重点在北方,元明以前历朝经营南部边疆均不甚积极。至元清两朝,由于缓解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因此加强对南部边疆的经营。
至于封建王朝治理边疆的政策,也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过程。以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进为例。据研究,[14]秦汉至唐宋历代王朝的边疆少数民族治策,通常被称为“羁縻之制”。“羁縻”的本意,言朝廷若掌握马之“羁”(笼头),牛之“縻”(鼻绳),便能有效控制少数民族而又较宽松随意,“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15]羁縻之制是历朝经营边疆的一项重要创造。但羁縻之制也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朝廷对边疆少数民族重在羁縻而约束不足,管理较随意且缺少制度化规定,同时在全国普遍推行大致相同的治策,并无南北方等区域性的差异,由此反映出羁縻之制尚不完备。
元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由于具备以下新的特点,而与羁縻之制有较大区别:朝廷任命少数民族首领出任的土官,为国家的正式官吏,不可随意废除,但可世袭;朝廷在边疆设立军事统制机构宣慰司,并广泛任用土官为边疆地区州县以及宣慰使司及所属机构的长官;土官有相当大的权力,其权力为朝廷所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土官可统辖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土军,朝廷有调用土军出征之权;土官接受朝廷相对规范的管理,并缴纳一定的赋税,还承担其他义务。元朝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官制度,还具备施行范围较广、推行力度较大以及成效显著等特点。
土官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能成功推行,与当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关。南部边疆多山且地形复杂,气候类型亦复杂多样。不同高度的地区其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相异,居住不同高度地区的居民,对特定生态环境及其动植物资源有明显的依赖关系。在共同族源基础上形成的大小村落,又以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为纽带,结成更大的势力并相互依存。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生存及其相应活动,以相对稳定占有土地、山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依附于斯的人口为前提。南部边疆少数民族众多,内部结构复杂,他们既杂居共处、相互依存,为争夺土地、水源、山林与矿藏等资源,以及因复杂的历史纠葛又常结仇并长期争斗。另一方面,各地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不同派别之间,又存在经济上的互补共生关系,以及家族与社会方面的复杂联系,因此,当地社会形成了内部矛盾尖锐突出、需时常调整以维持平衡的特点。
土官制度的实质,是朝廷承认各级土官占有土地等资源的合法性,同时根据土官忠诚与否,决定是否收回其资源占有的权力,从而掌握了干预其内部争斗及左右平衡的钥匙,并减少了因争夺土地等资源而发生的争端,为稳定土官地区的统治提供了制度化保证。土官制度的施行,也因此受到南方少数民族的普遍拥护。《明史·土司传》正确指出土司制度的特点:“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6](卷三一〇P7981)当然,对土官制度的内在机理,蒙元统治者尚不可能有深刻认识;但土官制度适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施行亦属有效,乃被确定为可行制度并予推广。
为加强对主要对手汉人的统治,元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较为信任,对各级土官堪称宽容。元代前期统治机构官僚化的弊病尚不明显,根据具体情形较为灵活地选择政策,推行各类治策亦较为快速且彻底,这些都促使土官制度取得较大的效果。凭借土官制度,元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明显深入,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土官制度的实行,还在土官地区真正实现了历朝梦寐以求的“以夷制夷”。元代以前历朝的“以夷制夷”,施行对象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做法多属利用各政治势力间的矛盾,使之离心相攻而从中渔利。但朝廷支持的某一政治势力,可能在敌方衰落后迅速转变为支持者的新对头。如南宋先后与金、蒙古联手对付宿敌,最后在政治博弈中吃了大亏。至于凭借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土军镇压其他少数民族,在元代以前十分罕见。历朝虽招募夷兵,但大都属于雇佣兵或将之混合编入军队,少见单独组成土军并形成相应制度的记载。土官制度则使元朝统治者能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使之相互监督和牵制,并有效干预各派势力的平衡。在少数民族内部为争夺资源占有与官职继承等的争斗中,封建王朝可坐观成败,而不至于惹火烧身。朝廷支持少数民族的方式,也由过去公开为某些政治势力撑腰,改变为以土官职位及其合法承继为诱饵,驱使少数民族为之尽忠奔走。至于朝廷调用土军镇压其他少数民族,由于涂上维护封建统治合法性的色彩,更易取得“以夷制夷”的效果。
另一方面,推行土官制度抑或导致土官坐大,朝廷因此鞭长莫及,此即明清两朝在一些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至于在北方草原等边疆地区,因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与南部边疆有异,元朝大致沿用适合游牧生活的万户制度,由此开创了封建王朝统治边疆的治策南北有别的时期。明清两代沿袭元制,将土官制度发展为堪称完善的土司制度,使中央政府对南部边疆的控制更为深入;清朝针对不同边疆地区分别施行的治策,在元明经营的基础上亦更趋成熟。
其二,边疆经营史与边疆开发史。近年在该领域尝试应用中长时段方法的研究,大致体现在历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经历由低潮至高潮的过程,以及这一地区经济门类的重心相应发生改变等方面。
就经营的规模与深入的程度而言,历朝经营主要包括今云贵两省和川西南的西南边疆地区,大致可分为秦汉至宋以及元至清两个差异较大的时期,其中以元代为改变的契机。在前一时期,封建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设置郡县、开通道路及向郡县治地少量移民等方面。但统治的有效性仍较有限,原因是受到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影响,也由于西南边疆偏僻落后及自然资源尚待开发,历朝遂将西南边疆归入四川大行政区管辖,并基本上不在这一地区收取赋税。西汉武帝时,在番禺以西至蜀地以南的区域置17初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7](卷三〇P1440)唐神功元年(697 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上书请罢姚州(治今云南姚安),理由是“(姚州)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于戎行,宝货之资不输于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少数民族”。[18](卷九一P2940)张柬之所说的情形较为普遍。出自朝廷施治不善与边疆民族崛起等方面的原因,云南出现南诏、大理国500余年的地方割据。南诏、大理国实现了云南地区的局部统一,推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创造了条件。
元明清是西南边疆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但各朝的情形又不尽相同。云南为忽必烈所率兵平定,亦出自以云南为基地用兵邻国的考虑,忽必烈十分重视云南。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子云南王忽哥赤出镇,忽必烈面谕之:“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其善抚吏民。”[19](卷七六P510)在老臣赛典赤·赡思丁的主持下,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大力推行增州县、设官府、开驿道与置屯田等治理措施,并在各地征收秋税和夏税,在边远地区则按人口或住房之数征收金银。[20]《元史·地理一》亦言:“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2](卷五八P1345)元代之前,历代王朝经营边疆主要由国库出资,致使治边的成本极高,而收效十分有限,这是历代议论开边得失颇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元朝重视经营边疆并实质性收取赋税,既减轻朝廷的经济负担,亦开明清两代汲取边疆资源以裨国用的先河,同时对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促进的作用。
元朝将云南行省的治地置于今昆明,使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滇西移至滇东。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开通由今昆明经贵阳达镇远入湖南、连接沅陵以东“常行站道”的驿道,⑤致使今云南与四川间的旧道逐渐衰废,今贵州的腹心区域则自黔北移至黔中。《元史·地理六》说:“贵州(治今贵阳)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12](卷六三P1536)滇东和黔中一带因有多条驿道经过,亦逐渐成为人丁辐凑、经济繁荣的地区。为保护经今贵州中部的重要驿道,也因今云贵两地脱离四川的行政管辖已成定势,明朝建立贵州省,形成今西南地区滇、黔、川三省鼎足而立的格局。
明朝将积极开发的地区,延伸至云南南部以及贵州的其他地区。太祖朱元璋认为云南诸夷叛服不常,原因是“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⑥因此在云南等地大量驻兵。明代卫所制度允许军人携带家眷,大量军户便以卫所驻守的形式移居各地,并在居住地屯田自给,乃形成较大规模的垦种营农高潮。至今西南边疆尚有为数不少的营、屯、卫、所一类地名,便是明代卫所的遗留。《明史·沐英传》言沐英镇守云南时垦田至100万余亩。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子沐春袭职;沐春镇滇7年辟田30余万亩。《明会典》说云南都司有屯田110万余亩,粮38万余石,⑦可与《明史》谓沐英时云南垦田达100余万亩的记载印证,至此云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至空前的规模。贵州、广西的农业也有很大进步。但明代西南边疆的农业生产,仍以传统的农业地区为基础,而与清朝加强对边疆、僻地和山区的开发有所区别。
清朝统一全国后,内地人口急剧增加,至乾隆时形成人口高峰,大量流民遂迁入人口稀少地区以谋生路。清廷虽颁令禁止流徙,但实际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减税、贷给种籽、准为永业等为优惠条件,招徕流民至边疆及僻地垦荒。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户部许之。⑧由于盆地和交通沿线地区人口密集,外来移民主要移居西南边疆的边地、山区与僻地,形成西南边疆新一轮的经济开发浪潮。嘉庆重修《清一统志》记载康熙末年云南各府厅的人口数,⑨以今大理、昆明、建水、保山、曲靖和楚雄等较大盆地的人口最为密集。嘉庆年间,若按人口数量的多寡排列,云南各府厅的顺序发生变化,在排序中位置前移的府厅大都在山区或边远地区,说明这些地区发展的速度很快。贵州、广西也有类似的情形。
西南边疆古代的社会经济,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矿冶业、交通业、商业与家庭手工业等门类。在不同的时期,历代经营经济门类的重点有所改变,古代前后期的差别亦较明显。
西汉数度经营西南夷(指今云贵两省与川西地区),缘由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僰道(治今宜宾)沿牂柯江(今北盘江)达番禺(治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由蜀地经西南夷、身毒(今印度)达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邦交通道。[17](卷一一六P2994,2996)西汉在西南夷数次设置郡县,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保护通道的安全,由于武帝设治的决心动摇不定,出现过既置复撤、其后又复置郡县的情形。[17](卷一一六P2995,2997)唐朝亦极为重视经过云南通往邻邦的通道。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遣梁建方率兵平定松外蛮,缘由是为复通过今滇西至天竺的道路。永徽二年(651年),郎州白水蛮(在今昆明至大理一带)反,唐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率兵征讨破之,主要也是为了保护上述道路。唐朝在今滇东北和滇中的统治巩固后,将势力扩展至今滇西一带,亦寓保护经滇西至天竺道路的用意。天宝间唐朝丧失对云南地区的控制,起因便是唐朝实施打通由交州经今滇中、滇东北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道路的计划,导致地方势力爨氏大姓反叛,毁道路所经之安宁城。唐朝令南诏前往平叛,致使南诏势力坐大,最终与唐朝决裂。⑩
汉至唐前期西南边疆的种植业有所发展,但范围大都限于郡县治地及附近地区。由此可见,在封建王朝统治的前半期,边疆地区的通道(尤其是经过边疆的邦交通道)以及较小范围的种植业,是当时经营的重点,而矿冶业、商业等经济门类,以及大部分地区的种植业则较落后。
元朝在西南边疆广为设治,积极拓建驿道、清查人口、开采矿藏和征收赋税。发展交通是元朝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最大成就。如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有马2345匹、牛30只、船24艘。⑪而实有驿站尚不止此数。云南行省的道路以省治为中心,以今大理、楚雄、西昌、昭通、曲靖、通海、景洪、保山、丽江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形成贯通全省的交通网络,并有驿道通往今缅甸、越南等国。元朝在全国广开屯田,“以资军饷”。云南、八番、海南、海北等地因是“少数民族腹心”,尤“设兵屯旅以控扼之”。[12](卷一〇〇P2558)云南行省辖中庆路军民屯等10余处军民屯田,垦田71667双及 1250 顷,约合 483335亩。[12](卷一〇〇P2575,卷六一P1458)另据《元史·食货二》: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等15处产金,威楚、大理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中庆、大理等处产铁。[12](卷九四P2377)贵州、广西的情形与云南相去不远。元朝在西南边疆经营的重点,似可按交通、农业、矿冶业、商业的顺序排列;尤以省内交通业最为发达,农业、矿冶业与商业发展的水平,较此后的明清两代仍有较明显差距。
明清两代西南边疆各省新开的道路不多,但道路的管理与运作进一步改善。明朝在传统农业地区大兴屯田,伴随农业的进步,马牛猪等大牲畜的饲养业十分发达。明廷还扩大对金银铁铜铅锌及宝石的开采。云南矿税之重屡见于边吏奏疏。⑫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奏:国家最重之征,“莫过云南输金一事”。[21](卷一一八,卷二五〇,卷四二四)但明朝大量搜刮云南等地的金银和宝石,有一部分是为满足皇帝的私欲,这一点与清朝在云南大量开采铜银以供各地铸币不同。明朝还在贵州、云南等地大量采伐巨大原木,以满足宫廷建设需要。采木较集中的时间前后达90余年。清朝在西南边疆努力发展农业,目的之一是为征收农业税。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确定各省常平仓岁储粮额,云南、贵州分别为70万石与50万石;三十一年(1766年)各省报存粮之数,云南与贵州均为80余万石,广西为 183 万石。[22](卷一二一P3558)清朝则大量开采云南的铜和银,作为京城乃至长江以南数省铸造钱币的原料,《清史·食货五》称全国多省产铜,“而滇最饶,”“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22](卷一二四P3666)明清两代西南边疆主要的经济门类,得到较均衡的发展,并可按照有色金属采冶、种植业、畜牧业、交通业、商业(包括玉石与原木的供应)的顺序排列。
尝试用中长时段方法进行研究,还表现在边疆民族关系史方面。有研究者认为,⑬西南边疆的居民包括土著民族与外来移民,早期移民主要居于郡县治地所在之大中盆地,土著民族与之杂居并在其他地区广为散布。早期移民因势力单薄而逐渐被土著民族融合,形成白蛮等新的民族,唐宋时以白蛮为主建立南诏、大理国。明清时外来移民大量进入,乃融合白蛮、僮等民族的一些人口形成各农业地区的汉族,并在当地占据主导的地位。盆地边缘及盆地以外的广大区域,则主要为各土著民族所居。清代一些内地移民移居边疆、山地和僻地,促进与当地土著民族的融合,乃形成近代西南边疆各民族分布的格局。
近年就以上问题进行的探讨,初步揭示了一些深层的因素和内在的关联,表明合理应用中长时段方法,可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开阔,研究亦得以深入,为推进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有效的新方法。
注释:
① 《尚书·禹贡》篇:“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撰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所言“九服”,与《尚书·禹贡》之“五服”说大同小异。
②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赞》:“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少数民族之常道也。”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833页。
③ 《贞观政要》卷九《议征伐》,李大亮言:“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第503页。
④ (唐)狄仁杰:“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实绥边之故事。”,《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1726页。
⑤ (明)《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二十二·勘·站·站赤三》,《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二十二·勘·站·站赤四》,引(元)《经世大典》,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⑥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四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条,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⑦ 《明史》卷一二六,第3759页。(明)《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万历刻本。
⑧ (清)《圣祖实录》卷一,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条,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⑨ (清)《一统志》卷四七五至卷四九八,嘉庆重修本。
⑩ 《南诏德化碑》,碑文见汪宁生著:《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⑪ (明)《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二二勘·站·站赤八》,引(元)《经世大典》。
⑫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第1971页。
⑬ 参见尤中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4页;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8页;方铁:《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 何兆武.沃尔什和历史哲学[A].[英]沃尔什,著.何兆武,等.译.历史哲学导论·附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A].[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等.译.论历史·附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徐浩,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 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地理论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1980.
[7](明)桂彦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条[A].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刻本.
[8](清)高宗实录[Z].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9] 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 (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Z].清抄本.
[12] 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 方铁.论元朝的土官制度[A].方铁,等.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90华诞庆祝会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5](东汉)卫宏.汉官仪[Z].四部备要本.
[16]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 蒙兀儿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20] 方铁.元代云南行省的农业与农业赋税[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4):57-64.
[21](明)神宗万历实录[Z].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22]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