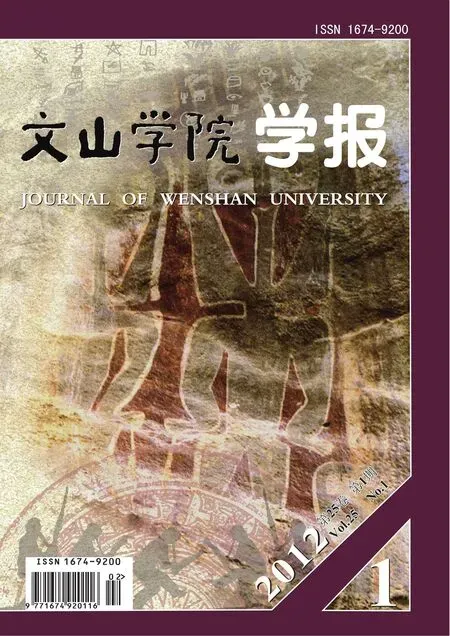壮族麽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
黄懿陆
(云南省政协 民族宗教委员会,云南 昆明 650028)
广西壮学会整理出来的《布洛陀经诗》,于1991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原始版本流传于我国广西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龙江流域,左江流域及云贵南、北盘江流域的广大壮语地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是,“布洛陀”并非一个抽象的人文始祖神祇,而是一个具象者。有学者研究, “布洛陀”有四解:一为“山里的头人”;二为“山里的老人”;三为“鸟的首领”;四为“无事不知的老人”。[1](P85)查找文献资料、研究考古文物得知,“布洛”,即汉语中的“鸟人”,与“鸟的首领”吻合,其他三说仅有壮语言学方面的依据。此外,“陀”还有“从天而降”的意思。笔者所理解的“布洛陀”,亦即“由天而降、来到地上普渡众生崇鸟族群的神祇”。
一、文献古籍中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
(一)越王与鸟文化
一般地说,尊鸟崇鸟是稻作文化的产物。先秦史籍《山海经》,早就有了关于“羽民”的记载。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嚥蹀嚥蹀,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吴越春秋》中的这段记载讲了三层意思:
1.讲述了百越之王——禹崩之后的事:说是大禹治水之后,泱泱九洲之地恢复了生机,农业生产随即转入正常。既然是人类能够控制水患,自然有了很多的农田。由于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农田耕种不过来,上天就派了很多鸟来帮助人民耕田。人民对大禹治水的功劳念念不忘,大夏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也就是禹的儿子启颁布诏书,建立了禹王庙,要求百越民族每年春种秋收之际,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仪式纪念大禹。
2.大夏王朝从启开始,传到少康已是第六代。每年祭祀大禹的活动都是中原的夏王直接对百越民族进行安排和指挥,少康担心越地祭祀大禹的活动不能持续下去,就派了小儿子无余到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去当越王,专门主持祭祀大禹的仪式。这个时期,从大禹时代开始的鸟田耕种一直没有中断,代代相传。
3.从无余开始,越王传了十几代,最末一代没有能力,祭祀大禹的活动于是就停止了。在百越民族中有一个能人挺身而出作“鸟禽呼”,自告奋勇为民请命,因而得到了百越民族的拥戴,成了第一个纯百越民族血缘的越王。于是,人民又恢复了夏代开国时的“禹祭”,“安集鸟田之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无论谁为越王,都要“安集鸟田之瑞”。也就是说,百越民族有云集“鸟田”、期盼百鸟耕耘“鸟田”、祭祀鸟神、崇拜鸟神的传统。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二十五别史》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下有群鸟耘田也。’《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皇览》曰:‘禹冢在会稽山上’。”《吴越春秋》是东汉人赵晔的著作,至少可以说明,百越民族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崇尚鸟神,农耕时节寄希望于“布洛陀”来到人间。从中可以看出,那时人们的耕作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低,与其说是请鸟助人耕田,不如说是惧怕漫天鸟类吃掉人民为数不多的稻谷,希望鸟类是人类的朋友,甚至于宁愿把它们当作神灵崇拜供奉,其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收成不减。由是,越人的鸟神崇拜油然而生,代代相传。
其上文献所说的“鸟田”,是汉人说汉语。如果依百越民族的发音,“鸟田”之“鸟”的汉语注音,应写为“洛”。杨孚撰《异物志》引《交州外域记》说:“昔交趾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曰‘骆田’。”根据其上文献史料,所谓“骆田”,其实就是越人语言与汉语的混称。其“骆”为百越民族语言“鸟”的发音:“田”即汉语发音;“骆田”则“鸟田”。《交州外域记》之“骆”,亦即“布洛陀”之“洛”的同音异写。
(二)鸟神帮助越人建国
从抽象的角度看,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春秋时期的吴、越,就是以越人为主体建立的国家。
百越民族崇鸟、尊鸟、信鸟,自称“大越鸟语之人”。《吴越春秋》中继承越王事业者,不也是作“鸟禽呼”吗!由于越人崇鸟,于是,所种之田被称为“鸟田”,所说之话被称为“鸟语”,所写之字被称为“鸟书”,就连越王的模样也是“长颈鸟喙”。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被称为“长颈鸟喙”的模样,说明外人也知道越人崇鸟,所以描写越王长得像鸟一样。古代传说,越王勾践复国曾经得到鸟神的帮助。王嘉《拾遗记》载:“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陶元藻、凫亭撰《广会稽风俗赋》亦称:“越王入吴时,有鸟夹王而飞,以为瑞也,因筑鸟台。”这里,“鸟夹王而飞”,指的就是从天而降的“布洛陀”神祇。究其内涵,讲的就是越人集团使用了鸡卦巫术,能掐会算,从而能够趋吉避凶,取得战争的胜利。198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壮族文学史》,就认为“布洛陀”是壮族人民“鸟的首领”。而作为壮族“鸟的首领”崇拜的传说,早在东晋时期,就见诸于文献记录了。百越民族视鸟如祖,祭拜布洛陀人文始祖,最早的文字记载,盖源于此。
自古以来,鸟神一直是越人逢凶化吉的神祇。《吴越备史》卷一载: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越州董昌称帝时,“有客使倪德儒语昌曰:‘中和辰己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
1.“罗平鸟”之“罗平”。所谓“罗平”,其实是越人语言,而非汉语。其“罗”即“布洛陀”之“洛”的同音异写;而“平”则百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语言“飞”的发音。壮语倒装,汉语“罗平”则百越民族后裔之一壮族语言中的“飞鸟”也。《吴越备史》中的“罗平鸟”,即王嘉《拾遗记》,陶元藻、凫亭撰《广会稽风俗赋》中支持越王建国“夹王而飞”的“飞鸟”。《吴越备史》反映越州董昌欲建国称帝,借助越人的神话传说来做发动群众的准备工作,认为董昌的举事,一定会像当年的越王勾践得到飞鸟之神的帮助而获得成功。由此看来,在吴越之地支持董昌的基础力量多是越人,方才借助了越人崇拜的鸟神作为国名。由此可以知道,这是文献上出现明确以布洛陀文化建立的越人国家之后,第二个以布洛陀文化维系民心取得胜利的政权。
2.越人中流传有《圣经》。试问,在百越人民当中有什么可以称为《圣经》呢?所谓《圣经》,非《布洛陀经诗》莫属。文献记载说明:《布洛陀经诗》在百越人民中流传甚广,并且为与之杂居的汉族人民所接受。同时,亦可证明壮族发明的“土俗字”也就是“古壮字”已应用于抄写经书。他们抄写的经书,被唐代越人居住区的汉民族视为《圣经》。这部见诸唐代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布洛陀经诗》。其占卜威力巨大,信众极多,乃至居住在越人地域的汉人利用越人的宗教信仰聚众造反。自唐代越州董昌利用越人《圣经》(《布洛陀经诗》)称帝,建立“大越罗平国”,农民起义首领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元朝大德年间(1297年),“平阳陈空崖同嫂苏锦娘反,又建罗平旗号”[2](P42,44),可见越人的鸟神崇拜在汉族人民中间影响至深,乃至他们接二连三地利用越人的宗教信仰发动起义。其起义的旗帜图像为鸟,举事者的签名亦“与当时鸟状相类”,表明鸟篆文也是鸟崇拜的表现形式,说明鸟或鸡卦占卜深入人心,造反者不得不以鸡卦占卜作为改朝换代的推演工具。由此推及出土文物中,越人把自己当成鸟神的后裔,摹仿鸟的模样,把自己装扮成“羽人”,以表示自己是鸟神的后裔,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在百越地区出土的铜鼓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壮族先民模仿鸟人(羽人)的形象。
(三)鸟神是越巫之祖
鸟神不仅是百越民族建国的救星,而且是百越民族通天之灵巫,通晓世间万物的始祖。晋朝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越地深山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冶鸟’。”“此鸟白日见其形,是鸟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有观乐者,便作人形,长三尺,至涧中取石蟹,就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显然,百越民族不仅视鸟为神祇,而且把鸟视为越祝之祖。其之所以是越祝(巫)之祖,乃是指越巫使用了鸟或鸡卦的占卜方法。鸡卦起源于鸟卦,后来在越人当中发展传世的“鸡卜”,是布洛陀文化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看过《山海经》的学者都知道,里面有一句令学术界困惑不解的话:“使四鸟,虎豹熊罴。”这句话揭示了什么内涵,代表什么意思?至今无人确解。其实,它和“布洛陀”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以鸡卦巫术为信仰图腾的“虎豹熊罴”民族共享布洛陀文化的一种文献证据。研究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红山文化等地遗址出土的相关文物之后,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从鸟卦到鸡卦占卜文物的解密,就是打开“布洛陀”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
众所周知,只读一部《易经》,并不可能占卜。同样的道理,把一部《布洛陀经诗》背得滚瓜烂熟,也不可能指导人们如何进行占卜,预知天下大事,明辨古往今来。《布洛陀经诗》没有具体的筮法,就不可能预知如何趋吉避凶,从而引导勾践建立越国,乃至号召广泛民众,帮助董其昌建立高高飘扬着“飞鸟”画像的“罗平国”。所以,研究《布洛陀经诗》,不可能不研究《布洛陀经诗》特有的占筮文化,寻找《布洛陀经诗》的真正筮法。
二、考古学上的布洛陀文化
笔者的研究认为,研究寻找《布洛陀经诗》的占筮方法,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中国号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排列顺序分别为:古巴比伦文明,出现于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古印度文明,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古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2070年。彼此之间,间隔500年;中国的文明以夏代的建立为起点。但是,国际学术界并不同意中国自己的说法,一概把殷墟出现的甲骨文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凭据,公认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也就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殷墟甲骨文时期。换言之,国际学术界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始于殷商。考古证实,百越语言在商代后期趋弱,逐渐被先汉语言挤出主体文化圈。
在代表中国文明起源最高成就的殷墟,百越民族布洛陀文化的考古证据见于卜辞及其卜甲。换言之,壮族先民的布洛陀文化,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很明确了。主要依据如下:
(一)语言学方面的证据
东汉《说文解字》中有一个“秏”字,著者许慎解释说:“秏,稻属。从禾,毛声。伊尹秏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在这里,“秏”是表音文字,义为“饭之美者”。伊尹是商朝的有功之臣,在其言中伊尹仍含有表音文字,称“饭”为“秏”,正是如今百越民族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对饭的表音。有学者认为“南海之秏”即“岭南之秏”,表明“商汤时代南北交通更加便利,西南、东南诸族已向商朝有所进贡,许多农作物随着民族的交流传入黄河流域,稻谷可能在此时传入商地,而稻谷的语音‘秏’也因此流入中原”[3](P10)。我们认为,商汤时代,恰恰正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交织、碰撞的时期,汉语的“禾”与百越语言“秏”的共用,就是证明。在伊尹说这些话的时代,说“禾”或“秏”,可能都不需要解释,说者心知肚明,听者亦如此。说明商代的主流语言有可能是吴越民族的语言。
(二)甲骨文上出现越人的记载
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殷代的“西戉(越)”》一文中指出:“殷卜辞中有关戉之刻辞,见于《类篆》页940~942。戉又称戉方(仅见于《合集》
29648 )。晚期卜辞有‘西戉’一名。” [4](P1)
乙丑,王……伐西戉……余其比……示余受[出祐](《合集》36532)
他若7隐若7100云:
……自西戉……
根据卜辞上述记载,饶宗颐先生认为“殷时有西戉断然无疑”。而且,“殷时已有西戉,戉人足迹于西北,由来已久……先秦以来,戉人足迹,拓殖甚广,分布几乎远至域外”[3](P10)。
(三)戉人是进行巫术占卜的主体
甲骨文出现戉人为巫术占卜主体的记载。《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列举了戉人进行巫术占卜的甲骨文资料:
“贞,戉不其来”。
“贞,戉获羌”。
“贞,戉不其获羌”。[5](P57)
以上甲骨文记载了和“戉”这个部族有关的占卜活动。想必越人是这些卜骨筮辞占卜的主体。
(四)氐羌人是商族祭杀的对象
甲骨文既然出现以越人为主体的卜辞,显然他们是占卜集团的主体民族,独揽着“巫师和巫术独占二者之间的沟通权”。据统计,甲骨文出现被斩杀者约有万人,多数是氐羌人。卜辞告诉我们,越人捕获了氐羌人;同时,卜辞还告诉我们,氐羌人是商人集团斩杀祭祀的对象,甲骨文上曾出现商族一次杀掉1000人的记录。在征得上苍的同意之后,商族对征伐而得的氐羌人战俘和奴隶大开杀戒。[6](P67-74)《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是一个崇鸟民族,越族也是崇鸟民族,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越祝使用鸡卦占卜时,以氐羌人作为祭杀对象,可见越人集团是殷商时期的主体民族。
(五)殷墟卜甲上发现鸡卦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肖南先生在《考古》第一期发表《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提到一片卜甲正中有“九”、“六”二字,这两个字上有“”的符号和“九”、“六”并列”。 认为,“九”、“六”就是《易经》的代表数字,因为易学又叫“九六”之学,因此,这对符号被认为是与《易经》联系最为紧密的符号,“很可能是表示‘易’之重卦的一种特殊符号”[7],它“把《周易》中最基本的数字符号和概念以及占卜方式等都体现出来了”。[8](P46)
第二,合作社法人说。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坚持的价值取向及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分析,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更接近合作社法人,应从法律上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合作社法人地位。
《史记·孝武帝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敬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这种“越祠鸡卜”,至今仍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使用和流传。
鸡卜这种筮法始自新石器文化时期,持续数千乃至万年,一直没有改变。到了晚商时期,还在使用。最早见到的是在江苏省海安县青墩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骨角。骨角上刻有“数字符号,即‘463353’、‘135326’。如果我们依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之转换成卦画,这两组数字分别是遯卦……和大壮卦……”。[9](P15)
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的研究证明,易经符号卦是在数字易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让学术界困惑不解的是,数字易卦建立在什么具象基础之上?殷墟卜甲上出现了许多数字易卦。鸡卦本身是一种筮法,鸡卦象与数字易卦同时出现在殷墟卜甲上,表明数字易卦来自鸡卦筮法。其中,它们可以分别组合成易经中的乾坤两个经卦。
(六)百越民族退出主体文化圈的证据
《殷墟文化研究》介绍,“江南百越民族文化分布区是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发源地”,“在殷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印纹陶和原始瓷,其中印纹陶出现较早,在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遗存中均有发现”。这种包含着鲜明的百越民族特征的“器形种类数量较少,仅有罐、豆、壶、器盖等五六种”。[10](P206-207)考古出土文物告诉我们,越文化在殷商时代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仍然有一席之地;与商族使用“越祠鸡卜”巫术占卜的巨大作用显然不能成正比。他们以巫师和巫术在商王朝中拥有着唯我独尊“绝天地通”的沟通权。
根据殷墟一、二、三、四期均有越文化出现的事实,笔者认为:可能属于上古语言的百越语言在商代后期出现趋弱现象,逐渐被先汉语言挤出了主体文化圈。商族先王时期,也就是商汤之前,商族先王有报乙、报丙、报丁三位“报”称之王;商汤到盘庚的商朝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有祖乙、祖辛、祖丁三位“祖”称之王。其实,“报”称之王是百越民族语言,等同于“布洛陀”之“布”的近音。称之“报”,其义为“祖”;甲骨文中颇多“帚”和“妇”之记载,笔者认为,“卜辞中的‘帚’就是‘妇女’之‘妇’字”。“帚”字的发音是百越民族语言,“妇女”之“妇”是“帚”字的汉译。也就是说,“帚”是表音文字,“妇”是表义文字。这就说明,商代时期,确实是百越民族语言处于一个与先汉语言发生碰撞,二者之间产生分离的时期。换言之,是百越民族及其后裔保留了上古时期的主体语言。[11](P225-235)可见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先汉民族已占有绝对优势,百越民族讲述的语言或者说“上古汉语”正在退出主体文化圈。
三、探索筮法,才能知道布洛陀文化的真相
(一)百越民族绚丽多彩的鸟神文化
仿鸟态的人,故称羽人、或羽民。这是我国南方先民在鸟图腾崇拜延续和深化中一种人鸟合一化的文化现象。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痕迹,从出土文物看,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6000年至7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江苏省吴县草鞋山出土良渚文化陶壶(草M198II)上的鸟纹饰,都可以看见鸟纹样饰十分广泛。1984年,江苏省丹徒母子墩墓出土的鸳鸯形尊和飞鸟盖双耳壶,可说是鸟饰造形传统文化承袭的典范。[2](P42,44)至今出土的许多越王刀剑,都刻有“鸟篆纹”,这也是越人崇鸟,尊鸟为神的印记。在农作活动中,越人希望得到鸟神的护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在军事行动中,越人希望像鸟一样兵贵神速,来无踪,去无影,常胜不衰;在日常生活中,越人亦希望鸟神能够“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
石寨山型铜鼓上有“羽人”形象。在晋宁石寨山M2:1号铜鼓面所见的23个羽人,为首者髻插羽毛,腰佩利剑,主持礼仪祭祀。其后羽人皆头饰羽毛,髻后缀以翼形羽饰,一手执折羽,一手作鸟飞翔状,整个画面仿佛一幅群鸟飞翔图,蕴藉着百越民族与鸟同类的情愫。在广西左江流域的许多岩画中,往往可以见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心人物,或腰佩刀剑,或手抓小人(俘虏)。在这些图像中,惟有此人头戴羽饰或羽冠。《壮族图腾考》说:“据统计,当地数百个岩画点的人物形象中,95%以上的人为剪发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为部落的首领或巫觋一类人中,头上才出现羽饰或牛角饰物。这些羽饰不仅为图腾崇拜的象征,更是某种特殊人物的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惟有他们,才是代表人与鸟(神)的联系人。”[12](P212)
(二)布洛陀文化出现于人类原始宗教崇拜时期
《布洛陀经诗》有这么一个特点:凡是布洛陀、米渌甲出现,必有敢卡王出现。布洛陀、米渌甲本身就是一对男女鸟神,属于阴阳文化的范畴。那么,依附二者出现的“敢卡王”是什么意思呢?
敢卡者,人之两腿之间也;人之两腿之间,生殖器之处也。人有男女性之分,男为阳,女为阴。“敢卡”的壮语为男女性生殖器所在之处;敢卡王者,则阴阳之王也。
何谓阴阳?《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行阴阳者,行使占卜之巫者也。
由此可见,《布洛陀经诗》建立在生殖器崇拜的基础之上,是属于人类原始宗教时期的文化。《史前易学——人类文明起源的百科全书》出现了人之“敢卡”为阳、为阴的考古证据,具体表现为女性生殖器阴刻,男性生殖器阳雕,它们分别与日月、三角形、数字连为一体,是典型的生殖器崇拜、日月崇拜、数字崇拜、天地崇拜、人神崇拜的考古证据。这个证据出于百越人居住地的古滇国地区——抚仙湖水下遗址,乃是人工使用金属器錾刻于石质构件上的图案。其后,这个代表性的符号及其意义为长江流域出土、现保存于湖北博物馆8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太阳神”[13](扉页彩图)石刻画像所证实。
一般认为,生殖器崇拜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人自身在种族繁衍当中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瓦解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成,男女结合与生儿育女的因果关系日益为古人认识,生育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掀开。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使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日益明朗,这样,原先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所取代。”[14](P20)从米渌甲到布洛陀崇拜,就是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人类社会性崇拜的必然发展阶段。比较国外同类考古文物,发现敢卡王的这个特征在全世界具有新旧石器文化上的一致性。但是,只有壮族的布洛陀文化,延续了这个一致性,从而成为揭示中国文明起源之谜的一把金钥匙。
(三)从鸟卦到鸡卦是壮族麽文化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6000年前的上海市青浦福泉文化遗址上已经出现了数字易卦,而数字易卦的占筮方法就是鸡卦。与数字易卦同时出土的有属于良渚文化双鼻陶壶上的飞鸟群饰,可证以鸡卦、崇鸟为标志的越巫文化一直是易学的代表性巫术。上古《三代文》收集的是夏、商、周时期的文献,其中有《黄帝做黄雀占》一文,说的是上古时期,黄帝时期兴黄雀占。我们认为黄雀占是上古时期的一种占卜法,亦即筮法。其后,飞禽进化为家养鸡后,鸡卦占筮就取代鸟卦占筮,慢慢就发展成为主要的占筮方式。那么,这种占筮方式就会出现筮辞,以讲述涉及到人类社会起源的一切问题。所谓筮法,需要巫术人员来实施和完成。这类巫术人员,壮语叫做“卜麽”。“壮族敬奉人文始祖‘布洛陀’,卜麽会念诵《布洛陀经诗》,用于各种祭祀布洛陀、消灾解难的民间宗教仪式中。壮语“布洛陀”中的‘洛’可作‘鸟’、‘鸟部落’解,“布洛陀”则可解释为‘鸟部落的首领’”[15](P80)。鸟部落的首领施行的民间宗教仪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麽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麽文化是布洛陀的内容。但我们的看法是:《布洛陀经诗》只是筮辞的载体。从一部《布洛陀经诗》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筮法。如果使用比喻的话,《布洛陀经诗》等于殷墟甲骨文,表现的是商族统治者的占卜结果,也就是筮辞,而没有具体的筮法。研究甲骨文起源或研究易学起源的学者,无不为寻找不到打开这些筮辞的书感到头疼、困惑。现在我们开展对布洛陀文化的研究,总是没有想到研究《布洛陀经诗》的筮法,把研究《布洛陀经诗》与筮法视为二者互不关联的东西,就与把研究甲骨文、研究易经与筮法视为互无关联的东西一样,我们就永远不知道客观历史事实的真相。所以,研究《布洛陀经诗》的筮法与研究甲骨文、易经的筮法同样重要。
李零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讲,我们要想理解古代易学,有两点必须抓住,一是‘数’,即卦如何由数变成,这是筮法的关键;二是‘象’,即上述由数而变成的卦,作为占断依据,只有象征意义,后面有特定的理解和解释系统。但这两个方面,很多线索都已失传……”[16](P260)
金景芳先生也认为古代另有一套占筮方法。他说:“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卜辞,辞有记载,但用什么来卜,怎样卜,我们都不知道。原因是这些卜书没传下来。甲骨片倒不是很重要,书若能流传下来,则是很重要的。现在只能研究甲骨上的文字,或通过文字研究一些东西。至于这些文字是怎样得出来的,它的好坏用什么来判断,没有办法知道了,卜书失传了。”[17](P12)
以上学者颇有见地。他们认为殷墟卜辞、易经自有一套原始筮法,或另有卜书,从书中可以知道卜辞另有“特定的理解和解释系统”,他们认为失传了,没有办法知道了。现在人们知道和理解的,是一些后人杜撰的似是而非的占筮法。但是,没有人想到,易经的原始筮法、卜辞的“特定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就是司马迁讲到的“越祠鸡卜”。
《布洛陀经诗》是壮族的百科全书,而司马迁在《史记》提到的“越祠鸡卜”就是壮族先民的一种筮法,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关键是鸡卦巫术与《布洛陀经诗》有没有联系?鸡卦是不是其主要筮法,这在壮学界没有更多的考虑,也很少人研究。在这里,我们要说,鸡卦其实就是《布洛陀经诗》的主要筮法,也是殷墟甲骨文的占卜方法。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壮、布依等民族为主的百越民族,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一部分,他们一度成为殷商早期的主体民族,后期被强势崛起的汉文化所同化。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鸡卦巫术一直是代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代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筮法。其后,在鸡卦筮法基础上形成的数字易卦发展成为了符号卦《易经》,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本《易经》,而百越、氐羌等民族的后裔仍然停留在鸡卦原始筮法的基础上,造成了与《易经》没有联系的假象,这也就是殷墟卜辞、通行本《易经》一直寻找不到筮法的根本原因。
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证实,布洛陀文化根源于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这是研究《布洛陀经诗》的基础。倘若离开了这个基础,布洛陀只能是一个具备民族、民俗和神话意义而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创世之神和文化英雄。我们在探讨布洛陀神作为人文始祖的历史地位时,必须明白壮族麽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布洛陀经诗》的研究,还涉及到复杂的筮法论证系统。笔者认为,《布洛陀经诗》是筮辞,并不包含具体的筮法。倘若不研究《布洛陀经诗》的筮法,就不可能真正切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可能知道布洛陀神话的真相,更不可能知道驱动壮族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秘密!
[1] 廖明君.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陈勤建.中国鸟信仰 [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 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4] 江林昌,朱汉民,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5] 马雪芹.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
[6] 王平. [德]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7] 肖南.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J]. 考古,1989,(1):66-70.
[8] 史善刚.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
[9] 杨军.周易文化大学讲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1] 黄懿陆.商族源流史[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
[12] 丘振声.壮族图腾考[M]. 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13] 黄懿陆.中国文明起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14] 郭方.全球通史·人类的文明[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5] 梁庭望,李斯颖.稻花飘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16] 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7] 金景芳.周易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