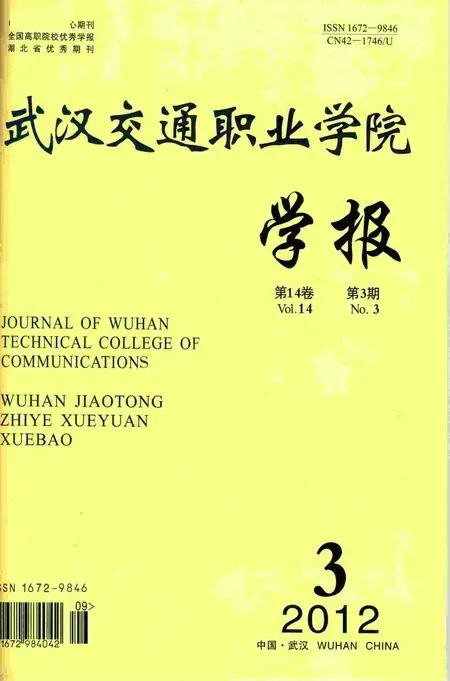城市道路拥堵收费政策的公众接受分析*
张晓莲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交通拥堵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经济学家认为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道路的供给不足,而在于道路的免费使用。[1]交通拥堵是一种典型的“公地的悲剧”。当交通发生拥堵时,每新增一单位的交通量都会给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比如环境污染、潜在的交通事故隐患等。因此,经济学家建议使用边际成本定价法对城市道路使用进行定价,即为了获得最大的道路使用效率,对车辆的收费应当使边际车辆支付的费用等于其边际成本。城市道路拥堵收费(congestion charging)就是经济学“使用者付费”原则的运用,简而言之即在特定时段和特定路段对过往车辆进行收费管理,其目的是鼓励居民出行放弃小汽车而转向公共交通,以此缓解交通拥堵,实现城市交通设施的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
尽管城市道路拥堵收费政策得到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其效果并不理想,国际上失败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挪威的奥斯陆、英国的伦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荷兰等。不得不承认部分国家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的瓶颈阻碍了方案的实施,然而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方案实施的最大障碍来自公民对该政策的抵触。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公众接受对拥堵收费政策的重要意义,以及影响公众对拥堵收费政策接受程度的若干因素,以期对城市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一、公众接受对拥堵收费政策的重要意义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体现在其主体、所持价值观和政策对象三个方面。就主体而言,公共管理者的任务是超越自身利益促使公民发现公共利益并按照公共利益行事。[2]在价值观上,与市场追求效率不同,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安排,其追求的目标更多的体现在公平、民主和责任上;再次,公共问题作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和逻辑起点,也具有鲜明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源于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政治系统将财富、知识、机会、权利等诸多价值通过公共政策分配给社会成员。由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分配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在民主社会,政府不能将自己的分配方案和决策强加于公众,而是必须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接受。这是使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进而体现公共性的必然要求。
PRIMA曾经针对道路拥堵收费方案在八个欧洲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方案的公众支持率不到30%。[3]2005年2月,苏格兰爱丁堡针对城市拥堵收费方案举行了全民公投,公投结果表明只有不到一半(37.4%)的公众信任该方案。就国内民意来看,凤凰网调查显示,超过79%的网民对征收“拥堵费”持反对意见,腾讯微博发起的投票也显示,84.51%的网民投反对票,82.29%的网民认为征收治堵费不能缓解堵车现象。[4]尽管拥堵收费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是有效的治堵良方,但是由于公众对方案的接受程度低,很多城市的拥堵收费尝试都宣告失败了,而更多的城市则处在试探民意的阶段。
二、影响公众接受拥堵收费政策的主要因素
(一)利益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所努力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相关。利益是影响公众接受某政策的关键因素,城市拥堵收费政策的目标群体是城市所有公众。公众在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行为方向时,会根据拥堵收费政策对自己的福利影响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如果接受该政策会使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则拥护和支持,如果政策实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则会持抵触和反对态度。
以S.Jaensirisak为代表的研究小组,于2000年针对拥堵费征收问题在英国利兹和伦敦两个城市对居民进行了显示偏好调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有车一族认为自己已经向政府交纳了足够的税收,征收拥堵费是一种重复收费,放弃驾车出行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相当的麻烦,而且他们并不相信征收拥堵费能够缓解拥堵和改善环境。而半数以上来自利兹和伦敦的无车一族却认为目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强烈支持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研究结论显示,拥堵费政策在城市的无车一族中有更高的支持率,其原因在于,在政策实施后,无车一族将会享受到比以前更多的好处,如更加畅通的城市道路、更加清新的环境和更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而有车一族则要增加额外的支出,尽管这笔费用只占他们日常开支的一小部分,但是人们往往习惯于为得到什么而缴费,而不是为避免什么缴费。
(二)拥堵费收入的再分配
英国伦敦在2003年开始实施道路拥堵收费政策。2007年,在伦敦汽车平均每前进一公里需要等待2.27分钟,而在2003年2月,也只需要2.3分钟。实践证明政策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将拥堵费收入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2007年伦敦用于拥堵费行政管理的支出上升到1.6亿英镑,而用于巴士和交通流量改进的资金不足1000万镑,这种结果无疑与初衷大相径庭。
Jones的研究发现,当拥堵收费方案没有和相关收入的再分配承诺联系时,公众的支持率只有30%;如果承诺收费方案实施后所产生的收入将用于为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者改善公共交通设施时,支持率则上升到了57%。这一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Jones进一步得出结论:政府如果没有承诺并践行拥堵费收入的再分配,将其用于发展地方公共交通和和改善环境,拥堵收费方案便不会被公众接受。[5]
(三)政策的社会公平性
城市道路拥堵收费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出行者的福利有不同的影响。时间价值较高(value of time,VOT)的出行者在拥堵费政策实施后尽管被强制交费,但是交通拥堵程度的减轻使得他们由于出行时间的减少而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们支付的拥堵费。而时间价值较低的有车一族虽然也能享受到出行时间减少带来的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并不能弥补他们所必须支付的额外费用。他们会认为,拥堵收费政策将出行者人为的划分为两类:有能力支付拥堵费的富人和较少能力支付拥堵费的穷人,这会造成社会不公平。
除此之外,在我国大中城市,越是中心城区,公车的比例就越大。反对拥堵收费的声音认为,如果简单的在中心城区划定收费区域,则意味着私家车拥堵费由车主掏,公车拥堵费则由纳税人掏。这不但人为造成新的交通资源占有不公平,加剧纳税人供养公车的总成本,对缓解交通拥堵收效十分有限甚至可能还适得其反。本来,中心城区私车、公车一起堵,客观上也抑制着公车的行驶频率。假如改收拥堵费,在减少私车行驶的同时,则变相鼓励公车出行,因为甭管收取多高的拥堵费,对公车而言都属事实上的零成本。[6]
三、提高公众接受度的政策建议
任何一项收费政策一旦遭遇政策对象的强烈反对都终将成为泡影,拥堵收费政策也是如此。尽管拥堵收费方案在公众中只得到了较低的支持率,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可以提高公众接受度。
(一)配套措施的综合运用
《北京宣言: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指出:城市交通的目的是实现人和物的移动,而不是车辆的移动,即鼓励市民出行放弃小汽车而转向公共交通,以此达到缓解拥堵的目的。如果单单实施拥堵费政策而没有其他措施配合,很有可能发生“溅出效应”,导致市中心的拥堵转移到周边路段,形成新的拥堵。这些配套措施包括汽车限行、汽车数量调控、停车管理等。其中,完善公共交通系统是关键,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在引导出行方式转变方面意义重大。以韩国首尔为例,其公共交通速度提高10%,可吸引5%的小汽车出行者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7]因此,城市交通管理应当根据各种交通方式运送人和物的效率来分配道路的优先使用权,为公共交通提供优先保障。
(二)拥堵费收入的合理分配
拥堵收费应该是公共交通“一揽子计划”的一个部分,相关收益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PRIMA于2000年针对道路拥堵收费方案在八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于“开征拥堵费是否一定会带来公共交通设施的改善”持怀疑态度。方案的反对者反对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能否合理使用相关收入并接受公众监督不信任。伦敦征收拥堵费“越收越堵”的教训告诉我们:不仅拥堵费的开征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以确保其合法性,拥堵费的运行同样需要设置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其有效性。这些制度安排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所有拥堵费的收入都必须用于公共交通项目,[8]比如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直接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同时,对于征收过程和费用流向做到信息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三)公平的政策设计
一项政策如果减少富人的福利而增加穷人的福利,如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付费多,在职者比失业人员付费多,这个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公平的,因此拥堵治理要体现公平还需多考虑政策“受害者”的福利补偿。拥堵费政策实施后时间价值较高的“富人”是政策的“受益者”,而时间价值较低,和只有较少能力支付拥堵费的“穷人”是政策的“受害者”。德国学者Creutzig提出保持公平的方法之一,是向市民提供一张拥堵收费卡(smart card),其功能至少可用于乘坐公共交通和道路缴费。
除此之外,还需要大刀阔斧进行公车改革、加强公车管理。北京在奥运会期间采取车辆按车牌尾数单、双号对应日期出行措施,约减少了道路上50%左右的车辆行驶。奥运会后,北京又颁布新规,除特殊公务车外,各级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车按车牌尾数每周少开一天,这一措施相当于减少了道路上20%左右的车辆行驶。
(四)广泛有效的政策宣传和解释
公众对于交通拥堵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对拥堵费政策的接受度:人们习惯于为得到什么而不是避免什么而交费;人们认为自己是拥堵的受害者,而很少认识到自己也是拥堵的贡献者;人们认为拥堵是路网能力不足造成的;人们不相信政府会透明公正合理的使用拥堵费收入;拥堵费收入会导致违章驾驶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不喜欢政府把收费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等。国外研究指出,随着对拥堵收费政策的逐渐熟悉,公众可能会提高接受度,[9]这个观点在挪威和伦敦的拥堵费征收实践已经得到了证明。基于此,政府在政策实施前应该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全面客观的解释开征拥堵费的缘由、政策目标、预期效果(包括负面效果),争取公众的支持。
为了将抽象的拥堵概念具体化,北京市首创了交通拥堵指数。指数在0至2之间为“畅通”,2至4之间为“基本畅通”,4至6之间为“轻度拥堵”,6至8之间为“中度拥堵”,8至10之间为“严重拥堵”。在城市交通拥堵指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拥堵收费或许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措施,只是如何使政策通过民意关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率,还需城市政府和学界的共同努力。
[1]王冰,王国华.伦敦的交通收费及其福利经济学解释[J].城市问题,2006,(2):83.
[2][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著.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方兴,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7.
[3]Björn Härsman,Sirje Pädam,Bo Wijkmark and INREGIA.Ways and Means to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Urban Road Pricing[R].Pricing Measures Acceptance Project,2000.
[4]傅达林.重视“交通拥堵费”背后的民意焦虑[N].法制日报,2012-02-13.
[5]S.Jaensirisak,M.Wardman,and A.D.May.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Road Pricing Schemes[J].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2005,39(2):127-153.
[6]鲁宁.收拥堵费不符合中国“车情”[N].广州日报,2010-05-28.
[7]Lee S,Lee Y H and Park J H.Estimating Price and Service Elasticity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Demand with Stated Preference Technique:A Case in Korea[M].Washington,D.C.: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3:167–172.
[8]伦敦拥堵费越收越堵的启示[EB/OL].(2012-02-17)/[2012-6-15].http://blog.66wz.com/?uid-199634-actionviewspace-itemid-663311.
[9]Maria Börjesson,Jonas Eliasson1,and Muriel B.Hugsson1.The Stockholm Congestion Charges-5Years on Effects,Acceptability and Lessons Learnt[J].Transport Policy,2012,20(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