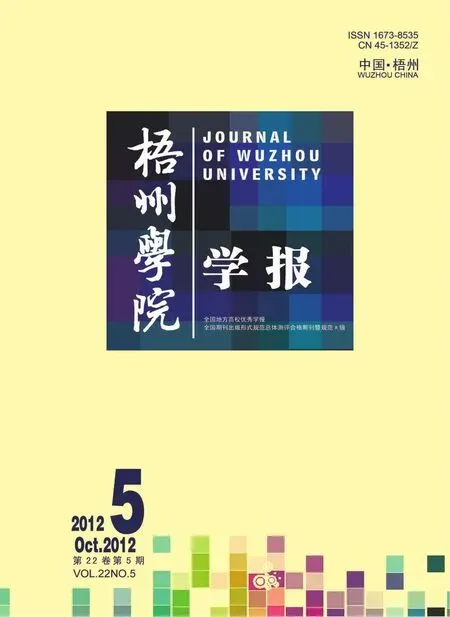身体性的“此在”
——论穆旦诗歌的身体意识
刘纪新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云南昆明 650092)
身体性的“此在”
——论穆旦诗歌的身体意识
刘纪新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云南昆明 650092)
穆旦笔下的身体意识最早出现在《野兽》一诗中,此后,身体与穆旦的创作主题融合,成为揭示“此在”真实境遇的一种角度,通过身体揭示孤独、虚无的真实处境。不仅如此,穆旦还将这种身体意识推广到大自然之中,营造一个欲望燃烧的大自然。最终,由于不堪虚无的折磨,他把身体推上了神坛,不过,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精神慰藉。
穆旦;诗歌;身体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穆旦诗歌的身体意识尤为突出,从1937年的《野兽》开始,身体进入穆旦的诗,到1948年身体退出穆旦的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艺术价值极高。王佐良曾经评价说:“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1]唐湜也认为:穆旦是“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的抒情诗人”[2]79。近年来,研究者再次关注穆旦诗中的身体意识,他们认为:“穆旦具有肉感的诗思呈现方式建立在穆旦对身体言说方式的强烈认同上”[3],“是以浓密而坚硬的情感、血肉郁勃的感官去重新思想”[4]。上述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大多是总体性的概论,本文希望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对穆旦诗中的身体意识做出详细阐述。
一、身体的出场:《野兽》
穆旦的早期作品就表现出鲜明的身体意识,写于1937年的《野兽》第一次展示了身体意识。首先,诗中有传神的动物身体描写:“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其次,该诗还表现了蕴含在身体之中的非理性的生命力:“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它发出“凄厉的号叫”,它“锐利的眼睛”,射出“可怕的复仇的光芒”。谢冕在评价穆旦的诗时曾经说:“他的诗是丰满的肉体,肉体里奔涌着热血,跳动着脉搏”[5],以此来评价《野兽》是非常恰当的。
《野兽》在当时就得到好评,其后也常常被当作穆旦的代表作之一。一方面,它被解读为表现抗战初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契合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从《野兽》中看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子,于是大做文章。客观地说,《野兽》应该还属于穆旦探索时期的作品,模仿痕迹较重。穆旦本人似乎对此也有清醒认识,所以其后三年再没有创作此类作品,身体意识仿佛从他的诗中消失了。直至1940年,《我》问世,身体才重新回到穆旦的诗中,不过,此时穆旦诗中的身体已经与《野兽》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身体与“此在”
从1940年开始,穆旦诗中的身体不再只是对西方人的模仿,而是与自身的创作主题相融合。穆旦诗歌的核心主题是揭示“此在”的真实境遇,当身体与之融合,穆旦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这一切中都回响着身体状态。它使人超脱自己,或者,让人囚于自身而变得麻木不仁。我们并非首先是‘生活着’,尔后还具有一个装备,即所谓的身体;而毋宁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肉身存在而生活着”[6]。
《我》一诗通过身体彰显“此在”的孤独境遇:身体“从子宫割裂”,从母体分离,成为“残缺的部分”,从此生活在孤独中,独立就意味着孤独,从此人就被锁在荒野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在穆旦的诗中,肉体与精神是合一的,“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7]。
在第二段中,诗人感到生命在时间的洪流中逐渐消逝,无法把握自己。即使爱情也不能让人摆脱孤独,那不过是“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最后,穆旦绝望地哀叹:“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该诗从肉体割裂体验精神割裂,从肉体孤独体验精神孤独,精神与肉体相互交融,共同呈现“此在”的孤独处境。
《诗八首》同样是这样,“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8],诗的主题是消解爱情神话,并进一步直面“此在”的虚无境遇,这个过程正是通过身体实现的。《诗八首》把爱情比作火灾,这是一场欲望的火灾,诗中的爱情不过是成熟的身体在自我燃烧:“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在第三首中诗人又写到: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爱情化作身体中蠢蠢欲动的野兽、春天的小草,诗人从爱人的身体中看到欲望,来自身体的非理性力量,推动着现实中的爱情。千百年来被人们讴歌的神圣爱情,在这里却成为成熟身体的自我燃烧。
《诗八首》还表现了爱人彼此之间的身体感受,在身体的沉醉中,诗人得到精神安慰,虽然只是短暂的沉醉:“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最终诗人不仅把爱情消解为身体自身的燃烧,而且这身体的燃烧也难以摆脱虚无的境遇,“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在《诗八首》中,我们看到的是心灵与肉体的融合,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是身体化的思,是“用身体思想”。类似的身体意识也表现在《春》、《发现》、《在旷野上》、《春底降临》等诗中。
在上述诗歌中,身体成为诗人探寻存在的一条长路,由身体出发,诗人看到生命在身体中呼吸,欲望在原野上燃烧,诗人看到爱情的虚妄,也看到了生命的本体性孤独。
三、身体的外化:欲望化的自然
穆旦不仅写出人的身体欲望,而且将其推广到所有生命现象和大自然之中,看到自然万物都是欲望的燃烧,这时的欲望已经不仅是人的存在形式,也成为万物的存在形式。由身体的“眼睛”望出去,整个世界都燃烧着欲望之火,到处是茁壮生长的非理性生命。正如唐湜所说:穆旦的诗“以肉体的感觉体现万物”[2]80。其中,最为杰出的例子是《春》,诗中的春天是一个到处燃烧着欲望之火的世界,诗人的身体意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感受,而是将其延伸到万物,用身体的“眼睛”观看世界,春天成为一片生命与欲望的火场。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春天是生机盎然的时节,同时又是一个充斥着欲望的世界,鲜花盛开,蜂蝶曼舞,百鸟争鸣,到处回荡着昆虫求偶的声音,飘散着花粉、柳絮,处处是身体的焦渴与欲望,无数的生命蠢蠢欲动,天地之间回荡着生命与欲望的交响曲。《春》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世界,摇曳的草化作绿色火焰,花朵与绿叶的关系,不再是滋养、衬托,而是“渴求着拥抱”。花朵盛开,是反抗泥土对生命的压抑,连春天的暖风也充满欲望,给生命带来躁动的情绪。春色在这里化作“满园的欲望”,这是诗人用身体“看”到的世界,用身体重新阐释的世界。
此后,穆旦又回到人的身体。“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也如万物一样被春天点燃,加入了春天那漫天的欲望大火。诗中,“抽象观念与官能感觉相互渗透,思象和形象密切结合”[9]36,形成一个感性化、肉体化的世界。
在《玫瑰之歌》中,穆旦塑造了一个与现代社会对立的大自然,这里没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田园牧歌,而是一个生命和欲望的世界:“大野里永远散发着日炙的气息,”“朵朵盛开的大理石似的百合,伸在土壤的欲望里颤抖”,“莺燕在激动地歌唱,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燃烧”。
同属九叶诗人的唐湜也看到穆旦诗歌的这个特点,所以他说:“穆旦也许是中国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Identification)的抒情诗人之一”[10]。
四、身体的僭越:《我歌颂肉体》
穆旦在《祈神二章》、《隐现》中曾经写到,为了追寻永恒的、真实的、至高的存在,需要挣脱“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习惯的硬壳”是指遮蔽了存在的习俗,“欲望的暗室”就是指蕴藏着欲望的身体。在追寻存在的长路上,身体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它也是要被超越的意义驿站,而且只有抛弃它,才能接近那个至高的存在。《诗八首》虽然用身体消解了爱情,但是身体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真实,仍然是此岸的虚无之物,正如诗中所言:“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在《我》中,“我”只是通过身体体验孤独,身体并不能将“我”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在这些诗中,身体就是一条通往存在的幽暗的长路。
但是穆旦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逐步将身体推上了神坛。在《我歌颂肉体》中,他在身体中找到了“肯定的岛屿”、“大树的根”和不会被洪水冲走的“岩石”,从而把精神家园建立在身体之中,身体变成了终极存在。至此,身体由存在的敞开,变成存在的遮蔽,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完成的形而上学之中的这种显明,甚至可能同时是存在的极端遗忘”[11]。
《我歌颂肉体》可以说是对现代身体观的形象化阐释,诗人将自身的体验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身体的理念巧妙融合,但是,过度依赖既成的理论观念也成为这首诗的缺陷。诗中写到:
我们从来没有触到它,
我们畏惧它而且给它封以一种律条,
……
但是我们害怕它,歪曲它,幽禁它;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的生命认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把它的发展纳入我们的历史,
因为它的秘密远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
这显然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家视野中身体历史状况的诗化表述,是用诗化的语言转述了既成的理论。
“我们幻化了它的实体而后伤害它,/我们感到了和外面的不可知的连系/和一片大陆,却又把它隔离。”“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的大胆的网罗/而投在我们怀里。”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身体的认识:我们存在于我们的身体,身体把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的感觉、知识都来自身体的感知,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不洁的、邪恶的。
至于下面一段对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批判就更为明显了:
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
(笛卡尔说:我想,所以我存在。)
但什么是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服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
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
《我歌颂肉体》不仅是对现代身体意识的诗化表述,而且是一首写给身体的赞美诗,身体成为诗人顶礼膜拜的上帝,成为“岩石”,成为“肯定的岛屿”,成为“美的真实,我的上帝”。这样,穆旦诗中的身体意识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穆旦诗歌中的身体没有达到如此高的地位,没有构成一种终极存在,仅仅是追问存在的一种途径。随着身体由道路变为存在本身,身体也就由对存在的敞开变为对存在的遮蔽。好在以冷静、深刻著称的穆旦,仅仅在此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很快就回到怀疑和虚无的心境中去了。
像《我歌颂肉体》这样,充斥着无条件的肯定、赞美情绪的诗歌,在穆旦笔下极少见,他是以怀疑、否定著称的,那么穆旦何以写出这首诗?何以把身体提高到如此高的位置,使身体由存在的敞开变成新的遮蔽呢?可以回到当时的创作情境之中寻找原因。
就在穆旦创作《我歌颂肉体》两个月之前,写出了那首著名的《隐现》,将这两首诗进行对比,可以明白穆旦为什么会把身体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在《隐现》中,诗人哀叹一切都在流逝,什么也留不住。而在《我歌颂肉体》中,开篇就出现了“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在《隐现》中,穆旦写到“全是不能站稳的/亲爱的,是我脚下的路程;/接受一切温暖的吸引在岩石上,/而岩石突然不见了”。而在《我歌颂肉体》中,却多次出现可以站得稳的岩石:“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是在这个岩石上,成立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在这个岩石上,自然寄托了它一点东西。”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根”:“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摇吧,缤纷的树叶,这里是你坚实的根基”。在《隐现》中,诗人感到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一切都是幻象,最终我们只是一无所有。但是在《我歌颂肉体》中,诗人写到:“一切的事物令我困扰,/一切事物使我们相信而又不能相信,就要得到/而又不能得到,开始抛弃而又抛弃不开,/但肉体使我们已经得到的”。《隐现》中充斥着怀疑、虚无和绝望的情绪,诗人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歌颂肉体》却是肯定与自信的,仿佛真理在手。在《隐现》中,诗人仿佛置身于幽暗的流沙之上,不知命运将把自己带向何方。在《我歌颂肉体》中,诗人的双脚已经踏上了坚固的岩石。可以说《隐现》是在绝望中追问,《我歌颂肉体》是在自信中回答;《隐现》是撒满痛苦的生存探寻之路,《我歌颂肉体》是铺满鲜花的虚妄的黄金国。
《隐现》是穆旦的一部杰作,是一篇滴满灵魂之血的诗歌,在《隐现》中穆旦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隐现》给人一种感觉:穆旦再向前一步,就要崩溃了,他的痛苦已经达到凡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我歌颂肉体》,它不过是穆旦痛苦的精神之旅上一次短暂的后退、一次精神小憩、一次自我精神调整,是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首诗中居然出现那么多经过艺术处理的理论话语。《我歌颂肉体》正是穆旦的一次精神小憩,他在身体以及种种关于身体的既成理论中找到了暂时的港湾。此后,不仅身体退出了穆旦的诗歌,而且这种赞美、肯定的情绪也成为昙花一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把身体引入诗歌的是新月派诗人。在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在感官享乐中寻求精神安慰,从而把身体引入创作。但是他们或者流于表面,或者把身体引入肉欲的泥沼。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把身体的品格提升起来,但是仍然是主要停留在感觉层面。只有到了40年代的穆旦笔下,身体之感与深邃的哲学之“思”、痛苦的生命追问相互融合,使得诗歌中的身体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1]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M]//曹元勇.蛇的诱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13.
[2]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李蓉.现当代文学“身体”研究的问题及其反思[J].文艺争鸣,2007(11):83.
[4]张同道.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论穆旦[J].诗探索,1996(4):20.
[5]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J].山花,1996(6):45.
[6]海德格尔.尼采:上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9.
[7]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M]//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5.
[8]王佐良.论穆旦的诗[M]//李方.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8.
[9]唐祈.现代派杰出的诗人穆旦——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J].诗刊,1987(2):36.
[10]唐湜.搏求者穆旦[M]//新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11]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86.
“Existing”of Hum an Body——On the Body Consciousness in Mu Dan’sPoems
Liu Jix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enm ing 650092,China)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 body can be traced back to Mu Dan’s poem Beast.From then on,body consciousness blendswith the theme ofMu Dan’s poems,serving as device to show the concreteness of“Existing”so as to reveal the reality of body’s loneliness and nothingness.Moreover,Mu Dan spread such a body consciousness to the whole nature,creating a world of fiery desire.As a result,being unable to endure the suffering from nothingness,he put the body on a pedestal,which,however,ismerely a temporarymental relief.
mu Dan;poem;human body
I226
A
1673-8535(2012)05-0054-05
刘纪新(1969-),男,河北沧州人,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2-07-08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011Y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