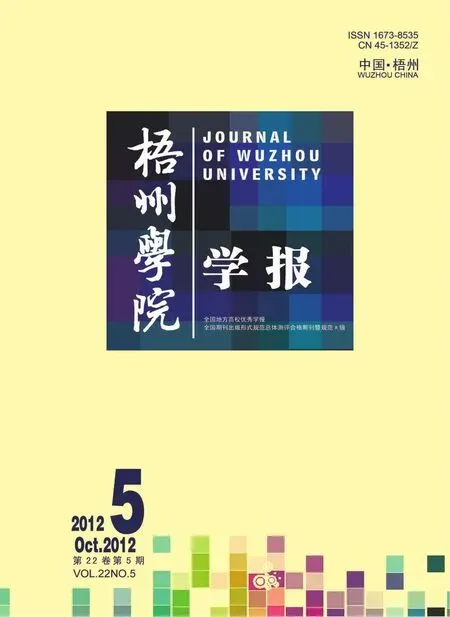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及其理论困境
田新元
(中共梧州市委党校,广西梧州 543002)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及其理论困境
田新元
(中共梧州市委党校,广西梧州 543002)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价值是事物的一种内在属性,具有客观现实性,它是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有机统一。正是自然的这种价值,人类才对自然界承担道德义务。罗尔斯顿的价值论开创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但其理论内在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应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
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理论困境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境伦理学也随之兴起。纵观所有这方面的研究,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可谓是独树一帜,它超越传统伦理学的研究思路,实现了价值范式由主观价值论向客观价值论的转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范式和方法视角,开创了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其自身又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应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
一、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
罗尔斯顿认为,怜悯、博爱、权利、人格、正义、公平、快乐等属于人际伦理学的范畴,这些范畴存在于文化习俗的范围,用来保护那些与人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它只有在主体性和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才是真实存在的。西方学者把他们用于环境伦理学研究是不可取的,犯了范畴误置的错误。罗尔斯顿提出,如果把它们运用于环境伦理学中,无形中就会忽略了被道德代理人所发现的、在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于大自然中、被认为是适宜的、有价值的东西。
罗尔斯顿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应该从“内在价值”这个范畴展开,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内在价值”范畴没有被重视,“现代人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变得越来越疯狂,对大自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却越来越麻木无知”[1]3。现代人持有的是一种主观工具价值论,抹杀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抬高了人类的自身价值,最后导致了人类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新环境伦理学应该试图改变这种处境,要推翻自然仅是资源的范式,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自然本身的“价值”。
关于“价值”的探讨,“价值主观论”长期占据价值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中以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最为典型。他认为,只有人才能成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尺度,“人类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1]151。罗尔斯顿把上述的这种观点指斥为“主观论”、“唯我论”。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价值是指事物的某种属性——自然界中存在的有序性、组织性和进化性。评价自然价值的过程其实就是标识出生态系统的这种属性的一种认知形式。如何去标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完全是靠体验来标识。
被人类意识到的价值,属于体验性的价值,而未被意识到的价值,属于非体验性的价值;有些价值依赖于被意识到了的偏好,有些则不是。“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价值的有部分可能受偏好的制约,有部分则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它具有客观实在性。价值部分是基于人类的有意识偏好,但部分是基于人类的生物化学机制。这种机制与人类有意识的偏好无关。”[1]152因此,他认为,把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偏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罗尔斯顿认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固有属性而不是人类赐予的。“在人类发现价值之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中很久了,价值的存在先于人类对它们的认识。”[1]294自然价值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创造性,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和谐、复杂。“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凡存在自发创造的地方,都存在着价值。”[1]271它使得自然机体日益复杂化,生命物种愈加多样化和精致化,使得地球生态系统保持长期稳定和可持续运转,“大自然既是推动价值产生的力量,也是价值产生的源泉”[1]290。
罗尔斯顿认为,地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够产生价值且一直这样做着。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跟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相比,人具有一种高级价值,但是,人类所具有的主观性价值,只不过是“发生在生态系统中的更大的、客观的价值生产和价值支撑事件的一个子集——虽然处于子集的顶点,但仍然是一个以客观价值事件为基础的子集”[1]6。个体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自然的产物;而自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创生万物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有能力推动一部完整而辉煌的自然史”[1]P259。人类的出现本来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认为是人类的出现才使得其他事物变得有价值,那就未免对生态学太无知且太狭隘了。
二、自然价值的三个维度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价值是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有机统一。
工具价值是指“某些被用来当作实现某一目的和手段的事物”[1]253,也就是说,对大自然的评价以“人类自我”利益为中心,功用性是判断自然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大自然仅仅是作为人类资源,它表现为一事物的存在对他事物的用途。
内在价值又叫目的价值,是相对于工具价值而言的,指“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1]253。是指自然的内在目的性、非工具意义,这种价值观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它突破了单一的人类的价值尺度,承认生态系统中,存在不以人的主观偏好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目的。
生态系统既不拥有任何完整的计划,也不护卫任何东西,但作为生命的发源地,它拥有内在价值,拥有自己的善和自己的存在目的,但个体生物的内在价值不是孤立的存在体,而是与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相联系存在。也就说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在一个整体中体现它的善,于是我们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来描述的事物。
系统价值是一种超越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整个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系统价值既包含了内在价值,也兼备工具价值的作用。自然生态系统将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统一起来,使之从属于系统价值。系统价值不是部分价值之和,它也不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而是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要在关系性中发挥对他者、对整体的工具价值功能,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看,个体的内在价值与系统的内在价值要始终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的统一。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自然及其造物的价值,罗尔斯顿还描绘了一幅金字塔型的创生万物的自然的不同存在层面的简图来加以说明。
罗尔斯顿认为,生态系统中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还有内在价值。但它们又不是均匀地分布在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尽管总是以某种比率同时出现,但是,它们的比例随存在物等级的升高而变化。随着自主活动能力的提高,生物身上的个体性价值逐渐超过了其身上的集体性价值,而到了人这里,个体性价值有时甚至取代了集体性价值。从人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来看,人既依赖于生态系统,同时又具有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力;而生态系统的存在既支撑着人类,同时又具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性。“生存于技术文化中的人类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但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哪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要依赖于处于生命金字塔顶层的人类。”[1]304
三、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道德义务
罗尔斯顿认为,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是一致的,人类只有树立了自然生态的价值理念,才会把遵循自然规律作为人类的道德义务。这就是罗尔斯顿所寻求的“一种恰当地遵循大自然”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要求应该把大自然当作人类的根源,而不是一种资源。主张人类应该尊重大自然,应该从大自然的视野来理解人类自身,而不能只是根据人类思维来理解大自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生态系统的绚丽、和谐与稳定都是判断人类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1]307
罗尔斯顿认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尽管人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人类的语言、心计、自我意识及其对世界的认知水平都是其他动物所不能匹比的,他具有的对世界的评判意识更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但是,从人的优越性中推导出来的不仅仅是特权,还有责任,人的生存应具有其他动物所不能比拟的道德色彩。如果价值总是、而且仅仅是一个满足人类偏好的问题,那么从价值保护引申出来的道德就完全被限制在人类这一物种的私利的范围内了。只有当人认识到,他并不是价值的唯一聚集地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价值觉醒的最高表现。
在他看来,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因此,不应该把非人类存在物排斥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而应该把人具有的普遍仁慈的义务与关于生态系统(它容纳了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的完美“仁慈”(等于善)的信念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它需要的是某种“不干涉大自然”的金科玉律:人应该以一种欣赏的方式遵循大自然,尊重生态系统及其他物,做自然界得天独厚的辩护人。
四、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理论困境
在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生存困境的今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盲目开发、征服、控制、统治自然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有利于培养、提高人的生态意识,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它建立在生态科学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用科学解释伦理,未免使它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具体表现为:首先,他犯了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的谬误”,混淆了价值和事实之间的本质区别,直接把事实和价值划等号,使存在论视野被价值论视野所涵盖,这样既取消了哲学存在论视野,也取消了价值范畴本身。其次,在他看来,自然的固有价值是人们尊重、保护自然物的义务的基础,只有承认自然物的固有价值才能把尊重、保护自然物的义务贯彻到底。这一观点不管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中西文化的视角来看都是缺乏合理根据的,对于指导普通民众的生态实践来说似乎带有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且容易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环境法西斯主义”,即为了生态系统的价值而牺牲个体,特别是人类的利益——因为人类对于生态系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敌人”。发达国家无顾自身原因作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借口保护生态环境为名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正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第三,他没有认识到,作为真正的主体,除了具有目的性以外,还应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自我意识能力,特别是能够实现相互交流,拥有交流所需的统一的话语系统,或者是可以相互转译的信息系统,并且双方都能认识到对方是主体。他把自然界的目的性和生命的本能作为自然界和生命具有主体性的立论基础,犯了泛主体性的错误,其后果是把人降低到与动物相等同的地位或是把动物抬高到与人相平等的地位,抹杀了人对于动物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人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第四,他痛恨并斥责人类中心主义,把环境问题产生及其恶化的根源归于人类中心主义歪曲、忽略了自然固有的价值。但是,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的层面上,他来了一个急转弯,不是让自然适应于人,而是应该让人适应自然,自然生态系统的美丽、和谐与稳定是最大的“利益”;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创造的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尽管是高级的物种;人类对自然客体的评价并没有把它纳入“自我的场域”中,相反,人类本身就处于“自然的场域”中,在更大的自然系统中,人类的评价也是一种生态事件。因此,在罗尔斯顿的视野中,自然变成了纯粹的主体,人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他虽然摆脱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但又陷入了一种自然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其导致的后果依然是人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
[1]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B018
A
1673-8535(2012)05-0039-04
田新元(1974-),男,湖南株洲人,中共梧州市委党校教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2-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