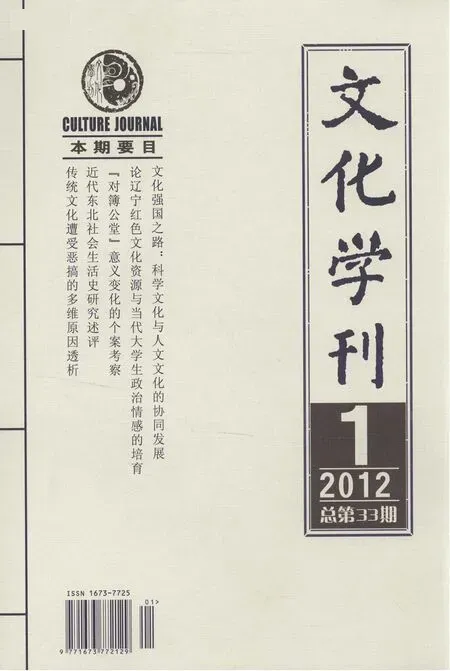文史随笔的哲思妙悟
吴玉杰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王充闾以历史文化散文奠定他在中国当代散文上的地位。但阅读其近作发现,虽然他对历史仍然兴致盎然,然而其写作的路向和风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在的基于当下的文本,融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是自我文本的解剖学,是升华的生命智慧的哲思妙悟;其透视出自我形象的嬗变,彰示了疏放自如的闲谈式文风。我们可以把王充闾近期的这些创作称为文史随笔。
一
显在的当下性哲思是王充闾文史随笔的文本指向。文史随笔题材广泛,从国家民族到生命个体,从历史探问到公园小记,从自我体验到创作经验,从想象力到文化赋值等等,无不包含鲜明的当下性。虽然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也具有历史文本的现实张扬,然而那是隐含的当下性;而文史随笔的创作是显在的、张扬的当下性。历史文化散文是一个自我的“封闭系统”,它的当下性等待着读者在艺术空白与召唤结构中想象与填充。而随笔文本,是回到当下,针对当下,作者的创作意向更加明指。王充闾从当下老电影赢得观众青睐中探求电影丰富观众审美经验、提高观众视听文化水平、滋养和熏陶观众精神世界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文坛上活跃几十年的作家,他时刻关注着文坛现状,时刻保持着如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王充闾关注文学的当下性,他总是在宏阔的视阈中把握文本与文体。在谈到杂文时,他简约概括了当下的四种流行病:“俗套”加上“熟套”,“新闻腔”与“八股调”,远离现实与空泛议论,装腔作势与故弄玄虚。《散文的文学性》是王充闾担任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评委、阅读散文、深感当下散文文学性的缺失而做的文章。他谈到散文创作上的三病:语言比较粗疏;不善于驱遣意象;诗性淡薄,情怀、襟抱不够开阔。他站在古今中外优秀文本的至高点上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从语言、意象与诗性等方面审视散文文学性的生成。在“语言缩略化、情感缩略化、人生过程缩略化”的当下,他谈文学性与想象性问题,这种针对性的指向比历史文化散文更加鲜明。
文史随笔当下性的立场和他创作历史文化散文不同。在历史文化散文中,历史性、文学性与现代性并不平分秋色,历史性与文学性是其显在的特质,而现代性是作为一种立场和意识,其隐含的当下性被包裹在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或者说,当下性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是一种曲折的表达。而当下性在王充闾文史随笔中占有突出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当下性就没有其文史随笔。《这里有个小山村》写泰戈尔《吉檀迦利》诗中所追求的深邃、神秘的“梵我一体”的理想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安宁的美好气氛,以及“天然去雕饰”的清淳的艺术风格,这“使得蜗居尘壤之中,深为生存烦扰、都市喧哗、商品化的人际关系所苦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清风拂面、如饮醇醪的解脱感和舒适感”。也许这也是作者拜访此地的当下性用意所在。
他谈想象力、谈读书阅世、谈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等等都是如此。然而,他的当下性不是停留在现象表层,而是透过现象直逼真相,穿越表层开掘深层,指向形而上的哲思。哲思的获得首先源于哲学视角的选择。王充闾文史随笔(也包括他的历史文化散文)自觉选择哲学视角。他在《学习与思考》中说:“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哲学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视角,一个是立足点。立足点高,眼界、视野就开阔。”《这里有个小山村》以哲学视角观照小与大的关系:小山村和大作家的精神与生命之联系,小山村与大学、大学与中国、印度诗人与中国文化等等。随笔《龙墩余话》讲历史文化散文《龙墩上的悖论》,从悖论即“从哲学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圣朝设考选奴才》也是以哲学思维审视英才与奴才的悖论式存在。在其他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谈即文史随笔中他也多次谈到哲学视角问题。可见,在哲学视角的选择上他非常自觉。哲学视角的选择和哲学思维有关,视角的成功运用才能最终获得形而上的哲思。王充闾在“哲学思维、思辨能力”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得益于文化修养的长期积淀和哲学思维的有意识培养。王充闾谈的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以哲学思维、哲学视角关注当下。在信息爆炸、知识膨胀的当下,较少有人关注智慧,而智慧对于人是最重要的。他说:“信息是平列的;知识是组合起来的信息,二者有深浅、高下之分;智慧是在生命体验、哲学感悟的基础上,经过升华了的知识。”关于信息、知识与智慧的这种哲学思考非常富有针对性与启发性。
王充闾的文史随笔坚守着和历史文化散文一脉相承的哲学思维,这是他在散文创作领域保持深度与高度的话语密码。而文史随笔在哲学思维下以哲学视角关注当下,是王充闾拓展文体空间和张扬文本空间的成功实践。
二
自我的智慧性妙悟是王充闾文史随笔的文本表征。智慧一词在文史随笔中是一个高频词。《中西会通的文化坐标上》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他说:“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其值得珍视的,还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智慧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哲学促使知识转化为智慧。《学与思》讲智慧、出世与入世、放开视野、动脑筋、创作出新等,是作者的生命体验,也是他的人生智慧。在哲思之下,王充闾文史随笔是其生命体验与人生智慧的传达。传达分为两个层面,针对创作主体而言,随笔是其智慧的载体;针对接受主体而言,随笔把王充闾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智慧传达给读者。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场景,王充闾以哲性思维观照,并达成对生命现象的形而上思考,彰显出充满智慧的绝妙悟性。《银幕情深》谈电影,对人生与戏的“互动”关系却有如下认识:戏如人生,从奥赛罗的故事中总结人生爱情的经验,“保鲜爱情的真谛,莫过于相互信任”,“理想信念,对于一个人像生命一样重要”,“嫉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人生如戏,但“人生这场大戏是没有彩排的,每时每刻进行的都是现场直播,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像电影(当然还有戏剧)那样,可以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不断地重复上演。但也正是为此,不可重复的生命便有了向电影、戏剧借鉴的需要与可能,亦即通过电影、戏剧来解悟人生、历练人生、体验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银幕、舞台都应该是灵魂拷问、人性张扬、生命跃动的人生实验场”。人生和戏之间的这种认识,尤其是人生是现场直播的比喻性表述对于受众来说更具冲击力和警醒作用。
文史随笔中的智慧性与历史文化散文的智慧性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智慧性和历史性哲思结合,那么智慧性在文史随笔中则和当下性哲思与学术性追求结合。如果说,历史文化散文注重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那么,文史随笔则注重文学性与学术性的融合。《蹈险余生作壮游》写朝鲜崔博的传世名著《漂泊录》的学术性价值,从他者的眼光观照明代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大欲无涯》是文史随笔,而并没有把它认定为历史文化散文。显然,作者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学术性。这篇文章有和历史文化散文一致之处,即对人性的复杂性思考与欲望的悖论性观照。《大欲无涯》中成吉思汗欲望满盈,南征北战,功绩显赫,然而屠杀平民等负面影响并不随此“灰飞烟灭”。作者进入生命本质的深层,探求“生死之谜”:“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也包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他们成为尸骸之后,就同普通的贩夫走卒的尸骸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从恢弘的历史场景到渺小的个体生命、从显赫的历史功绩到淹没的尸体残骸,作者观照的是欲望对历史与生命的双重效应。也正如他在 《龙墩余话》中所说:“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然而,与《用破一生心》、《终古凝眉》等历史文化散文不同,创作随笔《大欲无涯》,作者并不担心“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在文本中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中西,智性的议论时刻跃动于文本之中,学术性成为显性追求。学术性在《想象力谈片》、《闲堂说诗》、《散文的文学性》等篇章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作者以灵动与巧妙的方式把人生智慧对象化到文史随笔中,所以虽然学术味道浓,学术性强,但文本中的自我形象却陡然站立,而这一形象和历史文化散文中的自我形象有着很大的区别。或者说,文史随笔透露出作者生命体验与自我形象的嬗变。历史文化散文的自我形象,如同一个历史老人“面对苍茫”,“叩问沧桑”,追思“龙墩上的悖论”;如精神分析师,绘制历史人物的的“人格图谱”,解剖历史人物的心灵,追问“终古凝眉”、“用破一生心”的内在玄机。虽然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有和对象主体的精神同构性,但我们似乎也看到保持审美距离的冷静观照,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零度叙事”。但是,在文史随笔中我们发现,“我”与历史和当下的随影随行,“我”从“历史幕后”走到“文本台前”。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我”眼中他者的历史,而文史随笔中我们看到的是“我”的历史。如《联苑忆丛》中我们既看到自由穿梭于中国楹联文化的学者,又看到一个悟性才高的神童。尤其老师上联“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我”的下联为“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的“顶尖对决”让“我”的形象跃然而出。文史随笔中的“我”不仅仅有对历史文本的解剖,更是对自我文本的解剖。在一定意义上文史随笔是自我文本的解剖学,是基于成功经验的创作诗学。王充闾的随笔有多篇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他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一是关于历史性哲思与当下性鉴戒。他“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追求“思想意蕴的层层递进、逐步深化”的深层结构的开掘。二是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创新。《为骆宾王祠撰联》详解自己“剥掉一切强加给他的‘伪装’和‘时装’,除去罩在头上的各种‘恶谥’与光环,还他以本真的面目。”《一部散文集的诞生》谈散文《张学良:人格图谱》为何能够产生?他阅读张学良的传记,发现“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取其貌而略其神’,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与挖掘”。至此,王充闾追求“诗、思、史”融合的文学至境。三是关于艺术构思与艺术想象。随笔《为张学良写心史》是谈《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创作经验,作者从思想即张学良的人格图谱及其成因(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以及艺术(文体定位、谋篇布局、文学手法、广泛借鉴)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从务实传统、应试教育、需要匮乏、心情浮躁等方面对文学性的缺乏做历史与现实的精到分析。《龙墩余话》讲《龙墩上的悖论》的“五个专题”(欲望的无限扩张、欲望的最高实现、维护“家天下”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封建王朝递嬗中文化传承与知识分子地位问题)和“三个突出”(探寻人生困境,引进悖论范畴、辩证观照历史人物)。所谓“余话”,是在“正话”之后的表述。从出版与传播的时间上来说,是先“正”后“余”的逻辑顺序;然而,从作者的艺术构思上说,是先“余”后“正”。“余话”所含是正话的统领。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说,余话对正话的解释与阐发为接受主体揭开了“写作之谜”,作者是如何构思、如何想象,对接受主体对文本的理解与补充具有提升与深化作用,为批评家对于创作心理的把握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想象力谈片》从民族的想象力谈到自我的想象力,谈到散文创作的想象力,谈到自己的想象力匮乏,并提出自己弥补的方式。
作者进入自我的文本世界,勇于解剖自我,真诚总结创作实践的得与失,这些基于自我创作体验与经验而生成的智慧与悟性,是关于创作的学问,是创作的诗学,它的可借鉴性与指导性对于其他的创作者与研究者来说都是十分是宝贵的财富。
三
疏放的闲谈式言说是王充闾文史随笔的话语特征。《闲堂说诗》、《想象力谈片》、《龙墩余论》、《文化赋值丛说》、《貂蝉趣说》、《公园小记》等标题表明,作者改变了严谨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风格,而以闲谈与趣说等方式进行文史随笔的话语表达。这让我们看到主体形象的另一个侧面。自“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才胆识力使他们的随笔成为经典之作。随笔虽是随性而为,但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着随笔的高度与深度。
闲谈是王充闾文史随笔的重要体式特征。汪曾祺认为:“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夹叙夹议’,但是有些事是不好议论的,有的议论也只能用曲笔。‘随笔’的特点还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王充闾的《闲堂说诗》中谈到说诗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系统地、有条理地讲;一种是漫谈式的,依据古人的名篇和自我的创作实践。”他的说诗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作者不受束缚,挥洒自如,自由与疏放。表面看来,是闲谈、漫谈,而实际上运用与文本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在给李仲元《缘斋诗稿》写的序《云锦天机妙手裁》中,作者说:“缘斋为诗,由于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上下古今,充塞胸臆,名章、词汇,信手拈来,暗用、化用诗古文辞,浑然天成,一似自然流洒,毫无窒碍。”和《缘斋诗稿》的文本保持一致的古风神韵,使序和文本和谐地融为一体。
闲笔的运用在随笔中随处可见,任性闲谈是作者的“无心之心”。《依旧长桥》中作者好像是无意中走出历史上的状元与相爷之乡,而讲到现在的长桥,实际上是作者有意从桥(物象)到晋江(空间),从空间到人,发掘历史和现实内在的连贯性,即长桥人“独占鳌头的心性”,是一种文化性格的传承。从文本第二部分的叙述 “还是回到桥的话题”来看,作者似乎认为第一部分游离了自己的《依旧长桥》,而这正是作者的“无心之心”。或者这正是自己的“别有用心”。闲笔中的婉转叙述耐人寻味。任性闲谈是表层的游离、深层的统一。《貂蝉趣话》上篇最后说 “关于貂蝉的话题也就此打住了”,而下篇的开头即是,“关于貂蝉的话题临时打住,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探讨。比如,前面引述的除了杂剧,就是小说、平话,都是出于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凭借着一定史实,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可以凭空结撰,羌无故实。那么,有关貂蝉、吕布的历史真迹,是否有踪迹可寻呢”?作者和文本中同行关于貂蝉的话题是打住了,但作者自我关于貂蝉历史真实的追问刚刚开始。若是创作历史文化散文,作者可能保持着文本叙述的一致性,会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秩序接着说。但创作随笔,作者可以任性闲谈,不拘泥于文本表层结构的一致性,而是探讨貂蝉的真实性。如果说上篇是闲谈的趣话,那么,下篇则是闲谈的正说。这样的闲谈藏庄严于诙谐之内,寓绚丽于素朴之中,有助于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闲谈式的话语言说是一种对话方式的改变。历史文化散文是作者与历史人物的显在对话,虽然作者以小说笔法通过人性与生存困境的书写、主体情思的融入等方式实现与读者的对话,但这种对话性是潜在的。文史随笔,是作者试图用一种闲谈的方式和读者对话。闲谈的话语方式营造日常氛围,作者和读者处于平等的对话性地位。如果说,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散文家的严谨的王充闾;那么在随笔中,我们看到的是“任性”的“杂家”的王充闾,谈赋、谈旧体诗、谈杂文、谈史书、谈元杂剧,谈电影、谈摄影等多种艺术与文本,随性谈任何之想谈。虽然他的闲谈可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文体或文本,但具有超越性的指向,比如对提升摄影艺术的看法等等。《貂蝉趣说》中对貂蝉人物真实性进行历史考察,对不同历史文本与文体中的貂蝉形象加以概说与趣说,涉及到史书、历史小说、元杂剧、川剧乃至于流行歌曲等等,在形象变迁中探问文体规定性与历史文化蕴涵。如果说,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陌生化”的王充闾,那么,在随笔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熟悉的、在我们身边的王充闾。他以每个人都去的公园为题写 《公园小记》,谈到公园的功能,“流连风景、美化环境,供人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具备着休憩所、排气筒、缓冲器之类的特殊功能”。他通过把自我人生经验与智慧的总结传达给读者,获得与读者心灵上的交流。《寻觅一个安顿文心的场所》写到数十年“我”和图书馆之间的不解之缘,其中关于读书等人生经验、人生智慧的传达给读者以启迪。他把“心交给读者”,主动营造对话氛围,《我写历史文化散文》谈到自己最初创作上出现“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在其他篇章中谈到自己的想象力匮乏等。这种与读者零距离的亲近与坦诚更利于实现对话性,益于产生共鸣。
随笔的闲谈式看似枝蔓,实则疏放自由,是无技巧之技巧,是“非完美”之审美追求。
显在的当下性哲思、自我的智慧性妙悟以及疏放的闲谈式言说成为王充闾文史随笔的重要特征。回到当下、回到自我,被王充闾称作是“我”的“点滴体会”的文史随笔,是自我体验的哲思妙悟,是高度浓缩的生命智慧。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哲思妙悟的智慧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