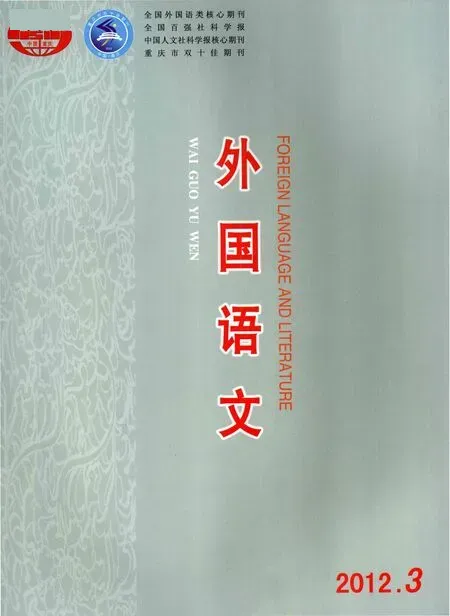文化翻译中的转喻功能
李小川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长沙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3)
1.引言
在翻译理论史上,译论家们很早就对翻译中的文化现象给予了关注,翻译本来就是跨文化的双语转换活动,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才有意识地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认识和观念的变化,翻译观的演变也概莫能外。当前,随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东西合璧的趋势,并由此带来翻译过程和策略的改变。
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1960/1965)将人类思维分为两大基本方式:隐喻与转喻,前者是相邻性、结合之可能,后者是相似性、替代之可能。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玛丽娅·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于1999年在《后殖民环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中创造性地将这一区分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所谓隐喻,指的是选择(selection)与替换(substitution),即一种语言中的字词、语法结构、文化标记、文学形式为另一种语言中的相应成分所代替;所谓转喻,指的是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partiality)(李欣,2001:43)。铁木志科(Tymoczko,1999:56)认为,翻译不仅有隐喻的一面,还应有转喻的一面。她进一步指出,翻译是一种转喻,可以透过局部看到整体,特别是透过所谓的折射(refraction),即译者对原文进行的摆布与修改,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铁木志科对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现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历史时代即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问题,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以及译者在其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李欣,2001:43)。本文将运用铁木志科所强调的翻译的转喻理论,论述转喻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必然性,阐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种转喻过程所体现的动态优选性,从而论证转喻是为了动态、辩证的“忠实”和“对等”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2.转喻的分类
根据赵彦春教授(2003:72)对转喻的划分,转喻分为必然性转喻和或然性转喻,他们分别包括全局性和局部性两种类型。
2.1 必然性转喻
必然性转喻指由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译者不能逾越语言固形特征时而采取的转喻策略,因此造成了翻译的部分性,不可避免地引起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偏差。
局部性:(1)A:How do you like Kipling?
B:I don’t know,I never kipled.
甲:你喜欢拿破仑吗?
乙:不会拿,我从来就没拿过破轮。
这是为传达原文的幽默而采取的转喻手法,宥于文字或正字法,如不运用部分性的转喻策略,就不可能再现全面的忠实和对等。
全局性:(2)The sixth sick sheik’s sixth sheep’s sick.
四只狮子私吃四十只涩柿子。
这是为了传达原文的绕口令特征而进行的全局性转喻,在词和句子层面上好像既不忠实也不对等,但在整体效果上可视为对原文的动态忠实。
2.2 或然性转喻
或然性转喻指原文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潜在方法,译者不一定非要采取转喻法,因为译者对源语语篇理解或处理方法上的局限性,或为了达到某种美学效果而采用的转喻手法。
局部性:(3)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许渊冲译)
其中,Snow bends the bough.便是“雨雪霏霏”的转喻,是明显的联系和创造。众所周知,诗歌中形式是非常重要的,译者为了押韵效果(押au韵)对译文进行调整,一改原文的动态意象为静态意象,使译诗达到了“音美”和“形美”的目的。
全局性:(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林语堂译)
这是全局性转喻,译文和原文在文字层面上不对应,意境再造靠的是头韵和词的叠现。
3.转喻在翻译中的功能
转喻与语言的表征性是默契的,是合理的交际手段,因为它的本意就是以部分代整体,如“新面孔”代“新来的人”,或以此物代与之相关的彼物如“锅开了”代“锅里的水开了”。铁木志科认为,翻译也不例外,翻译这个局部的背后体现了整整一个文化,译者对译文的摆布,反映出了一个时期文化的走势与特征(林克难,2001:158)。
3.1 逾越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可以体现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言特点不同,文化意象迥异,文本类型的复杂多样、译者的审美和感悟力的差异、两种语言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各异等因素,致使翻译中存在无法理解、不能传达的现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运用“转喻”来表现这些难以逾越的固性特征。
在语言特点方面,每种语言都是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符号系统,都有另一种语言难以传达的成分;转喻是因不能逾越语言类型特征而采取的必然的变通手段,并根据语境决定保留或改写原作中的某些成分。如:
(5)三个人品字式坐了,随便谈了几句。(《子夜》)
The three men sat down facing each other and began casually chatting.(许孟雄、A.C.Barnes译)
句(5)汉语中特有的形象词语在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表达,翻译时通过运用转喻中的联系手段将其语义传达出来。
汉语中有许多表示具体概念的词语往往表示某种泛指或引申意义,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同的表达,翻译时可通过转喻创造.性地体现出其引申意义。如:
(6)爷们儿怪罪下来,大不了我一个人拉着家小逃之夭夭,可天津卫还有我的老宅院,还有我的姑姨叔舅,让人家受我连累,我对不起人。(林希:“天津闲人”)
Should the locals take umbrage,I can just disappear together with my family.But I have an old house and some relatives in Tianjing.It would be fair to implicate my relatives.I certainly don’t want to get them into trouble.(孙艺凤译)
英语中没有具体的下义词表示“姑姨叔舅”,所以在译文中没有精确对应的表达,句(6)译文中,译者通过运用转喻将其泛指意义再现出来。
就文本类型而言,艺术性高的文本具有很强的抗译性,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态的话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翻译都有不同程度的操纵,以适应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心理。如被视为“性戏剧”的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剧中有一句话(赵彦春,2005:81):
(7)En me dido ten cheira,tes sathes age.
(7a)要是他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拉住他的阳具吧。(孙致礼,2001:20)
(7b)要是有人不肯把手伸给你,就牵住他的鼻子走吧。(西基,1902)
(7c)女士们,拖着他们的手吧;要是他们不愿意,那就随便拖什么都行。(费茨,1954)
(7d)要是他们不肯把手伸给你,就温文地拖他们的生命线吧。(迪金森,1970)
以上四种译文,(7a)为直译,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性戏剧”施乐于众的特点,但很难被受到几千年礼教文化熏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为了避免“有伤风化”,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译文(7b)、(7c)、(7d),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操纵,转喻的运用虽背离了原文的字面意义,甚至否定了“性戏剧”这一根本性命题,但却迎合了大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使译文得以承认和接受。
就译者主体而言,由于受其语言能力和感悟能力的限制,译者对相同语言的解读和感悟不同,翻译时表现出不同的释解和表达倾向,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贾芸对卜世仁说:
(8)巧媳妇做不出没有米的粥来,叫我怎么办呢?
(8a)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杨宪益、戴乃迭译)
(8b)...And 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David Hawkes译)
杨先生和夫人的译文保留了中文的意象,旨在将中国的文化元素传递给英语读者,而David Hawkes运用了转喻手段将“米”、“粥”创造性地译为“flour”和“bread”,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迎合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虽然在语言形式上做了调整,但整体上还是忠实传达了原文意义。以上译例有力地证明了由于译者的知识结构、解读和感悟能力不同,各自都在整个理解、阐释和表达过程中通过运用转喻策略发挥了联系和创造性作用,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译文,从而逾越了可译性限度。
3.2 弥补可证性限度
语言具有不完备性,不能把描述对象一切都准确无误的记录下来,读者只能进行见仁见智的阐释,这种不完备性决定了语言的意义潜势,因此也就产生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对于译文正确与否的论证标准也必然受到限制。语言的不完备性还在于自身的演变,由于时代久远就可能出现可证性限度问题,比如“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在没有被证实为“井栏”之前,我们都把它理解为现代意义的“床”,几乎都译为“bed”或“couch”:
(9)床前明月光
(9a)I descry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my bed.(徐忠杰译)
(9b)Abed,I see a silver light,(许渊冲译)
(9c)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Tr,Witter Bynner)
(9d)I saw the moonlight before mycouch,(Tr.S.Obata)(冯庆华,2002:417-418)
文化翻译中可证性限度问题普遍存在,因此,译者须根据文化语境和已有知识适当发挥创造性想象进行翻译。请看下面例句(黄振定,2001:30):
(10)《老子》第七十一章开头有文曰: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湖南出版社“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老子》(1994)读作:
(10a)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最好;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缺点。(陈鼓应)
To know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best.
To think one knows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a dire disease.(Arthur Waley)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5)中与这一英译对应的却是: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该书还列出了:
(10b)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To know the unknowable,that is elevating.
Not to know the knowable,that is sickness.(Carus)
(10c)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To be aware of one’s ignorance is the best part of know -ledge,
While to be ignorant of this knowledge is a disease.(W .Gorn Old)
(10d)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To know ,but to be as though not knowing,
is the height of wisdom.
Not to know,and yet to affect knowledge,
Is a vice.(Lionel Giles)
(10e)(以)知(为)不知,上。(以)不知(为)知,病。
To regard knowledge as no knowledge is best.
To regard no-knowledge as knowledge is sickness.( 吴经熊)
由例(10)可以看出,在读译中同样出现了可证性限度的现象,年代久远使人们无法考证其精确含义,恰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Derrida)所言,古人(老聃的)早已死去,他沉默不语,无法言说,那写下的、流传的《老子》的文字远离了(老聃的)言说,更远离了(老聃的)思想意识,毋宁说“背叛”了它们(黄镇定,2001:31)。读译之间差别,读译与原文的断裂,使老子的本意根本无法追寻,译者只能通过借助转喻手段,结合文化语境和自身的知识积累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尽量弥补由历史的沉淀造成的可证性限度。
3.3 服务于政治目的
英国社会学家米歇尔·芭蕾认为:若把语言看作建构意义的过程,那么翻译的政治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了(谢天振,2000:76)。在后殖民环境下,翻译是在多语、多文化的条件下发生。在这样一个多文化、多语言而又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译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行动,翻译的作用与翻译的内容一样重要,翻译的环境与翻译的文本一样重要(Tymoczko,1999:62-65)。古爱尔兰语英雄传奇作品的翻译在爱尔兰有着十分奇特的地位,它成了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需要的精神支柱,促成了爱尔兰1916复活起义。在爱尔兰翻译传奇故事的实践中,“忠实”已不是翻译的标准;翻译内容的取舍,完全取决于怎么翻译才能够达到既定的政治目标。爱尔兰英雄库秋林的英雄事迹主要体现在传奇故事《偷袭牛群》里,他是以强悍、凶猛、面目怪诞、好斗善战的形象出现的,每次战斗之前他都会七十二变,变成凶神恶煞的模样。奥格兰地(Standish O’Grandy)翻译的目的是鼓舞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如果亦步亦趋“忠实”地去译,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相反,“忠实”翻译所传达的形象倒是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人的印象十分吻合。在当时殖民主义者眼里,爱尔兰人嗜好暴力,好斗、易怒、性格粗暴、动不动就寻衅滋事。于是奥格兰地在他的译文里大胆果断地把这些细节悉数略去不译,把库秋林渲染成一个中世纪骑士的英俊模样。正如铁木志科指出的:翻译爱尔兰传奇故事的历史——或者说爱尔兰传奇故事的非翻译或部分翻译的历史证明,翻译为爱尔兰民族政治的成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Tymoczko,1999:83)。这里的“部分翻译”就是转喻策略在翻译中的运用,译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求,发挥了联系和创造的作用,略去了凯尔特语的形式特征,一方面尽量使译文贴近欧洲文学的规范,使英雄史诗得到主流文化的接受,一方面尽量保持《偷袭牛群》内容上的奇特性。
3.4 表征译语文化
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指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在两种文化交往时,我们往往会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去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当需要行动时,我们也以自己的行为模式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行动。这就往往会造成文化误解。”(郭建中,2000:281)转喻的运用有时能反映对另一种文化有意的误解与误释,表征译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观。如:玄奘译佛经,以忠实确切著称,但是日本学者中村元则指出,佛法禁止纳妾,而受儒家观念影响的玄奘视纳妾为当然,因此把佛经里的“妻子”译成了“妻妾”(谢天振,1999:6)。
由此可见,即使在两个东方古国间的文化交流尚且产生了沟通上的“阻滞点”,那么在差异更大的东西方之间,加上历史发展阶段先后的错落,又是涉及“性”这一最敏感的区域,译者就更需要运用转喻来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以迎合译语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在决心死去的前夜,盼望夜色降临,好挂一条软梯在楼窗前,让她的心上人在流亡之前,爬进闺房和她度过难解难分的一夜;此刻她对着软梯发出如下感叹:“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方平认为:“思想本可以自由飞翔,何须借软梯牵引、做桥梁呢?”(谢天振,2000:82)查找原文,原文是:
(11)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
原文“to my bed”的含义很清楚,是“上我的床”的意思,但是“受到我国几千年礼教文化干扰的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译为得体得多的‘相思’,顾不得因而产生了经不起推敲的语病”(谢天振,1999:6)。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怎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要她心上人“上我的床”呢?朱译运用了转喻手段,略去了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规范部分,用“相思的桥梁”表达原意,这样处理避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忌讳”,表征了中国传统文化诗学观。
4.转喻的动态优选性
翻译行为本身是由变量组成的动态系统:源语文本是开放的,可以进行无限的阐释;翻译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可以进行无限的调变;译语读者反应是动态的,可以进行无限的解读。无论是从翻译的过程还是翻译作品而言都应体现出优选性,所谓优选性就是指译者尽量采用转喻策略,通过恰当的联想和创造使译文能动态地忠实于原文,趋于最优化以便“将读者拉近文本”。
4.1 顺应时代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译者知识结构的改善以及解读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翻译过程中创造能力的发挥也将趋于合理,并不断向原文趋同。
如前面所举的翻译爱尔兰英雄库秋林的英雄事迹一例,到了1969年,当金塞勒重译这本《偷袭牛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爱尔兰在美国的影响下,强调文化的个性与差异,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金塞勒把当年删掉的细节无一遗漏地统统翻译出来。并对爱尔兰民族史诗的五种形式特征给予了全面地再现。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在决心死去的前夜的那两句独白,到了90年代,翻译家方平将它们译为:
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
(谢天振,2000:82)
两个译者面对同一句话,却有不同的翻译,这是因为译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因为方先生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同一部作品的。具体地说,40年代译者在处理“登床”一语时所感受到的性忌讳和性压抑的民族心理,到90年代的翻译家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译者尽量按原文风貌再现原意,尽可能地使译文从意义内涵上忠实于原文。
4.2 趋同证实性
随着人们考察问题的角度的改换和读者视野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从原来简单的译文阅读转移到阅读原文,查读难句的翻译,仔细品味异域文化的层次上。一些曾经被证伪的问题得到了证实和说明。
众所周知,半个多世纪前赵景深把Milk Way译成了“牛奶路”,从此赵译“牛奶路”就成了中国译坛的一个笑话。然而,如果我们从传递文化意象的层面上考察一下赵译“牛奶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赵译“牛奶路”倒是基本正确的,而被我们视为比较正确的译文,如:“银河”,“天河”等,却颇值得质疑。因为在文学翻译中,Milk Way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天文学术语,而是一个文化意象,在它身上聚集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对欧洲民族来说,只要一提起Milk Way,他们就会想到这是聚集在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下山的“路”,也是朱庇特获胜回朝的必经之“路”。因此,把Milk Way翻译成“河”,即使是“天河”,也意味着无异是断了他们的“路”,那些美丽的希腊传说将无从说起(谢天振,1999:176)。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封闭状态使当时的读者对异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是在情绪上也格格不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读者综合素质的提高,译者也调整了理解和接受的心态,因此也相应的调整了转喻手段的运用,使之趋于最优化。
5.结语
Maria Tymoczko(1999)提出的独到的望远镜与显微镜的观点,即宏观的文化研究与微观的语言学研究,就好比是前者借助于望远镜后者借助于显微镜对翻译进行研究,两种研究的方向或角度其实并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林克难,2001:157)。本文通过将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其转喻功能,阐明了文化翻译中转喻运用的合理性,论证了它在动态翻译系统中的作用,即为了动态、辩证的“忠实”和“对等”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转喻在翻译理论中应有其合理的定位,只有将转喻和隐喻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翻译才能动态忠实地再现原文思想。
[1]Berman,A.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Cultural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M].trans.by S.Heyvaer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Tymoczko,M.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9.
[3]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4]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5]黄振定.语言、思维和翻译:矛盾与统一[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8):30-33.
[6]李欣.翻译的换喻过程——Maria Tymoczko教授论翻译[J].福建外语,2001(4):42 -46.
[7]林克难.文化翻译研究的一部力作[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2):156-158.
[8]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9]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1]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2]赵彦春.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J].外国语,2003(4):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