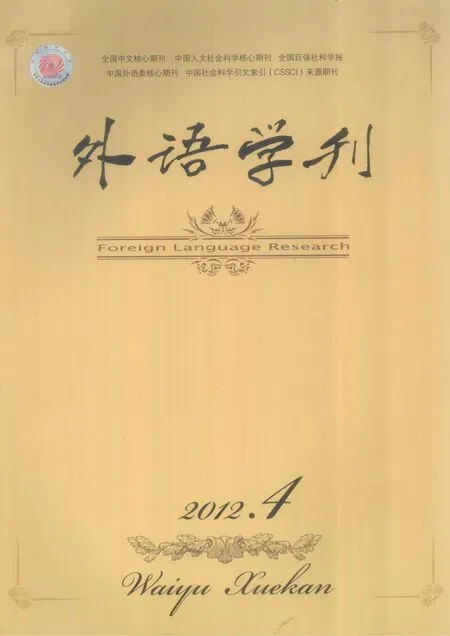论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中的“经验证实”
杨晓斌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401331)
1 引言
在意义证实论中,维特根斯坦对经验证实的考察与逻辑证实同步展开,其初衷是检验前期“图像论”对命题的语义要求。经验证实就是将符合句法要求的命题投入经验事实中,进一步考察命题能否获得其陈述内容的经验对应物,从而验证命题的意义是否具有“经验的可能性”,洪谦把这种验证称为“事实的答复”(洪谦1989:9):“一个命题所表达所叙述的事实能否由经验证实,就是这个命题之为真为假或有无意义的标准”(洪谦1989:6)。
经过逻辑证实的反思,加上经验证实的“经验要求”,维特根斯坦对经验证实的研究在日常语言中展开。讨论初期,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可以用逻辑分析日常语言达到证实目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指示性的解释及其依然处在语言之中,与此完全不同。这里不存在与事实相映证的符号”(维特根斯坦2003a:185)。也就是说,在经验世界中,逻辑分析得出的基本命题或记号失去指称——命题不能反映事实,只能反应事实。这就决定经验证实某个命题的主要方式是“观察与比较”,“命题与事实之是否一致,仅有从观察中判断,从证实中证明”(洪谦1989:9)。这种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的动态考察表明,中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意义的探索逐步向后期思想过渡,意义证实论就是意义使用论的前身。
2 证实方法
经验证实的目的是排除与事实脱离的句子。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句子如果被理解为它可能是不可核实真假的,那么这个句子就完全与事实相脱离,并不再作为句子起作用”(维特根斯坦2003b:275)。也就是说,语句只有在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或经验与之相符或不符的时候才有意义。他对经验证实方法的讨论并未囿于“如何通过直接观察证实某个句子有意义”,而是从宏观上通过“语言”和“人”两个维度回答:语言怎样被事实验证。
从“语言”出发,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判断,“我们的句子只是由当前来验证。它们必然是这样构成的,即它们能够被当前所验证”(维特根斯坦2003b:66)。他甚至认为,“为了能够被当前所验证,句子必须具有某种能力。这样,它们就以某种方式与当前有了公约性”(维特根斯坦2003b:99);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将无法交流,信息将无法传递。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断言,“事实的验证作用对于语言来说是本质的”。他设想某个人向他提问:“你从哪知道,全部的现实都可以由句子来表述?”随即作出回答:“我只知道,只要它能由句子表述,它就可以由句子表述,而且在语言中,我不能在可以这样表述的部分和不可以这样表述的部分之间画一条界线”(维特根斯坦2003b:202)。就是说,句子表述现实,语言是句子的总和,不存在不能表述现实的句子,所有句子都可以验证,事实验证天然作用于语言。总之,“语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联系”(make contact)(维特根斯坦 2003b:274),事实是经验证实的可靠保障。
维特根斯坦从“人”切入,发现语言描述事实,但这种描述具有一般性——句子只能通过我们的直接经验证实其陈述内容的“某一方面”来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句子与事实相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多少有点松散”(维特根斯坦2003b:202)。比如,当我们只看见软椅的一个侧面时,我们就说“这儿有一把软椅”。“在极端的例子中(例如某些否定句——引者),联系不复存在,事实可以肆意孤行而不与句子发生冲突”(维特根斯坦 2003b:202)。那么难道说句子失去意义吗?对此,维特根斯坦昭示“全部重要之点”与“全部必要之点”。前者在于,符号不管以何等复杂的方式存在,最终总要与直接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一个中间环节(一个自在之物)相联系……”(维特根斯坦2003b:203)。也就是说,符号或基本命题总是直接指称现实,它们之间的联系无需任何中介,这是人对语言的约定,它构成经验证实的前提。此外,“要使句子有意义”也就是能够被经验证实,后者在于,我们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与这些句子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人的直接经验的有限性决定,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会主动掌握对其作出规定的“特权”,因此当我们只看见软椅的一个侧面时,我们就说,“这儿有一把软椅”。因此,“人们可以对能够通过事实进行检验的一切作出断言”(维特根斯坦2003b:274),并且这种断言无需中介,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使用语言的”(维特根斯坦2003c:19)。
如石里克所言,“证实是真理的标准,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须要强调,虽然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怎样可以决定这个句子是真是假”(陈嘉映2003:50)。真理的确与意义紧密相关,但是“通过经验可以判断的是句子的真或假,而不是它的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b:50)。判断命题内容得出的真或假是经验证实的结论,而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证否的命题已经具备可证实的性质,即意义,意义并不经过判断得出。可见,维特根斯坦此时已经放弃把真理标准等同于意义标准的观点:“人们可以说:哲学不断地收集句子材料,而不关心其真假。只是在逻辑学和数学中,它才只致力于'真'句子的探求”;“证明并不是对真理性的一种宣示,而是命题的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b:191)。可见,证实不必求真;哲学不必求真。要获得命题的意义,只须知道它的证实方法,也就是“怎样可以决定”命题真假的方法,而不须知道命题究竟是真是假。维特根斯坦举出例子进一步说明,“测量的方法,例如空间测量的方法,与某种特定的测量的关系就像一个句子的意义与其真假之间的关系一样。尺度的使用并不以被测的客体的长度为前提……由此我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学会测量,而不必去测量每一个可测量的客体。我唯一需要的是:我必须能够肯定,我会应用我的尺度去测量”(维特根斯坦2003b:63)。这段话深刻体现出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到中期的思想变化:“测量的方法”即命题的证实方法,它显然是对逻辑要求的“某种特定测量”的释怀与超越;“可以测量”才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而“被测的客体的长度”(测量结果)并不决定意义,甚至可以说与意义无关。与“图像论”和逻辑证实相比,经验证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挣脱意义确定性的枷锁,破除真理的迷信。此时,维特根斯坦已经沿着他的“梯子”爬到更高处,其视域变得更加开阔。
3 证实困难
面对广阔的经验世界与丰富的日常语言,经验证实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它们与“观察与比较”的证实方式以及语言与事实之间的“松散联系”共同作用,造成经验证实的一系列困难。经过笔者的初步归纳,这些困难主要包括:第一,如何处理证实方式的多样性;第二,如何处理物理学命题(假说)的证实;第三,如何证实观察者从未有过的经验(包括“启示”、“无限性”等概念)。针对以上困难,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由强转弱”的作法,作为推动哲学语言转向的领头人(洪谦1982:7),维特根斯坦牢牢把握住意义的承载者——语言。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证实困难的探索就是利用语法分析解决哲学问题的初步尝试。这一部分内容在维特根斯坦的证实论中所占比重最大。下面,将围绕证实困难的以下3个方面讨论:
(1)经验证实中,证实方式的多样性主要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人经验的“多样性”引起。前一种情况如“这是黄色的”。在逻辑语言中,它显然是不可怀疑的“基本命题”。然而,“‘黄色的’在实际生活中与在物理学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关于黄色的命题通过观察来证实,而在物理学中则通过测量波长来证实”(维特根斯坦2003a:162)。后一种情况如“赛茨曾被选为市长”。维特根斯坦说,“我究竟应如何着手去证实这一语句呢?正确的方法是否就是:我上街向别人探问?或者我去询问当时在场的人们?一种方法是从前面看问题,另一种是从后面看问题。或者我应通过阅读报纸来证实?”(维特根斯坦2003a:16)。可见,与日常语言和经验世界发生关联的命题,呈现出证实方式的多样性,而证实方式的变化自然会引起意义的改变。
对于第一种情况,在经验证实初期,维特根斯坦似乎不以为然:“同一语词,在以不同的方式被证实的命题中,就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就是使用了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也只是偶尔具有共同的记号”(维特根斯坦2003a:121)。就是说,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命题的证实方式,需要不同方式证实的命题必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们由不同句法规则组织而成。这样,“当我们推导这一命题的时候,我们早已按照不同的规则来作了”,它的“证实方式”的“出发点”已经不同,该命题本身已经具有“一种不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a:144)。可见,维特根斯坦此时依然将句法规则视为不变的标尺。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认识到,句法规则也要服从于人们对语词或句子的不同理解,甚至作用于精确的数学语言。例如,他曾与魏斯曼讨论如何证实“线段AB如许长”这一命题。维特根斯坦指出,“这完全要视人们如何理解‘测量’一词而定”(维特根斯坦2003a:162)。这就是说,人们对“测量”的不同理解决定将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测量,即选择何种句法规则去规定命题的证实方式。他接着说,“如果我把'测量'理解为重复摆尺、目测和确定相符的过程等等,那么我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报道,经验的事就是看结果是否一致。另一方面,如果我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基础,又用句法固定的语言来描述测量结果,情况就与之相反”(维特根斯坦2003a:162)。由此,我们的理解决定语词用法的不同情况,每一种情况对应着命题的一种句法规则,不同句法规则为证实选择不同方式。维特根斯坦在对这一问题的总结中将“句法规则”换成“语法”:“如果我把'空间'理解为视觉空间的话,那么几何学就是我用以描述这些现象的词语的语法。但是如果我把'空间'理解为物理空间的话,那么正如物理学一样,几何学就是一种与测量经验有关的假设”(维特根斯坦2003a:162)。
对于第二种情况,经验的多样性似乎决定命题的证实方式要在多样的经验中选择,这就引发了“命题能否得到充分证实”的问题。调查显示,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到1931年间主要持强证实原则。他主张,“如果我不能充分证实语句(命题)的意义,那么我就不能用语句来指任何东西。于是,语句也就没有任何意谓”(维特根斯坦2003a:16)。然而,维特根斯坦后来也承认,“何时能充分地证实一语句,是没有保障的”(维特根斯坦 2003b:129)。维特根斯坦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毕竟他更加关心语言,而不是经验。
(2)在经验证实中,维特根斯坦注意到一种比较特殊的陈述:它们有意义,因为它们可证实;然而,它们不能被确证,因为它们描述的是对其证实不能穷尽的经验。这类陈述主要由物理学命题构成,维特根斯坦将它们与一般的现象学命题区别开来,统称为假说或假设(hypothesis)。“一个命题可以被证实,一个假设却不能。”(维特根斯坦2003c:26)举例来说,物理学陈述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表述。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规律比其他规律更为可信,因为它们经常被证实可靠;然而,区别于现象学命题的是,“自然规律决不仅仅是对至此所做的观察的概括。我们只能说,它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或许'是真的(假的)”(维特根斯坦 2003a:210)。“或许”在这里体现一种概率——自然规律不能被确证,因为人们“没有表达这种在数量上的差别的测量手段”(维特根斯坦2003a:63),而一个陈述(现象学命题)只能是真的或是假的——它要么被证实,要么被证伪。维特根斯坦指出,物理学陈述之所以不能被确证,是因为它们构建假设系统,而我们对这些假设的证实却并非由观察所能穷尽。被证实的现象学陈述是真的或假的,它们是对现实的表述,其真值具有稳定性;而物理学陈述既不能是真的,也不能是假的,因为物理学不是对迄今为止人类所有观察经验的概括,它不是历史,它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与未来的关联——物理学的目的是预见。因此,假说从来不会被证实,“人们永远保留让它们失效或者改变它们的可能性”,假说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指示了无穷的未来”(维特根斯坦2003a:64)。
他得出结论,假说与现象学命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语法:虽然假说同样是关于感觉事实和直接经验的描述,但是它的语法即我们使用它的目的,是通过事实总结确认规律;相比之下,我们对现象学命题的使用则是为了确认一种可能性。我们虽然说出一个假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是“力求一个非假说式的表述”(维特根斯坦2003a:276)。我们容许它在将来被证实,“因而它产生了一种期待”(维特根斯坦2003a:278)。这就是假说的本质,这种本质决定我们对它的证实永远不会终结。
(3)经验证实的主要方式是观察与比较,这就需要观察者及其观察经验作为“证据”。然而,经验的无限性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发生矛盾。比如,维特根斯坦设想一种人们可以认识但却无法经验的东西,他将这种东西称为“启示”(implication)。维特根斯坦说,“只有在具备解答方法的地方,才有问题。这意味着,在那些只能期望某种启示性解答的地方,也不会有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与一种启示相对应。这就如同人们想对一种人们还不具有的感觉经验提问。人们也不能去寻找一种新感觉(感官感觉)”(维特根斯坦2003a:161)。类似“启示”的东西无法证实。事实上,语言经常言说人们从未有过的经验,使这样的语句陷入无法证实的境地,难道这样的语句就没有意义了吗?!为解决这一问题,维特根斯坦通过分析“无限性”等概念又一次将证实引入语法范畴的讨论。
在《哲学评论》中,维特根斯坦以专题形式细致讨论“无限性”(维特根斯坦2003b:294)。讨论是从他对拉姆塞(F.P.Ramsey)的反驳展开的,“有一次我说过不存在延伸的无限性。拉姆塞接着说:‘难道不可以想象,一个人永远活着,简单说就是永远不死,这难道不是延伸的无限性?’然而我确实可以想象,一个轮子不断地旋转,而且永远不停下来”。维特根斯坦挖苦道:“多么稀奇的论据:‘我可以想象!’”这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在这里似乎成了证实的根据,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显然不通:“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可以把哪一种经验看做对此的证实或证明,即这个轮子永远不会停止旋转”。可见,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在这里遭遇经验的碰壁,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此时面临的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语法分析。于是,他接着说,“让我们把这种经验与使我们知道这个轮子会转一天、一年、十年的经验比较一下,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永远不停下来’和‘一百年以后停下来’这两种说法之间的语法区别”。维特根斯坦将人们无法经验的“无限性”还原至语言中,与“有限性”进行对比分析,在语法中考察“无限性”的特别之处。
按照经验证实的要求,要实现对“无限性”的证实,我们首先要理解含有“无限性”这一概念的语句,由此找到与这一概念相联系的全部经验。然而,“无限性”显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概念,维特根斯坦这样描述:“‘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无限的树行?’当然可以,如果我们已确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概念与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与为我们确定了树行概念的经验联系起来的话……”;“我们有一种经验,当我们沿着一行树走时,对这行树我们可以说行列终止。而一个无尽头的树行却是我们永远不会有这种体验的行列”。应该注意,维特根斯坦多次提到一个能够代言“无限性”的关键词“永远不”(never)。“‘永远不(从来没有)’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一种用这个词来描写的经验:‘他在这一个小时中一次没有咳嗽过’,或者‘他在一生中从来没有笑过’”。经过语法考察,维特根斯坦注意到,在含有“永远不”这一概念的命题中,能够被经验证实的必然涉及一个时间定域。时间定域为含有无限性概念的命题圈出有限的考查范围,在此范围内才能谈论经验。对不涉及时间定域的命题,他强调“必须重新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使‘从来没有’这个词用得有意义。——我们当然可以找到这种使用,但是我们必须专门根据它们的规律去研究它们”(维特根斯坦 2003b:296)。可见,维特根斯坦此时已承认,不可证实不等于没有意义,并且意义显然同语法密切相关,而证实原则只是“我在使用命题之前对命题的一种承诺(determination)”(Wittgenstein 2003:117),证实方法只是弄清语法的一种手段。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得到澄清:“问一个命题是否和怎样才能得到证实仅仅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问‘你是怎么意指那个的?’对此的回答是对该命题语法的一种贡献”(维特根斯坦1996:169)。
4 证实反思
在经验证实中,维特根斯坦对证实方法与证实困难的探索真实记录他从中期到后期的思想演变:对证实方法的研究使维特根斯坦破除对真理的迷信,进而使意义挣脱确定性的枷锁。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对假说以及“无限性”概念的研究让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认识到语言的多样性以及语法的基础地位,进而将意义与日常语言用法紧密结合,通过语法分析消解证实难题。他在对“无限性”问题的总结中强调,对于人们经验上无法证实的概念或命题,必须要根据它们的使用规则作专门描写,因为类似于“永远不”这样的语词并不是仅有一种有意义的用法,而“每一种使用都有其自己的规律”(维特根斯坦2003b:296)。对于假说,他指出,“我们所涉及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句子(或者说具有另一种意义的句子)”(维特根斯坦2003b:296)。他得出结论:“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找到现成的表达形式,这是不够的,因为日常语言中每个词的用法具有极不相同的意义,我们理解这个词在一种情况下的使用,并不能省却我们对这个词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时的语法的研究”(维特根斯坦2003b:297)。石里克曾说,“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证否)这个句子的方式”(洪谦 1982:39)。不难看出,意义证实论本身就孕育着意义使用论的种子,而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标志着它的萌芽。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对证实方式多样性的思考使意义摆脱了句法规则的束缚,这也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的理解对语法的导向作用。值得关注,证实方式的多样性不同于无法证实的概念或命题。后者包含我们对经验世界的普遍认识,而前者在经验判断上却带有一定主观性。罗素甚至认为,这种主观性就来自“可证实”这一概念。他说,“'可证实'(Verifiability)与'真实'(Verity)不是一样的东西;前者比后者更是主观的,更是心理的。如果要使一个命题是可证实的,不但必须这个命题是真实的,而且必须这个命题的真实可以为我们所发现。所以,可证实乃是依靠我们的知识本领,而不依靠客观的真实”(罗素1982:184)。可见,在罗素等人看来,证实论中的意义似乎就是主观臆断的产物。
其实,从逻辑证实到经验证实,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停止对意义产生机制的探索,这也提供了考察维特根斯坦思想演变的另一个视角:在“图像论”的意义观中,人的思想就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意义就体现为命题符号与事实要素的一一对应;在逻辑证实中,维特根斯坦从“理解”出发,在强调句法的同时,将意义与人的理解联系起来。在经验证实中,维特根斯坦更深刻地认识到,是人的理解决定命题的意义。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的考察显示“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逐步参与语言与世界的互动。因此,一些认为中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走向“唯我论”的学者其实曲解了他的深意:维特根斯坦并非以“我”为视角,论述“我”对命题的证实或是“我”对语言的使用,而是从“人”出发,强调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并列于语言和世界的本体地位。他说,“只有对于一个活着并且具有人类行为的人,我们才能说他有无感觉、有无视觉、有无听觉或是有无意识”(Cook 2006:117)。这一思想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5 结束语
经验证实以逻辑证实为基础,初步尝试通过语法分析解决意义问题。因此,中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如下:第一,将意义研究引向语法,消解了意义证实论在其本质上难以规避的困难;证实不单是对语言的要求,在意义的生成机制上,对现实的考察始终是证实思想的应有之义。而语法考察将语言和现实有机结合并将意义的生成交付于语言本身,这就消解了证实对经验的现实要求——语言本身的“自救能力”(李洪儒2009:8)使证实对语言工具性的考察变得不再必要。第二,经验证实承接逻辑证实对意义的实证性考察,完成向后期维特根斯坦“游戏论”意义观的过渡;伴随意义证实论发展的是语言地位的逐步提升,这促使纯语法分析超越与事实世界相照应的语言证实成为考察语词意义的最直接、最根本方式;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切语言的意义都在于使用语言的活动;意义使用论因此成为“游戏论”意义观的内核。可见,“游戏论”意义观建立在经验证实对意义的语法考察基础上。第三,经验证实突显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倾向,他在此基础上将意义考察引入语言的生活世界;通过语法分析获得语词意义的研究方式依靠语言本身的建构与运作,这种研究方式将语言视为能够自给自足的特殊在者/是者,即语言本体。上升为本体的语言通过其实际用法融入经验世界;经验证实在研究语言的同时,回到“语言的生活世界——话语或言语”(索绪尔1999:10)——语言的日常使用中。而“日常使用中的言语具有特殊性、个体性、现实性、变异性,它们与个体人对语言和言语的使用、构拟、解读相联系”(李洪儒2010:22)。这样,维特根斯坦对经验证实的研究不能脱离使用话语或言语的主体——人。他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语法的正是人对语言的理解,人的地位在生活世界中甚至超过语言——这种人本思想的潜出为后期维特根斯坦“人本主义语言存在观”(李洪儒2006:29)的形成埋下伏笔。因此,意义证实论在衔接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意义理论的同时,完成它最重要的使命——将语言和意义引向生活,引向人。
洪 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李洪儒.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J].外语学刊,2006(2).
李洪儒.言语行为间接意向的语言哲学批判[J].中国俄语教学,2009(2).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外语学刊,2010(6).
罗 素.“我们对于外间世界的知识”[A].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C].北京:三联书店,198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意义和证实”[A].洪 谦.论逻辑经验主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二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a.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三卷:哲学评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b.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五卷: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c.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John,W.Cook.Human Beings[A].In Peter Winch(ed.).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C].London:Routledge Press,2006.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Remarks[M].New York:Barnes& Noble Books Press,1975.
Wittgenstein,L.et al.The Voices of Wittgenstein:The Vienna Circle[M].London:Routledge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