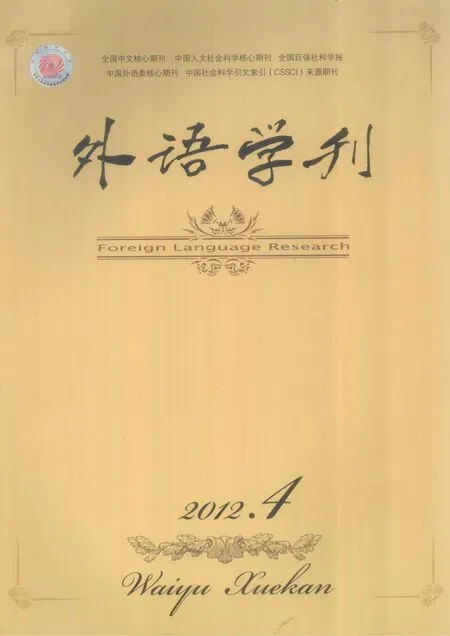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解读《犀牛》的荒诞主题*
王 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150040)
1 引言
就其本质而言,戏剧演绎人生哲学。如“在悲剧中,主人公具有激情、理想、欲望、创造力和抱负,然而他们和周围环境中的神秘力量发生矛盾,处于困境之中,经历内心矛盾和精神痛苦。这种个体性格特征和周围环境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廖金罗2009:184)。
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的理性社会架构与传统的价值观以毁灭性打击。“在意识到永远失去以往同上帝的联系之后,人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茕茕孑立。于是,世间的生存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和荒唐的表演。在这幕与人作对的戏剧中,人成为命运摆布的玩偶。现行的法律、种种道德准则迫使每一个个体在全人类荒唐的剧院里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任何一种对现实世界法则的反抗都将受到死亡的惩罚。”(戴卓萌 2012:128-129)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为荒诞派戏剧提供了理论基础。荒诞派戏剧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盛极一时,被称为“反戏剧”的先锋派戏剧。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基本戏剧冲突。对白逻辑混乱,词不达意,人物纠结于自身的存在:我是谁?“当然,你可以对你的个性、爱好、信仰或者人生追求描绘一番,最后总结道:‘这就是我’。”(陈杰 2009:1-2)然而,在强势的大众文化侵蚀下,人逐渐丧失自我,最终丧失理性与是非的判断力,成了千人一面中的一份子。就像二战期间的欧洲,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文明的、以理性社会自居的欧洲肆虐,善良的人变成恶棍,甘心情愿变成法西斯的走卒。这一切是所谓人的理性所致还是人本身对他人生命的蔑视,抑或就是人的悲剧?荒诞派的代表作家尤内斯库在其作品《犀牛》中,以独到的视角解读了人存在的荒诞与世界的荒诞。以一副混乱不堪、绝望、荒诞不经的末日景象演绎存在主义关于人生存的荒诞命题。
2 存在主义与尤内斯库的《犀牛》
尽管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有许多争议,甚至互相否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的存在是孤独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悲剧性的。
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创造了人的概念,在此之前,人的存在不存在。而且,不论是从宗教还是世俗的角度看,存在主义者都反对将所谓的人性归因于事物的因果”(Myerson 2002:50)。人的存在既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由外部影响力创造的。人,只有决定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后,才使人作为有人的本质的存在。萨特认为,“自我和世界都是在意识的活动中,即在意识的虚无和否定过程中产生的。现实世界的人试图逃避虚无和否定,所以进行自欺,呈现出与自身并不同一的非本真生存状态。因为他人与我都是具有自由意识的主体,因此,自由受到他人存在的处境限制,相互之间必定发生冲突。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是这是在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纷争之中的自由。因此,荒诞是人类在与格格不入的世界中任凭摆布的、极度苦闷的状况下产生的意识结果,这种苦闷的郁积令人呕吐,感到恶心”(李元 2007:118)。荒诞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
他极为关注异化问题。“作为哲学概念的异化,其含义是指主题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而反对主体本身。”(李元2007:121)
加缪在《局外人》中向我们描述一幅现代社会人“异化”的机械生活画面:“起床、有轨电车、4小时办公室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节奏,循环往复。人类创造的社会机器与物质文明最终会吞噬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意志,使人沦为社会机器与物的奴隶。流行的社会主流文明也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成为其追随者,最终丧失自我存在的价值。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
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肆虐欧洲,尤内斯库痛恨不已。他这样描写当时的处境和心态:“我周围的人像石头一样硬,像蛇一样危险,像老虎一样无情。人怎么能和老虎、眼镜蛇沟通呢?怎么能说服一只老虎、一头犀牛来了解你、宽容你呢?我们用什么语言和他们谈话呢?怎么让它们接受我的价值观、内心世界呢?”(黄晋凯 2008:78)《犀牛》(Rhinoceros)是尤内斯库创作的剧作中政治意图最为明显的一部。“此剧的意图就是要描写一个国家的纳粹化进程以及由于这种传染病的变态反应和集体精神变异给这个国家造成的混乱。”(黄晋凯2008:77)
《犀牛》讲述一个看似极为荒诞的故事,它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镇。小职员贝兰吉是一个窝窝囊囊、不修边幅的人。他厌倦平淡乏味的生活,却没有想过摆脱这种庸庸碌碌的日子。酒精成了他忘却烦恼的依赖。他的朋友让努力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并且喋喋不休地教导贝兰吉。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人变的犀牛。第一只犀牛的出现对周围人与物没有造成伤害,人们对此事半信半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犀牛,人们对变犀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变犀牛的行列,变成犀牛成了时尚和社会流行病。贝兰吉的朋友、上司、同事甚至恋人也乐此不疲,争先恐后地变成犀牛。贝兰吉是唯一保持清醒与理性的人,他拼命抵抗着别人传染给他的相应欲望,一直让自己相信人比犀牛美丽。该剧在贝兰吉的呐喊声中结束:“Oh well,too bad!I will take on the whole of them!I will put up a fight against the lot of them,the whole lot of them!I am the last man left,and I’m staying that way until the end.I am not capitulation!”(Ionesco 1962:124)
尤内斯库表现的荒诞主题具有多重性。首先是人的异化问题。由人变成犀牛是人性到兽性的转变,这一看似荒诞的转变实则意味着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同时,人变成犀牛暗示着作者对纳粹主义风行欧洲的批判,是对荒诞人性的失望。其次,人的生存状态是焦虑和孤独的。无论是贝兰吉还是让们,都处在对自己、他人以及周围事物的焦虑状态中。他们之间的沟通似乎充满障碍。再次,世界荒诞、不可理喻,人也无助。在《犀牛》一剧中,构成社会权利机构的人物纷纷变成犀牛,甚至大主教也未能幸免。最后是人对存在的选择与对荒诞的抗争。存在主义一直以其对人生的悲观态度而备受谴责,无论是尼采绝对意志论的超人还是萨特选择的绝对自由,最终都指向人的终点——死亡。萨特的绝对自由选择看似尊重生命,却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加缪虽然指出对荒诞的抗争是人们走出困局的道路,但是结局难料。
3 犀牛的象征意义与人的异化
丑陋的、粗鄙的犀牛象征着残忍、丧失人性的纳粹主义。人变成犀牛象征人类丧失自身的品格和本性,屈从于兽性,而兽性也是人性中深深隐藏的、极为黑暗的一面。人在强大社会机器面前,最终走向异化。尤内斯库通过描写这个荒诞的演变过程,解读了整个德国被纳粹主义吞噬的过程。
在第一幕中,犀牛的第一次出现并没有对人造成伤害,人们也没有意识到犀牛是人变的,大家对犀牛的出现只是好奇,然后很快就淡忘了。第二头犀牛则踩死了家庭主妇的猫。新闻对此的报道也极度简单:“Yesterday,just before lunch time,in the church square of our town,a cat was trampled to death by a pachyderm”(Ionesco 1962:49)。当勃夫太太发现她的丈夫变成了犀牛,决心追随他的时候,人们的心被触动了:“It’s no more than her duty...She is a good rider”(Ionesco 1962:63)。人们对勃夫变成犀牛,不是困惑、恐慌,而是同情。勃夫是第一个被赋予人性的动物。这种不质疑存在是否合理的态度,是人们追随社会潮流的潜意识,也是人们对脱离大众文化的恐惧,究其根源是人恐惧孤独。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犀牛,从普通百姓到逻辑学家,从社会名流到红衣主教,变成犀牛成了社会时尚。狄达尔(Dudard)说:“I feel certain scruples!I feel it’s my duty to stick by my employers and my friends,though thick and thin… It is my duty to stick by them.I have to do my duty”(Ionesco 1962:108)。最终,善良单纯的苔丝也在强大的社会潮流面前放弃坚守:“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bsolutely right.It’s the world that is right— not you and me”(Ionesco 1962:119)。人放弃人性,转而变成充满兽性的丑陋犀牛,正是纳粹主义在掌握国家机器后,教化普通百姓的体现,也是人异化的集中表现。
在加缪看来,异化是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分离、断裂的状态,是人背离人的本性。尼采则认为异化是自己对自己意志力的放弃。萨特的自由选择是为异化进行辩护。无论是勃夫太太出于爱变成犀牛,法学家处于追随所谓的事业变成犀牛,还是苔丝仅仅为追随大众意志而变成犀牛,变成犀牛的选择终究是背离人的本性,选择兽性,最终走向人自我的对立面,掉入荒诞的异化陷阱。正如让所言:“It’s not that I hate people.I’m just indifferent to them — or rather,they disgust me;and they’d better keep out of my way,or I’ll run them down”(Ionesco 1962:76)。
4 贝兰吉的孤独与让的焦虑:存在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激烈的商业竞争无处不在,因而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原始、朴素、互相依赖的互助关系。立足于社会,意味着排斥他人,人因此而处在与他人的敌对状态。萨特指出:“他人即地狱。”孤独与焦虑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孤独与焦虑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与疏远感,在荒诞派戏剧中的表现是人物之间的交流障碍,人们经常断章取义或者答非所问。
如开场的时候,让与贝兰吉同时出现,而让却问贝兰吉:“Oh,so you managed to get here at last.”该句表现出让的焦虑,他似乎等了贝兰吉很久了。在第十页“Jean:late as usual,of course.(He looks at his wrist-watch.)Our appointment was for 11.30…I wouldn’t say that”一段对话中,让一直居高临下地指责贝兰吉,理由是贝兰吉总是迟到。但是,就像这次贝兰吉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迟到一样,让也无法推断出贝兰吉从前总是迟到。两人之间的地位不对等,让一直控制话语权。紧接着,贝兰吉提出喝点什么,让将口渴喝水的话题直接转换到贝兰吉的生活状况:“You are in bad way,my friend”(Ionesco 1962:11)。贝兰吉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反应过来,让又立刻批评贝兰吉酗酒,批评贝兰吉乱糟糟的头发、皱巴巴的衣服、肮脏的皮鞋等。当贝兰吉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生活无聊的时候,让则宣称自己有毅力:“I’m just as good as you are;I think with all due modesty I may I’m better.The superior man is the man who fills the duty.”让以自己有责任感,比贝兰吉谦虚自居。让自顾自地表明态度,完全没有顾及贝兰吉的感受。在《犀牛》中,随处可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越是熟悉的人,到头来变得越是陌生。就像贝兰吉的同事与朋友不顾贝兰吉劝阻,纷纷加入变成犀牛的行列。唯独剩下贝兰吉一人独自面对陌生、荒诞的世界。贝兰吉注定孤独,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犀牛,没有谁能听懂他的心声。在本应属于人的世界里,贝兰吉反倒成了怪物。这就是人存在的荒诞。
而让的焦虑则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贝兰吉到底迟到多少次无从考证。但是,让的心理有阴影,由此是否可以推断他的朋友贝兰吉经常使他处于焦虑状态?如果是,贝兰吉何以使他焦虑?在犀牛第二次出现后,大家争论犀牛有几个角的时候,贝兰吉逐渐成了对话的中心,而让则显然失去了主动权。人们越是向贝兰吉求证,让的插话越是文不对题,最后让干脆暴跳如雷,拂袖而去。在让与贝兰吉的对话中,让逐渐暴露出内心对贝兰吉智慧的恐惧。虽然让一再使自己相信贝兰吉笨嘴拙舌,头脑糊涂,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贝兰吉思维敏捷,知识渊博。同样,让批评贝兰吉的生活,说他一到周末就寻欢作乐,但又非常羡慕贝兰吉每个周末都有朋友聚会,而自己经常不被邀请。让的焦虑实质上也是人存在的常态。世界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充满竞争,因而是对立的。孤独与焦虑的荒诞在于人往往选择荒诞的逃避,却又难逃宿命。
5 萨特的让们与加缪的贝兰吉
选择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特点。人存在的本质由人的意志决定,即人存在的本质由人选择成为什么样的本质或者人自己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来决定。作为理想与公正裁决代表的上帝不存在,人来到这个支离破碎、绝非完美的世界是绝对的偶然。在萨特看来,人的一生都处在企图跨越这个残缺的现实困境,到达一个理想、完美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但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彼岸。事实上,加缪一直拒绝被称为存在主义者,因为他与萨特的观点有些分歧。加缪认为,“所谓荒诞,是一种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但不是目的地。加缪从人与世界既定的荒诞关系出发,探索处于理性的特殊存在状态中的人的出路,赋予人以现实实践的反抗精神,在原本并不自由的荒诞世界中积极探索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才是他的理想归宿”(李元2007:3-4)。
在《犀牛》中,勃夫变成的犀牛是法律出版社的同仁们遇到的第一个由人变成的犀牛。权力代表人物巴比雍威胁解雇勃夫,甚至劝勃夫太太考虑离婚,苔丝对勃夫变成犀牛给予同情与怜悯。而作过小学教员的博塔尔,则决定找官方问清整个事件。法学家狄达尔认为犀牛的存在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让则认为,勃夫是一个勇敢、虚伪的家伙,他和太太之间根本就不是看上去的那么恩爱。因此,让得出结论:勃夫是自己故意变成的犀牛,是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勃夫的犀牛的存在是愉快的。当贝兰吉提出犀牛的兽性可能会摧毁人类文明与道德的时候,让则为犀牛的兽性辩护。他认为天性有其自有的法则。道德反天性,人道主义老掉牙了。而狄达尔对人变成犀牛合理性的辩护更加具有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思想:“You leave the authorities to act as they think best!I’m not sure if morally you have the right to butt in.In any case I still think it’s not all that serious.I consider it’s silly to get worked up because a few people decide to change their skins.They just didn’t feel happy in the ones they had.They are free to do as they like”(Ionesco 1962:93)。
当贝兰吉认为人变成犀牛是背离人性与道德,违反自然规律,是罪恶的时候,狄达尔则认为:“The evil!That’s just a phrase!Who knows what is evil and what is good?It’s just a question of personal preferences.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own skin — that’s the truth of the matter.…It was his way of sublimating himself”(Ionesco 1962:94)。
让变成犀牛,逻辑学家变成犀牛,从普通百姓到社会名流,甚至红衣主教,人们纷纷变成了犀牛,最后不顾贝兰吉苦苦相劝,苔丝迫不及待地追随时尚的脚步变成犀牛。犀牛的影像充斥着整个舞台,犀牛的嚎叫不绝于耳。贝兰吉成了一个真正的孤胆英雄。他质疑人变成犀牛的合理性。理性的消亡是荒诞的根本。代表理性的逻辑学家也变成了犀牛,贝兰吉还能指望谁呢?贝兰吉意识到他们被抛弃在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但是,贝兰吉最终选择坚守:“Now I’m all on my own.(He locks the door carefully,but angrily)But they won’t get me.(He carefully closes the window.)You won’t get me.(He addresses all the rhinoceros heads.)I’m not joining you;I don’t understand you!I’m staying what as I am.I’m a human being.A human being”(Ionesco 1962:122)。
贝兰吉的反抗印证了加缪的观点:“荒诞仅仅是个出发点,重要的不是意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在荒诞的条件下的人应该如何行动……加缪认为,反抗是荒诞世界中唯一的出路。尽管反抗并无解决一切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反抗是人之为人的态度,是人拒绝神话,共同承担荒诞命运的现实宣言”(李元 2007:144)。
6 结束语
两次世界大战使无数无辜的人丧命,尤其纳粹主义的疯狂使以理性为骄傲的西方社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道德规范受到质疑,人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混乱中寻求意义,在恐慌中寻求拯救……世界逐渐变得不连续和不确定。(刘春芳2012:76)正如《犀牛》里的人们一样,丧失理性的逻辑是荒诞的,对人性与兽性转变的焦虑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以人存在的状态与本质为研究核心的存在主义,契合了荒诞派戏剧的戏剧创作。同样,《犀牛》中世界的荒诞、疯狂、非理性也印证了存在主义对世界荒诞状态的基本观点。正视人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正视人生无奈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如《犀牛》中的贝兰吉,正视现实、积极地坚守必定是人类的希望。
陈 杰.我是谁——指称的一种物理主义观点[J].外语学刊,2009(2).
戴卓萌.索洛古勃与西方存在主义作家之比较[J].外语学刊,2012(1).
黄晋凯.尤内斯库画传[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08.
李 元.加缪的新人本主义哲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廖金罗.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悲剧成因的后现代主义阐释[J].外语学刊,2009(6).
刘春芳.《心理之城》中的荒原后都市摹写[J].山东外语教学,2012(2).
周 宪.戏剧学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Camus,A.The Myth of Sisyphus[M].London:Hamish Hamilton,1955.
Ionesco,E.R.The Chairs.The Lesson[M].London:the Penguin Group,1962.
Myerson,G.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M].London:Hodder Arnold,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