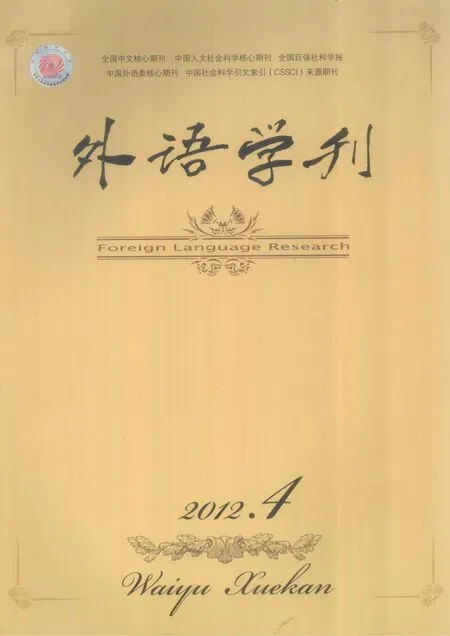语言与意识*
——后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解析
成晓光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130024)
1 引言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破解意识这个“世界之结”。从古时的灵魂崇拜到当代物理还原论对意识的本体否认,各种解释使这个现象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毫无疑问,意识是我们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首当其冲要面对的问题。我有主体感受,除此之外,我还能意识到我的主体经验感受。因此,否认意识或离开一个作为有意识经验的主体来谈论意识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在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意识之谜。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人类特殊意识的启动器,两者是一种因果关系。只有把对语言的考量带入到意识的研究中,才能更全面地来解答意识这个“永恒之谜”。
2 意识的哲学探讨
意识本是最显而易见的现象。意识在人类诞生之时便与人类同在。有了意识,自然就有了思维。于是哲学家们就开始了“我”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思考。形而上学本体论便是这种思考自然而然的产物。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客观地认识了世界。随着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繁纷复杂,哲学家们逐渐把视角从认识客体转向了认识主体。在这种哲学转向中,意识自然成为了哲学研究的第一对象,原始的本体论哲学自然演变成为了今天的心智哲学。
2.1 容易问题还是困难问题
意识究竟是什么?其实在我们讲意识的时候,就已经是先入为主了。有没有意识这个东西?意识究竟是个物体?是个概念?还是个现象?如果是物体,那它的本体特质是什么?存在在哪里?如果是概念,那它从何而来?如果是现象,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因此,研究意识首先要定义意识。这本身就是个哲学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就连这个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这就预示着对意识的研究注定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果。
Chalmers 1994年在“建立意识的科学基础”专题研讨会上提出区分意识的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容易问题(the easy problem)就是要解释人的感知、学习、注意、记忆、甄别、综合、行为调控、清醒与睡眠状态等认知现象。而研究意识真正的困难问题(the hard problem)则是要解释经验(experience),即我们的主体感觉经验怎样有别于那些无感觉经验、无意识的物理系统,“为什么任何物理系统不论多么复杂和有序,却能给我们带来经验?为什么这一切不是在没有主体感知的情况下偷偷地进行?正是这个现象使意识成为真正之迷”(Chalmers 1995:202)。按照这个两分法,意识的容易问题可以通过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方法如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来描述解决,但是经验的问题则不然。回答意识的困难问题,我们只能回到哲学上来,通过心智哲学,建立起新的心理物理原则(psycho-physical principle),从而把物理过程的属性与经验的属性联系起来。
Chalmers的观点受到了不少质疑。研究意识的著名哲学家Churchland(1995)就不无讽刺地把困难问题叫做“欺瞒问题”(the hornswoggle problem)。她认为,我们不能预先假设哪个问题容易,哪个问题困难。两者无法分割。把意识从认知现象中剥离出来,本身就是犯了直觉上的错误。国内也有人认为Chalmers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李恒威2006)。
2.2 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哲学家们关于意识的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争论。Chalmers的立场是自然主义二元论。他秉承的是笛卡尔的身心两分法的衣钵。不言而喻,我们通过感官获取了经验感受。这些主体经验构成了我生存的世界,有时亦被称作“心”(心理)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感受却是来自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另一个物理世界。我可能不了解那个物理世界,但是我绝不怀疑它的存在。于是笛卡尔就提出了二元的“身心交感论”。他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物质(包括身体)是具有展延性的实体,心灵则是非展延性的实体,不占有任何空间。其它的身心二元论还有莱布尼兹的身心平行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等。
身心二元论符合大多数人的认识观。就宗教而言,世界上3大宗教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笃信灵魂与永生。佛教则不同。佛即“觉者”,佛法认为宇宙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则能所是一、心物不二,没有丝毫的分别对立。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其形成三足鼎立的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儒教宣讲天人合一,体现的却都是二元的思想。当然,宗教不同于哲学(但哲学从来都研究宗教),但两者都蕴含着一元或二元的认识观。即便是没有宗教信仰、不懂哲学的人,也会在身心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都持有身心两分的观点。这就是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认识原则,即从常识的概念框架出发,接受心灵的本体论承诺。二元论似乎已成为人们的默认原则。如我们相信,意念可以作用于物体。甚至连我们的语言也浸淫着二元论。我们说,“我的痛苦”,“我的身体”,这样的语言表达式好像就预设(透露)了“我”可以与“痛苦”和“身体”分开。
然而,身心二元论并没有解决身体与心灵转化介质的属性问题。对此,笛卡尔的假设是:在人的丘脑上后方有一个极小的松果腺体,这里是身与心的交集地。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绝非信口雌黄,因为松果腺体早已被发现具有至少3种功能:退化了的但仍能感光的“第三只眼睛”、调节分泌周期的“生物钟”、影响神经和激素信号的“转换器”。但是,笛卡尔掉进了自己的陷阱:松果腺体本身是一个生物实体。一个生物实体怎样与“心”互动交流?笛卡尔没有做出回答。
二元论的困惑导致一些人转向一元论。一元论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唯心主义一元论认为心灵先于物质,但是如何解释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却成了难题。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先有物质而后才有心理活动,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科学哲学家。但是一个由物质构成的大脑,又是怎样生成出我们那些难以言表的主体感受和有意识的经验呢?
2.3 关于意识的争论和研究路径
意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意识究竟是我们人类除感觉、知觉和思维能力以外的一个额外成分?还是感觉、知觉和思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lackmore 2005)如果答案是前者,那我们面对的就是意识的本体论地位的问题,就要给意识一个本体论承诺,研究意识的作用和意识的起源,解释意识是怎样进化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同时,我们也要研究其它生物是否也经历了意识进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这一切有关意识的问题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任何有感知、记忆、智能和情感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也必然会经历意识的进化。所以,除了能力和程序外,其它什么都不存在,当然也无意识可言。
在当代的意识研究中,虽然二元论已逐渐失去其主流地位,而成为大多数人唯恐躲避不及的“幽灵”(赖尔1988),但实体二元论,还有属性二元论,都认为在人的身上存在着物理和心灵两种并列、独立自主的、不能相互归结和还原的实体或属性。当代心智哲学围绕“主体感受性”(qualia)问题而产生的种种论点,如副现象论(epiphenomenonism)等,也都属于二元论。Dennett戏谑地把这种身心二元论叫做“笛卡尔剧院”(Dennett 1991)。有一个小人(homunculus)坐在大脑里,通过感官的屏幕,感知外部世界。然而,大脑是一个并行处理系统,里面并没有一个意识中心在统一处理各种信息。Dennett用“笛卡尔唯物论者”来调侃那些声称已抛弃了二元论但仍然信奉“笛卡尔剧院”的科学家。他们骨子里仍然秉承着常识心理学中身心二分的本体论原则。其他许多重要哲学家,如新行为主义的 Quine,Davidson,Dummett,Rorty,Churchland以及功能主义的Putnam,Fodor,Armstrong等都参与到这场“本体论的变革”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构心灵”,“驱除心灵的神秘性”,以颠覆常识心理学的心理概念图式,阐发一种新的心灵理论。他们的共识是,心灵和意识在自然界中没有本体论的地位,它们要么是类似于“以太”、“燃素”等实体,要么只是我们强加于人身上的一种构念(construct),类似于人类加在地球上的坐标系和经纬线。实际上,世界上除了物理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高新民殷筱2005)。
身心一元论就这样在这场“本体论裂隙”运动中夺取了当代心智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身心一元论只承认人的身体(大脑)或心灵二者只能其一的独立实体的地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只认可灵魂或心灵、精神、心理的独立存在。但现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占绝对优势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有身心同一论、等同论、格式塔心理学的同型论、突现论、动力模式论及现代西方的物理主义(自然主义)、功能主义等。这些理论只认可身体的物质实体的地位,认为心灵不应再被理解为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依附于物质之上的同一物,是人类大脑活动的产物。在这场变革中,有温和或强硬的物理主义(自然主义),更有极端的取消主义,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以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契机,以实验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及心灵哲学等为平台,提出用心灵的功能来定义心灵的观点,认为这种功能就是表现为外在的因果关系,如Crick提出了关于意识的“惊人假说”:意识“实际上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Crick 1998:3)。Edelman也坚称“意识与特殊的大脑神经事件同步,是物理事件的过程”(Edelman 2003:5520)。
鉴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论争,Searle提出一种关于意识经验和身心问题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的观点(Searle 1998)。他认为,意识或心灵在本质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非自然的独立实体。它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是一种大脑机制产生出来的更高层次的特征。Searle既不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同时也反对任何一种二元论的解释,认为把两种解释割裂开来都不足以充分地解决意识的问题。在他看来,意识是由内在的、质的主观状态和感知过程所构成。意识的本质特征是质性(qualitativeness)、主观性(subjectivity)和统一性(unity)的结合,主观特性和感知过程并非互相排斥,所以并非要么接受唯物一元论,要么接受二元论。他认为无论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基础上,即心灵和物质是彼此排他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时不仅要摈弃对身心的排他划分的假定,还要绕到问题背后检验双方设定的前提,这才是对哲学中互相冲突的默认点的典型的解决方法。Searle认为,意识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的主观特性,但这并不妨碍意识作为在大脑机制上产生出来的更高层次的特征而存在,正如消化是胃的更高层次的特征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像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取消论那样,全盘否定常识心理学,“常识心理学在整体上一定是真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Searle 1992:59),也不能像二元论那样,把意识说成是脱离了自然世界的范畴系统(李恒威于爽2004)。
我们认为,Searle的观点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身心关系的假说。他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也是本文论点的理论支撑之一。意识既衍生于生物的大脑机制,不能独立存在,但又区别于大脑的一般物理属性。它是更高层次的特征。对我们来说,造成这种身心转化的介质就是语言。这也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3 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再到后语言哲学
语言和意识(心灵)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初出现的“哲学的语言性转向”使语言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这个转向来自于分析哲学的发展。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问题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造成的,所以必须用语言分析作为现代哲学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彻底的清理。分析哲学虽然流派庞杂、观点各异,但都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和特征,即重视分析方法和重视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语言性转向”的第一时期是以 Frege,Russell,早期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他们以数理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对象,旨在建立起简洁、抽象的形式逻辑系统,以便来确定语言的意义。Chomsky也属于这一派。他的生成语法就是一套典型的形式逻辑系统。他最基本的哲学假设就是,语言的运作是以有限的短语结构,通过转换生成规则,生成出无限的、新的句子来。第二时期是后期Wittgenstein,Austin,Grice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一反形式主义的窠臼,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并以此为分析工具,将研究的对象转向日常的自然语言,主张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才能破解和把握丰富的语言意义。到60-70年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已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在意义理论中引入了意向性问题等诸原因,人们的兴趣逐渐开始转向了心智哲学,这是因为,处理语言、知识、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许多问题,都要通过对心灵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于是到90年代,心智哲学便取代语言哲学,占据了“第一哲学”的地位。
心智哲学研究心智的本质与特质(包括意识)、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等,以及它们与大脑的关系。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的联系纽带在于语言和心智的互为依存性。大脑对现实的表征依赖于语言对现实的表征。意识的本质是思维,思维的本质是表征,而表征的本质则是语言。根据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加工理论,表征是指信息或知识在头脑里的呈现方式,是外部事物在心理活动中的内部再现。当我们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输入、编码、转换、存储和提取等)时,我们是用语言把从这个世界中得来的感性经验加以抽象化、概念化、归纳分类,以便可以表征。虽然关于表征的方式目前有一些争论,如Paivio的双重代码理论(dual-code theory)就认为,表征的方式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意象的,但没有人可以否认语言在表征中,尤其是在抽象的高级表征活动中的主要作用(Paivio 1971)。所以,语言活动在心智哲学中被看作是心智活动的反映。“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分支之一。”(Searle 1983:VII)心智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目标有两个范式:以形而上学为取向的语言意义研究和以科学为取向的语言认知机制研究。这两个范式都是通过语言分析(包括现代的科学仪器实验),来澄清有关心智的疑惑。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心智哲学关心的心灵、意识、愿望、意向等心理现象以及它们的指称,在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是根据已知对象和未知对象的类比来进行词语命名,通过类推、移植的方式虚构出来的。Jaynes就宣称,“主观的、有意识的心灵是我们称之为真实世界的东西的一种类似物。它是一种由语汇或词汇域建构以来的,此域的术语都是关于物理世界的行为的隐喻或对应词”,所以“意识起源于人类做出隐喻和类推的语言能力”(Jaynes 1985:135)。
心智哲学的蓬勃发展虽然使形而上学恢复了它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语言哲学的分析潮流并没有结束。相反,心智哲学的演化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语言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又对心智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随着心智哲学研究的展开,特别是随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语言研究在心智研究中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由于心智哲学的核心特征是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后语言哲学时代的语言研究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即从语言进,从世界出;从语言进,从人出。钱冠连在构建后语言哲学的思路时指出:“后语言哲学区别于经典语言哲学的特点在于:(1)吸取西语哲(分析传统和欧洲传统)的营养,但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在于节外生枝。(2)生出什么样的新枝呢?从日常社会生活中寻找一个一个具体语言问题,从词语分析(形而下)找入口,从世界与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关注入口与出口,但是让选题与风格多样化。(3)重视汉语语境,实现西语哲本土化”(钱冠连2010:1)。根据这个思路,后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语言来解释人与世界。这样,语言哲学就凸现出进入21世纪后新的研究特征:从传统的语言意义的微观研究,过渡到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宏观考察,为认识人类和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视域。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后语言哲学的视域下来考察语言与意识的关系。
4 语言对意识的解析
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第一,为什么有意识?因为我活着。身体消解了,还会有意识吗?第二,我怎么知道我有意识?因为我有思维。第三,我为什么能思维?因为我有语言,所以我才知道我是谁,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个顺理成章的因果关系:物质在先,语言在后。语言在先,思维(特指人的抽象思维)在后。思维在先,意识在后。所以,物质产生了语言,语言启动了意识。
4.1 意识的本质
关于意识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以上假设里的3组关系展开的,所以我们的任务也是要厘清这3组关系。
首先,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种系发生学(phylogeny)的意义上,“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Searle 2002:3)。这个论断里有两个内涵:第一,意识附着于生物机体之上。第二,意识是生物现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现象。关于第一点,活着才能有意识。细胞死了还能有功能吗?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灵魂不灭”的根基。200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Libet通过实验证明,在人身上存在着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实验中,Libet测量3个事件的时间: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RP),决定要行为的意志产生的那个瞬间,还有运动本身开始的时间。实验结果表明,RP的时间通常发生在对行动的有意识的知觉前350兆秒,而有意识的知觉大约发生于行动开始前的200兆秒。这意味着自由意志是被无意识所激起的。Libet对此作了突现论(emergentism)的解释,即发生在意识之前的大脑中的神经进程只是意识产生的神经关联物。这就否定了还原论关于意识等同于与之相关的神经关联物的说法,因为意识是从这些神经关联物中突现出来。Libet为此提出了一个“意识的心理场”(conscious mental field)理论,认为心理场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不能离开活着的大脑,它是人的大脑突显的属性(Libet et al 1983)。
关于第二点意识是生物现象,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现象。意识只产生于生物,其它物质不可能有意识,所以计算机没有意识。在著名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和“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试验中,尽管机器可以模拟人类的工作,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人工智能。它的运算功能和结果与人类的相似,但在本质上机器和生物仍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机器甚至都不具有除人类外的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意识。虽然有人坚称,在理论上计算机可以具有意识,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源于语言的混乱。此意识非彼意识。说机器有“意识”只是个隐喻。可惜我们的语言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由此可见,对语言进行哲学解构是多么的必要。人们的许多争论说穿了不过是个语言的问题。这印证了分析哲学的说法:哲学问题是由于语言误用造成的,语言哲学的研究就是要纠正这个偏误。
第二组关系是意识与思维的关系。当“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就在思维了。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意识才能思维,而是因为有了思维才能意识。这里的意识指的是人类特有的“我”的意识。“我”能意识到我自己、我是谁、我在做什么。这一切皆因为有了那个“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的形成只有在掌握了语言之后才有可能。动物当然也有意识。但是因为它们没有语言,而对人类来说是语言产生了特殊的抽象思维,思维产生了意识,所以动物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语言造成的混淆。可惜语言里没有两个不同的术语来把这两个不同的意识概念区别开。人类当然也具有和动物一样的生物意识或本能意识,但是在人身上,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已经无法分割。它们都被置于了语言的管辖之下。
第三,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这也是学者们研究最多、争论最多的话题。到如今,爱因斯坦关于自己在进行科学思考时无需使用语言的言论以及罗素的“我认为没有语言也可能有思想,甚至还可能有真伪的信念”(罗素2003:72)的说法,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甚至被当作戏谑之言。当前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有两极分化的两个观点。语言认知观认为,人的思维离不开语言。所以语言即认知。而语言交际观则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交际工具,是思维的附属物和外壳。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调和的观点。我们认为,人类范畴化的思维只有使用语言才能进行(成晓光2010)。钱冠连认为,“笔到意渐到,言显意渐显”(钱冠连2005:14)。这里的“意”指的是思想,也应该是支持语言在先,思想在后的观点。Wittgenstein甚至说,思维是一个被误解了的词汇,因为根本不存在思维这个东西(Wittgenstein 1953)。思维原本是人们的一个错觉。思维其实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思维就是语言使用。斯大林也指出,“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1950:38-39)。Piaget和Vygotsky虽然承认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但是他们都认为,随着语言习得的发生,低等的原始思维方式终将被抽象的、语言符号式的思维方式所替代(Piaget 1952,Vygotsky 1986)。“内部言语在缓慢的功能与结构变化积累过程中得到发展……其话语结构最终被儿童所掌握,从而成为基本的思维结构。”(Vygotsky 1986:94)换言之,儿童在习得了语言之后,思维就变成语言的了。必须指出,我们这里讲的思维是人类的高级思维。动物的“思维”和前语言阶段的婴儿的“思维”属低等的原始方式,不能产生高阶意识和自我概念。一闪而过的思绪是片状的云朵,不是高级思维。
最后,语言与意识的关系。人类意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语言能力。医生和科学家判断和研究他人的意识靠的都是病人或受试的自述。所谓无意识或潜意识里的东西被唤醒,指的就是能够使用语言加以陈述,反之就不能被人们所意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意识就是研究语言。语言和意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笛卡尔早就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生物反射行为,而是语言能力。动物没有语言,所以也就没有认知和思维。很多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Jaynes曾举证,意识出现的前提是语言必须要先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Jaynes 1976)。Donald也指出,意识离开复杂的运用符号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Donald 2001)。当然,有些人会反驳说,动物没有语言,并不等于它们没有意识。还有人类的婴儿、野孩子、丧失了语言能力的人,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意识。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话题:本能意识与语言意识的区别。
4.2 本能意识与语言意识
人有意识,其他动物作为生物当然也有意识。但是这两种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分别由不同的机制所驱动,分属不同的属性和机能。长期以来,人们在人与动物相似性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是因为,第一,人类出于一种移情心理,对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目动物有着特殊的偏爱;第二,对本质上不同的事物,语言往往只用一个词来指代。但是,此意识非彼意识。语言的这种无力和无奈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
一切动物都具有对外部环境的感觉能力,这是基本的、必备的生物本能。甚至一条虫子也会对外部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能力关乎到生死,因此所有生物都天生具备了刺激-反应的本能。Bickerton把这种原始的低等能力叫做第一意识(consciousness-1,C1)(Bickerton 1995)。我们认为,把这种本能反应称为意识其实并不恰如其分。这原本是生理机体的一种功能,是由神经感官系统所驱动,它只负责调节神经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平衡。当然,这种本能不仅仅感应外部环境,也能感应内部产生的体验,如疼痛。如果没有这种内部的本体感受,生命同样也无法维持。这两种内与外的本能反应都属于“在线”(on-line)操作。“线上”行为不具有可控性,因此,所有生物(人类除外)对机体内外的刺激都有着固定的行为反应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能力不是意识,而只是一种“下意识”或“无意识”,因为生物自己对此并不具有任何掌控,没有任何选择。仅此而已。Bickerton把这种属性称之为第一意识,或许是出于词语限制的无奈,或许是意图把C1与人类的特殊意识相对照。无论如何,C1清楚地指出了意识概念里的差异。
然而,人类的行为与动物大相径庭。人有自己的选择。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有的人可以逆本能而动,挺身而出,选择为他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人类不但具有本能意识,还具有更高层次的意识,即意识的意识。人类不仅能够感觉到疼,还知道自己疼,并能描述这种感觉。Bickerton把这种语言意识分为两种:第二意识(C2)和第三意识(C3)(Bickerton 1995)。这是离线(off-line)意识。语言在大脑里创造出反应C1的条件,并将原始的本体感应概念化。换言之,C1和C2、C3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感觉与认知的关系。C1本能地感觉各种刺激,而语言的C2和C3则创造出一个认识主体,对本能感觉加以认知。沿用我们以上的观点,C2就是用语言对自己表征“这种感觉是疼痛”,而C3就是通过语言交际告诉他人“我很疼”。C2和C3互为彼此的蕴含,所以可以统称为语言意识。这种高级意识只能由语言来启动。正是这种语言意识催生了自我概念,催生了对行为的自由选择,也把人类彻底地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用一个比喻的方法。在没有语言的动物的大脑里,信息输入系统和行为反应系统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没有任何感应本体的主动、有意识的表征活动。有了刺激,就必然要做出相应的本能反应。猎食者逼近,“我”只有本能地逃生。感应本体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没有表征,它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身不由己地做出相应的反应就是了。但是有了语言的人类则不一样。语言在信息输入和行为反应这两个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信息进来,我们不必立刻加以反应。语言这个表征系统总是迫使我们先进行概念加工,去问“这是这么回事”,然后再进行选择并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不做反应。Chafe有一个类似的区分,叫做“直接意识”(immediate consciousness)和“移位意识”(displacement consciousness)(Chafe 2007)。前者只感知即时的感觉,而后者却能够对感觉经验进行意义解释。所以,是语言启动了人类特殊的意识,产生了人类特殊的行为,使人类的行为具有了不可预见性。
意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Block&Dworkin提出的“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即处于一种状态是什么样子(Block&Dworkin 1974)。Rosenthal从分析心理概念的基本特征出发,指出“意识”一词指的是高阶思维(higher-order thinking),因而意识就是一种语言思维。他认为,如果没意识到那个心理状态,那个状态就不具有意识(Rosenthal 2004)。我们只有意识到自己处于那个状态之中,才能意识到那个状态。在生活中和实验心理学中,能够用语言报告那个状态是识别有意识的心理状态的基本特征。我们意识不到的状态则根本无法予以报告。高阶思维永远伴随着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有了高阶思维,我们就可以对那个心理状态进行报告。Rosenthal这番分析的意义也在于指出了语言和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只有具有语言的人类才具有高阶思维能力,因而才具有特殊的意识。
4.3 意识的进化
我们在本文里探讨的是语言意识,而不是本能意识。因此,研究意识的进化也就是研究语言的进化。
任何生物现象都是进化的结果。语言也是生物现象,所以语言也是进化的产物。脑神经科学已证明,语言在人脑里有着神经基础。MacLean曾提出过一个大脑演化的理论(MacLean 1990)。他认为现代人大脑的进化经历了3个阶段,即远古、中期以及新时期,分别演化了大脑里由下而上排列的不同的脑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底部有一个古老的状似爬行动物的内核叫脑干。它掌管着非理性的行为,执行着一套固定不变的、无法控制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机体的本能反应。到了中期,包括海马、丘脑以及一些其它结构在内的脑边缘系统得以进化。这一部分结构构成了古哺乳动物的大脑。它同样不按逻辑行事,只负责情感情绪的变化。演化的最后阶段位于顶部的那个多摺的大脑皮层,也叫作新皮层。这个大脑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可以生成语言、抽象概念、想象、自我意识等。MacLean的这个研究给Searle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观点提供了一个佐证。
语言和意识始肇于生物的进化,同时必然伴随着行为模式的变化,所以对语言进化的考察除了神经生物学的路径之外,最直接的线索和证据就是人类在进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制造的工具。这是因为,工具不断改进的前提是语言和意识。人类首先得具有想象能力,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单纯的需求不会使任何物种发生变异。北京猿人50万年前就生活在周口店,一直到20万年前消亡。在漫长的30万年里,他们居住的洞穴没有任何人为的结构上的改进,所使用的石器也没有任何变化。不能说他们没有需求。相反,他们的需求极为迫切。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语言,没有意识,所以不会想到要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改造。他们只有本能意识,本能地去感应外部环境,被动地对刺激做出反应。
出土的化石表明,最早的现代人类出现于埃塞俄比亚,追溯到19.5万年以前。然而,虽然他们已具有现代人的生理结构,但却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证明他们的行为和之前的欧洲史前人种有什么区别。他们使用的仍是20万年前的阿舍利时期粗糙的石器手斧。直到1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人的石器制作技术才有了进步,出现了两面刃口的刀形、镞形石器。这也是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的代表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工具出现在7万到5万年前。这些工具已采用了不同的材质,如兽骨或兽角,并按其功能分门别类。学者们认为,这说明这时的智人已具有了完整的语言,因为只有语言才能把这种手工制作的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
Aitchison认为,语言是在大约25万年前左右出现的(Aitchison 1996)。最初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但却给语言的进化奠定了基础。其后则是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到了10万和7.5万年前间,语言进化到一个关键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直到5万年前才又缓慢地趋于平稳。这和同时期人类文化的突然发展与兴旺是吻合的。Bickerton也把语言的进化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原始语(protolanguage),一个是现代语言(Bickerton 1995)。原始语具有一些实义词语,但缺乏句法关系,所以它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和思维。然而它的词语符号本身所具有四种特质——范畴化、刺激联想、分离性和等级结构,却可以使它的使用者从本能意识发展到语言意识。如果说范畴化和刺激联想不是人类语言的专利,还不能使人类脱离本能意识的话,那词语符号的分离性和等级结构则足以使其使用者把概念表征从物质实体中剥离出来并形成具有等级结构的意义关系,这就给语言使用者提供了“表征全部意识场的潜在能力”(Bickerton 1995:52)。Carruthers也指出,原始语虽然抽象程度低,但却能使其使用者以听觉及运动想象的方式来产生原始语句(Carruthers 1998)。这就是想象思维的开始。语言既是直接的概念思维的载体,也是有意识的命题思维的载体。在欧洲生存了25万年之久的尼安德塔人就是具有这种原始语的最后一支远古人类。他们凭借着原始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但是,由于语言能力的低下,尼安德塔人缺乏高阶思维能力,所以当有着较为丰富的语言文化的现代人种克罗马农人出现的时候,他们终于在3万年前被彻底淘汰。
语言进化过程中最具意义的一步是从原始语到现代语言的转化。一般认为,这个转化只能是以大脑的生物变异为前提。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已发现一个FOXP2的基因。正是这个基因的变异使得人类开始有了语言。至于语言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是一个突发事件,目前渐变论和突变论各持自己的观点。其实双方的焦点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渐变论侧重的是语言进化的过程,而突变论则强调瞬间的质变,但双方对语言作为进化的产物和人类独有的特质并没有分歧。Bickerton提出了一个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有突破了动物交际系统的局限,才能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态位(Bickerton 2009)。这就是语言的生态位(the language niche)。无论初始系统有多么原始和粗糙,它都必然要遵循进化的规律,即从行为到基因,再到行为,再回到基因。这是任何形式的生态位的建构路径。语言的进化也必然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正如伽利略的著名论断,“大自然是完美的”。只是人类进化到现在,对自己的语言、意识和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个体发生的现象远比种系发生的过程更容易理解。
4.4 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
语言给人类带来的最明显、最本质、最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人称代词“我”建构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我知道我是谁,完全是语言使用的结果。有了“我”,才有了你和他,才有了认知视角和表征主体,才有了我们所认识的现象世界。Benverniste认为,“主体性就是言语者把自己建构成为主体的能力”(Benverniste 1971:224)。他还说,“人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来把自己建构成一个主体,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建立现实中的自我概念。这个现实就是存在的现实”(同上)。他的这种说法同海德格尔(1982/1959)的“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这一著名论断如出一辙。钱冠连也提出人是活在语言中的观点(钱冠连2005)。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来推理,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不但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甚至都不存在。这个“存在”,当然指的是意识和概念上的存在。没有语言,人作为生物仍然具有本体存在,但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是根本谈不上的。而有了语言,self和ego就都成为了现实。在这个问题上,语言习得和认知发展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佐证。如Piaget就认为,婴儿在理解和掌握物体恒存性之前,是没有物我之分的概念的(Piaget 1952)。Vygotsky也通过实验证明,儿童的内在心理发展要经过4个阶段:1)他人用语言作用于儿童,2)儿童与他人产生互动,3)儿童用语言作用于他人,4)儿童用语言作用于自己(Vygotsky 1929/1979)。因此,只有在习得语言之后才能从本能意识进入到语言意识,从而产生“我”与“非我”的概念。而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活动。当然,人类也会因此变得如此“自我”和“主观”,以至于会深陷于一个“永恒的我”和“我即宇宙的中心”的幻觉之中。这也就是,意识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的主观特性(Searle 1998)。
如同Bickerton区分3种意识一样,Tulving在研究记忆的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识的3元说:失知意识(anoetic consciousness)、觉知意识(noetic consciousness)和自知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Tulving 1984,2001)。失知意识处在最底层。Tulving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意识,还不如说这是一种状态,一种受制于刺激和此时此地原则的状态。失知意识当然无法产生任何自我概念。觉知意识则是一种和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相关的内在表征,它可以使生物在物体和事件不在场的前提下依然能够意识并建构这些物体及事件之间的联系。但遗憾的是,Tulving虽然这样定义觉知意识,却不认为它可以产生自我概念或自指性。他认为只有自知意识才是意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概念只能在这里产生。在Tulving看来,自知意识和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有关,因为情景记忆可以使自我在时空中穿梭,所以这是一种意识的意识,只有过了婴儿期的人类才具有这种特征(Tulving 2005)。
我们认为,Tulving的意识说也指向了意识的两元性,即本能意识和语言意识。失知意识是本能意识,不能产生自我概念,而觉知意识和自知意识都是生成自我概念的语言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同Tulving看法不同。我们相信,只有语言才是产生自我概念的唯一条件。觉知意识既然是一种语义记忆,那它一定是以语言为基础。一切概念都是抽象的符号概念。内部表征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意识活动,所依赖的只能是范畴化的词语。在英文里,representation(表征、再现)由 re-(又、再、重新)加上 presentation(呈现)所组成。“呈现”原本指的是一种原封不动、未经加工的展示活动,而“表征”则是展示经过加工的新的内容。因此,这是一种表征主体的语言再现活动。语言意识和表征主体是共生现象。Tulving的“觉知”是感觉而知之,“自知”是认识而知之。“觉知”已经是一个包含了“感觉”和“认识”的复合词。因此,“觉知”和“认知”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表征的资源和方法不同。而“失知”只是本能意识的现象,这里没有任何感应本体的主动、有意识的表征活动。所以,觉知意识和自知意识都是语言意识,都蕴涵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
5 结束语
关于意识的研究,仍在继续,一定还会有各种新的观点和见解被推出来。但是,要想解开人类的意识之谜,只有从人和其它生物的根本区别入手。这就是语言。这也就是后语言哲学的精髓所在。不必问语言能为人类做什么,只要问没有语言人类还能做什么就可以了。没有语言,能有意识的意识吗?没有语言,当然也没有这里的这番讨论。意识之谜就是语言之谜,而语言之谜就是人类之谜。研究人类的视角自然有许多,后语言哲学的视角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所以,“只有了解了我们的语言,人类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Bickerton 1995:161)。
成晓光.语言思维、语言模块与语言进化[A].钱冠连.语言哲学研究[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高新民殷 筱.心灵的解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本体论变革”[J].江海学刊,2005(2).
克里克.惊人的假设——灵魂的科学探索[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赖 尔.心的概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李恒威.意识经验的感受性和涌现[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1).
李恒威于 爽.意识的“难问题”及其解释进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2).
罗 素.人类的知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钱冠连.人自称、人被称与物被称[A].钱冠连等.语言哲学研究[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
Aitchison,J.The Seeds of Speech: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Benverniste,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FL: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Bickerton,D.Language and Human Behavior[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Bickerton,D.Adam’s Tongue:How Humans Made Language,How Language Made Humans[M].New York:Hill and Wang,2009.
Blackmore,S. Consciousnes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Block,N.& G.Dworkin.IQ,Heritability and Inequality,Part I[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4(3).
Carruthers,P.Thinking in Language?Evolution and a Modularist Possibility[A].In P.Carruthers & J.Boucher(eds.).Language and Though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Chafe,W.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A].In P.D.Zelazo,M.Moscovitch & E.Thompson(ed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nsciousness[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Chalmers,D.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J].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1995(3).
Churchland,P.S.The Hornswoggle Problem[A].In J.Shear(ed.). Explaining Consciousness:The Hard Problem[C].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95.
Dennett,D.Consciousness Explained[M].Boston:Little,Brown,1991.
Donald,M.A Mind So Rare: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01.
Edelman,G.M.Naturalizing Consciousness:A Theoretical Framework[J].PNAS,2003(9).
Heidegger,M.The Nature of Language[A].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2.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erlag Grunthere Neske,Pfullinger,under the title Unterwegs zur Sprache.1959.
Jaynes,J.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6.
Jaynes,J.Four Hypotheses on the Origin of Mind[A].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1985.
Libet,B.,Gleason,C.A.,Wright,E.W.& D.K.Pearl.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readiness-potential):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J].Brain,1983(3).
MacLean,P.The Triune Brain in Evolution[M].New York:Plenum Press,1990.
Nairne,I.Neath,& A.M.Surprenant(eds.).The Nature of Remembering: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G.Crowder[C].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1.
Paivio,A.Imagery and Verbal Processes[M].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71.
Piaget,J.The Origin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M].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2.
Rosenthal,D.M.Varieties of Higher-order Theory[A].In R.J.Gennaro(ed.).Higher-order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C].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4.
Searle,J.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Searle,J.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2.
Searle,J.Mind,Language and Society: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M].New York:Basic Books,1998.
Searle,J.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Tulving,E.Multiple Learning and Memory Systems[A].In K.M.J.Lagerspetz& P.Niemi(eds.).Psychology in the 1990’s[C].1984.
Tulving,E.Origin of Autonoesis in Episodic Memory[A].In H.L.Roediger,III,J.S.
Tulving,E.Episodic Memory and Autonoesis:Uniquely Human?[A].In H.S.Terrace,& J.Metcalfe(eds.).The Missing Link in Cognition[C].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Vygotsky,L.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Forms of Attention in Childhood[J].Soviet Psychology,1929(18).
Vygotsky,L.Thought and Speech[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6.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