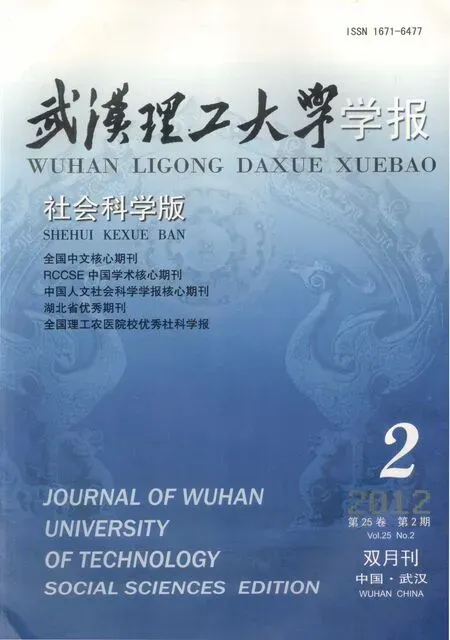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的生态损害赔偿*
黎 桦
(湖北经济学院 地方研究法制中心,湖北 武汉430205)
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的生态损害赔偿*
黎 桦
(湖北经济学院 地方研究法制中心,湖北 武汉430205)
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以及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损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下对于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讨论理论丰富,但鲜有涉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问题的的研究。结合当前生态损害的探讨,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救济制度,有必要建立生态损害的事前防范机制。国家层面要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生态损害赔偿评估制度,并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的救济提供法律支持。
生态损害;地下空间;全面赔偿;预防为主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急速膨胀,各地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入了新的时期。地下空间的利用涉及地铁、地下管线,以及“共同沟”①、地下商场、地下街、地下停车场、地下储藏室、地下人防工程以及大量军事设施等等多种形态。不断加剧的商业形态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天坑现象频现。保护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相关主体的权益,规范地下空间开发,可持续利用地下空间已成当务之急。为此,应梳理、界定相关赔偿制度和救济制度,借鉴域外地下空间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相关的民事立法和财产立法。
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之困境
现阶段我国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领域面临着理论和制度的双重法律困境。理论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界定不清和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路选择不明两个方面。界定不清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赔偿范围划定不明,制度进路选择不明,涉及赔偿模式的选择问题。而就制度层面的困境而言,其主要体现为当下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领域立法的空缺和救济制度的缺失。
(一)理论困惑
1.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界定不清。对于生态损害的界定,国内外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根据荷兰Brans教授的归纳,对生态损害定义的模式大致有三种:“(1)基于对部分生态给予保护的立法而定义,但受到传统侵权法上可赔偿性损害类型的约束;(2)基于某些自然资源的非经济性物理特性而定义;(3)更多地面对对象,即基于对自然或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损害。”[1]
第一种主张的学者如德国Lahnstein博士认为,“生态损害指对自然的物质性损伤,具体而言,即为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间相互作用的损害。也就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人为的显著损伤”[2]。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公共所有而非私主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上,且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损害不包含在内。
我国马骧聪教授在介绍《苏联东欧国家环境保护法》时使用了“生态损害”这一术语,在介绍前苏联的自然保护法律责任中的“物质责任”时,指出物质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别包括“它保护的客体不是具有商品价值的物质财富,而是自然环境”[3]。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无法进行商品定价的物质,即自然环境上,实际是采纳第二种定义。
主张第三种定义的学者典型的如俄罗斯的姆·姆·布林丘克教授。他认为,“生态损害,就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要求所导致的任何环境状况的恶化和与此相关的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利益,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的损害和减少”[4]。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所有的生态系统内,包含自然人和法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利益。其所欲确立的是一种终极的生态赔偿观。
以上三种生态损害赔偿观的争论归根到底是赔偿范围的界定问题。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界定,即应当树立怎样的赔偿观,是我国当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立所面临的首要困境。
2.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路选择不明。第一,以侵权法为视角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传统的以侵权法为立足点的生态赔偿观是建立在传统的侵权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对生态损害、环境损害的赔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基础之上的。当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较具有代表性的如蔡守秋教授,他认为,作为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损害结果,按照内容可以分为: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5]和自然环境损害四种,“有些法律规定,对自然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即使没有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也应承担赔偿责任”[6]。
第二,以环境权为视角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环境权为立足点的生态损害赔偿观是为了将侵权行为中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区分开来,对生态和环境进行独立的保护。该观点认为生态损害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环境权。将生态利益或称为环境利益与人身和财产一样,作为侵权行为的客体。只不过,环境权作为一种客体存在其特殊性罢了。持这种观点的李艳芳教授认为,“公民环境权是在社会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公民基本权利,它不依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存在而存在。它具有与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7]。在我国,倡导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公民独立权利的学者不在少数,较有代表性的吕忠梅教授将公民环境权在其著作中单独成章进行详细论述,并引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宣告对公民环境权进行定义:“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8]55
第三,以环境法等单行法为立足点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环境法等单行法为立足点的生态损害赔偿观是我国当前在生态损害和环境损害中最常用的方法。即依靠环境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其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管理模式,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解决。这种赔偿主要是针对不涉及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情形下的生态损害。
以上三种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立足点各有利弊:第一种赔偿模式是我国当前私人发动生态损害赔偿的主要模式,随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出台,配合已有的诉讼制度,获取赔偿途径的通达性较好,但其对生态损害的赔偿绝大部分建立在对人身和财产的侵权基础上,显然不能对生态损害做到全面赔偿;第二种模式对于生态损害赔偿来说无疑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就我国当前的立法实际而言仍有诸多问题没有解决,无法付诸实践,例如:立法中公民权利中根本无环境权这一权利,公民也不能单单就生态损害和环境损害提起诉讼等;第三种模式的生态损害赔偿方式最为直接,见效最快,但其不能对生态损害进行全面赔偿,往往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层面上,且对行政部门的执法主动性要求极高,无法有效地对生态损害进行全面而有效地救济。因而生态损害的这三种赔偿模式的选择问题构成了我国地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另一重困境。
(二)制度缺失
1.公法层面。我国当前国家层面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立法近乎空白,在部门法规和地方立法上,也仅仅一笔带过。如:2001年建设部修改后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管理规定》只在第27条提到: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地下工程的使用安全责任制度,采取可行的措施,防范发生火灾、水灾、爆炸及危害人身健康的各种污染。其主要是为规定地下工程施工安全的,且对污染的防治规定也非以生态损害的救济为考量,而是以人身健康为考量的。2008年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办法》,仅在其第22条规定:城市地下空间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和防护措施,科学合理地协调地表空间和地下空间的承载、震动、污染、噪声及相邻建筑物安全,不得破坏地下市政管线功能,尽量减少对地面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得妨碍地表的规划功能,不得对他人建(构)筑物、附着物造成危害。可见,这一规定对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损害救济而言也是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其他的最近颁布的如《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福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若干规定》也都大体相当。由此,在现阶段主要通过《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进行救济。在具体单行法的规定上,我国对生态损害的处罚明显失当。例如:在《水污染防治法》的责任篇第70条至第82条中,其处罚数额都是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固定区间内的,且处罚金额相当小,100万的罚款便已经达到了上限。其处罚并非依据生态损害实际所带来的危害而确定的。第83条第2款规定: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此款对直接的生态损害都只赔偿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规定无疑是欠妥的。除此之外,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都忽略了对政府的监管。在我国当前的生态损害赔偿体系下,政府机关的主动监管和执法是极其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在公共生态损害领域和尚未造成私主体明显损害的生态损害领域,政府机关的救济可谓是唯一的救济途径。而如果缺少对政府机关的监管,无疑会让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2.私法层面。在私法层面,《民法通则》第124条、《侵权责任法》的第65至68条对侵权主体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固然可以从侵权的思路进行展开,但从救济的层面来看,其仅将遭受侵害的民事救济权利赋予被侵权人,即在侵权法的视野下只有生态损害的被侵权人才能通过诉讼的形式进行救济,其他主体都无此权利。这里的被侵权人从理论上来讲应当包含所有的被侵权人,即直接被侵权人和间接被侵权人。直接被侵权人,是指在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中权利直接遭受损害且受害人明确感受到这种损害发生的被侵权人;间接被侵权人,是指在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由于生态损害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虽然权利遭受损害,但其并未很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侵害发生的被侵权人。一般情况下,直接被侵权人的权利救济意愿较为强烈,而间接被侵权人绝大多数根本无法意识到自身权利受损而无法主张权利。由此不难发现,在实践中当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发生时,一方面,间接被侵权人的损害无法获得有效救济;另一方面,当直接被侵权人放弃救济或无直接被侵权人时,则无疑对其无计可施。这便是前文所提到的以侵权法为中心的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赔偿救济模式,正如前文所阐述的在此背景下所体现的是一种狭隘的赔偿观,不能使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获得全面赔偿。由此,就私法层面而言,我国当前在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赔偿领域的救济手段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二、域外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上已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笔者选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颇具特色的美国和日本来介绍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美国的地下生态损害救济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对生态损害赔偿采取的是普通法和制定法双轨制。以美国为例,其最初是依靠普通法赋予公共机构对生态损害的起诉权来实现生态损害赔偿的[9],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展了如:《清洁水资源法》、《综合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法案》等制定法,由此形成双轨制。
1.赔偿程序的发动。在普通法层面上主要依靠私主体和公共机构对生态损害提起诉讼进行救济;在制定法层面上,美国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可以受托人的身份作原告进行诉讼,要求生态损害人进行损害赔偿,并能作为受款人收取赔偿金。首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使得地下空间生态损害造成公共利益损害情况下的救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其将裁判权赋予法院可以有力克服依靠行政处罚对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进行处理的诸多不足;其次,通过这种双轨制的规定,私主体、公共机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将可以作为地下空间开发生态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充分考虑了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生态损害发生的各种可能,无论是对私主体造成侵害,还是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都可以由不同主体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由此也充分克服了侵权救济模式下地下空间生态损害保护不力和救济途径单一的弊端。因此,就我国当前的实际而言,赋予公共机构生态损害诉讼请求权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无疑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2.损害赔偿的确定。一是确立全面赔偿原则。规定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修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评估费用三个部分,确保所受之生态损害能受到全面而准确的赔偿。二是建立损害赔偿评估制度。设立专业的评估机构,制定科学的评估规则。现行的CERCLA法案下的生态损害评估程序分为五个部分:即评估前阶段;评估计划阶段;A程序,针对小型事故;B程序,针对大型事故,通常由损害的确定、损害的量化和损害赔偿金的确定三部分组成;评估后阶段。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按照严格的损害评估程序对损害结果进行量化,为全面赔偿原则提供保障[10]。
全面赔偿原则的确立,一方面可以使得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获得有效的救济,因为评估费用的支出使得获得合理的修复费用和过渡期损失成为可能,而修复费用和过渡期损失则可以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将地下空间生态损害从评估到修复再到过渡期的所有费用都由施害方承担,大大增加了其施害成本,可以对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的生态损害行为起到较好的遏制作用。损害赔偿评估制度则使得全面赔偿原则的实施成为可能。专业的评估机构可以确保评估结果的科学性,而严密的评估程序则能确保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这些无疑也都是我国构建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所应当借鉴的。
(二)日本的地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在日本,生态损害和环境损害被称之为“公害”。日本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3款给公害下了定义,所谓公害,是指因伴随着事业活动及其他人的活动在相当范围发生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的污染、噪声、振动、地面下沉以及恶臭,使人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发生的受害[11]。
日本对公害即生态损害赔偿体系是由公害控制法、公害防止事业法和公害救济法三大部分构成。其中,公害控制法主要是力图起到防范于未然的作用,其主要内容为公害的控制措施的法律体系。具体立法有:《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染防治法》、《下水道法》等。公害防止事业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措施防止因重叠污染造成的复合公害。具体立法有:《工厂再配置促进法》、《自然环境保全法》等;公害救济法是在民事侵权行为法之外的一种行政纠纷处理制度和救济制度,其目的是及时解决因公害引起的纠纷。具体立法有:《矿业法》、《煤矿损害赔偿等临时措施法》等[12]。
从这些地下生态损害救济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预防为主的理念,在其救济逻辑上,首先是通过公害控制法防止公害的形成,防患于未然,即从源头上降低公害形成的可能。在公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则通过公害防止事业法防止已形成的公害发展成为复合公害,即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以便减轻危害,降低治理成本。最后通过公害救济法对地下生态损害进行救济。这种预防为主的救济理念无疑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除此之外,其通过公害救济法体系在私法救济层面之外确立一种及时高效的行政救济手段,以期待更加及时有效地解决所发生的公害,这一模式与我国当前的现状有些相似,但却又存在不同之处,其行政机关参与其中,主要是为了解决纠纷而非直接取代受害人直接进行行政处罚。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行政机关的过度介入而导致诸多不良后果。由此,我国在构建地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过程中,也可将行政机关定位为一个纠纷处理和协调的机关。
三、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赔偿的路径选择
在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生态损害赔偿双轨制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害”预防制度之后,结合我国国情,相关立法应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进行。
(一)加强理论探讨
1.树立大生态损害赔偿观。正如前文所言,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赔偿的界定问题归根结底是赔偿范围的界定问题。笔者认为,前文对生态损害的第三种界定是较为可取的,即将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以及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都纳入到地下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中来,树立大生态损害赔偿观。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合理的地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因为,无论是从私主体遭受损害还是单单发生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都有可能被涵盖进来。
2.确立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当前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要确立预防为主的原则,主要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环境物权制度。从我国当前私主体以侵权法为基础的生态损害救济手段而言,无疑只能停留在事后救济的层面上,从行政机构进行生态损害处罚的角度看,其也只能是事后救济。要从根本上确立预防为主的原则,必须通过立法确认环境物权,通过物权的排除妨害这一权能来彻底实现事前救济。对于环境物权制度,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证和探讨,吕忠梅教授在《环境法原理》一书[8]357-384中便对 其 进 行了 专 章 的具 体论述,详细阐述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二是严格确立单行立法中对行政机关的责任监督。我国当前涉及生态保护的单行法中对政府监督责任几乎无强制规定,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生态损害救济方面,政府监督和管制的作用对预防生态损害的重要性前文已经提及,因而,必须对政府机关的失职和失察行为进行监管,以促使政府机关加强监督和管理,从而达到预防为主的目的。当然,我国有学者提出“风险预防原则”[13],其目的和本质与前面所述原则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建立生态损害的事前防范机制。
3.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我国当前生态损害赔偿主要以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和行政处罚为主,很少涉及对生态损害人进行技术革新或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的层面,且在行政处罚上没有严格的计算标准,只规定了一个处罚极小的罚款区间。由此,导致损害人责任的严重真空,造成生态损害愈演愈烈。为此,我们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对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损害确立全面的赔偿原则。具体应当包括:恢复费用、过渡期损失和评估费用三部分。由此可以彻底改变我国当前一些企业理直气壮地交钱排污的局面,给生态环境以强有力的保护。
(二)构建相关制度
1.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从前文在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立足点的选择所面临的困境中,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私主体只能基于侵权而提起诉讼对生态损害进行救济,政府机关只能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生态救济。这样就给生态损害的救济留下了很大的空白面。因此,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共机关生态诉讼的权利,赋予政府以公众受托人进行生态损害诉讼的权利,将很好地填补这个空白,并能很好地解决政府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况且,在我国自然资源国有的大背景下,赋予政府生态损害诉讼的权利似乎更合情合理[14]。
2.建立生态损害赔偿评估制度。我国当前行政机关在生态损害处罚过程中无具体的评估标准,主要依靠行政机关勘察而自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确定处罚数额。这种处理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一,行政机关并非专门的生态评估机关,根本无法对生态损害具体数额作出精确的量化。因为不同领域的生态损害赔偿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而这些往往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二,没有法定的评估程序原则,只有期待行政机关在执法中自行做到公平、公正,在没有制度和程序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的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建立专业的评估机构,制定法定的评估程序。这样由专业评估机构通过法定的评估程序进行损害认定,不仅具有很高的公信力,且有利于全面赔偿原则的实施。
3.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在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中坚持全面赔偿原则无疑意味着赔偿主体的赔偿责任将是十分沉重的,一旦出现赔偿主体倾其所有仍不足以赔偿其所造成的损失时,多出的部分无疑会转嫁到国家或政府的身上,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和不合理的;或者,在出现赔偿主体无法确定时,也会出现以上现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由此,笔者认为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是十分必要的。就基金的性质而言,笔者认为以公益性的信托基金为宜。基金的资金应当主要从政府通过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主体的税收获益而来,当然接受社会捐赠也可成为其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基金由政府委托第三方中立机构进行管理,接受全体社会的监督。由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让政府和全体社会成员都承担过于沉重的负担,而只让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受益人分担责任,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基金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4.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地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具有以下功能:第一,保险公司会对被保险人进行监督,从而促使其加强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减少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第二,可以在使无辜的受害者获得合理的赔偿的同时减少政府和社会的支出;第三,由于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其必然对保险资金进行有效投资利用,在分担社会风险的同时发展经济。就责任保险而言,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实践,“交强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应具有有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由此,在我国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并非空谈。
(三)区域内先行先试
我国当前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便是地方立法已经远远走在了国家立法的前面。虽然在2010年11月我国《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框架稿已经成型,但就已有的内容来看,其对地下空间生态损害的规定也鲜有涉及,例如框架稿第9条便规定:“生态补偿的范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矿产资源开发、海洋、流域和生态功能区。”其更多的是关于生态损害的宏观立法,而具体到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的生态损害赔偿则并非其调整的重点。因此,期待未来的《生态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来对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全面规定是不现实的。况且,该《条例》的颁布还是一个未知数,而问题的解决却刻不容缓。由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地方先行先试立法的形式对地下生态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或在其已有的地下空间开发管理规定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规定,及时有效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一方面,地方行使先行先试立法权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赔偿问题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其可以充分反应各地方在地下空间生态损害赔偿领域所面临的不同情况,为以后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提供有效的参考。
注释
① “共同沟”即城市地下管道综合走廊,是指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的各类公用类管线集中容纳于一体,并留有供检修人员行走通道的隧道结构。通常是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市政、电力、通讯、燃气、给排水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彻底改变以往各个管道各自建设、各自管理的零乱局面。在发达国家,共同沟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在系统日趋完善的同时其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早在1833年,巴黎为了解决地下管线的敷设问题和提高环境质量,开始兴建地下管线共同沟。此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汉堡、西班牙的马德里等欧洲城市也相继建设地下共同沟。1926年,日本开始建设地下共同沟。1933年,前苏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开始修建了地下共同沟。目前中国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城市也相继建有“共同沟”。
[1]Brans Edward H P.Liability for Damage to Public Natural Resource:Standing,Damage and Damage Assessment[M].Dordrecht: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17.
[2]Lahnstein Christian.A Market-Based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suranc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aking Special Account of Germany,Austria,Italy and Spain[M]∥Faure Michael ed.,Deterrence,Insurability,and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New York:Springer-Verlag/Wien,2003:307.
[3]竺 效.生态损害的社会化填补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51.
[4]布林丘克.生态法(俄文版)[M]∥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24.
[5]张梓太,吴卫星.环境与环境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23-128.
[6]蔡守秋.环境法学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60-163.
[7]李艳芳.环境损害赔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7-29.
[8]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陈聪富.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J].台大法学论丛,2000(2):232.
[10]王树义.刘 静.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探析[J].法学评论,2009(1):71-79.
[11]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75.
[12]原田尚彦.环境法[M].于 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4-17.
[13]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71-293.
[14]李承亮.侵权责任法视野中的生态损害[J].现代法学,2010(1):63-73.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Compensation for the Ecological Damage in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LI Hua
(Law Center for Local Studies,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Hubei,China)
The process of urban land diminishing has been sped up by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As a result,a series of legal problems will follow up the process.One of them is ecological damage by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Despite the rich theories in the discussions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little of which involves the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damag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the urban underground space.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discussions on the ecological damages,this paper analyze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ief system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ecological damage prevention mechanism.It includes a national principle for the compensation,a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an evaluation system and special fund for the underground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so as to provide legal supports for the relief in this process.
ecological damage;underground space;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prevention first
DF4;DF31;DF417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02
2012-01-08
黎 桦(1968-),男,湖北省武汉市人,湖北经济学院地方研究法制中心副教授,博士,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立法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YJA82003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2D039)
(责任编辑 易 民)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