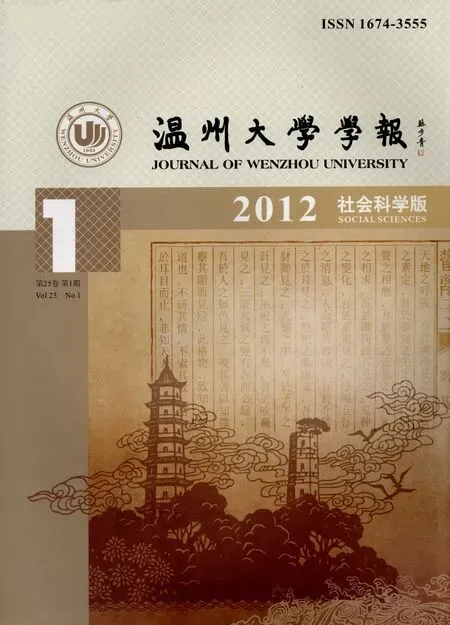亚当·弗格森《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道德评判新论
姚正平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亚当·弗格森《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道德评判新论
姚正平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亚当·弗格森的《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体现出鲜明的道德说教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罗马元老院和马尔库斯·加图的称颂与对盖乌斯·凯撒和格耐乌斯·庞培等专政者的批判上。这招致了后世诸多史家的非议。但是,重新认识《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的道德评判依然很有必要。首先,道德评判是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们普遍具有的倾向;其次,亚当·弗格森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自觉地抑制住自己的道德评判,而且作出了深刻的历史性论断;最后,对于《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的道德评判,亚当·弗格森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可见,绝大部分情况下,亚当·弗格森还是努力恪守其“叙而不断”的著史风格。
亚当·弗格森;《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道德评判;叙而不断
亚当·弗格森(1723 – 1816)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哲学家。其《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以下简称《罗马史》)于1783年首次出版,它的影响力同《文明社会史论》一样,超出了英伦三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引起广泛关注。道德说教是《罗马史》的一大鲜明特点,而这与其极为强调的史家应“叙而不断”、“消灭自我”的撰史风格是明显相背离的。亚当·弗格森道德评判在《罗马史》中具体有何体现?何以会产生治史理念和史学实践的严重冲突?对于亚当·弗格森来说,“叙而不断”的求真与“道德说教”的致用到底孰轻孰重?学界对此并未有专门研究,本文不揣浅陋,试对以上诸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罗马史》中的道德评判及其所遭致的非议
(一)《罗马史》中的道德评判
亚当·弗格森在1782年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及《罗马史》的写作时,曾明确表达过其“叙述、陈述事件,详述人物性格而不加入我自己的判断”[1],让读者自己去评判的治史原则。然而,亚当·弗格森并没有把他自己所标榜的“叙而不断”的著史理念贯穿到全部《罗马史》的写作,而是对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体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诸多的道德评判。
1.对罗马元老院、马尔库斯·加图的称颂
弗格森曾说过:“如果有一种群体适合统治全世界的话,那它就是罗马元老院。它由担任政府高级职位的官员组成,他们在执行议会决议和掌控它的军队时,研习过国家的事务。需永远铭记的是,它代表的是希望维护它的权威的那些人。如果这些人(试图)摆脱他们曾经维护的格局是可取的和合乎当时历史形势的话,那是因为这种格局已和他们更渴望的事物不相称了。”[2]77在这里,亚当·弗格森完全将他“客观叙述”式的著史方式抛到一边去了,他不是对元老院进行历史性质的叙述,而是代之以完全毫无顾忌的称颂,而且,这种歌颂似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眼里,元老院俨然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管理国家的最合适的政权机构。此时,“弗格森不再是满足于分析的历史学家了,而是道德学家那种随意的评判[3]49。这种道德学家所表现出来的“随意的评判”同样可见于弗格森对马尔库斯·加图、盖乌斯·凯撒和格耐乌斯·庞培等人的评价中。对于马尔库斯·加图,他给予了无尽的赞美,他说马尔库斯·加图用他的洞察力、勇气以及富于男子气概的稳重坚持同盖乌斯·凯撒、格耐乌斯·庞培这些企图颠覆共和国的专制独裁者作不懈斗争,而其他的人要么犹豫、屈服,要么连这些专断者的阴谋都没有察觉,这就使得马尔库斯·加图相较其同时代人表现出了备受瞩目的卓越[2]77,对于他来说,“美德本身就是其目标”,而对其同胞,美德只不过是他们获得最终利益的一种手段[2]78。
2.对盖乌斯·凯撒、格耐乌斯·庞培等专政者的批判
与对罗马元老院和马尔库斯·加图大加赞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当·弗格森对共和国晚期的专政者尤其是盖乌斯·凯撒、格耐乌斯·庞培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认为“有像格拉古、阿彪利阿、马略、秦那、克劳狄和迈罗这样的公民,共的国是很难保存下来的。但有像凯撒、庞培这样的公民,共和国更是完全没有可能维持下来,或许从权利掌握在他们手中去摆脱共和体制的那一刻起,共和国可能就被终结了。”[2]81亚当·弗格森将盖乌斯·凯撒、格耐乌斯·庞培等专政者斥为“投机分子”,进行着罪恶的行径,认为他们利用民众的混乱和武力进行着统治,而“当他们不能滥用国家正常的体制达到他们的目的时,就使用暴力把它们丢在一边”[2]81,而这些专政者还虚伪地披着共和体制的外衣。亚当·弗格森指出:他们“有预谋地进行着所有使他们的祖国遭难的罪恶,……在一段时间里,庞培俨然已把自己当成了君主,而与此同时,凯撒也对自己所采取最有效的措施而获取的权力欣喜若狂。也许,有人会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共和国已经很难维持了,以此作为凯撒等人破坏共和体制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种观点无异于为罪犯提供他们犯罪的借口。”[2]82亚当·弗格森认为:这就好比说“当国外出现拦路抢劫的盗贼时,旅游者肯定会被打劫”[2]82。他进而指出:“凯撒和庞培被谴责,不是因为共和国终结了,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罪恶,因为这些罪恶,共和国灭亡了。”[2]82
可以看出,亚当·弗格森此时表现得像一位十足的道德学家,而不是严格叙述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家。他在这里似乎已完全将自己所强调的“叙而不断”的治史原则抛到一边去了。他不仅对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体制、历史人物进行了大量的评判,而且这种评判不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做的历史性评价,而是一种基于他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标准的道德评判。亚当·弗格森把其政治思想同其对历史相关事件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可以看出:亚当·弗格森对共和政体是十分倾心的。正如有论者所言[4]35:
对于弗格森而言,那种教养不凡、品德优良的公民能将一切权利都稳定地委托给公职人员的政体是最幸福的政体。从这种表达中,我们可以发现,弗格森最喜爱的政体其实就是共和政体。对于他来说,共和政体是一种混和政体,共和政体实际上是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的一种结合。……二者的结合就能创造出来一种比较完美的政体即混合型的共和政体。
与对共和政体赞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亚当·弗格森对于专制政体的痛恨:“这种基于恐怖原则的罪恶政体所带来的只有暴政和腐败,它所展现的除了人性的最终堕落之外别无其他。”[4]36这些政治思想同其对相关历史事实的看法联系起来,就形成颇具亚当·弗格森个人色彩的但也广为后世所诟病的道德评判标准。即在很多情况下,但凡和他的政治思想保持一致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体制,他都会予以高度的赞美。如对作为罗马共和国共和体制集中体现的罗马元老院,努力维持罗马共和体制、积极提倡公民美德的马尔库斯·加图,他都几乎作为完美无缺的典范或道德楷模而大加称颂。而对那些明显和他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公然践踏罗马共和政体的所谓独裁者,他则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和强烈的谴责,尽管这些专政者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亚当·弗格森在此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倒不如说他在进行道德说教,他在为世人树立一个孰是孰非的道德标准。
(二)《罗马史》道德评判所招致的非议
亚当·弗格森这种极具个人偏见式的道德评判将其道德说教的特点暴露无遗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露骨的道德评判自然招致后世猛烈的批判和嘲讽。格奥尔格·尼布尔认为其《罗马史》毫无价值,“完全是一种失败”[5]。他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亚当·弗格森的“写作是实用主义的,并且伴有道德说教的倾向”[5]。哈里·巴恩斯则嘲笑道:“尤为可笑的是他对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贪财不义且目光短浅的罗马元老院的称颂。”[6]即使是为弗格森积极进行辩护,对其多有赞美之词的托马斯·皮尔登也指出其对罗马议会进行了颂词般的赞美,对“马略、庞培和凯撒进行了过度地谴责”,批评其在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人物和对罗马帝国早期历史的论述中其“历史学家的身份被其道德学家的身份所掩盖”[3]49-50。
二、重新认识《罗马史》中的道德评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亚当·弗格森在《罗马史》中进行了不少的道德评判,而且这种道德化的倾向的确已经对《罗马史》中的公正、客观的叙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绝不能成为否定《罗马史》史学成就的理由。托马斯·皮尔登的批评有失偏颇,而格奥尔格·尼布尔将《罗马史》中道德化的倾向作为其对《罗马史》毁灭性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的做法则更不可取。如果对亚当·弗格森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在《罗马史》中道德化倾向进行更深入认识,我们更多地看到的将是《罗马史》的成就,而不是其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说教的特点了。
(一)应注意《罗马史》写作的历史背景
18世纪是理性主义史学大行其道的时期,而理性主义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历史被认为是个人美德和正确公共政策的导师”[3]10。换言之,道德说教是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所普遍具有的特征。从法国启蒙巨匠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到英国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大卫·休谟、威廉·罗伯逊都无不在其史著中表现出明显的道德说教倾向。如汤普森认为:伏尔泰“撰写历史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是政治家的一所学校。他在《查理十二世》序言中写道:‘难道有谁在读过这位国王的传记之后,还不应当把好战的痴心妄想彻底治好吗?’于是乎历史就变成道德家为说教而选择事实的东西了;凡是不合乎这个要求的东西都不要了。”[7]107对于大卫·休谟,历史同样具有“作为道德教师的价值”[7]102,而“罗伯逊也像休谟和伏尔泰那样喜欢说教”[7]115。可见,道德说教是理性主义史学家们普遍具有的倾向。亚当·弗格森很难不受这种史学写作风格的影响,再加上其本人在爱丁堡大学执教道德哲学多年,因此《罗马史》中表现出“道德化”的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当·弗格森在史著中所进行的道德说教尽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叙述的公正、客观,但后世史家不能因此就否定《罗马史》的史学价值。否则我们在否定弗格森《罗马史》的同时,实际上,把贯穿18世纪明显带有说教气息的理性主义史学也一并给否定了。
(二)后世史家对《罗马史》的批判有夸大之嫌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亚当·弗格森的确在《罗马史》中违背了其“叙而不断”的著史风格,表现出了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自然也就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然而,这种批判未免有夸大之嫌,如托马斯·皮尔登对弗格森在《罗马史》中道德说教的批评。实际上,亚当·弗格森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中,不仅自觉地抑制住自己的道德评判,而且还作出不少深刻的历史性而非道德说教式的论断。
例如,他对盖乌斯·屋大维的评价。盖乌斯·屋大维相较盖乌斯·凯撒在专制方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同马克·安东尼、马库斯·雷必达在公元前43年公开结成了后三头同盟。为谋取其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将联军开进了罗马,解散了原来的政府,并利用军队的威摄力,迫使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承认三头同盟的合法性。接着,后三头同盟实行血淋淋的公敌宣判,消除反对势力。后三头同盟打着“为凯撒报仇”的旗号,对所有曾反对他们或对他们有不恭言行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被宣布处死和没收财产的元老约有3 000人,被处死的骑士约2 000人”[8]121,此外,他们还乘机“聚敛财富,装备军队”[8]122。公元前31年亚克兴战役中击败马克·安东尼后,盖乌斯·屋大维打着“共和”的幌子不断加强自身的权力。公元前30年,他重新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的称号;公元前28年,获“元首”称号;公元前27年,又获得“奥古斯都”的称号。他还是执政官、行省总督的统治者、大祭司长等。“他打着‘元首’的旗号,挥舞着帝王无限权威的大棒,对共和制的大本营——元老院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和改造,使其成为毫无实权、完全听命于元首的忠实工具”[8]155。可见,不论是盖乌斯·屋大维所获得的权力,还是其专横的程度,都远超盖乌斯·凯撒,而且表现得更像一位专制的君主。然而,对于这么一位公然藐视、破坏共和体制的阴谋专权的独裁者,亚当·弗格森却并没有像对待盖乌斯·凯撒那样给予猛烈的抨击,而是对盖乌斯·屋大维的专权报以宽容理解,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性分析。他指出:盖乌斯·屋大维也是反共和国的,但相比盖乌斯·凯撒,在很多方面他又是可以被原谅的。他所处的形势与盖乌斯·凯撒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持续的专制统治背景下,“他的国人已经屈服于君主制了”[2]83,他自己被认为是拥有无上统治权的盖乌斯·凯撒的继承人,“因此,至少他是更加靠近世袭君主的处境了”[2]83,在这种背景下,他将最高统治权当作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2]83。可见,亚当·弗格森从当时的罗马公民对君主制的态度和盖乌斯·屋大维从盖乌斯·凯撒那里继承的最高统治权所受到的普遍认可这两个角度为屋大维的专权进行了辩护。此外,他还通过论证当时盖乌斯·屋大维所处的险恶形势来表达对其独裁专政的理解,他指出:盖乌斯·凯撒被刺的命运让盖乌斯·屋大维充分地意识到他应表现得像一个罗马公民,更加的谦恭,等到合法年龄时,通过宪法选举获得国家的统治权。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不可能像一般的公民那样,通过正常途径去获取统治权。他生活在为争夺统治权血雨腥风地厮杀的年代。作为一个派别的领袖,摆在其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获得最高统治权,要么死于他人刀下。受此影响,他继承其养父盖乌斯·凯撒的目标,压制公民政府,铲除一切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竞争者[2]85。如果说亚当·弗格森对盖乌斯·凯撒的批判表现的是其道德学家的一面,那么对盖乌斯·屋大维的评论则更多地反映出其尊重事实的历史学家的形象。
再如,他对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院以及马尔库斯·加图等人的评议。尽管弗格森由其对共和制度的热爱而对罗马元老院、马尔库斯·加图大加称颂,但同时,他也认为共和体制、马尔库斯·加图等维护共和国所进行的奋勇抗争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所统治的庞大疆域以及其内部的严重腐化已经是罗马元老院所无法驾驭的了。罗马元老和普通的罗马公民也已腐化不堪[2]74。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需要一种强权统治。因而,可以说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也就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尔库斯·加图等人维护共和国的努力就是一种错误[2]75。但是,弗格森又进一步指出:不应因此对这些人扣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帽子。他说:在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人们必须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历史形势[2]75。在这里,亚当·弗格森不仅对罗马共和国衰落的原因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认识到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疆域的日益扩大,原有的政治体制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局势的要求,共和体制向帝制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对马尔库斯·加图等人的评论也体现出了其颇具前瞻性的历史主义观点。可见,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判,亚当·弗格森尽管有“道德化”的倾向,而且这种“道德化”有时还表现得那么的强烈,但他在很多时候也并没有忘记自己历史学家的身份,他还是努力地在尊重历史事实,尽管这种历史事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三)对于《罗马史》中的道德评判,亚当·弗格森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亚当·弗格森说:“虽然在编辑这部历史时,本打算避免表达赞美和批评的情感,而是详述事实和具体说明人物的性格,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陈述历史本身,而不是作者的判断。然而,有关优劣的问题是相当难以处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最正直的读者也有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史家也就可能倾向于总的讨论了。”[2]73可见,只是因为涉及到诸如历史人物、体制优劣评判这些在弗格森看来较为棘手的问题,他才认为有必要进行道德评判,以防止读者得出错误的认识。通观他的整部《罗马史》,绝大部分情况下,亚当·弗格森还是努力恪守其“叙而不断”的著史风格,尽可能地对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的历程作出客观公正的叙述,而道德说教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维琴佐·梅罗莱认为:即使道德说教隐藏于《罗马史》中,也“仅仅微不足道地影响了《罗马史》的叙述”[9],此语是十分中肯的。亚当·弗格森自己也指出历史学家既应是道德学家,也应是事实的叙述者,但事实才是历史的本质[10]19。他认为:尽管有些道德学家认为真理应该在美德面前做出让步,但“历史的目标必须澄清为对过去公正的叙述”[10]22。《罗马史》就是亚当·弗格森在这一治史理念指导下的最突出的实践成果。
总之,《罗马史》虽然体现了亚当·弗格森道德说教的特征,但它更多彰显的还是一位秉笔直书、公正叙述的历史学家的形象。
[1] Ferguson A. Adam Ferguson to William Strahan, 15 July, 1782 [C] // Merolle V.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Ferguson.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95: 285.
[2] Ferguson A.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vol v [M]. Edinburgh: Bell &Bradfute, 1799.
[3] Peardon T P. The Transition i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1760 – 1830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3.
[4] 翟宇. 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政治思想[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5] Niebuhr G.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e [C] // Merolle V. The Manuscripts of Adam Ferguson. London: Picking & Chatto, 2006: 322.
[6] Barnes H E.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M].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3: 166.
[7] J W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 第三分册[M].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8] 宫秀华. 罗马: 从共和走向帝制[M]. 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9] Merolle V. Introductory Essay [C] // Merolle V. The Manuscripts of Adam Ferguson. London: Picking & Chatto, 2006: xxiv.
[10] Ferguson A. Of History and its appropriate Stile [C] // Merolle V. The Manuscripts of Adam Ferguson. London: Picking & Chatto, 2006.
New Discussion on Moral Judgment of Adam Ferguson’s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YAO Zhengp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China 235000)
Adam Ferguson’s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displayed obviously moral suas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raise for the Roman Senate and Marcus Cato and criticizing for the dictators such as Caius Caesar and Gnaeus Pompey. This kind of apparent moral judgment aroused criticism form many later historians.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moral judg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Firstly, moral judgment was a general tendency of historians of rationalism in the 18th century; secondly, Adam Ferguson not only consciously restrained his moral judgment on som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but also made profound historical conclusions on it; finally, Ferguson also provided a spec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moral judg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It could be seen that Ferguson still strived to comply with his style of historical writing of narration without judgment in most cases.
Adam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Moral Judgment; Narration without Judgment
book=1,ebook=20
K091
:A
:1674-3555(2012)01-0073-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1.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1-01-18
姚正平(1984- ),男,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