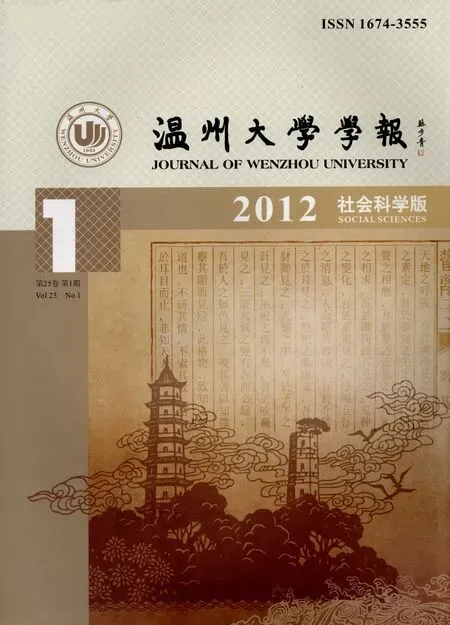论《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吴国强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论《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吴国强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春秋战国,儒墨颉颃,百家争鸣。即使是在《墨子》兴盛一时的战国,《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脱离援墨注儒的藩篱。儒学为宗,《墨子》绝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学者立足儒家学说,看墨必提儒、说墨必比儒,赞墨必赞儒。
《墨子》;援墨注儒;儒墨关系
《墨子》研究,渊源流长。李光辉认为,关于《墨子》的评说及研究在战国就开始了[1]。豪舍尓说:“观念史力求找出(当然不限于此)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2]按照这种方法论的要求,我们即可以逐一离析出《墨子》研究的核心观念,并与一个时期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历程相互印照。援墨注儒现象即为清以前《墨子》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战国至秦汉间的《墨子》取舍
春秋以降,大道废弛,诸侯以百姓为刍狗。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士民阶层形成。剧烈的社会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学派纷纷出现。各派各家都著书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儒、道、墨、法、阴阳、名、兵、农、杂、纵横各家在战国可谓争奇斗艳,百家争鸣。
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悬,安顿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远,战国时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仅有的鲁胜《墨辩注》已亡佚外,专门著作鲜见纸端,只是散见于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这一时期,赞墨者少,且浅尝则止,多为零碎的议论,《墨子》研究处于沉寂之中。
熊铁基指出,汉初道家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可见,诸子之间虽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长,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虽对墨子的做人立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却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墨家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墨家所谓主张“兼爱”即为“无父”,为“禽兽也”。荀子更是对《墨子》不屑一顾。《荀子·非十二子》中认为“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简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铏也。”反对墨子“僈等差”(《王霸》),“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反对墨家“自为之然后可”,《天论》攻击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解蔽》反对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国》篇则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认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进行专门批驳;又如《韩非子·显学》评说儒墨术等流派及儒墨丧葬之说优劣等;解释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因这些观点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场,故这些学说往往从儒家角度评述墨子及墨家,或只为一定目的“执其一端”,这种立场和方法客观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从侧面显示了诸子百家对墨家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研究不足,说明墨家当时已开始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
《史记》言墨家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侠,讲信重义。秦汉社会,此风尤盛。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靠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国,还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汉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会弥漫着尚武习气。即便是文人,也是“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4]秦的高压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发展及传播。
秦短祚而亡,诸子俱损,援墨注儒虽无从谈起,但《墨子》却在各种学说中变相传播。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尸骨未寒,儒术即被汉儒推为至尊,汉初“除挟书令”(《汉书·惠帝纪》),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晃错篇》)从汉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间仍薪火相传,不仅没中断,且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时指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足以证明《墨子》及墨家作为汉代六大学术之一的重要性。贾谊在《过秦论》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贤”,秦后首次将孔墨并称,可知,《墨子》在汉初学术流变中实际上是在其他学派体系中实行了思想流传,与其他学说共同构造了汉初的主流思想,其实是《墨子》的变相发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样:“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5]此种诸学皆出于墨的论点,使得《墨子》在儒家经义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视。
二、唐宋辞章之儒看《墨子》
隋唐是大统一的格局。到唐朝,战国时期那种国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没有了,对于《墨子》的研究就更显得客观与中庸。虽然很多士人研究《墨子》,但亦为援墨注儒的变例。
从赵蕤对《墨子》在内的诸子各家学说的普遍认同,即可看出,唐初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给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赵蕤引墨子“节用”论以批评当政者奢糜不恤民情,与魏徵编辑《群书治要》主旨相同,即为统治者施政提供理论借鉴,客观上巩固了儒家的文化统治。他在《长短经》记有“神农形悴,唐尧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6]对墨家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赵蕤这种把墨儒等同对待的态度,使得儒家与墨家皆为其所用。
唐儒韩退之开启“儒墨为用”的千年论争,不仅是墨家思想虽绝犹存的证明,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援墨注儒不仅抬高了墨家的主张,也把儒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它表面上试图调和儒墨,实际上使儒学的内容更为广泛,使得《墨子》成为阐释儒学的工具。
韩愈承汉代“儒墨并举”、“孔墨同称”的传统,一篇《读墨子》①见: 马其旭.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下引韩愈之文皆出于此本,不再一一注出.让其备受批评与争议。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仅就《读墨子》一篇或许还难以了解韩愈对《墨子》的全面态度。《与孟尚书书》中道:“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由此可以断定,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所主张的“孔墨相用”实意在说明:儒墨之辨,实“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所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韩愈的这种崇儒排墨的思想其实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表述。如《上宰相书》有曰:“仅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之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亦表明其对儒墨家的立场。而且在《问进士策》里,韩愈亦以“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表明了儒家立场。此外在《送王秀才序》中亦谓:“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字孟子始。”《送浮屠文畅师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问之名则非,校其行而是,可以与之游乎。”如果之前儒墨同用乃明智,“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韩愈把它“取以为法焉”,这就有点不正常了。更何况浮屠师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目的也只是“咏歌其所志”,与儒家读书报国的心理如出一辙。
然而后人对韩愈的评述更让人无可奈何、甚至啼笑皆非。程颐写道:“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7]欧阳修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言道:“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8],算是客观之说,然后世之评说就有失公允。首先黄震否定了韩愈之说,“墨子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孟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愚曰: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9]马端临亦在《墨家考》中说:“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之。”认为墨翟之言华而不实,“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并建议“深锄而力辩之”[10],他对墨家的学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儒家卫道士的立场。
朱熹更甚,在《墨子》中斥道:“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尽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11]对墨子惟恐避之不及。高似孙《子略》言:“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伪,型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12]。王令亦言:“墨翟固有罪”,“天下之大害者”[13],在援墨注儒的基础上,甚至压墨扬儒。栾调甫说:“《墨子》书自汉以来,已不甚显闻于世。宋元而后,益弗见称于学人之口”[14]总之,宋儒虽然不避谈《墨子》书,但其“辟墨”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评墨已趋于平心静气的学术分析(如朱熹、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子》中的思想和杨朱已区别对待,但援墨注儒贯穿于宋儒研究《墨子》的始终,阐释《墨子》即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终未变。
三、明清时的援墨注儒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体生产者成为社会上活跃的经济主体,经济上的自足引发了精神上的自觉,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和学说来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墨子提倡的平民意识等一系列主张正是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为《墨子》的重新振兴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基础,是《墨子》再度复兴的重要条件。张翰在他的《松窗梦语》中,描述当时商贾贩夫,“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追逐锚株之利至富的情状:财利之于人,甚矣哉……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15]。大量书籍被印刷和出售,客观上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墨子》一书也是其中的一种。
据郑杰文考证,自正统年间《道藏》之《墨子》由张宇初编纂以来到崇祯时金堡、范方等评点《墨子》,在276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墨子》刊、校、注、研究等著作共计28种。由于明人刊刻的序跋、评点较多,所以刊刻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墨子》研究的拓展与深入[16]。
明万历进士第一名、著名思想家、文献考据学家焦竑在《墨家小序》中认为:“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兼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不亲,此其弊也。”[17]焦竑有专门讨论义利关系的文章写道:“自世狠以仁义功利歧为二途,不知即功利而条理之乃义也。……一厚农一足国,桑大夫盖师其余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废也。藉第令画饼癖饥可济于实用,则贤良文学之谈为甚美,庸柜而必区区于此哉。”[18]对于义利问题,焦竑否定了墨家公利大于私利的主张,赞扬儒家义利并重才能使天下安定的思想。对儒家经典《易》将义利并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举了桑弘羊义利并重,辅佐武帝厚农足国的例子。指出施行墨家主张的后果是“取贫民则公利薄,而民去其业”。
对于《墨子》中的主张,宋濂持批驳的态度,“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者,固孔子之所弃乎?或曰,如子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哉?曰:为有二本故也。”[19]他认为孟子之所以弃墨是因为儒家中已有“二本故也”。
相对于宋濂,陆稳的取舍恰相反。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刻本,陆稳叙述了自己认识《墨子》的历程。他认为墨子“非圣人类也”、认为贾生“特言之过耳”,对韩愈谓其道与圣人相为用甚“疑焉”。他认为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并认为墨子“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孔孟并称,“宜也”。他批评孟子,出于孔墨之后,“孤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流欤?”[20]这与李贽反对传统思想,对《墨子》加以赞扬不谋而合。
相比陆稳,李贽与胡应麟的评说有点激烈。李贽认为墨子的救世主张是对的。“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人入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21]。对于孟子辟墨给予讽刺抨击。胡应麟则认为墨家异于儒家,是因为要争一席之地,标立意,立心说。他认为《墨子》“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至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与衰周之世”[22]。汪中表达的观点在当时是最有反儒色彩。他认为墨子所倡学说与禹相同,并非“墨子背周而从夏”,并认为“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并对墨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23]给予了极高的赞赏。针对此种“不伦不类”,翁方纲讽刺攻击道:“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24]。
散文家兼词人的张惠言则认为墨子影响系“炒作”之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虽他说悖于常理,不安于心者,皆从而则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25]。
此外毕沅在《墨子叙》中亦曰:“世之讥墨子,以其节丧、非儒说。墨者既以节丧为夏法,特非洲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对墨家的非儒说进行批评,并嘲讽“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26]。这也是后世学者批判毕沅《墨子叙》的理由,即好以儒言附会。毕沅说与孙星衍不谋而合,孙在《墨子后序》中也表达了孔墨同出,且墨高于孔的思想,并对司马迁、班固等人对墨子的理解给予批正[27]。对于司马迁与班固“皆不知《墨子》之所出”,只有淮南王知之,“‘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28]对于孟子批评墨子予以反击,评说还算中允。虽此四人为弘扬墨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毕竟是辞章之儒,他们的对儒墨关系的理解也流于表面,至多只能表达对墨子的敬意。
综上所述,由于乾嘉学人固守儒家的正统思想,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篱。被认为阐释《墨子》比较大胆的汪中亦是如此。他只是把墨子作为一个解释经书,证明事例的工具,校注《墨子》时往往使用经书的路数来穿凿附会,如此以来难免错漏较多。这在清代学人的著作中多有评述,此不赘述。汪中虽然让沉寂的墨子及《墨子》暂时受到了重视,但孔墨在汪心中地位高低不言而喻。汪中虽给予墨子极高赞赏但亦未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更遑论张惠言等人了。
清军入关后,虽然仍是孔儒独尊,但由于士人远离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讨论,文人们主观上远离政治,他们著书立说,渐渐走上了循经求义的路子。不仅如此,晚清孔孟之学受到公开批判后,为了从传统学术中发掘救国良策,一些学者结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对《墨子》中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进行归纳、分析和综合[29-30],此种背景下《墨子》研究的发挥经义亦成为《墨学》研究史上一大特色之一。
[1] 李光辉.《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J]. 殷都学刊, 2006, (4): 102-105.
[2] 豪舍尔. 序[C] // 伯林.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 冯克利,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5.
[3] 熊铁基.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J]. 文史哲, 1981, (2): 73-78.
[4] 司马迁. 游侠列传[C] //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722.
[5] 蒙文通. 儒学五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6-57.
[6] 赵蕤. 长短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9.
[7] 程颐. 宋程子遗书[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31.
[8] 欧阳修. 墨家小序[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29.
[9] 黄震. 墨子说[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32.
[10] 马端临. 墨家考[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28.
[11] 朱熹. 墨子[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31.
[12] 高似孙. 子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0.
[13] 王令. 书墨后[C] // 王令. 广陵先生文集: 第3册. 刻本. 刘承干, 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7-9.
[14] 栾调甫. 二十年来之墨学[C] // 栾调甫. 墨子研究论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39.
[15] 张翰. 松窗梦语[M]. 萧国亮, 点校.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80.
[16] 郑杰文. 中国墨学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98.
[17] 焦竑. 墨家小序[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29.
[18] 焦竑. 书盐铁论后[C] // 焦竑. 澹园集. 李剑雄,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272.
[19] 宋濂. 诸子辨[M]. 顾颉刚, 点校. 上海: 朴社, 1926: 22.
[20] 陆稳. 新刊墨子序[C] // 严灵峰. 无求备斋墨子集成.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2.
[21] 李贽. 墨子批选[C] // 陈梦雷, 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 第176册[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4427.
[22]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51.
[23] 汪中. 墨子序、墨子后序[C] // 孙诒让. 墨子闲诂.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20-25.
[24] 翁方纲. 书墨子[C] //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43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618.
[25] 张惠言. 书墨子经说解后[C] // 孙诒让. 墨子闲诂.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424.
[26] 毕沅. 墨子叙[C] // 任继愈. 墨子大全: 第1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2.
[27] 孙星衍. 墨子后序[C] // 任继愈. 墨子大全: 第1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7.
[28]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09.
[29] 章太炎. 诸子学略说[C] // 章太炎. 章太炎政论选集: 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95.
[30] 张纯一. 墨子分科[C] // 任继愈. 墨子大全: 第1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605-606.
Research on Phenomena of Studying Mohism for Interpreting Confucianism Purpose in Mozi Study
WU Guoq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is a period of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 of thoughts, among whom were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Eve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which Mozi was popular, study on it could not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effection of studying Mohism for interpreting Confucianism purpose. Because the Confucianism occupied the dominant role, the Mohism seemingly withered (actually, it still kept alive). It is the inveteracy of thought that Confucianism is the orthodox ideas that limits the later scholars of Mozi study in the thinking mode of studying Mohism for interpreting Confucianism purpose. Consequently, later scholars fall into a fixed thinking pattern of studying Mozi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ism.
Mozi; Studying Mohism for Interoperating Confucianism Purpose; Rela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编辑:刘慧青)
I206.2
A
1674-3555(2012)01-003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1.00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2-15
吴国强(1984- ),男,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