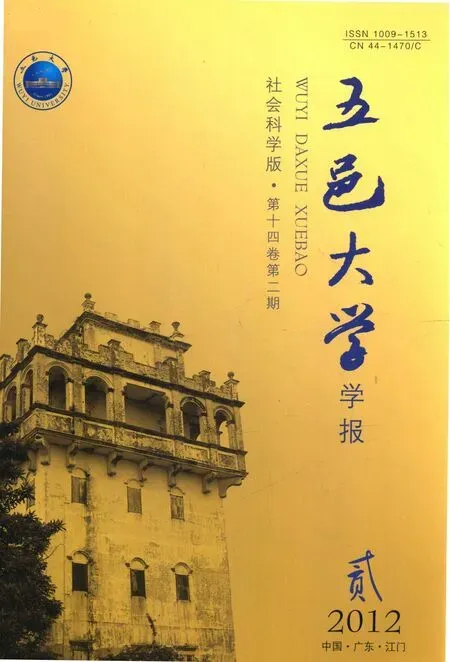试论我国 “见危不救”犯罪化制度性建构
姚万勤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试论我国 “见危不救”犯罪化制度性建构
姚万勤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见危不救犯罪化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目前我国从解释论的角度对真正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进行扩张、将见危不救纳入犯罪的做法似有不妥。但从法文化的传承性以及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性出发,可在我国刑法中增设 “见危不救罪”,并在立法论中对其成立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见危不救;不作为犯;保证人;先行行为
“见危不救”能否用刑法予以规制,这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位代表提出要在我国增设“见危不救”、“见死不救”罪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议案一直被搁置。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道德缺失泛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增设此罪名。尤其是经过湖北荆门的 “天价打捞门”事件以及于最近发生在广东佛山的 “小悦悦事件”之后,仅停留于口诛笔伐已不能有效遏制该类事件的再发生,从刑法的角度予以规制势在必行。
一、传统解释理论的困境——不作为义务的解读
在刑法理论中,存在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划分。作为犯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动静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即违反了刑法规范中的禁止规范而构成的犯罪,例如用刀砍杀他人的行为。不作为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命令规范而不去实施刑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即行为人负有刑法要求必须履行的某种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行为。[1]167如果以作为方式规定的犯罪,也可以由不作为的方式予以实现的话,在刑法理论中被称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例如杀人罪,既可以是积极利用身体活动结束他人的生命,也可以是在他人处于危难之中不给于救助而致他人死亡的行为。本来,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形式所规定的,应该只能认可作为的实行行为,但是也认可了与其正好相反的实行行为,因此,应当依据何种根据、在何种范围内承认该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成为重大课题。
(一)德、日刑法中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争论
在德国、日本刑法中,就不真正不作为犯而言,并不是只要不作为与构成要件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质言之,不能单纯地依据因果关系来确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否则必然扩大处罚范围,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德国刑法学者Johannes Nagler提出的保证人说,即指发生了某种犯罪结果的危险状态中,负有应该防止其发生的特别义务的人,保证人虽然能够尽其保证义务,却因懈怠而不作为时,就能成为基于不作为的实行行为。[2]于是在德国、日本刑法理论和判例中,将基于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视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要素,即只有基于保证人地位形成的作为义务才可视为义务的来源。这已经成为德日刑法中的通说。那么什么样的义务可以成为保证人的义务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存在形式的法义务说与实质的法义务说之间的对立。但是,对于该论题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成为国内的通说,就实质的法义务说而言并非没有疑问,就排他性支配领域说而言,“在过失犯的领域通常的承认同时犯的,但在过失犯的场合不能肯定个别的行为对于结果的排他的支配,也就是说承认同时犯和认可排他性之间是矛盾的,不能将排他的支配当做作为犯和不作为犯的共同的要件”[3]。具体的依存说提出的具体标准并不明确,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妥当。先行行为与危险创造说虽然在判断标准上予以明确,但在处罚范围的限制上仍不尽理想。
(二)我国刑法中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争论
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涉及到保证人的学说,目前最大的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形式的法义务说之中,即主要存在五义务来源说与四义务来源说之间的对立。五义务说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包括 “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上和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的先行行为、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1]171。而形式的四分说认为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并不能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4]换言之,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这样的义务能否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是目前最大的争议。例如,两个谈恋爱的人之间是否具有救助的义务?相约登山的人之间是否具有相互救助的义务?看见火灾而不报警能否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有论者认为将其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来源 “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刑法功能的需要。对那些严重侵蚀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不仅要从道德上予以谴责,更要用法律制裁之”[5]。有学者认为,“道德义务只有在法律有了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上升为法律义务,如果法律对此情状没有规定,单纯的不救助行为是不可罚的。”[6]
(三)解释路径的困境及笔者的立场
其一,如果承认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这样的义务能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话,那么针对本文开头的两则案例,就可以追究行为人不作为的杀人罪,但是这样的结论难以让人接受。诚如此的话,那么刑法不再是保障人权的大宪章,对他人权益反而可以恣意地侵犯,所以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角度而言,不能承认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这样的义务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
其二,日本法中的确存在包括先行行为在内的习惯、条理产生的作为义务,即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而产生的作为义务。但此处的公序良俗等是由先行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否则不能予以承认,因为先行行为为作为义务根据的趣旨,在于由自己的行为使产生结果发生的危险者能够立足结果发生的地位,在于道理上社会期待这种防止,可以承认能够支配构成要件结果发生危险的地位。[7]
其三,如果能够承认该种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的话,那么必然有违罪刑法定这一铁律。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处罚法,所以由其规定的犯罪和刑罚必须以其明文规定为限,这样才能保障行为人的自由。现代法治国家基本都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来限定国家的刑罚权,以防止根据国家权力的刑罚权的恣意行使,不至于扰乱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倘若承认了该种义务的话,那么刑法又必然沦为专制的工具。故国民道义观念的作为义务,也必须在国家刑罚法规的解释上作为考虑,这也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下的当然要求。
基于以上三种理由,笔者认为不应当将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这样的义务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换言之,如果想将本文上述的两则案例解释为犯罪至少在解释论上存在障碍。如果坚持日本刑法理论中实质的法义务来源说,也不能肯定见死不救的行为成为犯罪,因为至少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并不存在保证人的地位,从而也就否定了冷漠行为人的行为性,不能予以科处相应的刑罚。
二、“见危不救”立法路径可行性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对见危不救者尚无具体的法律对策,虽然公众的舆论可以对其进行多种形式道德意义的责难,但众多的批评和谴责并不能唤醒见危不救者的良知。所以仅仅通过道德舆论调整以防止该类事件的发生已显得力不从心,人们如果想避免该种情况的继续发生,有必要在立法路径中予以完善。基于以下理由,笔者主张可以在我国设立 “见危不救”罪。
(一)从法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我国古代早有处罚 “见危不救”的立法例。我国秦代的法例中规定:“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8]意为有贼人在大道上致他人受伤,而百步之内的旁人不予以救助的话,应当罚两件战甲。及至唐宋时期,法例如此规定的也不乏其例,如 《唐律疏议》第28卷:“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元、明、清朝也都有处罚 “见危不救”的规定。从法文化传承性的角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设立 “见危不救罪”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与不适。
(二)从法与道德关系的角度而言,两者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后,某些道德完全可以转化为现实中的法律。“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他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9]换言之,道德对法律的创制具有指导作用,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观念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为指导,反映道德的基本要求。就像我们可以根据道德了解法律应该是什么那样,我们也可以将法律作为道德领域的深度思考的指针。[10]例如英国历史上,通过拒绝死刑英国法采取了一种盖过 “大众道德观”强烈倾向的立场。同样,法律顺应 “大众道德观”的变化而改变的例子也很容易举出。例如我国历史上曾经一度依据刑事政策的考虑而处罚堕胎的行为,而现在在我国刑法典中没有将堕胎罪入刑。又如一些针对婚姻家庭的违法行为而将其犯罪化的做法想必也是支持 “大众道德观”的强烈倾向的结果,因为在大众看来,恋爱自主、婚姻自由是现代文明的象征,那些通过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必然有违大众的道德观,所以我国刑法中必然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见危不救”原本也是道德调整的范畴,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案件,我们一味寄望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但国民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法律的颁布可制定出诚实和人道的标准,最终改变和提高现有的道德水平。就此而论,“见危不救”入刑必然反映 “大众道德观”,并改善现有的道德水准。
(三)从刑法的目的而言,刑法着眼于保护法益。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法益造成了侵害或者威胁。立法伦理主义认为,区分法律与道德不能说明现代立法的现状,现代各国的刑法在内容上都充满了伦理规范,刑法上规定的犯罪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行为。[11]330这表明了刑法内容中包含了大量的伦理规范,除却道德伦理考虑的话,任何犯罪都可以用法益侵害予以解读。例如,世界上多数国家将通奸行为予以犯罪化,无不立足于社会公共风俗利益的考虑。更进一步而言,现在一些国家将某种道德法律化,并不是为了单纯保护道德这样的规范本身,也并不是该行为违反了道德,而是该种行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如果对某种道德规范的维持并不能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立法者就不会将违反道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11]332就 “见危不救”行为而言,只要该行为人在可以而且容易救助的情况下却不给予相应救助,这样的行为就对法益造成了侵害,将其用立法例明确规制也并无不可。
(四)处罚 “见危不救”已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将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有这样的立法例。虽然不能说这是国外普遍的做法,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例如德国刑法第323条C项明确规定,“对意外事件、公共危险或者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有可能予以救助,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科处相应的刑罚。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即“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者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科处相应的刑罚。除此之外,西班牙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奥地利刑法典、埃及刑法典均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法系的美国模范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也有类似之规定,如知道他人的财产面临火灾能报警而不报警,或者明知他人处于危难之中,能够拨打911而不拨打的,构成轻罪。
三、“见危不救”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设置的构想
任何理论的探讨最终都以服务司法实践为目的。就目前而言,将见危不救予以犯罪化是大势所趋。但具体到制度的设计上,我们不应该走法律浪漫主义的道路,即必须在制度的设计上明确化。[12]换言之,如果以法文的形式肯定道德、公序良俗这样的义务能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那么必须在立法路径中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样反而有可能对国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应有的侵害。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笔者认为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模范刑法典可以作为立法的参考。我国见危不救的罪状可以表述为:“对处在危险中的他人,行为人能够进行救助,而且该救助对自己或者其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不予以救助,造成损害的,处罚金。”详而言之如下:
第一,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他人的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一般而言,他人的法益处于危险的状态是指意外事故、公共事件或者其他危险事件的发生而导致的法益的危险状态,当然此处不能包括行为人自己的先前行为导致的法益的侵害,如果由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的发生的话,那么该种情形属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应该以他罪的不作为犯罪予以追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
第二,行为人能够对他人进行救助。法律不强人所难,在巨大的危险面前,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刑法不应该期待他人在不能救助的危险面前见义勇为,那样反而对法益的保护不利。所以行为人能否对该种危险进行救助,这必然要涉及到具体法益的权衡后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例如,在他人房屋失火的情况下,并不能期待行为人像消防队员一样去实施救火,但是在该种情形下,行为人完全可以拨打火警急救电话。再如 “小悦悦事件”中,并不要求路人都像医生一样对受害人进行专业的抢救,但是在那种情形下,完全可以将被害人搬离险境,再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可想而知,这对于一般人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被害人而言可能就是帮助其脱离命悬一线绝境的关键之举。
第三,该救助行为对自己或者他人均无危险。在法益权衡之后,救助行为应该不能影响到自己或者他人的安全。例如,看见他人落水,而自己本身没有游泳的技能却强行让其抢救,那么可以预想这样的规定毫无实际意义。笔者认为,见危不救罪的设计目的就是帮助他人脱离险境,尽最大可能救助需要救助的法益,而不是纯粹为了见义勇为而牺牲另一方的法益,否则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不符合刑法经济性的要求。
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故意不给予救助,客观上造成法益进一步恶化。如果行为人的确因为不知道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人发生了危险,即使行为人出现在事发现场,也不能对行为人进行责任的非难。所以本罪在责任的层面上,笔者认为将其限定为明知他人发生危险而不予以救助的情形为宜。如果在场的行为人虽然没有进行必要的救助,但是在场的其他人进行了相应的救助,并避免了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也不应该对该行为人科处相应的处罚。因为相对于被害人而言,其法益状态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
第五,从法律效果上而言,不宜规定较重的法定刑。见危不救罪如果上升为法律,那也是道德法律化的当然结果,对行为人而言,人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该类事件的发生,而且该种危险状态毕竟不是自己造成的,其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责任的非难性都应该轻于行为人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设定较重的法定刑的话,必然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
[1]马克昌.犯罪通论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大塚仁.刑法概说 [M].第3版.东京:有斐阁,1997:146.
[3]山口厚.刑法总论 [M].付立庆,译.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8.
[4]张明楷.刑法学 [M].第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4.
[5]吴爽,孙瑛.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 [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 (3):110-112.
[6]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70.
[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77.
[8]睡虎地秦墓竹简 [G].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94.
[9]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79.
[10]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的责任 [M].罗豪才,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23.
[11]张明楷.法益初论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2]王怀章.试论见危不救犯罪化 [J].青海社会科学,2003 (5):117-120.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riminalization of"Not Rescuing People in Danger"
(by YAO Wan-qin)
Criminalization of"not rescuing people in danger"is a world trend.China's current of practice of criminalization of such acts through expanding the sources of failing one's obligation is not pro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inherit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benefits by the criminal law,China should add the crime of"not rescuing people in danger"to its criminal code and restrict the scope of its establishment.
not rescuing people in danger;omission;guarantee;advance behavior
D924
A
1009-1513(2012)02-0059-04
2012-02-19
姚万勤 (1987—),男,安徽芜湖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