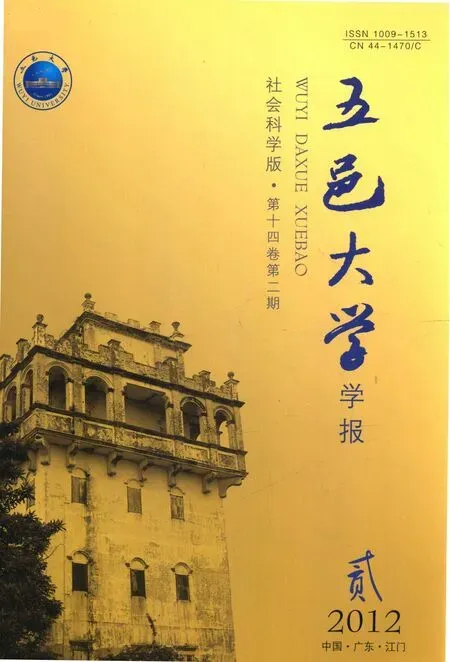“静坐中养出端倪”到 “随处体认天理”——陈白沙、湛甘泉心学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卓 进,王建军
(1.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2.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静坐中养出端倪”到 “随处体认天理”
——陈白沙、湛甘泉心学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卓 进1,王建军2
(1.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2.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湛甘泉的心学思想承传自陈白沙,但二人的心学教育思想却存在重大分歧。在教育理论层面体现为从 “静坐中养出端倪”到 “随处体认天理”的演变,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是否采用正规的书院式教学。这种分歧既是解决白沙心学内在学理困境的需要,还由于二人的时代背景与主体身份已发生重大转变。
陈白沙;湛甘泉;广东书院;心学
广东儒学自明代开始崛起,陈白沙标揭 “道”的至上地位,以 “静坐中养出端倪”为宗旨,讲学江门,弟子106人,形成一隐逸主义的精神共同体,岭南学派开始闻名天下。白沙弟子湛甘泉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到处建书院祭祀白沙,与王阳明平分讲席,宣讲心学,最后以95岁高龄谢世。他一生讲学倡道数十年,建置书院30多所,弟子门徒近4000人。白沙、甘泉的讲学活动,使得白沙学统影响岭南学人上百年,并在清以后还潜在地影响着岭南士子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在广东文教史上,造成深远的影响。白沙把衣钵传给甘泉,甘泉也到处建书院祭祀先师,但师徒之间的心学教育理念有着根本分歧。以下从心学理念与教学实践两方面来剖析两人教育理念的重大分歧。
一、白沙、甘泉心学教育理论的演变
白沙学说的发展本身有着阶段性的演变。这一演变首先表现在他的求学经历上。林见素在总结白沙求学经历时指出:“始求之博,久之曰杂矣,又求之静,久之曰偏矣。杂佛老而超佛老,张朱二夫子先迷而后获也。”[1]这说明陈白沙的求学有着认知上的演变。这种认知上的演变继而影响到了他的教育理念。他的学生张诩在 《行状》中曾说:
“其 (白沙)始惧学者障于言语事为之末也,故恒训之曰:‘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其后惧学者沦于虚无寂灭之偏也,故又恒训之曰:‘不离乎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妙。’门人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则,天下之人又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称,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2]880
这里讲得很清楚,陈白沙先是 “惧学者障于言语事为之末”,后是 “惧学者沦于虚无寂灭之偏”,导致他相应地奉行了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阶段的学生也就得到了白沙不同的指导。“门人各随其所见所闻执以为则”,也就必然导致其门人在释读和发展其学说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走向。
张诩与湛甘泉的理论分野就是一个明证。孟泽曾说:“白沙的两大及门弟子湛若水、张廷实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诠释方向。前者极力把白沙之学纳入淑世的范围,以为有益于名理纲常;后者则有意无意地彰显了白沙学术与人生历程中的神秘主义色彩。”[3]张诩在成化十七年 (1481)就师从白沙,主要受白沙早期学说影响;湛甘泉在弘治七年(1494)才从学江门,主要受白沙晚期学说影响。不同的影响带来了不同的诠释方向,也导致了两人不同的理论走向。张诩主要从 “主静”的角度诠释了白沙学说,而湛甘泉则更倾向于从入世的立场来发展白沙学说。但白沙对张诩之学给了极高的评价,他在 《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中说:
“盖廷实 (张诩)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4]12
在这一点上,湛甘泉对陈白沙有所不满。他认为张诩并未理解白沙之学的本真,陈白沙也不予以指正,以致遗留后患。“西樵游览志曰:甘泉谓常恨石翁 (白沙),明知廷实之学是禅,不早与斩截,至遗后患。翁卒后所作墓表以己学说翁,全是禅意”[5]10湛甘泉在此指斥张诩借为陈白沙作墓志之机,完全以自己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禅意来诠释白沙学说,根本没有揭示白沙之学的真谛。
湛甘泉坚信自己的诠释才是继承了陈白沙的衣钵。虽然陈白沙在早期倡导的是 “静坐中养出端倪”,诚如白沙所言:“学劳扰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6]在 《复赵提学佥宪》中,陈白沙还提到曾筑阳春台,静坐其中,足不出户数年,终于悟道。但白沙晚年则不再拘泥于静坐的修养方式,提出 “夫道无动静也,得之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欲静即非静矣。故当随动静以施其功也。”[7]湛甘泉认为白沙后期学说才是其真正的旨意。湛甘泉曾讲述过一个故事,希求从其先师处获得其言说的合法性。他说:“吾初游江门时,在楚云台梦一老人曰:‘尔在山中坐百日,便有意思。’后以问先师,曰:‘恐生病。’乃知先师不欲人静坐也。”[2]850湛甘泉借助这个故事,不仅推翻了白沙前期 “主静”的修道方式,而且赋予自己的主张以白沙学说承传的合法性。湛甘泉在继承与改造白沙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 “随处体认天理”的治学宗旨。他认为:“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穷年卒岁决无有熟之理”;[8]557“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静着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以非静矣。”[9]880
湛甘泉对白沙学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正?我们看到,白沙的修道方式有从 “主静”到 “随动静以施其功”的阶段变迁,但其修道宗旨都是追求“自然”境界。“所谓 ‘自然’是指心灵的自由,不受牵连制累,也就是 ‘无滞’”。[10]黄宗羲称:“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11]4白沙在给湛甘泉的信中也反复强调了此点:“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12]192但如何才能 “自得”,如何才能 “着意理会”,陈白沙的“自然之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困境。黄宗羲评价白沙之学,曾言: “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与,才欲自然,便不自然。”[11]5这种既想从 “主静”中求自然,又不可在 “主静”中求自然的困境,正是白沙 “自然之学”的内在逻辑困境。这种逻辑困境也最终使白沙的修道方式由 “主静”走向了 “随动静以施其功”。湛甘泉认识到了这种困境的存在,他说:“圣贤之学,原无静存动察相对,只是一段功夫,凡所用功,皆是动处。盖动以养其静,静处不可着力,才着力便是动矣。”[9]885湛甘泉认为,凡要追求自然,必须着力,着力即是动,“凡所用功,皆是动处”。也就是说,只有推翻 “主静”的修道方式,才有助于摆脱白沙 “自然之学”的内在逻辑困境。
但湛甘泉并没有停留于白沙后期的 “弄艇投竿”、“诗酒唱和”的优游山水式的 “随动静以施其功”,而是通过赋予 “支离”一种类似 “举业、德业为两截”、“读书、静坐为两截”的新意,以 “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一以贯之”为逻辑中介,使得白沙心学由隐逸主义的自然悟道转向了科举入仕的读书穷理。[13]甘泉把白沙心学的 “吟风弄月”的洒落自得,转换为 “纲常伦理”的社会秩序的为学旨趣;把白沙的塞断读书著述的自然悟道,转换为重 “进学在致知”的读书体道的修道方式;把 “非全放下,终难凑泊”的弃绝科举入仕,转换为 “德业”、“举业”二业合一的读书科考入仕。
理论内核的演变往往只是意义世界转变的投射。就修道意义而言,陈白沙注重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陈来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陈白沙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不仅在于他把讲习著述一齐塞断,断然转向彻底的反求内心的路线,还在于他所开启的明代心学特别表现出一种对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主要特点是 ‘乐’或‘洒落’或 ‘自然’”。[10]不同于陈白沙的吟风弄月,湛甘泉更在乎伦理纲常、社会事功的求道价值,他说:“吾儒学要有用,自综理家务至于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无一不是性分内事,皆有至理,处处皆是格物功夫。以此涵养成就,他日用世凿凿可行。”[8]558可见,从陈白沙的 “静坐中养出端倪”发展到湛甘泉的 “随处体认天理”,应该说是白沙“自然之学”合乎逻辑的走向。
二、白沙、甘泉心学教育的两种实践
从陈白沙的 “静坐中养出端倪”到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二人教育理念的分歧不仅仅表现在纯粹理念上,而且表现在其教育活动的实践取向上。在要不要采用正规书院式教学的主张上,白沙、甘泉存在分歧。把这种分歧放在明代广东书院两阶段发展的实践舞台来看,又展现了明代广东书院发展的轨迹。对广东书院发展而言,陈白沙只是提供了其发展的潜质,湛甘泉则标举白沙的学统和象征,使这种潜质在广东书院开花结果。白沙、甘泉心学教育的两种实践,对广东书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和作用。
陈白沙不重视传统的书院式教学。成化十七年,江西白鹿洞书院修复,邀请白沙任山长,被他婉拒。他在江门讲学,许多官员都资助他的讲学活动,象小庐山书屋、嘉会楼的修建。当时主管教育的广东官员胡荣,还经常选优秀的生员师从白沙学习。但是,白沙回避与反叛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愿运用传统的书院式教学来宣讲自己的心学。
陈白沙是当时大儒,其名震京师和朝廷徵诏的辉煌历程,使得不少名士情愿追随其左右,如湖北嘉鱼名士李承箕不远千里师从白沙。陈白沙在程朱意识形态笼罩的学术窒息氛围中突围而出,为时代送来了一剂清凉帖,其高洁的个人品性与悟道的圣贤风度,深深地吸引了当时的士大夫,被赋予了非凡的 “德性”魅力。贺钦听白沙议论,立即上疏辞官师事之;进士姜麟赴广西上任,绕道江门一见白沙,谓其为 “活孟子”。白沙从未提倡师道尊严,待弟子多介于师友之间,而白沙弟子却对乃师怀着深深的敬仰甚至神化之意。这种 “德性”魅力成为白沙先生聚群讲学的精神纽带。在白沙弟子中,多有举人进士的出身,他们浸润朱子之学日久,熟稔八股文章。对程朱理学的审美疲劳与对科名仕宦的倦怠之情,促使他们愿意追随白沙左右,吟风弄月、寓意诗酒、优游山水,追寻 “鸢飞鱼跃”的随机悟道之境。白沙心学成为学术时尚,也使得白沙弟子得到了科考上的优势,许多白沙弟子都获得进士出身,如湛甘泉在弘治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14]陈白沙凭恃着个人 “德性”的魅力,一反传统读书穷理的朱子之学,嘲弄鄙视著述讲习的教学悟道的传统,独创 “自然洒落”的江门学派。陈白沙被其崇拜者赋予了克理斯玛特质式的魅力,使得他能够自由组织、创新性地开展教学活动。
陈白沙倡道东南几十年,虽有小庐山书屋、嘉会楼、江门钓台等讲学会友之处,但他不立课程,不定制度规范,全凭个人魅力的教学活动,只能是一种规模有限的精英化教育。个人 “魅力”造就的繁盛也会随着个人的离世而消逝,白沙全新的教学旨趣与风格在没有陈白沙的 “德性”魅力支撑以后,很难传之久远。自陈白沙去世之后,湛甘泉通过构书院、立祠祀,使得白沙心学的教学传统得到扎根流传。在此,湛甘泉做了几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诠宗旨,修订白沙的 “静坐中养出端倪”,提出“随处体认天理”新宗旨。二是构书院,使得白沙心学有了固定的教学传播场所。自正德年间起,湛甘泉在增城建明诚书院,在西樵山构西樵讲舍、云谷书院、大科书院等。据罗洪先撰的 《湛甘泉先生墓表》记载,他 (包括帮他建书院者)一生所建书院精舍达36所之多。[15]244三是立祠祀,使得白沙心学成为书院教学的制度性知识资源。四是定规制,湛甘泉颁定 《二业合一训》、《大科规训》、《大科书堂训》、《求放心篇》、《心性图说》等规制性的条列,明确详实地规定了书院学生的为学旨趣、修习课程、尊卑礼仪、作息制度等一系列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使讲究自然自得、质朴自由的白沙心学得以纳入书院式的教学组织之中。在此,湛甘泉吸收利用传统书院的学规,突出地运用了制度性组织,把教育者的魅力性资源整合进学院教学活动之中。湛甘泉的诠宗旨、构书院、立祠祀和定规制的工作,完成了 “自然自得”的白沙心学与传统的书院教学的接轨,使明中后叶的广东书院发展到成熟阶段。
陈白沙以江门钓台为信,把湛甘泉定为其学业继承人的事件,具有 “魅力”传承的意义。白沙予甘泉诗曰: “皇王帝霸都归尽,雪月风花未了吟。莫道金针不传与,江门风月钓台深。”又有诗曰:“小坐江门不算年,蒲裀当膝几回穿。于今老去还吩咐,不卖区区敝帚钱。”跋云:“达摩西来,传衣钵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付与湛民泽收管,将来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15]243利用其学者与官宦双重身份提供的声望、资金及舆论在内的诸种便利,湛甘泉实现了白沙象征的 “魅力”资源与书院教学制度的整合,实现了白沙心学由 “魅力性”教学到 “制度性”教学的转换,使得传统性教学、魅力性教学、制度性教学得以融为一体,并取得建置书院近40所、培养弟子门徒近4000人的教育成效。
三、白沙、甘泉教育理念分歧在书院中的体现
湛甘泉建置数十所书院,祭祀先师,宣讲白沙心学,但二人在教育理念及教学方式上都有分歧。首先,在修道意义上,白沙注重得道的洒落自然,甘泉注重得道的整治伦理纲常与社会政治秩序。白沙教学不拘世俗礼节规矩,他说,“礼文虽不可不讲,然非所急”,“若四礼则行之有时,故其说可讲而知之。学者进德修业,以造于圣人,紧要处却不在此也。”[12]144湛甘泉却 “筑西樵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14]在他制定的 《大科训规》、《大科书堂训》中多有长幼有序、尊卑有节的戒条,始终强调 “事父兄诚切”、“求道于人伦间”等伦理纲常的习练。[8]553湛甘泉在 《大科书堂训》中有许多礼仪方面的规定,如 “诸生相处,一言一动,皆本礼仪;时言俗态,一毫不留”、“诸生相处务守长幼之节”;又如,“诸生每与先生同侪之人,必推先生之意,以前辈事之”;又如, “俟先生出堂,整班而升,长少各依次序,所以养其敬谨之心”[8]555。湛甘泉关注 “得道”的入世价值,所以为学讲究事上磨练,如他说: “执事敬,最是切要,彻上彻下,一了百了,致知涵养,此其地也。”又说:“本末只是一气,扩充此生意,在心为明德,在事为亲民,非谓静坐而明德,及长,然后应事以亲民也。一日之间,开眼便是,应事即亲民。自宋儒多分两段,以此多陷支离。”又说:“自意心身至家国天下,无非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即格物也。”[9]881,883,884
其次,在修道方式上,白沙认为 “道不可言状”,反对颂读经典、析词解句式的教学传统,进而提出 “为道当求诸心”的教育理念。他说:“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涉乎粗迹矣”;“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我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4]56故而塞断读书著述,运用 “境语”和“诗语”的独特传道方式,来接引后学。[16]相对于白沙的无言之教,甘泉定下了细致精密的学规,其《大科书堂训》共为61条,内分德性训率26条,学问修养26条,堂制纪律9条,自正心诚意、处己对人以至治事修学皆包括在内。湛甘泉并没有走上白沙的 “静坐中养出端倪”、“吟风弄月”、诗酒唱和的悟道之路,他似乎放弃了白沙通过 “境语”设置悟道之机的做法,而是偏向了程朱传统的读书明理之路。在湛甘泉制定的学规中,我们看到的是“读书调心合一”、“博六经以开知见”、“作文以发挥所得”的读书著述的悟道之路。陈白沙侧重于神秘主义感悟的悟道之路,而湛甘泉却偏向了程朱的知解悟道之径,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9]880
白沙并不完全反对读书,但他时刻警惕学者不要沉溺于言语事为的末习。他说: “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君子奚取焉?”[12]131-132又说: “学劳扰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6]在读书上,湛甘泉偏离了白沙的理念,更多地接近了程朱熟读精思的治学道路。他在 《大科书堂训》中规定:“诸生进德修业,须分定程限,日以为常。每日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巳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戌亥二时温书。然此等大抵皆不可失了本领,通是涵养体认之意”;“诸生读书务令精熟本经四书,又须随力旁通他经,性理史记及五伦书,以开发知见。此知见非由外来也,乃吾德性之知见,书但能激发之耳。须务以明道为本,而绪馀自成文章举业。”在这个课程安排中,读书无疑占据了主要部分。
如同朱熹一样,湛甘泉还讲究读书的循序渐进策略。他规定的读书顺序是: “学者须先看论语、次大学、次中庸、次孟子,乃书之序也。”又规定读书与讲书相结合的读书制度:“塑望升堂先生讲书一章或两章,务以发明此心此学。诸生不可作一场说话听过,亦必虚心听受,使神意一时相授,乃有大益”;“诸生塑望听讲之后,轮流一人讲书一章,以考其进修之益。”又规定了读书的范围:“诸生读文须诵五经,至于秦汉而止,看诗当诵三百篇,至于汉魏而止。”还专门为读书规定了纪律监察制度:“诸生用功,两廊皆各轮流一人,察觉勤惰。人人皆要读到二更尽,其有惰者,戒饬之,甚有鞭策。”[8]554-559
当然,湛甘泉的学规虽强调读书,却始终坚持把住本心,要随心力而读书。如规定 “诸生读书须先虚心,如在上古未有专注之前。不可先泥成说,以为心蔽”;又如 “初学习字便学运笔以调习此心,习文便要澄思以蕴藉此心,久之,文字与心混合内外皆妙”。[8]554-559在这里,湛甘泉虽有接近陈白沙的地方,但其细微之处存在着根本理念的差别。如湛甘泉的 “默坐思索”,似乎还保持了白沙 “主静”学说的痕迹,但白沙追求的 “静坐中养出端倪”,是一种何思何虑、屏绝智识的内外两忘境界,甘泉的静坐思考实质上与此貌合而神离。湛甘泉虽也规定,“诸生肄业遇厌倦时便不长进,不妨登玩山水以适其性”,但登山玩水在此已经只是一种辅助休息,而失去了白沙优游山水的自然得道之境。湛甘泉还规定, “诸生人人皆学歌诗作乐,以涵养德性”,并把白沙的诗歌编辑成集,辅助讲解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作为学生的学习教材使用,但这也已变成了制度化的课程事件,失去了白沙 “诗教”中随境唱和的 “魅力性”教学性质。
总之,在湛甘泉制定的书院学规中,可以充分看出师徒两人的教育理念,有着从修道意义到修道方式两方面的根本分歧。
四、结语
白沙心学向甘泉心学的演变,除了是白沙心学内在学理困境的解决需要外,还由于白沙、甘泉的讲学背景与身份已发生重大转变。陈白沙由朱入陆,追求至上至乐的 “道”,其闲暇适乐式 “浪漫主义”学术取向、超越伦理政治的心性追求,顺应了当时士大夫们欲摆脱生存困境与价值迷失的精神需要。在此背景下,白沙在 “道”至大、“道”不可言的理论基石上,形成塞断著述讲习、倡导随机悟道的祈圣求道的教学旨趣,造成了他不立课程、不定规制、不事科举仕宦的自然而然的教学风格。但是,这种教学与历史悠久的现实教学传统针锋相对,而其隐逸主义的修道方式又与个人利益的现实驱动和伦理纲常的社会需要形成一种无法缓解的紧张。白沙弟子湛甘泉和陈庸都在亲友的压力下科考入仕的事件,即象征了白沙的高格流风与世俗的功利取向之间的紧张存在。
湛甘泉讲学之时,正是岭南科名鼎盛、士大夫步入帝国中枢之际,他们自然更多地关注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湛甘泉的学者兼官宦身份,决定了其不可能重走白沙讲学之路。加上明代科举考试以朱子学为取向,使得他修正老师的学说,更多地靠向了朱熹式的读书穷理的书院讲学传统。面对白沙心学的理论与现实困境,湛甘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提出了一套新的主张。他提出 “随处体认天理”的治学宗旨,并在教学实践中,把白沙的 “魅力性”变为 “制度性”的教学组织形式,削足适履地把本来“自然自得”的白沙心学纳入到制度化的教学与修习的书院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偏转白沙心学的教学理念,靠向作为其对立面的程朱之学的教学理念。
[1]邓淳.粤东名儒言行录:卷五 [M].道光辛卯年养拙山房藏版.
[2]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孟泽.“自然”的三重境界——陈白沙的 “自然之学”及其审美涵义 [J].理论与创作,2003(4):31-36.
[4]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邓淳.粤东名儒言行录:卷八 [M].道光辛卯年养拙山房藏版.
[6]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7:269.
[7]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上) [M].北京:中华书局,1985:88.
[8]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六 [M].济南:齐鲁书社,1996.
[9]黄宗羲.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陈来.宋明理学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4.
[11]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二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五 [M].济南:齐鲁书社,1996:549.
[14]张廷玉.明史列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66.
[15]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6]卓进,王建军.陈白沙传道的语言困境与出路 [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56-60.
From"Achieving Understanding in Meditation"to"Experiencing and Recognizing Natural Principles Ubiquitously"
(by ZHUO Jin,WANG Jian-jun)
Zhan Ganquan(Ruoshui)inherited his idealistic philosophy from Chen Baisha,but the two differed greatly in educational thinking.On the educational theory level,their differences were embodied in"achieving understanding in meditation"and"experiencing and recognizing natural principles ubiquitously";on the practice level,their differences lay in whether adopting the regular academy teaching.Such differences arose from resolving Chen Baisha's inherent theoretical dilemma and also as a result of the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two men's times and subject identity.
Chen Baisha;Zhan Ganquan;academies in Guangdong;the idealistic philosophy
B248.1
A
1009-1513(2012)02-0010-05
2012-01-02
卓进 (1979—),男,湖南慈利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李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