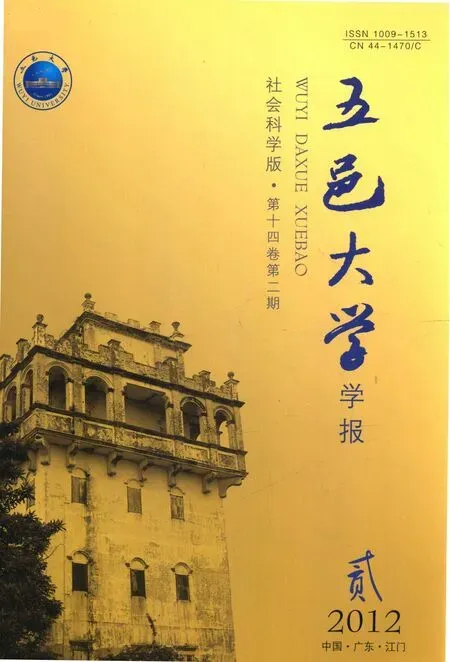六朝论体文的叙事性言说方式及特点
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六朝论体文的叙事性言说方式及特点
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六朝论体文叙事结构包括对话体、书信体、论序等,叙事方式包括寓论断于序事、寄情志于叙事、援古事以论今、就今事而发论等,言说特点包括浓缩式叙事、写意式叙事、叙思式叙事等。论体文在叙事中言理,在言理中援事,融文学、学术与思想于一体,使原本 “灰色”的理论之文散发出亮丽鲜活的生命之光。
六朝论体文;叙事性;言说方式
美国学者浦安迪在谈到 “叙事不外乎是一种传达人生经验本质和意义的文化媒介”时,曾特别指出:“传达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并不是叙事文独此一家的专利,戏剧和抒情诗的本义难道不也在于传达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吗?”[1]中国学者杨义在其著作 《中国叙事学·前言》中列举了历史、戏剧、小说中国叙事作品的三大系统之后,又指出“还有许多短小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之间”,如碑文、墓志、行状、诔碑、史传、杂文、谐隐等。上述二者皆注意到叙事在不少文体中的存在,却都对以言理为主要内容、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以思辨为主要特征的论体文是否具有叙事性未置一词。
与西方以概念为起点的逻辑推演体系建构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理论形态都无法摆脱 “未尝离事而言理”[2]的根本规定。冯友兰先生在贞元六书中曾将其概括为:中国人以事说理,西方人以理说理。其根源在于中西思维方式之大别:西方人“以理 (概念)说理”时,形成一套如数学运算一样的严格程式,前后的内在勾联,即是一种逻辑存在;中国人 “以事说理”,则形成另一套洋溢着诗性意蕴的美学存在。①古人甚为重视 “事”与 “理”的关系,常以 “事理”对举。 《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务事理者也。”又 《大略篇》云: “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三国时,王弼在 《论语释疑》中指出:“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叙事能够超越任何具体作品的体裁形式,而在叙事中言理,其理易晓。叙事性言说亦是论体文的重要言说方式之一,对于六朝时期论体文而言尤其如此。
一、六朝论体文的文体叙事结构
(一)对话体叙事结构
六朝论体文不少篇章借鉴吸收大赋的写法,采用客主问答的叙事结构,作者往往虚构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采用一问一答的行文方式,通过人物之间的论辩一步步推动事态的发展,最后曲终奏雅,以一方臣服另一方结束。如王粲 《三辅论》开端虚拟三个人物出场:“湘潜先生,江滨逸老,将集论云梦,玄公豫焉。”其他如阮籍 《达庄论》虚拟“先生”、“缙绅好事之徒”,嵇康 《声无哀乐论》虚拟 “秦客”、 “东野主人”,谯周 《仇国论》虚拟“高贤卿”、“伏愚子”,鲁褒 《钱神论》虚拟 “司空公子”、“繤母先生”等。这种结构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叙事,体现了论体文的叙事性。
在对话的过程中,作者往往利用虚构的情节和细节描写,使叙事起伏变化、行文生动活泼。刘熙载在 《艺概·赋概》中说: “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易悉举。”此语用于赋体论中亦非常合适。所谓 “设”字诀说明论体文作者有意识地虚构人物和情节,这是叙事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之一。为了使虚构的情节更具有现实性、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作者往往会对其进行细节描写,以简洁的语言使其神态凸显于纸面之上。如阮籍的 《达庄论》虚构了一位明达庄子大道、飘然优游的 “先生”,他委运自然,淡定从容,“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与之相对的是 “缙绅好事之徒”,他们 “奕奕然步,膪膪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临,莫肯先占”。在听了 “先生”的论述之后,作者没有直言那些缙绅好事之徒的言语,而是又一次描绘了其神态动作,与来时形成对比,“风摇波荡,相视膪脉,乱次而退,唐跌失迹”,其狼狈离开的情景再现于眼前。再如鲁褒的 《钱神论》中 “司空公子”“盛服而游京邑,驻驾平市里”,“綦母先生”则 “斑白而徒行”,不仅刻画出二者的相貌、年龄、贫富情况,而且暗示其不同的境遇,使其相会之地成为衬托论文主体的合宜背景,钱币的神奇可信力量已隐含在此画面中。通过对人物相貌、动作、神态的刻画,此类细节描写不仅使虚构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能够渲染论辩之后的结果,在叙事中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二)书信体叙事结构
书信,是一种更具实用性与灵活性的文体,颇受六朝文士青睐。运用书信进行论辩,不仅能够反映出作者的个性和情感,而且能够更直接地展露其思想变化的过程。六朝书信体论体文的构成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书信的格式,但其实质仍为论体文,如司马恬 《答张新安论孔释书》、张新安 《答谯王论孔释书》、郗超 《与亲友书论支道林》、《与谢庆绪书论三幡义》等;另一种是论体文是单独的,书信仅仅起介绍创作背景的作用。如曹冏 《六代论 (并上书)》、僧肇 《涅槃无名论 (并上秦主姚兴表)》、何承天 《安边论 (并上书)》等。前者视为以论理为主要内容的书信更合适,刘永济先生曾谈论过这一问题: “何曾天 《通裴难荀论大功嫁妹》,见 《通典》六十。裴松之有 《答江氏问大功嫁妹》,荀伯子著议难之,故承天通二家之论,而著此文。又是时所讨论者,尚有 ‘次孙宜持重否’与 ‘为人后为所后父服’二事。所与往复者,为司马操、荀伯子、裴松之等。大抵以书疏往还,非论式也,故不具列。”[3]此语甚为有理,此处谈的书信体以后者为准。
书信体叙事结构虽然不是虚设人物与情境,但作者在写信时往往与看信者预设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所以能够敞开心扉、直言不讳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如曹冏的上书与论文,其主题一脉相通,奔放之气势与宗臣之苦心亦前后一贯。上书中提出 “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宗旨在主张强宗固本,这正是 《六代论》中所要反复陈说的。较之论文中言古以衡今,以史实为据,深入分析封建之得、废封建之失的写法,上书则直抒胸臆,放言无忌,作者的一片丹心袒露于人主面前。换个角度来看,曹冏的上书又反映了当时曹魏政治潜伏的危机和当政者的麻木不仁,这也是其中所隐含的叙事因素。
(三)论序的叙事功能
关于序之功用,西汉孔安国 《尚书序》云:“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按 《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 ‘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又谓之大序,则对小序而言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清代王之绩对徐师曾强调序的议论性表示不满,他说:“序之体,议论如周卜商《诗序》;叙事如汉孔安国 《尚书序》。变体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有谓序文叙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此说亦可救 《明辨》先议论后叙事之偏。”[4]
早在西汉,论体文已有论序,例如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与王褒 《四子讲德论》均有论序。前者为: “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立克胜之功,寿王作士大夫之论,称武帝之德。”后者为:“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又作传,名曰 《四子讲德》,以明其意焉。”今人考证王褒 《四子讲德论》之序文乃来自史辞,吾丘寿王 《骠骑论功论》之序文似乎亦非作者所为。②尽管如此,二者均交代了正文之论的写作背景及创作目的,含有叙事因子。
六朝论序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品之外的文字,是论体文基本体式之外的一种外加形式,在论文题目上明确标出 “并序”,如慧远 《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并序)》、释道恒 《释驳论 (并序)》、萧琛《难范缜神灭论 (并序)》、江淹 《无为论 (并序)》、裴子野 《雕虫论 (并序)》、刘峻 《辩命论 (并序)》、释玄光 《辨惑论 (并序)》、傅縡 《明道论(并序)》等;另一种是作品内部用以引出作论情由意旨的开头部分,题目上没有标明,如夏侯玄 《乐毅论》、嵇康 《养生论》、张昭 《宜为旧君讳论》、孙绰 《喻道论》、皇甫谧 《释劝论》、《笃终论》、张载 《榷论》、范宁 《王弼何晏论》、伏滔 《正淮论》等。近代学者黄侃在评点 《高唐赋》时曾辩解该篇题目下写有 “并序”字样云:“‘并序’二字,未必昭明旧题,即令出于昭明,亦不足訾,至何焯所云序实与并序之序不同,盖如所论,履端皆可名序也。”[5]如此理解,不管题目是否标明 “并序”,二者均可视作有论序。还有一种论序是属于设置情境、人物以引出见解的,如阮籍 《达庄论》、鲁褒《钱神论》等。
就论序的创作者而言,有自序亦有他序。六朝论体文留存下来的论序多为自序,主要包括:其一,交代论体文创作的背景、目的。东晋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中追溯了晋成、康之世,庾冰与何充关于沙门是否要礼敬王者的争辩,引出其时桓玄与八座书关于这个问题的重提与朝士名贤的反映,将自己 “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6]1768的焦灼、担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二,引出要论述的问题。嵇康 《养生论》开篇序曰:“世或有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先将批驳的靶子树立起来,然后分别论述这两种观点的不合理性。
六朝论序亦有来自史辞的他序,这可能是严可均在辑录时将其从史书中摘录出来,使之成为论体文的一部分,将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意图与主要观点明确标识于论序中。范宁 《王弼何晏论》曰:“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7]1984,此语出于 《晋书·范宁传》,其时文士对清谈误国的认识于此可见一斑。
二、六朝论体文的文本叙事方式
(一)寓论断于序事
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提出孔子为何要作 《春秋》的问题时,曾引孔子的话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谓发表议论不如写出事实更有说服力,而事实之中自亦不无道理,故《春秋》一书可以称得上是 “王道之大者也”。这个认识,当是促使司马迁撰写 《史记》的思想渊源之一。顾炎武在评价 《史记》时指出: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但此处顾炎武是针对其史传叙事而言的,即司马迁将自己的观点寓于史实之中,以叙代议。换个角度看,此语亦道出了古代论体文的一个突出特色,不直接发论,而是以事寓论。
范晔的 《后汉书》史论,以 《光武帝纪论》开篇,并没有直言自己对光武帝的评价,而是列举了其称帝的诸多祥瑞,以致引起后人的误解与訾垢。唐人刘知几批评其 “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8],今人瞿林东则称其为 “不能脱俗的开篇”,“一切可以用来说明 ‘王者受命’‘有符’的手段都排上了用场。对于一个确信 ‘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的史家来说,这篇史论无疑是一堆胡言乱语”。[9]那么,范晔真的是在 “胡言乱语”吗?作为南朝史家,范晔距汉已远,关于刘秀事迹的传说只能根据前代史家的记载进行撰述。这篇史论实出自 《东观汉纪》卷一 《世祖光武皇帝》,只增加 “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等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东观汉纪》中,此是传中正文,而范晔将其放在论中,看起来似乎是在补传中之不足,实际上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一反问,一假设,表明他对这些祥瑞的怀疑。史传的叙事目的在于向读者传达所记载历史事件的真相,不宜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而史论则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范晔充分利用史论的这一特色,将自己的观点寓于反问与假设中,不必明言却意在其中。
(二)寄情志于叙事
六朝文士创作论体文,很多时候与其现实关怀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仕途受挫后抒发愤懑之气的成果,因此在借事说理、引事作论时,将对现实的不满寄予其中。如 《三国志·顾雍传附顾谭传》记载: “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 《新言》二十篇。”西晋王沈:“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 《释时论》。”[7]2381
陆机 《辩亡论》通篇旨在 “辩亡”,即 “辨吴之所以亡也”,但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的目的亦很明确。西陵之战足以决定吴之生死存亡,陆机写道:
汉王亦凭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4]1469
姜亮夫指出 “《辩亡》二篇,主旨亦在表彰先世德业,盖陆逊、陆抗、陆机、陆喜祖孙父子一门多才,与大吴相终始,而功业彪炳,皆有扶危匡乱之绩,且与孙氏甥舅之亲,故寄慨亦特深。”[10]所以,在 《辩亡论》中陆机将其作为功臣后裔的自豪感蕴含在叙事中。
(三)援古事以论今
六朝论体文之兴盛,与创作主体身处乱世、关注现实的心理动机有密切关系。秉承汉人重功利的文艺思想,其时文士对论体文的讽谏、教化作用予以高度评价。 《三国志》载: “(孙)权尝问 (阚泽):‘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 《过秦论》最善。”阙名的 《中论序》则指出 《中论》的创作缘起也出于教化的目的:“(徐干)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 《中论》之书二十篇。其所甄纪迈君昔志,盖百之一也。”基于这种考虑,文士在作论时,其叙事的目的是为了言理,论古的目的是为了言今,因此时常采用古今对比、借古喻今的写法。
伏尔泰说: “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人是什么,不是靠对本身的思考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11]东晋习凿齿对此亦有深刻认识:“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在 《晋承汉统论》论中采用了借古事以论今的方法,表明司马氏之功业远胜古人。西晋刘寔以 “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 《崇让论》以矫之。文章采用古今对比的写法,在肯定古人让贤之举的同时,批判当世争竞之风。
(四)就今事而发论
“论”是一种 “活”的文体,可随时随处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具有时效性与现实性。六朝文士借助于 “论”这种文体,对当时的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揭露与鞭挞。在谈到 《崇有论》的创作缘由时,史载裴頠 “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7]1044。文中罗列了当时虚无放荡世风的种种表现,将贵无者对贵贱长幼等级制度的破坏形象地刻画出来,一针见血地写出他们的放荡行径,表达了他对时俗竞尚虚无而导致 “风教凌迟”现象的痛心疾首。
三、六朝论体文叙事性言说的特点
(一)浓缩式叙事
六朝论体文受其时文风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语言美质。其文辞典雅、气势雄壮之特点的形成与其浓缩式叙事言说方式紧密相关。以密集方式排列的众多浓缩型事件具有双重意义:一则就单件事而言,是内敛、凝练的,每件事只用简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可谓惜墨如金;一则就整体而言,又是铺张的,体现的是以多为美的风尚。这种收敛与舒张、凝练与铺陈、简约与繁缛的有机结合,使六朝论体文叙事的张力得到充分发挥。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又形成浩大的气势,增强了论体文的说服力。戴逵 《释疑论》论曰:
是以尧舜大圣,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贤,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剋昌;夷叔至仁,饿死穷山;盗跖肆虐,富乐自终;比干忠正,毙不旋踵;张汤酷吏,七世干貂。凡此比类,不可称数。
他一气举出历史上八个祸福应报不合理的例子,互相对比,构成一个独立的版块,显得极为凝练。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观点,认为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所致,就有了事实支撑。
(二)写意式叙事
“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有写实和写意两种艺术表现方式,形成两种艺术流派。写实注意情节的完整合理以及细节的周到逼真,而写意则表现着一种诗化的倾向,不注重情节,甚至淡化情节,追求意境,追求意境的隽永。”[12]此处,石昌渝先生虽是就小说的叙事性而言,却也道出了各类文体叙事的共性。论体文中的叙事是为叙思服务的,所叙之思即思想在作品中才是主角。因此,它不可能如小说、长篇叙事诗等叙事文体那样,通过丰富的情节、曲折的过程、复杂的事件来构成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再现社会生活。论体文中的叙事是一种写意式的,以传神、明理为目的。
鲁褒 《钱神论》中刻画出读书人见钱眼开的神态动作:“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6]1197,就形貌行事揭其内心意念,可谓深刻。此乃一种漫画式写意笔法,嘲讽的意味寓于字里行间。鲍敬言的 《无君论》则采用青绿山水画的写意笔法,将 “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理想的社会画面勾勒出来,通过写其时人的饮食、作息等,表现出他们委运自然、无欲无求、无荣无辱、怡然自得的生活状况和不用智巧、抱朴守拙的精神状态。
(三)叙思式叙事
六朝论体文中有部分作品,属于有意识地通过叙事来表达系统的思想,表现创作主体倡导、关注和发现的世界观,并将这类创作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叙述模式。叙事是其外壳,叙思才是其内里。作家通过虚构人物、情节与环境,将自己的思想通过笔下的人物之口道出。前面所讲的对话体叙事就是这样的叙思式作品。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叙事中,作者采用客主问对的外在结构形式,其本质上反映的却是作家内在的自我冲突或对立的心理结构。冲突的契机或来源于外界,或来源于内心。嵇康 《卜疑》、夏侯湛 《抵疑》、郤正 《释讥》、皇甫谧 《释劝论》、束皙 《玄居释》、王沈 《释时论》、曹毗《对儒》、郭璞 《客傲》、徐勉 《答客喻》均属此类作品。由 “设疑”到 “自通”的过程是作者从内心郁结到自我排遣的心理历程,表现的是一种 “士不遇”情绪。
叙事性言说方式使六朝论体文成为融复杂思辨性与审美愉悦性于一体的文体,论体文著者面临将思想纳入文学形式的挑战。这些精彩的论体文,在叙事中言理,在言理中援事,使原本 “灰色”的理论之树散发出亮丽鲜活的生命之光。
注释:
①参见李赣、劳承万 《中西思维方式与理论形态之大别——兼论中西美学、文论比较研究之关键与偏向》一文(载于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②参见王书才 《〈昭明文选〉所录作品之 “序”问题考论》一文 (载于 《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
[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
[2]章学诚.文史通义 [M].上海:上海书店,1988:1.
[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1962:76.
[4]王之绩.铁立文起 [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01.
[5]黄侃.文选平点 [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7.
[6]严可均.全晋文 [G].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2.
[7]房玄龄,等.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刘知几.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3.
[9]瞿林东.说范晔 《后汉书》帝纪后论 [J].学习与探索,2000 (6):112-118.
[10]姜亮夫.陆平原年谱 [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8.
[11]米切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 [M].阎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55.
[1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 [M].北京:三联书店,1994:85.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Mode of the Argumentative Essays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by YANG Zhao-lei)
The narrative types of the argumentative essays of the Six Dynasties include dialogue,epistolary,and prefaces;their narrative modes include giving judgments in narration,expressing sentiments through narration,discussing the present by referring to the past,and expressing views by commenting on current affairs;their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condensed narration,free-style narration,and reflection-style narration.The argumentative essays argue through narration and quote stories in argumentation,blending literature,scholarship and thinking,and make the theoretical essays give off the bright fresh light of life.
argumentative essays of the Six Dynasties;narrative;narrative modes
I207.2
A
1009-1513(2012)02-0028-05
2011-12-0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魏晋子书流派及其文学价值研究”(批准号:07BZW023)的阶段性成果。
杨朝蕾 (1977—),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诗文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