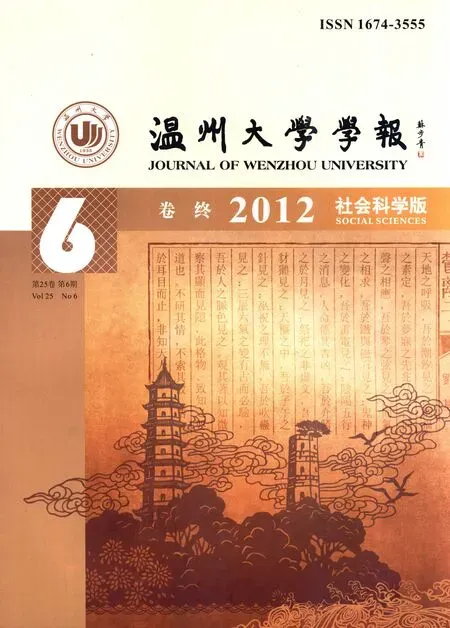“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
—— 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王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300)
“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
—— 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300)
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同时又表现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她对人性的期盼。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其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建精神家园。借用“元小说”中“戏拟”概念,可以揭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和隐藏于细节中的人性。
严歌苓;历史题材;戏拟;元小说;人性
对人类生命意义、价值取向等诸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文学界比较热衷的话题之一,严歌苓借助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学界也围绕这一热点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如胡静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评析了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中两个女子面临生存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复杂人性[1];刘艳《美国华文女性写作的历史嬗变——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剖析了严歌苓对人性的最终理解——它是“不受社会框架所控制的人之天性”[2];徐涛《论严歌苓作品中人性的冲突和变异》则从“文革”叙事背景和移民身份出发,阐述了严歌苓作品中人性扭曲和变异的原因[3]。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严歌苓在作品中无论赋予角色何种身世、经历,本质上都是在向读者阐明人性的复杂与魅惑。她笔下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单纯或者复杂,扭曲或者僵化。
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超越了以往作家的单纯历史记述,她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性思考。在这类作品中,她巧妙地借鉴了“戏拟”等叙事技巧,希望读者能从更高远的角度,客观清晰地对历史有个人化的认识。本文从严歌苓的历史题材作品出发,通过“历史”与“个人”两种角度,力求揭示出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彰显个人身上隐含的悲剧意味。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思考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的个人化,在个人中体现历史、在历史中折射个人,并最终在社会、历史的整体关照之下完成对于人性的追因式拷问和审视。
一、历史叙事:彰显“个人化”倾向的独特写作方式
戴锦华曾这样界定了个人化写作的涵义[4]:一是个性风格;二是只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切入历史,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对女作家而言,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意义。女性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从戴锦华教授所下定义的第二个方面来看,严歌苓的个人化写作依旧关注历史、政治等公共叙事的题材,但她用饱含“人之性灵”的笔触,建构起女性视角下的历史叙事场景,真实还原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境遇,批判了对女性不公平的道德话语。
透过严歌苓诸多融合个人化倾向的作品可以看出,严歌苓创作中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历史、政治题材的人性注脚,也是对男权社会话语、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其实,严歌苓的作品无不打上女性文学的烙印,将“个人-历史”、“女性角色-男权社会”这两组悖论放在了历史叙事的框架之中。无论是“文革”题材,如《白蛇》①参见: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本文论及严歌苓小说未另作注者, 均出于此.、《一个女兵的悄悄话》②参见: 严歌苓.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还是“新移民”题材,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都实现了个人化写作对叙事形式的超越。
以严歌苓早期作品为例,描写渗透了她本人经历的军旅生活和“文革”时期的生活体验,成为个人化写作的一大特色。严歌苓有长达十几年的军队生活,她上战场、下牧场、六游西藏,这些经历,再加上她天生的丰富感知以及由这些灵动的感知所引发的对社会、历史、个体、人性的相关思考,构成了严歌苓个人化写作的最初文本模式。严歌苓赋予作品主人公独立的思想,折射出她本人对女性生存的社会境遇的深切思考。
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的主人公陶小童是一名始终处于小说中心位置的年轻文艺女兵,同时她也是一个经历了对“英雄”由崇拜到寻找再到认定的新时期青年军人。陶小童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乐器),纵身跳入泥石流之中以致生命垂危。此时,陶小童借用不间断地游离于生命本体之外的“灵魂”,悄悄讲述着发生在“文革”时期个人游离于历史洪流、政治判断等价值体系之外的个体心灵史。在“文革”背景上,严歌苓把一个女兵真实的内心独白以一种私语化、个体化的讲述方式,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貌似杂乱无章的意识流般的叙述,却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文艺女兵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所适从的人生体验——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只能进行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文革”时期所强化的“标准”、“共性”、“模式”是人的个性被粗暴地“改造”。而文艺女兵的特殊身份,更能鲜明地体现出特定时代女性生存的迷惘与无助。严歌苓在创作《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时就曾经说过②:“陶小童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人格”的生命却要衰亡,如花的青春岁月只能被机械地压制,这既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悲剧,也是特定时代摧残人性的写照。
结束了军旅生涯的严歌苓,又完成了旅美写作的华丽转身。这一时期,严歌苓总会赋予其“新移民”题材小说的叙述主角“我”这样的定位:“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失眠的艳遇》);“三十出头的一个中国女人”(《抢劫犯查理和我》);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中国馆子味”(《学校中的故事》)……从这些线索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严歌苓个人化写作的真实体验。
创作于本世纪之初的《无出路咖啡馆》,被认为是以严歌苓亲身经历为蓝本书写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我”,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孩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异域爱情为楔子,引出了一段在FBI监视下的跨国恋情。严歌苓巧妙地借助美国的政治特色和中美历史背景,发出了无论当女性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还是精神困境时都毫无出路的感叹。
就是在这间“八平米审讯室”里,美国FBI调查员理查·福茨以他英俊潇洒的体态,开始了这场不慌不忙、东拉西扯的审问——
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吗?
……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派记者?……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那方面的报道?……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不断更换的联邦调查员向“我”展开无孔不入的轰炸式审讯,他们绞尽脑汁地想诱“我”说出一切有关“我”的历史和家庭背景情况。此处,严歌苓向我们展示的是联邦调查局以及安全部门怎样对一个毫无威胁性和抵抗力的女人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政治审讯与生活干涉。
上述作品既真切地体现了人性的扭曲、变异,又尊重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以“文革”和“新移民”题材的特殊性来论,严歌苓丰富的个人体验与深刻的人性思索是卓然不群的,这一个人化的痕迹被她用匠心独具的笔触糅合在小说创作之中,融入了对当代历史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判断与思考,并坚定了女性写作立场,使其小说创作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二、戏拟:探寻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深层人性寓意
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个人化倾向极其鲜明,无论是对于“文革”时期自身经历的深度书写,还是对移民者生活境遇的细致剖析,都能将历史叙事的方式和对人性的阐释结合得非常自然。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是如何处理历史叙事中的真实因素和个人虚构之间的关系的呢?文本在其历史背景笼罩下又是否会具有某种隐喻呢?在这里,严歌苓巧妙地借鉴了后现代的叙事手法,尤其是“元小说”的叙事技巧,让历史纪实与个人臆想得到了融合。
所谓“元小说”(metafiction),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它是小说家们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看,元小说写作实质上是一种极限性写作,它是对小说文本中诸种可能性的探索,是一场文学冒险,本身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在严歌苓笔下,它更是被不断地加以创新并超越,这也成了严歌苓有关人性的系列小说的写作模式和个人风格。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元小说”中“戏拟”这种写作技巧来分析严歌苓小说隐藏于细节背后的对人性理解的深层寓意。
我们可以把严歌苓的具有历史叙事色彩的部分作品理解为“针对前文本戏拟”。例如,“扶桑”本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神树之一。屈原《九歌》中曾唱到:“暾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离骚》中也讲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而严歌苓却将此神树之名赋予了百年前旧金山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女子(《扶桑》)。“亚当”、“夏娃”是《圣经·新约》里曾经被赋予繁衍重任的男女。在严歌苓叙写的故事中,“亚当”和“夏娃”背负着交易和契约,借助无爱且无性的试管,人工完成了从受精卵到婴儿的发育流程(《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青蛇”与“白蛇”,这对在《白蛇传》中经历了同性相吸、斗争过程而最终结为姐妹相伴一生的故事原型,在严歌苓的笔下,却引发了一场有关性与爱的大讨论(《白蛇》)。这些都是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改写传统经典文本,使传统经典文本的原有寓意为作品的思想主题服务,这种改写明显带有“戏拟”的痕迹,既是谙熟传统经典的严歌苓的文化基因,也是漂泊海外、开拓异域人生的严歌苓的心灵诉求。
《楚辞》、《圣经》、《白蛇传》——妓女、试管婴儿、同性恋,有人曾经毫不客气地指责严歌苓在亵渎经典,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理解为“戏拟”,对严歌苓作品的评价就会更加公允、客观些。因为所谓经典,绝不是指因流传年代久远而思维定格的作品本身。经典是指那种经得起历史反复,被人引用被人阐发的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性爱”、“海外”、“文革”,如果仅仅从文本所涉及的中心题旨来评判作品,并不适当。因为从历史史实、科学史实的角度来衡量,《扶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蛇》的确有很多违背真实的地方。但正因为它们不是简单描写移民、性爱等细节的作品,它们才能够在精神上凸显时代的怪诞和历史的真实。比如《扶桑》,正是源于女主角身上“健壮、自由、无懈可击”的隐喻义,才使“母性”、“雌性”的人性表达透过涅槃式的环境在历史中得到了永生。再比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随着试管婴儿“菲比”的离去,让我们看到了无性亦无爱而制造的生命个体是如此地脆弱、不堪一击。而与此同时,文本也揭示了:只有在性与爱的和谐结合之后,生命才能够遵循一种常态的自然选择。由此可见,极富个人化特色的“戏拟”这一创作手法,无论与什么历史情景相结合,无论与多么荒诞的情节相搭配,最终还是以揭示人性的深层主题为依归。
三、《白蛇》:揭示人性中幻想与现实的严重悖论
当代文坛涉及“文革”时期的作品不计其数,严歌苓作品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文革记忆”。《白蛇》,这部严歌苓创作于本世纪初的中篇,一举获得了第七届《十月》文学奖。沿用严歌苓的一贯风格,《白蛇》摒弃了直接描写或者回忆的叙事方式来揭露那段历史中的蒙昧与荒诞,而是借用了一个舞蹈演员在遭遇迫害时期与她的同性舞迷发生的特殊情感,冷静、客观地揭示了人性中幻想与现实的严重悖论。故事开篇三个版本就以不同的视角引入了“白蛇”孙丽坤这一角色,为“戏拟”所借用的《白蛇传》这一经典张本。
在“官方版本——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对孙丽坤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一九六三年,她所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同时《白蛇传》在全国十七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她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所独创的“蛇步”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也在广大观众中风靡一时。
民间版本对孙丽坤的白蛇形象是这样定义的:
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个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丽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想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液、孙丽坤。
不为人知的版本中也有此类描述:
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
不可否认,故事得以发生的所有因素都源于徐群珊通过舞台观看舞蹈演员孙丽坤的表演引发她对孙表演的传统名剧《白蛇传》的童年记忆。而孙丽坤则成也“白蛇”,败也“白蛇”。阅读《白蛇》,很多读者都会被文本新鲜的叙事结构所吸引而止步于此。的确,严歌苓此时并没有采取传统的线性情节叙述模式,而是由三个“版本”即官方版本(四个)、民间版本(三个)、不为人知的版本(六个)交叉拼贴而成。但是当我们透过作者的叙述模式以及作品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直指作者为故事设计的题目、楔子时,不禁会问:严歌苓此时为什么要以“白蛇”为题呢?自始至终,“白蛇”只是孙丽坤担当主角的旧目之一,直至故事结束孙丽坤重返舞台,这出《白蛇传》仍然没有上演,它只是隐藏在徐群珊脑中少年时期的记忆,是严歌苓创作需要用的“戏拟”符号。
《白蛇传》,这个最早起源于民间神话后被中国古典文化不断演绎、延深并最终定型的故事模本,此时被严歌苓用“戏拟”的手法借用到小说创作中。严歌苓将经典的《白蛇传》搁置在“文革”背景中,通过对人类性取向中某些特征进行夸大式的书写,从而将白蛇故事从整个原有叙事框架中完全抽离出来。严歌苓既让故事超越了它现实层面的意义,又让人性游走于极限性想象与现实存在的可能之间,向世人揭示了人性之富有的真实含义。对小说中白蛇、青蛇或许仙,严歌苓一方面借用传统模本中的人物外壳,另一方面却在人物中加进了更多的现代性因素和个人化理解,让角色在传统的有限意义之下流露作者对人性的复杂理解。至此,《白蛇传》中关于白蛇与青蛇的复杂纠葛由原来的“相遇(异性)-斗争(异性)-相伴(同性)”被小说《白蛇》改写成了“相遇(同性)-接近/实践(性偏至)-受挫(性回归)”。通过这种戏拟化的改写,古典传说背后的文学成规、叙事伦理被人为地变了形。而且沉积在伦理道德、价值规范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结构,也处于一种被消解和颠覆的趋向之中。
在小说《白蛇》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对女性命运自始至终的关注与热衷,更让读者了解到带有偏至色彩的性幻想、性取向的现实存在性和生长背景。透过《白蛇》,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对女性地位的认同、对男性书写的有意弱化以及作者本人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的最终抉择:提出问题却很难解决问题,发现新异却往往最终流于世俗传统。“这是个35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人。长相不坏,耳朵不招风,牙齿也不七歪八倒。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种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此处男性的出现成了严歌苓解决问题的最后杀手锏:她能够在传统中发现新异,却最终只能在先锋与通俗中谋求平衡。在此,我们可以把小说结局的处理解释为严歌苓作品对于艺术魅力和人性释放的尝试。
与此同时,严歌苓借助一系列带有“戏拟”色彩的文本结构,让我们透过看似支离破碎的故事,把她本人渴望拯救真实、消解类项的目的一步步地推向文本前台。在严歌苓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叙述中,我们很难清晰把握其中是否存在明显的价值判断和人性归属,或者说她只是忠实地记录着、描写着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和差异。在巨大的生存压力背后,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它坚硬而直接,击打着人们的感情,使人类一切正常的情感以及合理的欲求都因缩水而更加坚挺甚至异样起来。而作者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曾经这样说过:“生存总是最紧迫的事,我在美国什么都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售货员和助教。在中国写作常要专门去体验生活,可当生存成为第一需要时,这种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5]在严歌苓对于个人历程的重新整合和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丰富和隐喻。而此时,“生存”一词,才在它的抽象名词的性质之下,具象为一种能指并潜藏进她的叙述中。就像严歌苓小说《无出路咖啡馆》的寓意一样:在异域(异地),生存空间如此狭小,生存之路如此艰难,选择屈服或者逃避似乎都是可能的。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将面对心灵上“无出路”的困境。而这正是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人性的矛盾与复杂所呈现出来的斑驳色彩。
四、结 语
作为一名热爱生命、感受生活的创作者,作为一位心思细腻且敏感的女性作家,严歌苓总是在捕捉自身或者身边的文学素材。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一味地再现历史留下的那些东西,而是以文学创作者的思考能力着力地表现生活、重塑历史,孜孜不倦地完成写作过程。严歌苓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一段段历史的重新书写和深度挖掘,也是以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抒写着作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现世感受。在这里,历史的真面目与叙述者自身的现实生存境遇在内在本质上竟然如此相似。因此,严歌苓笔下的历史叙事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又是她对现实的理解:现实其实就是历史的一种延伸。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记忆的也是体验的。它们流动且沉淀,表达了对于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人之灵性的期盼。严歌苓小说以独特的“戏拟”手法,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她的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上,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造独特的精神家园。严歌苓以她独特且变化的历史叙述方式,在历史本应具有的面目和作者的理解之间成功地找到了重合点。
[1] 胡静. 关于生存与人性的对话: 对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的一种解读[J].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4, (3): 38-41.
[2] 刘艳. 美国华文女性写作的历史嬗变: 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J]. 中国文学研究, 2009, (4): 114-119.
[3] 徐涛. 论严歌苓作品中人性的冲突和变异[J]. 作家, 2009, (8): 21-21.
[4] 戴锦华, 王干. 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J]. 大家, 1996, (1): 194-204.
[5] 陈熙涵. 严歌苓: 性格顽强, 抓住梦想[EB/OL]. [2002-12-03]. 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223/2110 2747/20021203/880398.html.
“Parody”: Special Life Hidden in Classics—— Analysis on Humanity in Yan Geling’s Historical Theme Novels
WANG Jing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Design, Jinan, China 250300)
The unique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in Yan Geling’s novels not only is a metaphor of reality, but also represents her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exploring of individual survival value and expectation for humanity.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inner narrative pattern, in writing historical theme novels, Yan Geling focused on historical demonstration. In composition, Yan Geling aimed at basing on reflection of humanity itself to reconsider the meaning of real world and construct spiritual home. With the conception of “parody”in “metafictio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hidden in history and humanity woven in details could be revealed in Yan Geling’s historical theme novels.
Yan Geling; Historical Theme; Parody; Metafiction; Humanity
I207.42
A
1674-3555(2012)06-0050-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6.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1-10-02
王璟(1981- ),女,山东济南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