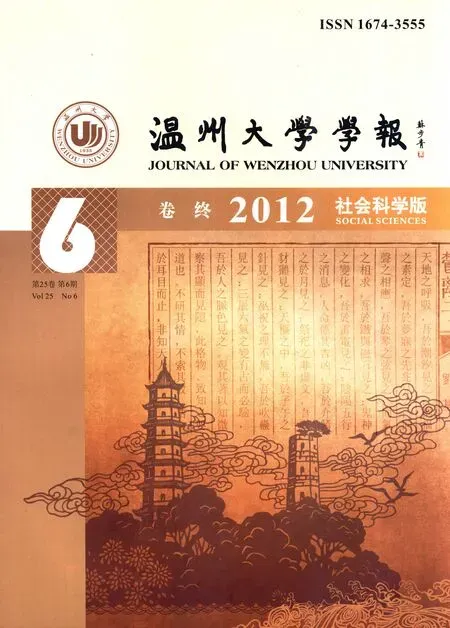论康德“根本恶”之思想
—— 兼论汉娜·阿伦特对根本恶学说的发展
高 明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论康德“根本恶”之思想
—— 兼论汉娜·阿伦特对根本恶学说的发展
高 明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康德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人性中“恶”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哲学家,这一反思集中表现为他对“根本恶”的道德形而上学论证。根本恶包含人心的脆弱、不纯和恶劣三个层次,在本质上是对准则中伦理次序的颠倒。根本恶学说深刻影响了后世哲学家对“恶”的探索。
康德;根本恶;人性;汉娜·阿伦特
1793年5月4日,康德写信给哥廷根神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司徒林称,其纯粹哲学之使命有三个: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我应该做什么(道德哲学)?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哲学)?并说他即将完成的新著《纯粹理性界线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教》)正是要解决当某人做了“应该”之事,在逻辑上他还可“希望”何事之问题[1]。然而,这部被康德寄予厚望的书却使他招致无数非议,其中最受争议的观点为,康德论述说人性中存在着一种可被称为“根本恶”的倾向。书甫一出版,即受到歌德和席勒的嘲讽[2],他们认为所谓“根本恶”不过是《旧约》中“原罪”的异名而已,康德对传统宗教的“讨好性”诠释违背了启蒙原则;另一方面,当局也不满意,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书报审查官批评该书“滥用哲学,以歪曲、贬低《圣经》和基督教”[3]47。现代哲学史上对根本恶思想做诠释最著名的是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4]99。本文拟对康德根本恶学说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做同情理解之诠释。
一、谁是德性的真正敌人?
尽管康德在致司徒琳的信中称,纯粹哲学的三个根本命题最终可归结为由人类学来回答的“人是什么?”的问题①1798年, 康德出版了讲授了20年的人类学讲义《实用人类学》.,然而事实上《宗教》开篇所探讨的人性论问题已经开始了对人这一族类的反思。作为一部经典宗教哲学专著,《宗教》以“人性论”而非“上帝论”开篇,集中体现了康德对“神-人”关系中,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强烈关切和深刻反思。
康德认为,作为一个族类的人,在其人性中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潜在维度:向善的禀性与向恶的倾向。前者包括三种禀性:动物性、人性和人格性。其中,动物性禀性是自然的、纯粹机械性的自爱(自爱又可分为自我保存、基于性欲繁衍族类和社会化本能);人性禀性是理性的自爱;人格性禀性是“敬重道德法则的敏感,此时,它自身就是决意的充足动机。这种仅仅敬重我们心中道德法则的敏感因此就是道德感”[3]76。作为禀性,动物性、人性和人格性都只是善的萌芽。假若人性中只有“善端”而无“恶端”,我们就无法理解道德家们对人性的悲观慨叹了。迁善黜恶是所有伦理学家的希望,康德认为,由恶而善的转变是一场心灵的革命。既云革命,就不仅仅是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善端,革命更像是一场殊死战斗,斯多亚派的“德性”概念就暗示了这一点。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德性”都是无畏和勇猛的表现[3]101,因而预设了一个敌人。那么,谁是我们需要去战斗的敌人呢?自斯多亚派以来,人类很多时候把德性的宿敌判为感性欲望和自然偏好。然而康德批评说,“那些勇敢的人们认错了他们的敌人,他们的敌人不应该在未经教化且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公开呈现给每一个人的意识的自然偏好中去寻找,相反,他们的敌人是隐藏在理性背后且更加危险的似乎不可见的敌人。”[3]102质言之,常被人们所诟病的人性中的动物性、感性欲求和自然偏好,在康德看来本身并非恶,相反它们还是原始的向善的禀性。毋庸讳言,从自爱、偏好、欲望可以发展出恶,如可以从自我保存、性欲和社会本能上发展出饕餮无厌、淫荡和野蛮的无法无天,但动物性本身并不是恶,以上嫁接的恶只是理性对动物性的滥用和放纵而已。自然、偏好和欲望既无资格邀功也不应拥有任何恶名。因此,康德郑重地说,“真正的恶在于,当偏好怂恿我们去行恶时我们却不愿意反抗,这种意向才是真正的敌人。”[3]102人性中这种不愿意反抗恶行的理性倾向才是真正的恶,这种“向恶的倾向”被康德称之为“根本恶”。根本恶才是德性的真正敌人。在这一点上,《圣经》显然比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深刻[5]。所以康德说,“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德性的敌人,也就不应该对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自然偏好),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感到不安了。”[3]103与“属灵的”恶魔争战就是与理性的根本恶争战,而不是与饱受非议的“属血气”的自然偏好和感性欲求争战——这是康德对《圣经》颇富洞见的诠释。
二、人性中的根本恶及其层级
康德虽然阐明,人性有向善之禀性和向恶之倾向,但善端显然并非他论述的重点所在,它的价值只是为了说明“根本恶”的根源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感性欲求和自然偏好。那么,何谓作为向恶的倾向的根本恶呢?要理解根本恶,首先要理解康德所谓“倾向”一词的意涵。康德所谓的倾向是指感性偏好之可能性的主观根据,这种主观根据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决意。显然,向恶的倾向是内在的,但这种内在性并不是由一种强大的外力置于人类,而是人类理性自愿接受,自我招致的。这种自我招致的内在的恶的倾向正如其德文原义“斜坡”一样,只要人居于其上就会下滑,因此,向恶的倾向是人性中的“根本恶”。具体而言,根本恶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人性的脆弱:意谓人心虽然已经接受善的准则,但在遵从实践此准则时却表现出软弱和无力。诚如使徒保罗的抱怨,“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6]或如冉求向孔子的慨叹,“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7]
第二,人心的不纯:意谓人心在道德动机中掺杂非道德动机的倾向。“人心的不纯在于,尽管准则就其对象(对法则的有意遵从)而言是善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足够强有力的,但却不是纯粹道德的,即准则并没有——而这是应该的——仅仅将道德法则采纳为充足的动机,相反,在为了规定决意去做责任所需要的事情之外,准则经常(而且也许总是)仍然需要其它动机;换句话说,符合责任的行为并非纯粹出于责任。”[3]77-78
第三,人心的恶劣:意谓人心采纳恶的准则的倾向,本质上乃是准则中动机之伦理次序的颠倒。这种颠倒表现为:决意在面临各种准则时,竟把非道德动机(如自利、偏好、欲求)置于道德动机之上,或让非道德动机优先于道德动机。譬如,当且仅当自利等非道德动机被满足时才愿意履行纯粹的道德责任。人心这一颠倒准则伦理次序的倾向必然导致如下结果:即使碰巧会出现律法上“符合”道德法则的善行,也不存在“出自”道德法则的德性。这是道德意向的彻底败坏。
康德把人性中的“脆弱”和“不纯”称为“无意的罪”,把人心中准则的伦理次序的颠倒称为“蓄意的罪”。蓄意的罪在具体实践中会造成两种可能结果:要么不可普遍化的特殊准则造成了恶的结果,要么这一颠倒的准则侥幸没有造成恶的结果。恶的结果是对恶劣的人心或颠倒的动机的直接暴露,在这一点上,人类无论对自己内心恶的倾向还是实践中恶的结果都无话可说。悲哀的是,在很多时候,倘若准则中所包含的恶的潜力并没有转化为恶的现实,即倘若结果仍然以“行为符合法则”的合法性表现出来时,人类竟无耻地假装自己也具有“行为出自法则”的道德性了,完全忘记了即使这种可怜的合法性也仅仅是由于恶的自我隐蔽而已。通过把“合法性”假装成“道德性”,或者说通过把符合法则的“现象的德性”假装成出自法则的“本体的德性”[3]91-92,人类在自欺、不诚实和虚伪中坠入了蓄意的罪——这才是人这种存在者在道德上最不光彩的地方,这种恶显然是根本恶。可见,康德最为重视的人心的恶劣层次上的根本恶,其本质特征是人性中的自我欺骗和虚伪。正是在自我欺骗和虚伪中,人类坠入了根本恶。
三、准则之主从关系视角中的根本恶
人性中存在着向善与向恶两个相反的倾向,前者被康德称为“向善的禀性”,后者被称为“根本恶”。如此一来,善恶两种潜力如何共存呢?在什么情况下,哪种潜力会转变为现实,而哪种潜力仍然只是潜力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基于康德对“准则的质料”与“准则的形式”的区分[3]83。质言之,无论是向善的禀性,还是根本恶、道德法则、自利、幸福和感性冲动都只是准则的质料,即各种动机,如果我们只在各种动机中,或者说只在准则的质料中寻找善与恶的区别,由于一般人不会拒绝任何自然而然的动机,于是在准则中将出现各种动机的“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人类在道德上会陷入两个被称作“宽容主义”的命题:人之本性在道德上既不善也不恶;人之本性在道德的某些方面是善的,而在另一些方面是恶的。这两个命题都被康德予以否定,因为就前者而言,准则在道德意向上要么是可普遍的,要么是不可普遍的,不可能存在中性状态;就后者而言,某人在道德上既善又恶的命题是逻辑自毁的,因为准则之普遍性与特殊性无法共存。
以上分析显然否定了从准则质料(动机)角度判断德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准则的形式——动机的主从关系来判断人心中隐秘的善恶,即:我们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动机中的哪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存在条件。下面试以法则和自利两种动机来进行分析。
第一,法则和自利是两个最平常的被选动机,某人自然而然地将这两者都纳入自己的准则,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此人是既善又恶的。
第二,在进行选择时,法则和自利显然处于不同位置,否则将会陷入“既善又恶”的逻辑自毁状态;因此,法则和自利被迫放弃了平等的并列关系而进入了一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第三,现在,假如法则被此人作为最高动机来予以遵从,而自利只能隶属于法则并遵从法则,从而处于次要位置,那么此人在道德上是善的;假如自利被此人作为最高动机来予以遵从,而法则只能隶属于自利并遵从自利,从而处于次要位置,那么此人在道德上已经是恶的了,因为他颠倒了道德上的善应该具有的伦理次序。
第四,若在准则中自利为主,法则为从,自利被此人当作最高动机来予以实践,法则需要遵从自利,那么此人在道德上的确已经是恶的了;然而在经验中,此人的自利准则仍然有可能导致行为符合法则的合法性,即行为侥幸“在经验性格上是善的”,但这种善的假相并不能掩盖恶的心灵,因为他“在理智性格上仍然是恶的”[3]83,他的内心已经失去道德性了。
第五,倘若此人敢于承认自己的行为只具有合法性而不具有道德性,他虽然在道德上是恶的,但仍然是诚实的;根本恶之逻辑为:大多数时候,人类都喜欢宣称(甚至在内心也这样自欺地认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就是心灵的道德性——这就是令人惋惜的人性中的根本恶的最高表现。
四、根本恶的起源
早在1786年出版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康德就对人性中这种恶的癖好做了精彩概括:“自然的历史开始于善,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而自由的历史开始于恶,因为它是人类的作品。”[8]可见,恶的历史开始于人,因为除了道德主体人之外,我们想象不出恶还会开始于别的地方,除非我们像神学家那样,认为恶开始于一个堕落精灵的蓄意谎言。由“开始”的概念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起源”的概念:恶也是起源于人吗?回答显然也是肯定的,难道我们要将恶的起源(即存在论根源)放置在人之外的其它地方?然而,说仅仅说“恶起源于人”毫无意义,因为我们还会继续追问:“恶起源于人的什么?”
具体而言,康德这样来论述起源,“起源可以被认为要么是基于理性的起源,要么是基于时间的起源。在第一种意义上,所考察的仅仅是结果的存在,在第二种意义上,所考察的是结果的发生,从而也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件与它在时间中的原因联系起来了。”[3]83然而,考察恶的时间起源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时间序列中,永远存在着一个“先行者”,这无疑会导致无穷后退。因此,只能探寻根本恶在理性上的存在论根源。然而,“当我们寻找恶的理性起源的时候,每一个恶的行为都必须被这样认为,即好像人类是从无罪状态直接堕入了恶中。……因此,他的行为能够并且必须始终被判断为是对其决意的一次原始的运用。”[3]86-87人性中固然存在着“动物性、人性、人格性”(向善)以及“脆弱、不纯、恶劣”(向恶),但在选择作恶还是行善这一点上,人完全是自由的,决意总是新的、原始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作恶,那一定是从无罪、原始的状态堕入了恶中。除了自由,根本恶没有任何其它理性起源,自由就是根本恶的唯一根源。
康德关于根本恶起源的研究与《圣经•创世纪》的表象方式完全一致。区别是后者采用了寓言的方式:人类在未具有任何向恶的倾向之前的状态是一种无罪状态,此时,道德法则在人这里表现为禁令的形式——“十诫”;然而,人类显然蔑视了这一禁令的严格性,并未将这一禁令作为充足动机(其原因是神学上最大的争论之一,此之谓“神正论”),而是将其降低为有条件的遵从;最终在撒旦“你们不一定死”的谎言的诱惑下,人类将感性冲动结合进自己的准则,并使其获得相对于道德法则(禁令)的优越性——这乃是道德次序的颠倒;于是,人类堕入了恶中。
然而,表象方式的一致并不能掩盖本质之相异,康德关于恶的思想毕竟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论有着根本区别:一言以蔽之,康德之根本恶乃是基于意志的自由,而基督教之原罪说却是基于意志的他律。根本恶的思想尽管表面看来,已经非常接近“人性本恶”这样的悲观论调,但既然人是从自由堕入恶中,根本恶的存在论根源是自由,那么,迁善黜恶的拯救也必将在自由中由人类的理性自己去完成,善恶乃由人自作主宰,而不必像基督教神学那样,由原罪说引出上帝救赎的神宠说。同时,根本恶作为恶的倾向就存在于当下人性的自由中,它是内在的、非时间性的,因而不需要继承《创世纪》的“始祖”概念。康德虽然援引《圣经》寓言,但经理性阐明的根本恶恰好是对原罪的祛魅[9]。质言之,善恶之命运最终都还原为人本身,而非外在的上帝。可见,康德并未像歌德、席勒所嘲讽的那样背叛了自己的启蒙原则。他并非要从宗教来论证道德和根本恶的依据——自由,相反,《圣经》和传统基督教充其量只是作为根本恶思想之补充和辅助,其功用仅仅用于阐明和提醒我们使用理性早已知晓的东西而已[4]58。
五、汉娜·阿伦特对根本恶学说的发展
康德关于根本恶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希伯来宗教-希腊哲学”传统中的后世思想家,如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尼采,以及当代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0],时至今日,仍然是学者们热议的主题。其中对这一思想最著名的发展来自阿伦特。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并作为犹太人饱受纳粹迫害之苦的阿伦特对人性中的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反思。在《极权主义之起源》第12章末尾,她指出,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不相信有一种为恶而恶的“根本恶”,基督教神学家和康德都作如是观[11]608。深入研究过康德政治哲学的阿伦特显然有着对恶之难题的深刻洞见,因为在基督教神学中,魔鬼本来是天使出身;而在康德学说中——正如上面所阐明的——根本恶之核心层次是指道德准则中伦理次序的颠倒,而非专门为恶而恶的纯粹的恶意①转引自: 参考文献[3].。康德既坚持根本恶,又反对将其诠释成“为恶而恶”的恶意。然而,在解释根本恶的存在论根源时,阿伦特与康德分道扬镳了。康德仅对恶做道德形而上学的剖析,阿伦特却更重视恶之社会制度根源。在1951年3月4日致其导师雅斯贝尔斯的信中,阿伦特谨慎地阐明,“我不知道根本恶究竟为何物,但对我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如下现象相关:根本恶使人之为人成为多余者。”②转引自: 参考文献[4].“多余者”是阿伦特频频使用的概念,根本恶如何使人之为人成为多余者呢?她总结道,根本恶是某种制度的伴生物,在这种制度中,人之为人成为多余的了[11]608。这种可怕的制度就是阿伦特所深刻分析的“极权主义”,在极权主义制度中,在工具理性的精密安排下,人的自由、个性都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有所谓上帝般的超人意志。极权主义极端蔑视人之为人的尊严,它不是把人性视为终极目的,而是当作可被根据罪恶的私意任意加以改造的工具,所以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11]607可见,阿伦特虽然使用康德的概念,但她把康德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根本恶拓展到社会制度领域,给予其超越人性论的政治哲学维度——这是对康德思想的重要发展。
如果说康德的根本恶重视的是人性中伦理次序的根本颠倒,那么阿伦特则重视的是这种恶在制度层面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深层伤害[4]84。这种伤害甚至真的改变了人性,使人类变得失去反思能力,最终完全蜕化为服从于罪恶制度的附庸。1963年,阿伦特出版了引起广泛争议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③参见: 汉娜•阿伦特.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M]. 孙传钊,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在这部著作中,她借助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原纳粹军官身上的表现出的惊人的麻木、浮浅和无思想,把人类服务于恶的技术理性制度的心灵状态称为“恶之平庸”。晚年,阿伦特基本放弃了根本恶,常常谈及的是人性中这种浮浅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没有深刻目的,也丝毫没有康德式的准则之伦理次序的艰苦斗争,除了沉湎于平庸的生活(如个人幸福、职称晋级)而外,什么也没有。阿伦特的论述揭示出一个冷酷的事实:平庸的人类连恶也是如此平庸!而正是这种恶之平庸,几乎毁灭了世界——阿伦特对人性的深刻嘲讽是对康德根本恶思想的有力补充。
[1] Kant I. Correspondence [M]. translated by Zweig 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8.
[2] Firestone C L, Jacobs N. In Defense of Kant’s Religio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79.
[3] Kant I.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C] // Kant I.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 translated by Wood A W, Giovanni G 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Anderson-Gold S, Muchnik P. Kant’s Anatomy of Evil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Reardon B M G. Kant as Philosophical Theologian [M]. New Jersey: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88: 111.
[6] Yancey P, Stafford T. The Student Bible [M]. Michigan: The Zondervan Corporation, 1987: 990.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7.
[8] 康德. 人类历史起源臆测[C] //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1.
[9] Rossi P J, Wreen M. 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Reconsidered [M]. Bloomington: 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64-65.
[10] Caygill H A. Kant Dictionary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182.
[11]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M]. 林骤华, 译. 台北: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5.
Study on Kant’s Thought of Radical Evil——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Hannah Arendt’s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of Radical Evil
GAO M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81)
In moder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Kant is the first philosopher who gave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evil” in human nature. This reflection is epitomized in his moral metaphysical argument of“radical evil”. Radical evil contains three levels, i.e. frailty, impurity and depravity of human hearts, and it is essentially a reversal of the ethical order of the maxims. The doctrine of radical evil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xploration of “evil” by the later philosophers.
Kant; Radical Evil; Human Nature; Hannah Arendt
B516.31
A
1674-3555(2012)06-008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6.01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2-01-06
高明(1978- ),男,甘肃宁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哲学,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