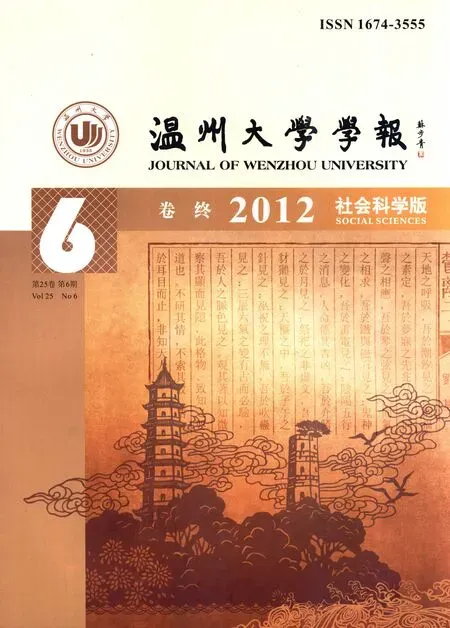空间批评和文化意义生成
黄继刚
(1.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 236041;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空间批评和文化意义生成
黄继刚1,2
(1.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 236041;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空间批评”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空间转向”背景下,以新的空间观念为前提,实现文学研究批判功能的一种新型批评形态。其在融合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三空间、文化身份认同和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文化理论。空间批评强调对文学空间的文化解读,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文化政治的融合。其从后现代美学和文化角度阐述了文学批评的多维属性,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空间批评;边缘空间;文化身份;女性地理
一、空间转向和空间批评的兴起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在激烈的震荡中,经历了一次称之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文化转型。“空间转向”以列斐弗尔于1974年以法语发表的《空间的生产》为标志,其理论关注的焦点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空间”还是传统静止的平台,而后者所讲的“空间”已经开始瞩目于自身的性质。在列斐弗尔看来,空间和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劳动、消费等概念有着必然的同构关系,他正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背景下,从空间的生产中推导出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并且确定了空间的总体性意义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1]。自此以后,有关空间的研究沿着两条路线展开:一方面,社会学家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在现代性视域下来研究空间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另一方面,后现代理论家通过大量的地理学隐喻来研究空间文化的诸多可能性。正是在列斐弗尔、福柯、詹姆逊、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空间转向”成为影响到整个西方学界的思潮,并在学术思想的言说方式、提问方式和解释方式上产生了诸多的变革。所以说,“空间转向”是关系到整体性的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变革。“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2]这种范式的转型广泛影响到哲学、美学、文化地理学和文学等学科,并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创新开启了广阔的空间。文化理论家菲利普•韦格纳将这种空间和文化理论的联姻称之为“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并将其和生态批评、伦理批评、性别批评等并列,称之为是21世纪西方最前沿的批评理论之一[3]。可以说,空间批评是在广泛吸收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哲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精粹的同时,融合女性理论、殖民主义、身份认同等诸多后现代理论,以实现对后现代文化的多维度解读。如果说在传统批评中,空间只是一种自然场景,或者故事展开的叙述背景,那么在空间批评中,空间将强调作品中的地理景观自身的文化涵义,并通过意义表达系统来呈现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身份关系、伦理道德等多层次的关系。
二、空间批评和文化政治
(一)后殖民背景下的“第三空间”
“后殖民”作为概念一直以来都充满着含混的张力,尤其是后殖民对空间地理学的重新解读,并以“第三空间”激励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边缘空间的文化意义。霍米•巴巴曾用“第三空间”来指代那些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的文化处境。作为一种创作策略,活跃在西方的非西方出身的艺术家,也往往从他们特殊的身份开始他们的文艺创作。相对于西方的主流文化,他们属于处于社会和文化边缘的少数族裔,但他们以此来寻找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霍米•巴巴从“第三空间”来分析这种文化的冲突和纠纷问题,他认为文化的形成都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中,混杂性的意义对于文化的发展而言,并不能够追溯本原,而在于能令其他各种文化立场相继出现[4]109。这种文化视角并非注重差异性与抗争性,相反它是“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是二元对立思维之外的某物。”[4]28
边缘困境源自于文化差异这一基本事实,尤其在欧美的移民国家中体现的更加明显。譬如在美国法律的范围内,非裔(包括华裔)都是合法公民,但是在衣食住行上都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所以无论从文化上或生理上都被看作是不可同化的种族。正是由于有着自己不同的移民背景与种族认同,以及长期以来在政治、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非裔(华裔)始终感到美国主流世界对他们的排斥,因而会感到无所适从,始终处于“两个世界之外”。多年的海外生活仍然无法让他们完全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去,当他们用美国方式来解决所碰到的问题时,在潜意识里又会受到本族文化的影响。两种碰撞的文化常会让他们迷惑不解,这种边缘事实和文化困境是“陌生的异类者与现代秩序建构的冲动之间凸显的不可化约的紧张”[5]。
空间批评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理解差异和激进主体性等最为有效的后现代方法论,其原因就是成功地对“第三空间”的引入,这是对传统殖民文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否定和批判,也是与传统研究中一种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后殖民文学家蓓尔•瑚克斯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二元对立,尊重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多样性,进而获得重新审视的眼界[6]。应该说,瑚克斯的代表作《渴望: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是空间批评认可的探索“第三空间”差异性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文本。在文中,瑚克斯有段著名的“铁路那边”的比喻,其讲述的就是边缘空间处于全体之中,但是在主体之外的事实。作为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铁轨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是边缘性的存在[7]:
铁轨的对面是平展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就餐的饭馆以及我们不能正视的人们。铁轨的对面是一个世界,只要它雇用,我们就在其中充当女仆、门房和妓女。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在其中生活。我们始终要返回边缘,要跨过铁轨,回到小镇边缘的那些栩屋和废弃的房子中去。法律规定我们要回去,不回去就要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我们这样的边缘生活使得我们形成一种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既从外面向里看,又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关心边缘也关心中心。
瑚克斯的这一譬喻充满了空间隐喻和空间指涉的话语,也充满了颠覆和重新定位的企图,她所表述的主体性建构,其选择的道路是“中心又是边缘(同时又双方都不是)”[8]123。这一譬喻类似于斯皮瓦克“中心即边缘”的论点,从而由对中心的重新界定引申到对边缘的重新界定,边缘不再是永远处于整体的外围,边缘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这正是空间批评所要表述的文化政治的核心内容:即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进入到由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空间领域中。在这里,人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联系、互不排斥的社会。这样,空间批评就在这些真实和想象的边缘空间中为新的差异和文化政治开辟了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二)真实和想象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在空间批评语境中被关注的关键性问题。按照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的界定,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9]。而乔治•拉伦则认为:“文化身份总是在可能的实践、关系及现有的符号和观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着。文化身份即是‘变成’,也是‘是’,既属于未来也属于过去。”[10]按这种定义,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持续的变化。空间批评家爱德华•索亚认为文化身份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人们的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至少有两种理解文化身份的可能:一种是本质论的,狭隘、闭塞;另一种是历史的,包容、开放。前者将文化身份视为已经完成的事实,构造好了的本质。后者将文化身份视为某种正被制造的东西,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8]215在当前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后者的观点。譬如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有助于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11]1,“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11]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却活生生地有着一个这样的共同体的意象,也正是在想象中,这样规模的集体才能存在。”①转引自: 阿雷恩•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M]. 陶东风,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163.应该说,空间批评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来介入到对后现代城市空间的研究,并解读了城市空间隐喻和城市空间实体的辩证关系,表明文化身份这个介于想象和真实之间的社会文化空间是开放的并且富有开拓可能性的,它使得人们能够从一个从未有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空间既存在于特定群体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和想象中,也存在于都市空间的重新整合和再创造过程中。
遵循以上空间批评的视角来考察现代都市空间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现代都市空间的形成过程,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文化杂交空间中,民族性、地域性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固有形态都被提取出来。在一些非常具有文化混杂性的城市,像洛杉矶、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等等,文化杂交的现象就非常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这些城市中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移民一面共同分享着都市的公共空间,一面却又保持着各自相对封闭的局域空间,比如著名的唐人街、纽约的小意大利城、洛杉矶的小日本城等等。尤其是我们熟悉的唐人街,尽管社会学家不断提醒人们并解释,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开饭馆的国度,但中式餐馆仍是唐人街的象征。无论几代下来,在唐人街生活的华裔仍摆脱不了“移民”、“另类”的文化身份。尽管这些区域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划分界限,却有着类似于蓓尔•瑚克斯的譬喻“铁路那边”那样的无形的界限。在这些区域里,相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自成一体。著名华裔旅美作家蒋彝曾经在“哑行者系列游记”中表达出对这种文化身份的自我意识以及对真实和想象家园的努力寻求。当人们处于比较稳定的文化状态下,一般不会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当人们离开家乡、流落异国时,文化的差异将会打破了传统相对稳定的心理认知架构。对于旅居海外的蒋彝来说,“家”的概念不光是具体的,也是想像的,是存在于他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在他的《波士顿游记》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12]:
意大利人:波士顿的一半居民来自爱尔兰,你知道另一半来自意大利吗?
中国人:波士顿有一个中国城,对吗?
爱尔兰人:是的,但很小,我常去那里吃饭,我喜欢中餐。
中国人:你们俩在波士顿生活了40多年,你们称自己是波士顿人吗?
爱尔兰人:不,才不呢。我们才不愿被称为波士顿人呢,我们只是住在波士顿,波士顿人也不把我们叫做波士顿人。
当蒋彝置身于不同民族文化构成的差异空间中,尽管各地的移民占据着波士顿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但是他们在波士顿的文化身份是缺席的。对于移民来说,他们拥有都市的公民身份,却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文化空间中,他们将一直游移在都市文化身份的真实和想象之间。
(三)女性空间和性别地理
女性对空间地理的诉求最为著名的要算20世纪初期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她的《一间自己的屋》①参见: Woolf V.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89.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对空间关注的开篇之文。“一间自己的屋”是女性想象身份的场所,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她们可以走出性别樊篱而走进一个短暂的、非现实的想象空间中。应该说,伍尔芙对“房间”的诉求表达的是女性想占有空间这个朴素的渴望,而“一间自己的屋”所包含的地理空间对女性生存的意义直到当下才被空间批评在理论层面上揭示出来。具体而言,空间批评认为,传统的地理学是建立在男性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的,缺乏性别差异的眼光,采用“中性的”或者说“男性的”标准来解决空间问题,将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位于“公共的男人”(public man)和“私密的女人”(private woman)。而社会分工一直将性别关系定义为:男性在“公共领域”,而女性在“私人领域”。这种性别分工最终导致了性别空间的出现,即女性被束缚在家庭这个狭窄单一的空间,而男性则成为社会空间发展的主宰。空间批评家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传统区分提出尖锐质疑,“前者是男性行动、生产和政治参与的场所,后者是女性消费、再生产和家居生活的场所”[13]。这种地理上的区分实际上是经济不公和性别歧视的结果。因此,空间的差异性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同样,城市地理作为一种空间再现的系统,传达着一种关于人类身体权力的隐喻,揭示了两性在城市和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垂直的结构通常作为神圣的“男性气概”的象征,如佛塔、摩天大厦、廊柱等;而住宅则反映着一种“女性气质”,如诞生地、温床、子宫等。城市空间对男性来说,是“浪荡者”(dandy)和“都市闲逛者”(flaneur)的天堂,是享乐和寻求猎奇的地方。在现代性文学的表述中,“浪荡者”和“都市闲逛者”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男性的城市空间体验为基础的现代性审美感受。“穿越城市,在城市的开放和内部空间里找寻冒险和娱乐,以这种方式,他创造了这座城市样貌的观念和实体的地图。在不断移动、追寻享乐、休闲和消费的过程中,‘闲逛者’成为都市再现的特定形式——他将城市再现为欲望的不同场所。”[14]但是“闲逛者”具备的“移动观看”的权力,在女性那里却是奢望,她们如若重复“游荡者”或“闲逛者”的行为,通常被赋予不道德和不名誉的联想并遭受世人的白眼,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曾经表述过这种性别地理差异:“村庄组织结构是女性特质的,而城市组织结构则是男性特质的……城市标志性的、代表着城市权威的建筑物,如尖塔、教堂、纪念碑就等同男性生殖器。”[15]这种貌似客观的性别表征却掩盖了空间的性别差异和“女性在空间中”的事实。这给空间的形成打上了性别不平等的烙印。这是造成女性在社会空间中的艰难处境的根本原因。
而空间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特点就是将这种性别空间和男子中心主义的性别歧视置于范域宽广的当代分析之中,并揭橥父权在城市人造环境上留下的种种印记和霸权地位。这种父权力量的空间化在公共场所的设计上处处留下痕迹,渗透到都市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市民不经察觉的潜意识当中。譬如纽约街头广为人知的雕塑“市民美德”(public vitue),这是一件基本全裸的男性雕像,“由一位目光严厉的具有大男子气魄的高大男性构成美德,他的肩上扛着一把剑,脚下踩着两个象征堕落和谎言的女性人物,他脚边围绕着海洋动物”[16]。设计者试图通过这尊雕像表明管理这座城市的男人是诚实的,并且在掌握法律方面是强有力的,面对诱惑能够保持尊严和高贵的思想。年轻象征着单纯和理想主义,剑喻之为执法的威严。但在空间女性主义批评家眼中,由于这尊雕像突出表现了男性的性别特征,雕塑实际上是性别权力关系在公共空间的再现。空间批评家通过对更多诸如此类城市日常生活形态的解读,发现了女性群体生活在城市空间边缘的事实。她们被特定的购物场所、特定的职业类别和家庭生活的狭小范围蓄意地孤立起来,当她们徜徉在化妆品柜台和超市的菜蔬肉禽几案,奔劳于锅碗瓢盆之间,安于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的时候,被蒙上面纱的父权意识正在都市公共空间中悄悄蔓延。
空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运用空间视角来对考察性别文化的批评实践,它一方面以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为依据,另一方面将视线转向了地理空间,是一种将空间和性别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批评。正是“她们”的学术理论和批评实践提醒着我们:空间不是中立的存在,而是刻有性别权力关系的印记。建筑物、街区、消费场所实际上都充满了性别权力的隐喻,而空间批评和性别地理的结合将会更有效地抵制一切形式的屈服和压迫。
三、结 语
空间批评是对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的解构和重构,必然会涉及到种族、阶级、边缘、文化身份、性别地理等等许多激进的文化政治立场。后殖民文化理论突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现代主义二元对立,进入了由差异所造成的多样性的“他者”空间中,其文化理论脉络之中的“空间”概念更深刻地蕴涵着批判意识,其批判的目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地理想象,而它对“边缘空间”的探索,将后殖民空间表现为一个弱势声音的世界。在对待文化身份问题上,空间批评家认为文化身份没有固定的本质,历史从未给它打上任何标记或赋予任何普遍超验的精神,所以对文化身份的体验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来完成的。而当代女性地理的崛起深化了空间批评对性别空间差异之构成的认识,她们的批评实践深入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文化领域中,从而直白地将自己的“空间想象”移植到充满反抗色彩的后现代文化政治之中。
[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Hoboken: Wiley-Blackwell, 1992: 18.
[2] Wolfreys J.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7.
[3] 菲利普•韦格纳. 空间批评: 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C] // 阎嘉.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
[4]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齐格蒙•鲍曼.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 郇建立, 李静韬,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18.
[6] Hooks B.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2.
[7] Hooks B.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9.
[8] 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 去往洛衫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9]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 // 罗钢. 文化研究读本. 刘象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09.
[10] 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 戴从容,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220.
[11] 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2] 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er in Boston [M].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59: 9.
[13]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79.
[14] Rendell J. Bazaar Beauties or Pleasure Is Our Pursuit: A Spatial Story of Exchange in the Unknown City: Contesting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Space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111.
[15]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 [M]. New York: Harcourt Inc, 2004: 28.
[16] Bogart M H. Public Sculpture and the Civic Ideal in NYC 1890-1930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64.
Spatial Criticism and Generation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HUANG Jig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China 236041)
“Spatial criticism” is a new critical form which sets the new concept of space as a precondition and achieves critical func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turn” of West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y, it absorbs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theories such as the third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feminism. It emphasize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space and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ace and cultural politics caused by modernity. It elabora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erspectives of postmodern aesthetics and culture, and further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Spatial Criticism; Marginal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Women Geography
I207
A
1674-3555(2012)06-0038-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6.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1-11-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2YJCZH075);阜阳师范学院青年项目(2011FSSK03)
黄继刚(1980- ),男,新疆塔城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