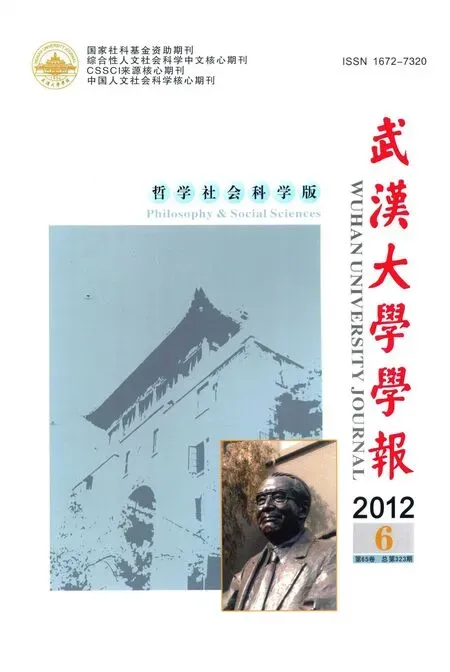析法律翻译暨目标语言的创造性
杨晓强
一、法律翻译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一个不囿于中国大陆的课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民商事交往日益增强。一国在适用外国法及援用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时都需要参照不同语言的法律文本,法律文本的互译因此变得日益重要。这种重要性在港澳的回归、欧盟的统一以及加拿大的双语立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一)香港的双语立法
为应对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内地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区间法律冲突,香港政府于1988年10月设立了法律咨询委员会,建议现行法律的中文文本应该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不久,一个法律翻译专门小组成立,负责所有香港法律的中文翻译。在香港,第一条双语法令制定于1989年4月13日①李昌道:《香港双语立法探析》,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56页。。此后,所有新制定的主要法令都要求以双语形式公布出版。
(二)澳门的法律翻译
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规定了维持和延续澳门特色的原则。法律和语言政策是维持澳门特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在法律制度方面,该政策欲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澳门法律体系从葡国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二是巩固澳门自身的法律制度。法律翻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战略性工具和实际履行《联合声明》的前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澳门本身拥有双语的法律体系;二是在立法程序上和在澳门本身的法院中,两种官方语言能被完全同等的使用。
(三)欧盟的法律翻译
欧盟从法律上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即:语言多样性是欧盟的财富。欧盟目前的成员国多达27个之众,欧洲理事会规定各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盟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欧盟内部机构的工作语言。为了保证欧盟内部机构的正常运转,欧盟设有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机构。为了让欧洲委员会的委员能够讨论某一个法律法案的提议,欧盟的翻译部门必须要提供三种称之为城市语言的提案文本,即英语、法语、德语。一旦委员会通过了提案,法律法案会被翻译成所有的欧盟官方语言,然后才会被提交给欧盟的立法机构,以对提案进行一些修改①赵建平:《欧盟的语言困扰及其解决前景》,载《对外大众传播》2004年第9期,第14页。。为了保证一个法律法规得到顺利实施,该法律法规必须在欧洲联盟公报上以各种官方语言发布。
(四)加拿大法律翻译者参与立法
由于历史原因,加拿大国内曾存在严重的英法族裔对立。1988年7月21日,加拿大正式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以国家立法形式制订多元文化政策,并推行双语立法,而且在法律翻译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该国的法律翻译者正从普通翻译人员向共同起草人转变,也就是翻译者一改过去被动的角色,直接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
(五)中国大陆法律翻译的现实需要
当今,中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如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它的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文译本的世贸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中国与其它世贸成员国在国际贸易往来中,还是可以将世贸规则条文的中文译本作为参考,以避免贸易纠纷。可见,法律翻译在中国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可或缺。
二、法律翻译的方法论:法律文本及翻译理论
在中国国势日强的态势下,中国已积极主动的融入了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浪潮。翻译出版外国法及法学著作供法学研究人员、法律的从业者以及立法者参考研究,可让上述人员拓宽视野,了解各国法学发展的前沿动态,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②杨晓强:《浅谈中国对外国法及法学的移植》,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95页。。法学翻译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普世的意义,是一项惠及当代、泽被后世的工作。
(一)法律文本的特殊性
法律文本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文本,它与其它非法律文本一样是一种特殊功能的文本(text for special purpose)。法律文本主要是由具有区别于其它文本特征的法律语言构成。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用于规范和约束全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规定性,因此其使用的语言表述和由此组成的篇章主要是服务于法律这种特殊的功能③李克兴、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第9~10页。。法律文本的特殊用途性决定了在翻译法律文献时应遵循不同于其它文本的方法和理论。
(二)格特④格特,著名翻译理论家,1991年出版其潜心研究五年后的关联翻译理论大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的目标语言关联论
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论的基本观点如下:翻译活动是一个大脑的推理过程。推理的依据是翻译所涉文本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关联性,亦即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程度。文本经翻译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关联性越强,也就是目标语言能最恰当的表达源语言的语境效果,则翻译的质量越高,反之亦然。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在翻译过程中大脑的推理努力与所实现的语境效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在同等条件下,译者为实现源语言向目标语言转换所作的推理努力越小,并且在转换后所实现的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运用推理,从文本的源语言中洞察出源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并谙熟目标语言受众的认知环境,使得译文能产生使源文本作者的意图与目标语言受众的期待视野相一致的效果。
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论是建立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具有潜在的语境关联性的基础之上的。在法律翻译的语境下,这种潜在的关联性取决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中都有相关语言概念的存在。如“constitution”译为“宪法”,宪法主要规定一国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力,当今任何一国文明法治的国家都有宪法。
(三)奈达①奈达,美国人,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翻译理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毕生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其学术活动。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的功能对等论
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基本思想是译文成品中目标语言和翻译文本的源语言应达到功能上的对等。所谓“功能上的对等”是指目标语言所阐述的思想的指向应对等于源语言的思想内容。如国家私法中的“proper law”,原来有人将之翻译为“恰当的法”,现在法律界广为接受的翻译是“准据法”。“恰当的法”是对其最直接的翻译。仔细审视下“proper law”的源语言的语境②有关proper law 的定义,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per_law中Explanation的第1段。,其实质上是指经冲突规范指定援用来具体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的实体法,因此,“准”和“据”这两个单词都很好的表达了源语言的意境,这两个单词所组合成的短语恰当的表述了“proper law”的法律功能。
(四)格特和奈达翻译论的同异
比较格特和奈达的两种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理论都主张语言是可议的,文本的源语言在目标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将一方的意思传递给另一方。但相较而言,格特的关联论坚持的是目标语境中定能找到一个与源语境相关联的词,而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论中初现专业文本的翻译需要发挥译者创造性的端倪,功能对等理论让译者悟到的是,当文本不能完全直译时,目标语言应能让受众立竿见影的感受理解到源语言想要表述的思想功能。
诚然,上述两种理论都还是忽略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法律语言作为法律文本的载体,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某一国家的法律活动和法律文化,其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具有不同于其它专业语言的特殊性。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皆源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不是每一个法律文本的源语言都能在目标语境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基于文化差异的目标语言的创造性不可或缺。
三、文化差异下的法律翻译中目标语言的缺失与创造
中国法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外来语世界,外来语构成了中国法的主要法律术语。19世纪末期,大清按照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法律起草大清律法;民国政府期间,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中文译本主导了法律的创制;中国解放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实质上都照搬苏联法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英文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这一代的学者大体上是喝着美国法律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学外语是从尝试翻译美国法律文献开始的③参见《法学翻译与中国法的现代化——美国法律文库暨法学翻译与法律变迁研讨会纪实》中贺卫方教授的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许多英美法成为中国立法的蓝本。
在中国法律领域西学的过程中,许多因素影响外国法律语言在汉语目标语言中的翻译效果,在翻译法律专业词汇时要考察词汇背后深厚的文化根源和文化背景及其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文例举探讨中西文化因素导致翻译在目标语言中的创造。
(一)例一:Act of God
该短语翻译为“天灾、不可抗力”非常的绝妙。译文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法律术语的特征性。
在西方国家,“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古欧洲部落国王的王权与天上的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国王的威望和权力都来源于神的授予,国王在神的权威之下,是为神服务,臣服于神的,国王不是神,而是在他身上体现了神的存在④王亚平:《西欧法律演变的社会根源》,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80页。。欧洲大多数国家信奉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也承载有基督教义的文化,即上帝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
西方基督教神学中包含许多对后世西方法律传统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学思想。例如,今天西方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源于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信仰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教义⑤陈洪涛:《法制是如何形成的— —神学与法律关系新探》,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第32页。。此外,在西方国家,证人在法庭作证前要宣誓证言和证词的真实性,“god is the witness,I swear that everything hereI say is true!。该宣誓词源于与《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中不得做假证以陷害邻人的规定。
在中国古代的周朝,周朝国王自称是上天的儿子。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从此皇帝又被称为天子。中国自古有“天意不可违”的说法,类似于“上帝的意志是不可以违背的”。
维基百科对Act of God的定义为:Act of God is a legal term for events outside of human control,such as sudden floods or other natural disasters,for which no one can be held responsible.(Act of God是一个法律术语,其指如突发洪水或其它自然灾害等人力不能控制的行为,当事人不对这些行为承担责任。)
“Act of God”被翻译成“天灾”,就“God”和“天”对应而言,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间找到了一种自然的联系,尽管西方人思想里的“God”不是中国人眼中“天”。但正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所期待的,两者所指事物在社会功能是对等的。再引申到法律术语上翻译为“不可抗力”,四字术语符合法律术语的简洁性的特征,并且表述出了其超越当事人意志之外的韵味。
(二)例二:Three-Strike Out
Three-strike Out是美国棒球运动的规则。strike就是投手投球,击球员没打到。击球员第一次击不中球叫做strike one,第二次是strike two,第三次就strike three,而且如果三次后还是一次都没有打中球,那么击球员得出局了,即out,所谓三振出局。美国仿照棒球比赛制度中“三振出局”做法,创立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累犯问题。
1994年美国通过“暴力犯罪控制暨执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Act),而俗称“三振出局法”或“三振法案”,规定对于已触犯二次重罪(folony)的重刑犯,再犯一次重罪者,则处终身监禁而不得假释①沈玉钟:《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之探讨》,载《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8页。。Three Strike-Out类似于中国的累犯处罚制度,但又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从重处罚,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对累犯从重处罚,法官应该根据累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刑罚,即法官有相应刑罚裁量权。但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能脱离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原则的约束。另外,对累犯从重处罚,是相对于不构成累犯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即对于累犯的从重处罚,参照的标准,就是在不构成累犯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②沈玉钟:《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之探讨》,第29页。。
Three Strike-Out虽然未能成为中国立法的舶来品,但对中国的法律学者从事中美法律的比较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三振出局”似乎已成为业内人士熟悉并能认知的一个术语。笔者没去考究最初是谁将“三振”这个译名引进到中国,但能臆测该名称的翻译者一定既了解中美法制,也熟悉美国的棒球运动。立法的目的是规范一国国民的社会行为。法律术语的受众应该主要是一国的广大国民,而非仅限于该国的法律精英人士。尽管美国的NBA球员的技艺不断撼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但美国的棒球规则却并不为大多数中国国民所知晓。
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找到和“三振出局”意义关联的成语,如“事不过三”。因应格特和奈达的关联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笔者建议Three Strike-out译文“罪不过三”,理由如下:第一,根据格特的目标语言关联的翻译理论,在翻译源语言时,应该从目标语境中寻找在意义上具有关联的词,而不是在源语言中搜寻。具体到该例子中,只不过是将“事”由“罪”来替代,信息时代已早早的到来,国人根据既有的短语再构派生的词绝不仅只有“罪不过三”一个;第二,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论,“罪不过三”中的“罪”字很容易切合受众的期待视野。毕竟“罪”和“刑”是同一个领域的名词;第三,翻译过来的外国的法律概念合乎本国的文化传统无论对于国内立法作为借用,还是让国内的法律学者作中外法学的比较研究都有现实的意义。
四、法律翻译创造法律术语的现实意义
从中华民国对日本法的再翻译,到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法的植入,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英美法的大规模借鉴,我国的法律术语库里存储的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如今的中国在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已开启了自主创新的时代。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的法律生产也开始了自主创新的年代。过去一百年来通过法律翻译创造的法律术语对今世中国的立法、法律比较研究以及对外推广都具有极大地现实意义。
(一)于普法和法学教育
中国法律是一个充满了多元文化的外来语的世界,在各种不同的部门法中能看到来自于不同国家法律概念的影子。不同国家的法律术语经翻译转化后在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个外来的法律术语多种汉化的概念并存的现象,这似乎倍增了中国法律术语的语料库,但同时给国人造成了对法律术语识别上的困难。这也是一个国家在法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随着一国民商事交往的增加,国人在社会实践中会深化对同一外来法律术语不同中文译本的了解,最终选择其中一个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最能代表源术语含义的译法,并将之永久的加载到中国法律术语库里,成为官方认可、人民接受的正式法律术语。相反,那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译名最终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在这个意义上,外来法律术语的选择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
在我国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法律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许多不规范甚至混乱的地方。当社会上不断发展着的语言必须进行调节以适应现实,各种各样的政治法律不断地产生,有时可能意味着新的社群的建立。新建立的社群可能会缺乏共同的交流手段。在类似这种情况下,语言规划会是众望所归的事情,而且的确是必要。身处社会中的人有形无形每天都处在法律规范之下,规范的法律语言于普法和法学教育都大有裨益。规范的法律语言相较于形形色色不同版本外来法律术语的汉译本就像普通话对地方方言一样,让工作在法律语境下的交流更加顺畅,其会更进一步强化国民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洞察。
(二)于中国法的对外宣传
法制是一国综合社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法制程度的强弱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中国不断深化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也需要吸引外来的经济实体加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一国的法制程度是衡量一国民主程度的重要的砝码之一。以欧盟的扩张为例,从上个世纪末至今,欧盟译者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吸纳欧洲非欧盟成员国加盟,但对同处欧洲的俄罗斯抱着谨慎的态度,理由源于欧盟准入制度的两点: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否则,拥有1.5亿人口的大国俄罗斯甚至会颠覆欧盟的整个制度①戴炳然:译《欧盟概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当今世界的大国都是有充沛软实力的法律共同体。没有软实力,硬实力也无从谈起。不论是什么国家,只要它是一个现代国家,就必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
再者,中国现在已是世贸组织的重要一员。WTO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WTO多变协议中很多都有关于透明度的规定,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有关规定TRIPS第六十三条关于“透明度”规定:由一成员实行的、有关本协定内容的法律和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终局决定和行政裁决应以本国语言予以公布,或者如此种公布不可行时,则应予以公开,以使各政府和权利持有人对其有所了解。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政府或政府机构之间缔结生效的有关本协定内容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虽然中文译本的有关WTO协议的规定仅作为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满载中国法律术语的中国法的对外公布是让国际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彻底改变中国法以往一直在国际上无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