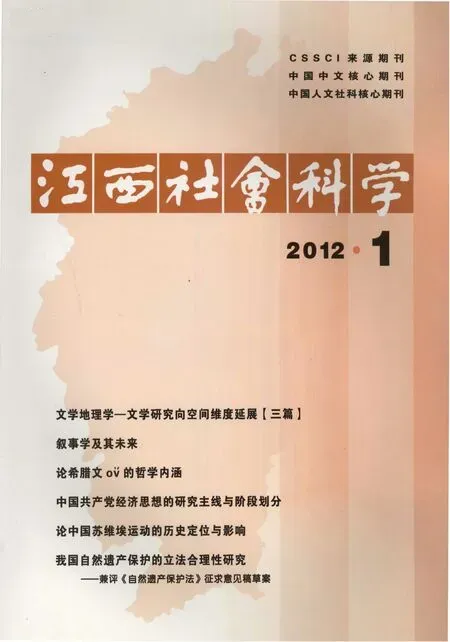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
——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汪 泓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
——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汪 泓
性情;格调;神韵;儒家诗学
对李梦阳诗学的解读是理解明代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格调论历来被视为李梦阳诗学的核心。围绕格调论,众说纷纭,难以明辨。笔者试以辩之。
一、“性情”与“格调”的“二难”问题
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历来是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格调”;一是“性情”。陈书录指出李梦阳的“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格调,二是情感。因而人们在对李梦阳的评价中往往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或侧重于从格调层面上观照李梦阳,认为他的理论批评与诗文创作以酷肖古人为最高目标,是彻底的拟古派;或侧重于情感的层面上观照李梦阳,认为他最根本的理论及创作是抒写真情,是明代文学新思潮萌芽的代表人物”[1](P199)。他认为李梦阳的理论批评与诗文创作成为格调与情感等矛盾的交织体,因而对李梦阳的评价出现了一种“二难”的现象。
朱易安以“格调论”为七子派的核心理论,认为:“李梦阳的诗学理论所探讨的,主要是性情、声律与法度的关系。”[2](P82)她的结论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格调的因素,性情和格调的冲突就展现得越来越尖锐。这使得李、何理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矛盾:在论述格调因素时,再三强调性情在汉魏古诗以及盛唐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以格调论述诗歌创作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则又无法顾及性情的因素。最终导致摹拟诗风的极度盛行。”陈文新则认为:前后七子“特别重视诗作为一种体裁的自身特征,热衷于从诗的文体规范入手来阐发对诗的一系列看法”[3](P143)。他的主要观点是:“七子派的尊汉魏(古体)、尊唐(近体),对‘情’的重视以及对诗的艺术表现的探讨,都是围绕着诗的文体规范这一中心来展开的。又它们所构成的主流派诗学是一个有机体系。在这个有机体系中,即使是‘情’,也是从属于对文体特征的探讨的。而这种探讨文体特征的热情又是来自对文体规范和艺术表达的重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七子派的追求:他们希望创造出像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那样的充分体现出诗的文体规范的作品。”[3](P148)他认为:“七子派论‘情’,是在格调说的整体布局中展开的。”这一评价突出了李梦阳对文体规范的重视。
上述几位学者有关李梦阳诗学的认识是深刻的,但问题在于,李梦阳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是否真正存在着格调与情感的矛盾?李梦阳的诗学是不是过分强调了的因素?体格声调是艺术理论的基本术语,一般的诗人都会论及,名家指导初学者学诗亦不可能回避格调之类的问题。难道诗人对体制规范、对艺术法则要闭口不谈才算是诗学吗?诗的文体规范能不包括对情因素的对论吗?原本就是一体的,为什么要特别分开,建立并列或从属的关系;李东阳与李梦阳都很重视文体规范,可是李梦阳“独讥其萎弱”,那么李梦阳与李东阳理论与创作不同处又何在?
特别提出的是,郭绍虞完成于1946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李梦阳诗论的评价很值得我们注意。以下为其主要观点的摘要:
论诗,空同并不专主盛唐,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则兼及初唐。这是他的诗学宗主。
空同论诗何尝不主情。
他所谓格调云者,原只是诗文之一端。他固不曾以主格调之故,而抹煞一切!
何况,所谓格乃是学古人之法,法不可废,则学古又何足病。
何况,学古之法,仍不妨碍其变化自得,则学古原是必经的步骤。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混高格与规矩而为一,则所谓规矩,乃是运用此规矩的标准格。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是标举第一义格,是正属情文并茂之作。因此,主格调与主情,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所谓“诗必盛唐”云云,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
何况,所谓第一义之格,不仅情文并茂,原是则法自然。[4](P161-168)
每一条结论,郭绍虞都有严密的论证,兹不赘述。总体而言,他是反对将格调与性情对立起来的。“即使说主情与主格调成为极端冲突,那也与空同之诗论不相妨碍……风雅异体,那么风可主情,雅颂不妨主格调。”[4]他对李梦阳诗学体系作的系统梳理,足可以解决评论李梦阳诗学的“二难”问题了。
不过,郭绍虞又指出,李梦阳“要于诗文方面复古,而不是道的方面复古。易言之,即偏重在文之形式复古,而不重文之内容复古。因此他的复古论终究偏在格调一方面”[4](P168)。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道的方面复古”与“文之内容复古”相关;而“文之内容复古”与“文之形式复古”又是不能剥离开来的。可见,郭绍虞在理论上最终还是把“性情”与“格调”对立起来了。
二、对儒家诗学传统的重倡
李梦阳诗学理论实际是自觉肩负着儒家“道的方面复古”的重任。当然,不是说他要在诗文中直接表达儒家的政治文化理想,而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诗学传统的重倡方面。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
李梦阳建构他的诗学体系时经常套用儒家诗论的经典名句,其《林公诗序》论诗歌的功能曰:
嗟乎,予于是知诗之观人也。……夫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声永而节,言弗暌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谛情、探调、研思,察气,以是观心,无癡人矣。[5](卷51)
诗,是人的一面镜子,通过诗,读者可以观人。诗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诗歌生成于情志与言、声、律相应相契合。此处套用了《诗大序》的程式,而言与志的关系更加清晰。李梦阳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状态,而不是诗艺本身。
情者,动乎遇者也……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故天下无不根之萌,君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5](卷51)
情,是主体人与客观的外物遇合而发生的感动。人的主观心态可以通过对外物的感受表现出来,诗就产生于诗人对外物所发生的感动。《鸣春集序》亦云:
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5](卷51)
物之有声是万物的共同特征,诗是人对内心情感的自然吟咏歌唱。李梦阳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对心物关系作了进一步阐释,较深刻地揭示了诗歌的生成原因。而儒家诗教是极重心物感应的,上述两段话很显然亦是对荀子《乐论》与《诗大序》及六朝以来陆机、刘勰等人“物感”说的进一步阐发。
与儒家诗学传统更为契合的是,李梦阳提倡抒发真情实感的“真诗”。作于嘉靖初年的《弘德集》自序引王叔武言曰:
何谓真诗?真诗就是能表达平民老百姓生活疾苦、喜怒哀怨的诗歌,《诗经》的风诗为其源头。真诗不存在于庙堂之上,“真诗乃在民间”。此处民间应该是针对庙堂、台阁而言。在话语空间上,民间相对于台阁更为自由,更无所顾忌。文人学士不敢抒发真情,不能为“自然之音”,因而他们的创作只是押韵之言,而非真诗。这是针对李东阳等人的台阁体而言。不敢抒发真情,自当“萎弱”,这不仅是体格的问题,它反映的是诗歌的内容、诗人的情感等问题。毫无疑问,李梦阳言下之意,他正处于一个“礼失”的时代,一个“《黍离》之后,《雅》《颂》微矣,作者变正靡达,音律罔谐,即有其篇,无所用之”的时代。[5](《论学》,卷66)所以,真正具有兴、观、群、怨之功用的“真诗”,只有往民间去寻找。
采访的最后,我问David是否想对自己在中国的粉丝说什么,他笑着回答:“我不确定我在中国是否有粉丝,但是我很高兴在拜访中国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想告诉他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享受日益丰富的国际葡萄酒,去世界各地寻找葡萄酒,亲自探索不一样的品酒体验吧!’中国的葡萄酒充满活力与热情,我希望它以这样的步伐持续前行与发展!”2019年,又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
对于民歌“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是否为真诗的疑问,李梦阳借王叔武之口回答:“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古者国异风,即其俗成声。今之俗即历胡,乃其曲乌得不胡也?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6](卷262)判断真诗的标准不在雅俗,而在于是否抒发真情,情之真的重要性超过了雅俗之辨。有不少论者往往把李梦阳诗学纳入雅俗之辨的体系中,这未尝不可,但与其论并非完全相符。
故而《诗经》的风人之诗正是李梦阳树立的最高典范。他还尤其强调继承《诗经》的比兴传统,又借王叔武之言曰:“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癢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有不比焉兴焉,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6](卷262)比兴手法的运用产生于抒情的需要。民歌是最富于比兴的,近世文人学士却大多背离了真诗的传统,比兴寡而直率多,而根本原因就在寡于情。
对于中唐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李梦阳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与徐氏论文书》曰:
夫诗,宣志而导和者也。故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简侈、浮孚之界分矣。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向使繁巧险靡之习诚贵于情质宛洽,而庄、简侈、浮孚意义殊无大高下,汉魏诸子不先为之耶?[5](卷62)
他重视儒家诗教“宣志导和”的作用,提倡汉魏的“情质宛洽”,反对中唐以后诗歌创作中由于单纯讲究技法而形成的“繁巧险靡之习”。把李梦阳归于纯粹重文章形式者,显然是片面的。
从创作而言,李梦阳“每欲自以求其真诗”,他有相当数量的诗歌是反映民生疾苦、为民代言的。一方面,李梦阳批判了居于庙堂之上的文学萎弱无生气的现象,力图挽救古文辞创作的衰颓现象;而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古文辞的创作已经难以达到新的高峰,而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形式正在民间酝酿形成。而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
由此可见,对现实的解构,李梦阳多从先秦两汉儒家传统获取力量;而李贽、袁宏道等则更多从狂禅中获取养料;对未来文学形式的建立,前者以恢复传统的面貌出现,后者则指向未来、指向发展,前者仍不越儒家诗学的范畴,后者则对儒家思想有所突破、甚至公开批判,然二者均意在求变。
李梦阳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精神。他论体制声调是在重倡儒家诗学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后七子论格调因为缺少了时代的批判精神,所以仅限于论体格声调,这正是李梦阳与后七子等人的区别,亦是他与李东阳等人的台阁体的不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然亦是李东阳、后七子等所不能企及的。因而,陈文新所谓“即使是‘情’,也是从属于对文体特征的探讨的”结论是不够全面的。李梦阳诗学体系并不存在所谓性情与格调的矛盾。李梦阳诗学有关“文之形式复古”与“文之内容复古”密不可分,而“文之内容复古”正体现了“道的方面复古”。
三、从体格声调到非色弗神
学界论李梦阳诗学一般是将其放置于格调派的系统中考察。这一观点又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呢?从提倡有感而发到对重视诗歌语言组织形式的规范再到提出总体的诗歌审美要求,李梦阳的诗学体系是自足圆满的。
李梦阳诗学重法、重体制规范,这是不可回避的。《驳何氏论文书》与《再与何氏书》更是体现他对法的重视,他非常强调遵循诗法的必要性,认为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基本规律。但他强调拟议以成其变化。其《徐功迪集序》曰:“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5](卷52)认为从事古文辞创作首先要对具体的文体规范进行学习,但要能灵活运用,不露痕迹。《答吴谨书》曰:“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终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迁乎?而足下以左氏、迁律人邪?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一笔:其不同特肥瘦、长扁、整流、疏密、劲温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笔之精也,乃其精则固无不同者。夫文亦尤是耳。谓迁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经,亦其象耳,仆不敢谓为然。”[5](卷62)《答周子书》曰:“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度音,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5](卷62)他所言体法格调更接近于刘勰所论“有常”之体与自然之“定势”。
但总体而言,在他看来,法、体、格制都是形而下的工具,诗歌创作应当实现特殊的审美追求。对《潜虬山人记》的解读是理解李梦阳诗学的关键所在。李梦阳诗学出发点是性情,而最后的落脚点,并不在“格”、“调”,而是审美视野中的“色”与“神”。其曰:
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5](卷48)
对于诗歌创作,他认为既要“情以发之”,又要达到体制上的种种要求,如体格古雅,声律圆转流畅等,不少论者的关注点仅限于此,然而文意的重点应当在末句。李梦阳指出理想的诗歌除上述七者之外,还有比体格、声调、字句更为重要的要素,这就是“色”与“神”。所谓色即兴象,神即风神、神韵,“非色弗神”指出诗歌创作总体上要达到一种声色流动、兴象风神具备的审美境界。在此,李梦阳是从审美的角度论诗歌的创作。其《论学》篇亦曰:“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5](卷66)很显然,李梦阳反对以理入诗,反对学宋诗,与他对比兴手法的重视有很大关系。这集中表现在《缶音序》中,其云: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朝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5](卷52)
所谓“主理而不主调”就是在诗歌中说理,以理语代替抒情,文辞艰涩而无声调之美,这样的诗如同徒有冠服的土偶木梗,毫无生气。真正的诗歌“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感触突发,情思流动”,而又含蓄蕴藉,声调和谐悠扬。这里再次强调了比兴艺术手法的重要性。他还批评了所谓“性气诗”,即理学家们借风云月露、鸢飞鱼跃等形象来宣扬理学思想的一种诗体。此类诗曾屡兴不止,明代中期的“陈庄体”在当时亦颇有市场。而“性气诗”与以理入诗的宋诗均违背了诗歌的基本特征。为纠时弊,李梦阳主张学唐调而不学宋诗。陈建华认为李梦阳“否定宋人诗文,原因是他讨厌理学”[7](P42),其理解有点偏差。李梦阳在《论学》篇固然说过“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5](卷65)的话,他亦反对理学对人的自然情欲的束缚,但反对宋诗的原因并不是否定理学本身,而在于反对在诗中过多的发议论、讲道理。正如陈国球所论:“宋诗的倾向既违反了李梦阳心目中的诗歌原理,则今人(当代人)有依此倾向写作的,当然要大力批判了。”[8](P41)
李何之辨,更多从体格声调一维论学诗,上引诸段则表明他对诗歌审美意境的重视,已经非常接近胡应麟由“体格声调”上升到“兴象风神”的诗学体系了。胡应麟下面一段话非常有名:
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畅;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岂容昏镜浊流,求睹二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9](内编卷5,P100)
这段话被不少学者视为明代诗学从格调论向神韵说转折的重要证明。持论者将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视为两种对立的风格,原因可能在于对格调涵义的理解偏于刚健豪放的风格,对兴象风神的理解归于含蓄蕴藉之神韵。在明清诗学风尚上,从重刚健雄阔到欣赏清新婉约之审美取向的相互取代的确客观存在。但此处不能作如是解;体格声调应指“有则可循”的文体规范要求,兴象风神是“无方可执”的审美趣味;前者为“水与镜”,后者为“月与花”;前者为实,后者为虚。胡应麟所论乃诗的形式与审美意蕴之关系。很显然,胡应麟论“兴象风神”,很大程度是受严羽诗学的影响,但亦不妨看作是对李梦阳诗学中“非色弗神”论的进一步阐释。李梦阳批评宋诗取法唐诗,不是因为李梦阳只崇尚盛唐雄阔气格,而是因为唐诗保留了中国诗学传统,体现了“言外之意”的诗歌审美理想,尽管李梦阳诗歌创作总体风格更接近于盛唐李杜纵横一派。
胡应麟有言:“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9](内编卷5,P100)其实并非李梦阳只讲法,只是胡应麟仅得一“法”字。其中原由亦正如郭绍虞所分析的,多少是受李何辩难的影响:“由这种思想体系上以建成的格调说,何至为后人诟病!然而竟为后人诟病者,则以与何大复往复辩难的关系。一般耳食者,习熟于大复所讥尺尺寸寸之语,遂亦妄谓空同此说为学古不化。”[4]尽管胡氏对李何辩难所下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站在李梦阳一边。
由此笔者以为,李梦阳诗学是否可以完全界定为格调派,是值得商榷的。明清诗学研究中格调、神韵流派之划分,当慎之又慎,不可仅从三言两语推断出来,而应全面系统地考察作家理论与创作的实际情况,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1]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陈伯海主编,朱易安撰.中国诗学史(明代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陈文新.明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5](明)李梦阳.空同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黄宗羲.明文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J].学术月刊,1986,(8).
[8]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9](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I206.2
A
1004-518X(2012)01-01100-06
汪 泓(1968—),本名汪群红,女,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明清诗文。(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诗歌辨体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05CZW012)、江西省高校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资助项目“中国文学批评与文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