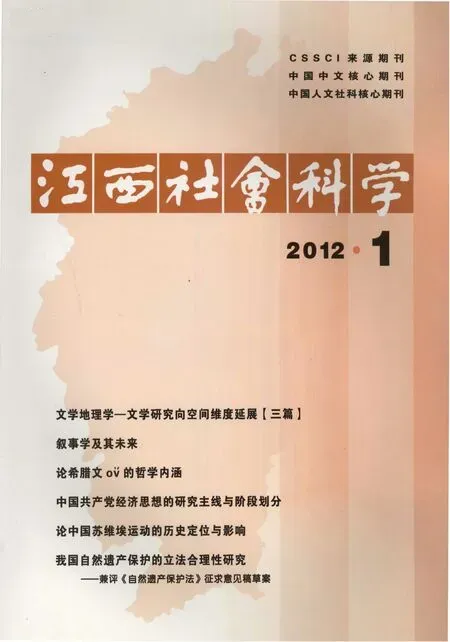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吴学丽 李秀金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吴学丽 李秀金
新历史主义;元历史;历史意识
一、历史意识回归中的历史叙事
传统上,文学与历史就有着难以隔绝的关系。“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中,它的一边是历史,另一边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于是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1](P12)传统的文学批评简直就等同于历史主义批评,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把文学看成一种历史现象,对文学文本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性的材料,以对文本本身进行说明。第二是对作家的研究。具体说是对作家生活和写作历史的研究。第三,传统的历史研究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系列历史和自然作用力的结果,也就是按照法国历史学家泰纳所归纳的“民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去看待文学。[2]这种传统的历史主义文学研究明显突出文学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伦理性),有着强大的话语力量和长久的学术影响。
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研究,以不同进路寻求“历史真实”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历史哲学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到培根、伏尔泰、卢梭,再到莱辛、康德、黑格尔,到施本格勒、汤恩比等,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研究绵延不绝。“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种证明包罗万象的法则或模式的企图,用这种模式来解释现存事物的(历史的)起源,同时探寻历史的目的或终结,或者至少想为重大事件的发生经过提供基本规律和一种宏大叙事。”[3](P11)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普遍做法就是用文学去印证社会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史的发展逻辑,构建起所谓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研究重视社会变动的律令和历史演变轨迹,其阐释方法有着浓厚的社会意识形态意味,构成传统文学文化研究的一条主线,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研究。到了20世纪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里,复杂的社会运作机制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巨大变迁,使得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视角并不能涵盖一切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个体人的精神现象。面对新的文化现实,传统单一性的社会学思维方式和叙事策略显得捉襟见肘,处境窘迫,宏大叙事研究的客观生活反映论受到诸多质疑而显现出机械偏执的一面;同时,宏大叙事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意识形态冲动为各种文学工具论大开方便之门,也引发了文学主体性的问题而广为诟病。正是在此点上,形形色色的分析哲学和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才有机可乘。
就文学研究而言,相对于传统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作为应对策略,力图从学科边界的角度重新明晰文学的内涵本质。所谓文学性,就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同时也指“文学与其他活动相区别”。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性”[4]。文学性成为区别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的概念,也成为颠覆传统社会学文学研究的基石与策略。借助这一概念,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基于对传统历史主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动,以注重语言分析和命题逻辑形式的历史分析哲学思潮成为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并广泛渗入诸人文学科之中,引导文学走向所谓的内部研究,催生了包括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这样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流派。这些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对传统文学研究进行了革命性颠覆,建立起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文学话语与文本策略。在此情况下,关注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传统文学研究不断受到诘难质疑,甚至被抛弃,最终由话语中心逐步退化为边缘性存在,基于反映论、目的论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常见的历史意识近乎沦为落后时代的代用语,无论是叙事修辞学还是结构主义,有关的形式主义文本研究话语对语境问题都普遍采取疏离、遗忘甚至是不言而喻的禁忌式态度。在文本研究的名义下,各种形式主义研究立足文学表达形式和修辞技巧,尽力把文学和社会历史分开,最终使文学研究完全脱离社会语境而走进自为的文本世界。
然而,在否定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有失偏颇的论断后,一些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很快走上了全面的内部研究,并在切割文本与语境的话语实践中把文学研究演变为对文本的无限解构和语词游戏,最终走向自我解构的陷阱。应该说,形式主义文本研究对确立文学的独立性、纠正传统历史主义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成效显著,但文本形式与语境或隐或现的关系总是形式主义文本研究难以长期绕过的障碍。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声音质疑形式主义文本分析的再现能力,并在历史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中质疑历史分析哲学的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正如反映论文学观走上极端沦为机械主义而受到诟病一样,文本研究的形式主义极端化引发新的质疑与反弹不可避免,新历史主义的机缘就此产生。在此背景下,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回应了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
当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历史主义,而是植根后现代文化语境,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孕育和演变,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理论等诸多话语理论,最终才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话语存在。新历史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代表性人物是哈佛大学的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大学的海登·怀特。格林布拉特致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研究,把文学史看成人的心灵自我塑造。他在1980年出版了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成为新历史主义文论兴起的发轫之作。1982年,他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撰写的导言中,正式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从此“新历史主义”开始为学界广为接受。1986年9月,格林布拉特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做了《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着力探讨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互文关系,提出以文化诗学研究替代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和格林布拉特偏重文学批评不同,海登·怀特进行了相当多的理论研究。他从历史哲学出发,关注19世纪欧洲历史,注重元史学的架构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提倡历史叙事诗学,尝试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中获取历史叙事的“真实”。怀特一系列创新性见解,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地位和基本的学术边界,他因此成为新历史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二、元历史维度中的历史叙事阐释
1973年,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正式提出“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他主张文学批评进行“历史转向”,回归“历史真实”,表现出一种历史回归意识。但这种回归显然是表象甚至是假象,因为新历史主义并没有兴趣讲述传统历史主义那些“真实”宏大叙事,这从新历史主义否定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举动可见一斑。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无意归附马克思主义,即使和马克思主义相关,那也是一种变节的关系。[5]新历史主义生成于后现代文化背景,正是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无论德里达还是福柯,都强调了语言的非确指性、文本的多义性、意义的无限延宕性、结构的非连续性和差异性。怀特大量采用后结构主义观念方法并以此对抗形式主义研究的历史虚无,但他所谓的历史真实并非仅指大写的单数“History”,而是小写的复数“histories”,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完整的历史进程,而是包含文化寓意和历史象征意味的片段式、碎片式存在。基于历史文化寓意的认识,怀特认为,对历史文本中零散的逸闻趣事、偶然事件等流于表象的“社会景观”有着被忽视的文化意味,对其历史内容的话语性阐释可以显示出文本与社会世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重构文本产生的“文化氛围”或“历史语境”。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历史学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的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6](P11)。
“叙事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中的一种,它是一种元代码(meta-code),一种人类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7](P2)怀特的这一认识意味深长——他用貌似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了叙事的构成要素、事件的情节编排之后却指向了文本历史性的探究 (即他所谓的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以此尝试重构历史的真实场景,确立宏大历史叙事被解构后的历史新维度——元历史哲学(Metahistory,又译作“元史学”)。怀特在《元史学》里通过对19世纪欧洲8位历史学家经典著作的分析,指出:“总的目的是要确定经典叙事中出现的有关历史过程的不同观念的相同特点。另一个目的是要确定当时的历史哲学家用以证明历史思维的不同理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将从最明显的方面看待历史著作,即是说,把历史著作看作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其目的是要成为过去各种结构和过程的一个模式或肖像,以便通过再现来说明他们究竟是什么。”[8](P370)怀特的史学研究最终回归到其元历史哲学观上。“一般而言,Metahistory(元历史)广义上指历史哲学,尤‘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别)。其方法论原则是力图建立一套阐释原则框架,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9]即认为任何具体的史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哲学观和方法论的框架中进行的,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阐释是一种叙述话语。在“元历史”的理论视野下,历史叙事不再是非连续性、偶然事件的展开,而是表现为“以叙事散文话语的语言结构”[8](P370)或者模式。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得到呈现。于是,在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语境与文本的诗性阐释中,对历史整体提供一个阐释原则框架——类似某种形式主义的“元历史叙事结构”,从而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历史过程或者规律,就成为“元历史”的基本内容和目的。
历史在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过去时间里发生的现实,如同时间的一维性,历史也被认为是客观真实不能被复制的。“历史在当时往往被描绘成单线程的、进步的,并且具有宏大叙事的形式。”[3](P7)在传统历史观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后,福柯提出:历史不过是一种真实性的幻想,它也是一种文本因而也是可以阐释的。这便为新历史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启发。海登·怀特没有直接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从历史文本性出发认为历史不可能想当然存在客观真实性,历史是在一些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一种编码式的叙述,从而使得大众能理解与接受。“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10](P499-500)这种文本表现为经过加工整理并经过意识形态化的完整性语言制品,其深层结构是融合了当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等文化寓意的话语结构。
怀特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历史书写的方式很多,但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传统的再现论反应论史观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律的单数历史的解释,属于历史编纂学范围。这种历史是一种“文化系统”,而社会制度和实践,其中包括政治在内,都被解释为这个系统的功能。所以,传统的建立在逻辑推理和历史必然律上的历史再现式书写,把当代人历史阅读过程变成了被动接受的过程,排除了当代人阐释历史的主动性,缺少当代人的精神对话关系因而并不真实。任何历史事实都需要经过某种语言的描绘才能得到解释,这决定了历史书写必然包含一种深层的诗意的语言结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11](P4),这个“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就是怀特所讲的“诗性预构”。历史叙事文本包含的深层语言结构性内容,其本质上通常是诗意的,尤其是语言上的。这种结构性内容充当了一种特定“历史”解释应该毫无批评便接受的范式。在所有的历史作品中,这种范式的作用是当作一种“元史学的”要素,它比专题文章或资料性报告有更大的理解空间。
三、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文化意味
新历史主义生成于后现代文化背景,其理论渊源并不是单线相传的理论承继关系,而是有着庞杂的多元化理论背景:“一是解构主义关于文本的论述;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理论;三是福柯有关权势与知识的关系的论说……最后则是Clifford Geertz的人类文化学。”[12]另外,加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启示也绝对不容忽视。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转向理论启发文学研究的转向,并不意味文学研究重新转向传统的社会史和作家生活史,而是要通向一种基于历史情境主义策略的当代性文化批评,力图在共时性的历史情景(语境)中重构历史文本的文化面目。情景主义的解释策略以对现象领域的描述为特色。“情境主义被认为是元理论反思的产物,它意味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既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也就是说,它们能够以一种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一般不会被认为的那种方式被赋予个性。”[13]在对历史阐释的情境主义叙述策略中,形成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结构,也形成了具体历史文本的叙事风格。怀特认为,新历史主义“要表现社会实在就需要把描述事件、行为、结构和过程与它们的历史情境之间存在的关系,作为它们要求真实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及要求现实主义的一个充分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其特点都是将它们在多少是叙事性的话语中为了种种社会现实的表现而提供的策略情境化,这在事实叙述中表现为历史主义,在虚构叙述中表现为现实主义”[13]。这就表明,对于新历史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不是要否定历史真实,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历史主义,而是要回归历史语境去触摸历史真实,是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
新历史主义认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4](P244)”的观点,认为文学史写作就是当代思想史的书写,文学历史文本也必然是一种当代话语形式,否则只能是对历史的编纂而不能成为一种“历史”,不能将“编年史”、“文学史”之类的著述和“文学史文本”等同。蒙特鲁斯说:“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我们所重构的历史(histories),都是我们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做的文本建构。”[15](P257)对历史文本的阐释解读伴随着当代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带有相当程度的当代性和主观性,夹杂了诸多意识形态逻辑和个体判断,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本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并不是随意拼贴杜撰的叙事游戏,而是植根于“自己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由“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做出的。因此,表面上看来个性化的历史文本实际包含了一个时代对历史阐释的共同理解,是一个时代“视阈融合”的产物,体现着一种当代历史精神。这种历史主义精神是意识形态化、诗化的精神,是一种更抽象更能与当代人对话交流的当代精神。
“由于文学理论习惯于把文本当作一个整体 (即小说),因而期待在这里能够发现某些有助于历史哲学家分析历史文本的理智工具,似乎是合理的。”[16](P5)在历史叙事中,历史既然要经过叙述者的话语建构,具有无法回避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因此,历史话语总是具有虚构性。面对历史语境中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历史文本的阐释必然是主客观一体的话语实践,其本身既是对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的阐释,也是人们对历史事件的主观选择和意识形态意蕴的呈现和描述,离不开比喻、转义等语言学内容。在此结构中,传统的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历史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性的叙事,那么“客观的历史”就不再“客观”,其与“虚构”的文学差异何在呢?如此,新历史主义颠覆了传统宏大叙事的历史客观性,也解构了遗忘历史语境的形式主义所谓科学的“文学性”研究。历史与文学的边界消失了,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历史客观性也就不再存在。这就产生了“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这样互文式话语叙事结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表面看来不同,但实际上呈现出异质同构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互文式结构表明了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构塑的张力,显示了任何叙事都难以脱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内涵。新历史主义由此建立起独特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文本。
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界发生的重要嬗变之一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兴起。新历史主义来源于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历史问题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难以回避的维度重新引起人们关注。在追问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中,新历史主义开始重新解读文学史和文化史,“尝试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与一种历史地灌注的、对于社会科学知识产生模式与它的社会文化情境之间获得的关系而具有的敏感性结合起来”[13]。新历史主义疏离了极端形式主义文本研究,在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中探究语境研究的当代意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推动着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历史主义逐渐形成很有声势的文学批评流派,成为纠正形式主义文本研究偏执的重要力量。
[1]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盛宁.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1993,(5).
[3](加)斯威特.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M].魏小巍,朱舫,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加)马克·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5]Richard Bernstein:It's Back to the Blackboard for Literary Criticism,THE NEW YORK TIMES,Feb.19,1991.
[6](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7](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
[8](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3).
[10](美)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A].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11]He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y Imagination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12]张宽.后现代的小时尚[J].读书,1994,(9).
[13](美)海登.怀特.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情景主义策略[J].黄红霞,译.东南学术,2005,(3).
[14](美)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5]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荷)F.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M].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I0
A
1004-518X(2012)01-0034-05
吴学丽(1971—),女,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化、叙事学;李秀金(1970—),男,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化、叙事学。(山东济南 250103)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