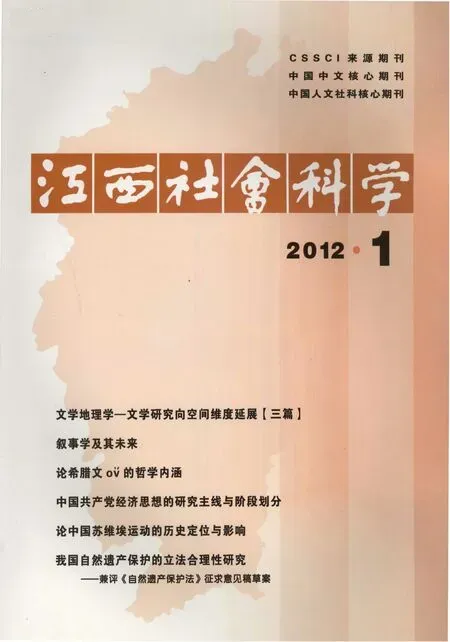论叙事反讽
■方 英
论叙事反讽
■方 英
叙事反讽;否定性;叙事对照;叙事范畴
反讽(irony)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从古希腊至今,反讽的意义不断演变,对其运用和研究的领域也从最初的修辞学延伸到文学、美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反讽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米克曾指出,“反讽是一种颇具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的现象”[1](P1),并且,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反讽现象。就文学领域而言,反讽与叙事的关系最为紧密。无论是情境反讽、戏剧反讽、事件反讽,还是浪漫反讽,或者是颇具哲学意味的宇宙反讽,往往都具有叙事性,都需要通过叙事实现反讽,又都可被视为一种叙事策略,甚至是叙事作品的创作原则。而米兰·昆德拉则断言:“从定义上来讲,小说就是讽刺(ironie)的艺术。”[2](P158)
然而,将反讽与叙事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却不够深入和系统。现有的成果大多集中于对作品中的反讽叙事和反讽技巧的研究。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领域,如韦恩·布斯、里蒙-凯南、J.希利斯·米勒、华莱士·马丁、詹姆斯·费伦、蒲安迪、申丹等学者都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过反讽的特征,但他们的相关论述都是分散的。
本文将提出“叙事反讽”概念,深入探讨叙事与反讽的关系以及叙事反讽的特征与价值。
一
经过漫长的发展,反讽不仅含义越来越丰富,而且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苏格拉底式的反讽、言语反讽、行为反讽、结构反讽、戏剧反讽、情境反讽、事件反讽、传统反讽、喜剧反讽、悲剧反讽,等等。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称,想要做出恰当的解释和分类都是十分困难的。某种程度上,对反讽的命名和分类无异于制造混乱。因为任何命名和分类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武断性,且必然落入圈定的冲动和现象的无限性的矛盾之中。那么,为何要提出“叙事反讽”的概念?
现象虽然是无限的,为了研究的方便,对对象范围的限定却是必要的。同时,提出这个概念也是现实的需要。有这样一类反讽,主要关涉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由叙事对照构成,可用叙事学相关理论阐释、说明和分析。同时,这类反讽也是叙事手段,与叙事作品意义的实现密不可分。为了对这类反讽做深入的探析,对叙事和反讽的关系做更深度的研究,本文大胆提出“叙事反讽”的概念。“叙事反讽”四个字正好涉及文学的几大关系。“叙”即讲述的动态行为,是对“事”的艺术干扰,属话语层面。“事”即相对静态的故事,是被叙的内容。“事”与“叙”是一对辩证关系,有什么样的“叙”,便有了什么样的“事”。“叙”和“事”的合适性决定了叙事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讽”是实现“合适性”的一种手段。“叙事”则限定了“反讽”的类别和特征。“反”,涉及文本、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与审美距离、阅读延宕、文本时空等待密切相关。而“讽”则既是反讽发送者的态度与立场,又与受者及读者有关,涉及意义的接受和实现。因此,从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意义等角度全面论述作为叙事模式或策略的反讽,应该有一定研究价值。
那么,“叙事反讽”与“反讽叙事”有何区别?笔者认为:反讽叙事的中心词是“叙事”,因而这是叙事的一种类型或风格,往往将一部作品或某位作家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将这个整体的叙事风格视为反讽类型。反讽叙事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某部作品、某种风格、某位作家的创作。而“叙事反讽”的中心词是“反讽”。叙事反讽主要由叙事策略和技巧构成。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反讽意义的叙事手段,并涉及叙事策略与反讽的关系、反讽如何产生、是否有共同的模式和结构、叙事反讽的特征、与其他反讽的异同等问题。
因此,对叙事反讽的研究以叙事学的概念和范畴为参照系,以具有反讽意义的叙事片段为考察对象,以探究反讽的形成机制、功能、价值等为研究目的。“丹麦语言学家叶耳姆斯也夫提出了形式对实质、表达对内容这两个二分法所构成的四层次图表”,查特曼则借用这个图表将叙事文分成四个层次:表达的实质、表达的形式、内容的实质、内容的形式。“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叙事文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具体地说,叙事文中的各种叙述方法和原称之为内容的情节、人物、环境均属于叙事文形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3](P13)本文将借鉴上述思想来限定叙事反讽的研究范围。因此,叙事反讽既涉及叙述的方式,也涉及叙述的内容。具体说来,叙事反讽可以涉及以下范畴:元叙述、不可靠叙述、戏仿、自由间接引语、视角越界、天真/无知的人物、出乎意料的事件、事件的对照、描写的对照、叙事表达与叙事内容的不协调,等等。
二
米克指出了反讽的几大要素:无知、事实和表象的对照、喜剧因素、超然因素、美学因素。[1](P36-71)本文不打算做这样的罗列,只准备讨论叙事反讽的一项必要的因素——叙事对照。不过,首先要讨论反讽的本质。笔者认为:反讽的本质在于“否定性”,由矛盾元素构成的叙事对照则是实现否定性的必要因素。在叙事反讽中,叙事对照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而否定性则是其本质与内核。
否定性是几乎所有反讽的本质所在。苏格拉底反讽的特征是“佯装”,而其实质则是对对手的自以为是的否定,是以“无知”否定人们面对世界自以为“有知”,更是哲人发现人类生存之悖谬而对人性自负的否定。言语反讽上是实际意义对字面意义的否定。情境反讽强调事件与情境之间的矛盾悖逆,事件反讽特指人物的期望或计划与结果相反,戏剧反讽指剧中人物的无知,宇宙反讽则强调无处不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和荒谬。这诸多反讽,虽然形式和所指不同,本质上都是对表象的否定,对真相的反思,对秩序、绝对、统一、整体等“终极话语”的否定。反讽是“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4](P60),是两者的互相限制和否定,从而实现自我主体性对绝对自由和无限完善的追求。
克尔恺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多次提到反讽意味着虚空、绝对的自由、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一切都应归结于否定性。“新批评”认为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将其视为诗歌的结构原则。[5](P377-395)然而,新批评却被指责为对反讽泛化,混淆了反讽与悖论的意义。因此,反讽的本质是否定性。不仅是真相对表象的否定,而且常常是多种因素的互相否定,是不断运动的否定,是对确定性和终极话语的否定。这里的否定性包含反思性与批判性,主张主体性。否定不仅在于破坏,而且在于创造,既是解构的,又是建构的。反讽所建构的意义是由对照构成的,是对原先单一信息否定之后的反思与创造。
对照作为反讽的基本要素,虽得到了普遍认同。但并不是所有的对照都是反讽。反讽中的对照是矛盾因素的对比,由此产生一方对一方、甚至双方之间的相互否定,并由此引出“故事下的故事”。而普通的对照只是差异因素的并置,缺乏否定性。这种对照十分常见,却并不是反讽。
因此,对叙事反讽的讨论,焦点是具有否定精神的叙事对照。与许多其他反讽不同的是,叙事反讽具有多重对照和否定以及更为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三
在上面的阐述中,笔者发现,叙事学的许多范畴与叙事反讽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有些范畴甚至必然具有反讽意义,可被视为叙事反讽。笔者将针对以下几个范畴展开分析:不可靠叙述、自由间接引语,事件之间的对照。
首先讨论不可靠叙述。针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有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和综合的方法。[6](P133)本文的讨论采用修辞方法的观点。修辞方法的创立者韦恩·布斯提出:如果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 (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叙述者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7](P159)布斯指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的叙述或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7](P300)
为何不可靠叙述容易产生反讽效果?此处以《红楼梦》的一个片段为例展开分析。第三十回中,王夫人午睡时听见宝玉与金钏儿调笑,抽了金钏儿一耳光,且不顾她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接着,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厚仁慈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去了。”[8](P130)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在肯定王夫人的人品德行。但是,根据故事的叙述,我们知道,此事是宝玉挑头,而王夫人当时在假寐,完全知道事情的经过,她却不发慈悲,严惩金钏儿。从后文中我们还得知,金钏儿因为此事而投井自杀。由此我们完全能推断出,叙述者对王夫人的判断和评价是错误的,其叙述是不可靠的。此处的不可靠叙述是一种极具批判力量的叙事反讽。反讽首先源自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对照。当读者发现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即作品的)的规范不一致,读者必然会选择相信隐含作者。面对这种不一致,读者会以隐含作者的价值规范来否定叙述者对王夫人的判断和评价,并会思考为何会产生这种不一致。其实,不可靠叙述是相对可靠叙述而言的。作品和隐含作者的规范是由其他部分的可靠叙述建构的。因此,这里又包含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的对照,可靠的部分对不可靠的部分形成否定的力量。读者会进一步思考,为何在这里采用不可靠叙述?作者为何不直接评价王夫人?作者采用不可靠叙述仅仅是为了批评这件事?或者仅仅是为了讽刺王夫人的行为?经过对几重叙事对照的分析,读者会发现,作者反讽的对象不仅是事情和人,而更是针对王夫人的“伪善”,针对当时社会对王夫人持肯定评价的一整套道德规范——某种程度上,叙述者的评价模仿了当时社会的评价标准,针对封建礼教“伪善”而“吃人”的本质。读者的深层次解读否定了之前的判断。至此,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不一致这一表层的对照演变成故事的深层意义与表层意义的对照,水平方向的否定也演变成垂直方向的否定。这里的“演变”是从读者解读的角度而言,而且是逻辑上的。就作者的写作和文本而言,这几重对照和否定是同时产生并存在于文本中的。当然,虽然包含多重否定,被否定的因素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以对照的方式存在,从而构成小说意义的丰富性,增添了小说曲隐、繁复、多元、整一的审美效果。
在叙事学范畴中,自由间接引语与反讽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自由间接引语常常也是一种叙事反讽。里蒙-凯南认为自由间接引语能帮助读者推断隐含作者对人物的态度。里蒙-凯南还指出其双重效果:一方面,一个不同于人物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会产生具有反讽意味的疏离性;另一方面,人物语言和经历染上了叙述者话语的色彩,可能会使读者对人物产生认同感。而当引语产生歧义时,读者便无法在反讽与认同之间做出抉择。[9](P115)笔者认为:里蒙-凯南所提到的双重效果——疏离性和认同感能进一步产生反讽效果,因为这两种态度的矛盾对照构成了相互否定和相互包容,并产生了不同于任何一方的新的意义,从而构成了深层意义对表面矛盾的否定。希利斯·米勒在《解读叙事》中以一章的内容分析了间接引语与反讽的关系。米勒在此处未区分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但此章的大部分分析是关于自由间接引语的。在对《养老院院长》中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中,米勒指出:叙述者的语言“通过间接引语的方式来反讽性地模仿人物的语言……叙述者的生存有赖于人物,人物的生存又有赖于叙述者,这种互为依赖的关系处于永恒的震荡之中……体现出反讽对于对话表层稳定性的颠覆”[10](P163)。其实,在米勒看来,所有的间接引语都具有反讽意义,因为间接引语是对原来话语的反讽性模仿。在这种模仿中,真实的意义摇摆不定,任何中心都被悬置,而反讽就是对中心意义的悬置。[10](P155-172)虽然米勒的“反讽”具有解构主义的意味,但他关于(自由)间接引语对原来话语的反讽性模仿的论点十分深刻。关于自由间接引语和反讽的关系,申丹从文体学的角度做过系统的分析。申丹认为:自由间接引语能有效地表达讥讽的效果,因为它“容易跟叙述描写混合在一起,在客观可靠的叙述描写的反衬下”,能增强文本的反讽效果。而从读者的角度看,自由间接引语中的第三人称与过去时“具有疏远的效果,这样使读者能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充分品味人物话语中的荒唐成分以及叙述者的讥讽语气”[11](P342-343)。
笔者认为:运用自由间接引语时所形成的多重对照是产生反讽意义的主要因素。现以《无名的裘德》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展开分析。这个片段描述了裘德矛盾的内心活动。朝着自己的求学目标和人生理想进发的裘德在途中受到亚拉贝拉的诱惑,为自己寻找种种理由去赴约会:
然而,他不是答应过要去找她的吗?他的的确确是答应过她的呀!她准会待在家里等他,可怜的姑娘,为了他而浪费整个下午的时间。撇开守不守约的问题不说,单说姑娘本身,她不是也有某些令人着迷的地方吗?他可不该对她背信弃义啊。……长话短说。裘德当时仿佛感觉到一只力量无穷的巨手,硬拽住他往一个方向去。这只巨手发出的力量跟过去推动他前进的力量相比,无论是精神还是影响方面,都找不到半点共同之处。[12](P48-49)
文中的前九句是描述裘德内心话语的自由间接引语。引文中的反意疑问句、感叹句、“可怜的姑娘”一词都体现了人物话语的色彩,似乎是人物在内心自言自语。而第三人称的运用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又酷似叙述者的声音,似乎是叙述者对人物的辩护。这几句生动地展示了裘德受到肉欲诱惑而远离自己远大目标的精神变化。在此,叙述者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似乎对裘德满怀同情,又好像在略带嘲讽地戏仿裘德的内心活动。而从“长话短说”开始,则是叙述者客观可靠的总结性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叙述者对裘德内心变化所持的否定与批评的态度。这样,叙述者口吻的前后反差突出了引语中的荒唐成分,叙述者貌似赞同实则否定的态度又与人物的态度形成对照,从而达到了讥讽与批评的效果。当然,自由间接引语的反讽意义不止于此。这个片段包含了理想与欲望、理性与感性、崇高与世俗、计划与现实、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等一系列足以构成反讽的矛盾对照。这个片段也奠定了裘德一生的悲剧,体现了人的命运与宇宙安排之间的悲剧性反讽。可见,叙事反讽的运用,赋予文本以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令文本的解读走向了开放与多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存在着叙述者声音与人物声音的对照。这两者的对照形成既互相否定、又悖逆共存的矛盾结构。很多时候,无法区分引语中是叙述者的声音还是人物的声音,或者哪部分是叙述者的,哪部分是人物的。自由间接引语常常是两者声音的混合。这两者声音的对照与另一种对照相关:自由间接引语和叙述者话语(常常以“言语行为叙述体”的形式出现)的对照。引语中叙述者的态度模棱两可,与叙述者话语中相对客观的态度形成对照。透过这一层对照能发现又一层对照和否定:叙述者对人物的表面态度与实际态度。这些对照又产生另一种对照:引语所表达的字面意与对照所产生的深层次意义的对照。这种垂直对照的两端依然是互相否定又互相包容的关系。反讽正是滋生于这多重的对照与否定,反讽的意义也来源于这多元的否定与包容。
以上分析的两个概念属于叙事文的“表达的形式”。下面,将分析有关“内容的形式”的一种反讽——事件之间的对照。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分析了《金瓶梅》作者以反讽削弱性描写带给读者的愉悦感,其中一种手法就是反差性事件的对照。他列举了很多这样的对照,并进一步指出,这样“刻意把性和痛苦糅合在一起”的反讽手法,有着深刻的寓意:既表现了“尘世一切虚幻的幻想——尤其是情俗淫乐——的破灭”,又“使我们感到,这种说教听起来似乎又十分的空洞乏力”。[13](P135-137)笔者发现,小说中的事件对照往往具有反讽效果。因而,笔者将其视为叙事反讽的一类。
例如在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小说一开头就提到马拉德先生的意外身亡。心脏不好的马拉德夫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未像其他妇女那样无法承受,而是大哭一场之后,把自己单独关进房间。在房间独处的一个小时里,马夫人逐渐意识到自己从此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因而兴奋不已。就在她眼中带着“胜利的狂喜”下楼的时候,她的丈夫活着回来了,她却心脏病突发身亡。医生的诊断是她“死于致命的欢欣”。申丹在《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一文中从标题、遣词造句、人物内心描写、人物形象描写、结局的出乎意料等方面分析了小说的多重反讽,并指出反讽的主要对象是马夫人所幻想的自由。[14](P102-113)笔者发现:这个故事还存在事件对照所产生的反讽。小说中有四类事件层面的对照。第一,故事的开头是关于丈夫死亡的虚假消息,故事的结尾是妻子真正的死亡,这两个事件——假死与真死——形成强烈的对照。第二,丈夫“死亡”(小说中的人物都认为这是事实)与妻子“复活”(精神复苏)之间的对照。第三,丈夫“复活”(在小说人物看来他是死而复活)与妻子死亡之间的对照。第四,如果借用布雷蒙的“叙事序列”的概念,整个故事的核心事件主要构成两个并列的复杂序列。一个序列代表“改善”:丈夫“死亡”→妻子“复活”;另一个序列代表“恶化”:丈夫“复活”→妻子死亡。这两个序列的鲜明反差构成了反讽对照。这四类对照具有深刻的否定精神。前三类中“假死”与“真死”、“死亡”与“复活”的对照形成不断运动的互相否定,令读者无法确定,“死”与“活”,何为真,何为假。最后,“死”的活了,“活”的死了,“真”的变成了假的,“假”的却变成了真的。原先对照的两级依然存在,只是在互相否定中变换了位置。第四类对照超出了现实生活的常见逻辑。无论是妻子因丈夫死亡而“复活”,还是妻子因丈夫“复活”而死亡,都令人难以接受,挑战着人们的情感限度和心理限度,而这两个序列之间的对照则否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秩序感和规律感,令读者在出乎意料中反思小说的深层次意义。小说的四类对照将读者的解读引向表层对照下面的“故事”:丈夫的死亡为何会导致妻子的精神复苏?丈夫的归来为何会导致妻子猝死?生与死之间的快速转换传达了怎样的意义?小说中包含了对人生、对世界怎样的理解?不同的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正是叙事反讽的开放性和含混性。但是,因为马夫人是小说的主人公,几类对照中的事件主要是关于她的,事件对照对马夫人的反讽是明显的。另外,读者还能感到作者对人生、对命运的反讽和不满。
四
叙事反讽将反讽编织在故事的展开之中,通过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实现对叙述对象的反讽,既蕴含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性,又引发读者的反思和参与,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多元化和美学意义的升华。
叙事反讽的否定性精神凸显了创作的主体性。作者在运用反讽时,体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作者掌握真相,运用技巧,制造反讽,与理想的读者合谋。作者通过反讽实现对世界荒谬性的展示,对生存之境的反思,对人生百态的嘲讽。
叙事反讽中的多重对照与否定赋予作品以多元性、含混性、开放性,能实现对无法言说之意的言说。其否定精神与创作主体性有利于实现作品的价值诉求、伦理功能和意识形态的表达。其矛盾对照式的平衡结构和在表层之下言说真相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品格。
叙事反讽通过否定,通过推翻表象的言说,引发读者的反思和对意义建构的积极参与。同时,由于文本意义深藏于反讽的多重对照和否定之中,叙事反讽对读者的阅读提出了挑战,对读者的叙事判断具有极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发现,较之其他反讽,叙事反讽具有丰富的内涵与价值:既凸显作者的主体性,又召唤读者的多重判断;既言说难以言说之意,又隐含价值诉求;既涉及意识形态,又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因此,叙事反讽作为反讽的一个类别,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1](美)D.C.米克.论反讽[M].周发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德)F.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M].李伯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5]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6]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4).
[7]Wayne.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8]曹雪芹.红楼梦[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
[9]Shlomith Ri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New York:Routledge Talor&Francis Group,2002.
[10](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英)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秭佩,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13](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申丹.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J].外国文学评论, 2004,(1).
叙事与反讽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因此,本文提出“叙事反讽”概念。叙事反讽是叙事层面的反讽,主要涉及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同时,这类反讽也是叙事手段,与叙事作品意义的实现密不可分。反讽的本质在于否定性,由矛盾因素的对照实现。在叙事反讽中,水平轴与垂直轴的多层次叙事对照和“否定”实现了反讽的意义。叙事学的许多范畴具有反讽意义,可被视为叙事反讽。叙事反讽具有丰富的意义:既凸显作者的主体性,又召唤读者的多重判断;既言说难以言说之意,又隐含价值诉求;既涉及意识形态,又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I0
A
1004-518X(2012)01-0039-05
方 英(1977—),女,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英美文学。(浙江宁波 315212)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