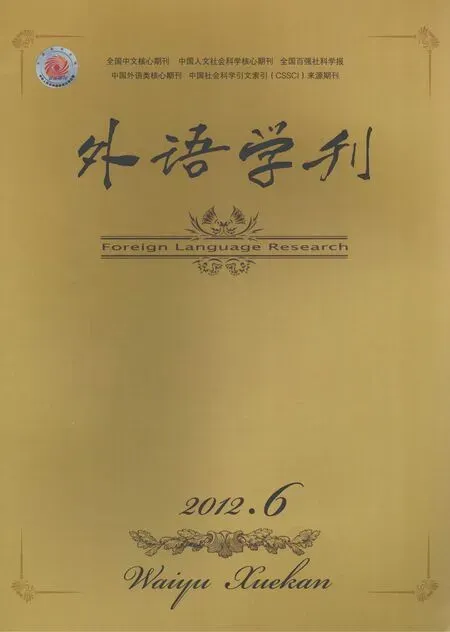对关联理论缺陷的微观性批评
孟建钢
(湖南科技大学,湘潭411201)
1 引言
自1986年关联理论问世后,该理论一直饱受争议,褒贬不一。在肯定关联理论的同时,不少人也对关联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批评(乔娜2010,胡旭辉2008,何奕娇2007,Hu Xu-hui 2007,熊学亮 2005,何自然 吴亚欣 2004,王建国2003,徐盛桓2002,姜望琪2001,刘国辉1999,何自然 冉永平1998,曲卫国1993)。这些批评基本上是从宏观上展开的,大都显得过于宽泛,有些批评或不够客观、或过于偏激,或因误解所致。对此,本文将在微观上对关联理论的缺陷进行分析。因为只有从微观上对关联理论的缺陷进行分析,批评才会更加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笔者将针对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以下简称《关联性》)存在的一些代表性缺陷进行剖析①。
2 一些重要定义的问题
2.1 关联性定义问题
综观《关联性》全书,作者始终没有对“关联性”在性质上给出一个定义,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在一本专门论述“关联性”的专著中,如果不首先在性质上给出定义,就无法从其他层面进行深入的论述和说明。虽然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书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解释:“我们并不力图给普通的英语单词‘关联性’下定义。‘关联性’是一个模糊性术语……在人类每一种语言中它都没有一个精确的解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对英语单词‘关联性’作一个合适的语义分析会解释清楚一个科学心理学的概念”(Sperber&Wilson 2001:119)。从这段说明中,可以看出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其实也意识到应该在性质上给关联性下一个定义,但却知难而退了。他们认为对“关联性”这个词进行语义分析无助于解释一个科学心理学的概念,但这种观点其实跟他们随后提出的看法是相矛盾的:“不过,我们的确认为科学心理学需要一个很接近关联性一般语言概念的概念,换言之,我们认为有一种重要的心理特性——一种心智过程的特性——关联性一般概念大致近似于该特性,将其也称为关联性(在此是技术性地使用该术语)很合适。我们力图要描述这个特性:将关联性作为一个有用的理论概念来定义”(Sperber&Wilson 2001:119)。显然,后面这段话表明《关联性》作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性质上给“关联性”下一个定义,但为此又过于勉强而不可为,因而选择放弃或者说选择避重就轻。
这里,所谓的“避重就轻”指的是,虽然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最终没有在性质上给“关联性”下定义,但还是分别从分类和比较的视角给出了定义。我们先看分类性定义:“如果且只要一个假设在一个语境中具有某种语境效果,那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22)。但他们觉得这个定义不够全面,因为关联性是一个程度问题,但该定义对此未能说明;另外,该定义将关联性定义为假设和语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却丝毫没有说明语境是怎样的问题,只是定义了一个形式特征,没有描述该特征跟心理现实性之间的关系。(Sperber&Wilson 2001:123)因此,他们认为关联性更应该从比较视角来加以定义,比较性概念可通过程度条件来很好地加以阐释,这样又提出了他们更加满意的比较性定义:“程度条件1:只要一个假设在一个语境取得了大的语境效果,那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程度条件2:只要在一个语境中处理一个假设所需的努力小,那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25)。
他们认为,这个比较性定义暗含了分类性定义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因此该定义不需要单独加以阐述(Sperber& Wilson 2001:125)。但实际上,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自认为很满意的这个比较性关联定义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该定义根本没有考虑以下问题:(1)如果一个假设在一个语境取得了较小或一定的语境效果,那么难道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不具有关联性了吗?(2)如果在一个语境中处理一个假设所需要的努力很大,那么该假设难道在该语境中就不具有关联性或关联性不大吗?因此,这个关联性比较性定义应该包括4个而不是2个程度条件,或者改为:程度条件1:只要一个假设在一个语境中取得了语境效果,那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程度条件2:只要在一个语境中处理一个假设付出大或小的努力且都可以取得语境效果,那么该假设在该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因此,一方面,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没有从性质上给关联性下一个定义;另一方面,他们退而求其次也未能给出一个较全面、较有解释力的比较性定义。
2.2 明示-推理交际定义问题
我们先看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给出的明示-推理交际定义:“交际者②生成一个刺激,它使得交际者意想通过该刺激将一个假设集明显于或更明显于听者这一点互明于交际者和听者”(Sperber&Wilson 2001:63)。单从这个定义看,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只是说明了交际过程仅是一个明示过程,却没有包括推理,虽然还是暗含了推理成分,因而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简单和片面。由于定义的含糊不清,读者在学习关联理论时就需要不断加入自己的阐释。《关联性》第一章的第十节标题是“明示-推理交际”,即本节应该分别详细论述明示和推理问题,但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只是详细说明了明示性质和过程,却完全不涉及推理,因而这个定义与其说是明示-推理交际定义,还不如说是明示交际定义。再则,这个定义给出的地方欠妥,作者应该在第十节就给出该定义,但直到第十二节“交际意图”才给出定义,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要说明清楚什么是明示-交际,首先必须先讲清楚什么是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否则读者在学习关联理论中极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或误解。根据关联理论,明示是说话者同时向听话者传递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但结果却是很多读者误认为明示仅是向听话者传递交际意图,进而将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混为一谈。虽然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第二章专门对推理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证,但之前至少就明示-推理交际定义而言,作者在解释和排序上是考虑欠妥的。
关联理论跟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格莱斯理论只注重对暗含(implicatures)的研究,而忽略对明说(explicatures)的研究;而关联理论则同时注重对暗含和明说的研究。(何自然1995)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明确提出,人类交际的模式就是明示-推理交际,但如果根据他们给出的明示-推理交际定义,不难看出这个定义实际上只涉及到人类的隐性交际,并没有包括显性交际。虽然明示是向听话者同时传递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但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分别由交际者和听话者来完成(Sperber&Wilson 2001:62),那么显然,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主观上仍然只注重研究人类的隐性交际。对此,他们自己也坦然表示承认:“我们没有将一个假设看成要么被表达、要么没有被表达的对象,而是拥有一个假设集,其中的若干假设由于交际而不同程度地变得明显或更明显,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交际本身看成一个程度的问题”(Sperber&Wilson 2001:59)。他们还说:“在言语交际中,显性内容和隐性输入之间的区别一直被看成仅仅是交际方式的区别而非交际内容的区别,而且暗含和词语非刻意形式的模糊性因一直被理想化而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根据假设的明显性来解释信息意图,这样不必加以要么很精确要么很模糊的描述,就可纠正这些被歪曲的观点”(Sperber&Wilson 2001:60)。据此,不难看出,明示-推理交际定义还不能上升到人类交际模式的高度,仅仅能说明人类隐性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
3 对关联性的评定问题
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认为,“关联性的评定,犹如生产率的评定一样,是一个将输出跟输入相平衡的问题:这里就是语境效果跟处理努力之间的问题……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假设所需的处理努力越小,该假设的关联性也就越大”(Sperber&Wilson 2001:125)。在此,他们混淆了显性关联和隐性关联,他们的结论其实只针对显性关联,而忽视了隐性关联。以幽默为例,越高级的幽默,表达起来越要婉转。婉转就意味着听话者要想实现话语的信息意图,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处理努力从而实现最佳关联,以取得更大的语境效果(幽默效果),这就是听话者在放大一个假设所固有的关联性。幽默效果的关键在于联想和婉转,如果我们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内容,不但不会取得幽默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听话者在处理直截了当表达的假设时投入的处理努力的确要小了许多,但由于没有取得应有的语境效果,我们能说这个假设关联性大吗?再以诗为例,诗的美在于一个“隐”字,正是诗的“隐”给了读者无穷的遐想,从而得到美的享受。如果用直白的方式写诗,则诗的意境美往往会丧失殆尽。幽默中的婉转和诗中的“隐”都属于弱式交际,“在这种弱式交际中,交际者期待将接受者的想法转向某一个方向(信息意图)”(Sperber&Wilson 2001:59)。我们再看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自己的看法:“言语交际中的隐性内容一般表达得都弱:听话人通过形成几个大致相似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假设,经常可以实现说话人的部分信息意图。在言语交际中,显性内容和隐性输入之间的区别一直被看成仅仅是交际方式的区别,而非交际内容的区别”(Sperber&Wilson 2001:60)。显然,他们自己的这段话跟他们前面的结论是相矛盾的。
另外,多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是否应该对关联性进行量化评定一直存在很大争议。笔者的看法是,如果关联理论要上升到更大的实用高度,就必须实现对关联性进行量化评定,否则,关联理论更多就是纸上谈兵。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认为对假设的力度进行量化是不可能的:“人类可能有一个进行计算和表征假设力度的系统,这种计算和表征既是完全无意识的,又要比反映在假设的有意识直觉中的任何举动都要复杂得多。我们因此否定这种可能性:当一个人不能有意识地评估证实值时,他可能会无意识地通过用由逻辑学家提出的那种数字计算来这样做。我们得出一个更一般性的结论,一个假设的力度不可能被量化评估”(Sperber&Wilson 2001:79),“人类在比较不同假设力度时的做法因此有力地表明,作为用于假设的一个基本心理概念的力度是比较性的而不是量化性的”(Sperber&Wilson 2001:81)。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关联性概念可以不作为一个比较性概念加以定义,而作为一个量化性概念来定义。他们认为,通过将一个假设添加到一个语境中所获取的语境效果,就可以通过计算语境含意来测量。涉及证实值变化的语境效果也可以测量,只要这些证实值也是量化性的。(Sperber&Wilson 2001:129-130)但由于他们不知道如何“用一个原则性或随意性方法来决定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的比重关系以及这个自动装置的关联性怎样才能被量化性地加以定义”(Sperber&Wilson 2001:130),因而选择放弃对关联性进行量化评定。可以看出,在对关联性进行量化性评定的问题上,他们存在一种矛盾心态,只能先给出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平衡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先忽视从外部来评定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而注重从内部评定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的关系(Sperber&Wilson 2001:130),这样的假设不免显得过于宽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他们在决定放弃对关联性进行量化评定时,却提出一个显得十分牵强附会的解释:“关联性是一个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不需要被表征、更不需要被计算的特性。当关联性被表征时,它是通过比较性判断和粗略的绝对判断来表征的(比如,“无关联’、‘弱式关联’、‘很关联’),而不是通过精确的绝对判断(量化性判断)来表征的”(Sperber&Wilson 2001:132)。这进一步突出了他们的矛盾心理,选择放弃对关联性进行量化性评定是目前尚不可为的缘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非不需要。
4 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问题
尽管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关联性》第一版中对“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进行了明显区分,尽管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对在Wilson(1996,转引自何自然冉永平1998)指出在《关联性》第二版中将关联原则由原来的一条改为两条是为了使大家注意到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之间的差异(何自然冉永平1998),但至今仍然还有许多人将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 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关联性》多处措辞不严谨所致。下面,笔者将从《关联性》中列举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我们认为一个人会自动地以最大关联为目标且影响其认知行为的正是对这个最大关联的估计。实现最大关联涉及选择处理一个假设的最好语境,即:可以最好地在努力和要取得的效果之间实现平衡的语境。当这样的平衡得以实现时,我们就说该假设经过了最佳处理。当谈论到个人假设的关联性时,我们指的是该假设经过最佳处理而取得的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44)。如果一个研究关联理论较深的人看了这段话,会看出《关联性》作者在此说的“最大关联”指的是人类认知取向而非实际交际行为。但对关联理论的初学者来说,就很难避免误解。尤其是《关联性》作者在此还使用了一个很敏感的词“最佳”,之所以说这是个敏感的词,是因为此“最佳”跟最佳关联概念中的彼“最佳”是不同的,此“最佳”指的是“最好”,而彼“最佳”非指“最好”,而是指一个为听话者所接受的一个含意。还有最后一句“当谈论到个人假设的关联性时,我们指的是该假设经过最佳处理而取得的关联性”中的“最佳”具有很大歧义性。特别是他们在说完这段话后,给出了个人关联的比较性定义:“程度条件1:只要一个假设被最佳处理时取得大的语境效果,那该假设对一个人来说就具有关联性。程度条件2:只要最佳处理一个假设所需的处理努力小,那该假设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具有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45)。接着,他们又给出了一个更具有误导性的点评:“可起到心理作用的唯一关联比较是那些有助于实现最大关联的比较:对某人的关联,或者,从交际者的角度来看,是对听者的关联”(Sperber&Wilson 2001:145)。那么一般的读者看到这里,都会很自然地把“最佳关联”理解成“最大关联”,误解由此产生。
又如,“每一个思维过程都使我们的大脑处于由一个初始给定语境和随后扩展语境来详细说明的一个状态中。人脑思维的列车是由找寻最大关联来驾驶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人脑就应该尽量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包括其自己的内在资源)去发现在初始语境中具有最大关联的信息,即:这样的信息要在可获取的扩展语境中找寻,不管该扩展语境是否包括百科记忆、短期记忆库或环境”(Sperber&Wilson 2001:147)。这段文字的误导性和歧义性更大,因为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指出“只需付出最小处理努力就可产生最大语境效果的信息”后,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本能取向,而是说这是人类在交际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同时说最大关联信息是在大脑可获取的扩展语境中寻找到的信息,那么既然是经过了寻找,也即听话者进行了主观思维,而一旦听话者在接受到外界刺激后进行分析和推理,这就意味着听话者随即进入一个寻找最佳关联性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实现最佳关联,而非是实现最大关联。
再看一例:“关联原则并不是说交际者必须给出最佳关联的刺激,而是说交际者必须有意使受话者认为他们在这样做。甚至令人讨厌的人都会明显地有意使其听者认为他们的话值得一听”(Sperber&Wilson 2001:158)。这段话本身就是对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自己给出的关联原则定义的明显违背。根据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行为本身都具有一种最佳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58)他们对最佳关联性是这样解释的:“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处理努力之后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 processing effort)”(何自然冉永平1998)。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最佳关联性:一是明示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二是听话者要付出处理努力去实现明示行为中所固有的最佳关联性。显然,上面“关联原则并不是说交际者必须给出最佳关联的刺激”中的“最佳关联”指的是“最大关联”,这难道是作者的笔误吗?
就在接着上一个例子后的下一段论述中,还可以看到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马上无意识地纠正了上例错误:“如果一个交际者没有使她在提供最佳关联信息这个现象变得明显于其听者,她还是可以使其听者明白她在尽力作到最佳关联。不过,明示交际必须要看成在表达意向关联,而不仅是意向关联的一个假设。受话者也许愿意相信交际者已尽力作到关联,但如果他又认为交际者完全没有作到关联,他就不会注意她。因此,无论交际者有多少自我怀疑,她必须有意使其受话者明白:她的明示刺激是有足够关联的”(Sperber&Wilson 2001:159)。这段论述有两句话是作者的自我无意识纠错:“如果一个交际者没有使她在提供最佳关联信息这个现象变得明显于其听者,她还是可以使其听者明白她在尽力作到最佳关联”,“无论交际者有多少自我怀疑,她必须有意使其受话者明白:她的明示刺激是有足够关联的”。但由于这种纠错是作者无意识进行的,所以读者在同一时间看到这几段话时,不免会将最佳关联误解成最大关联。
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关联性》全书中暗含了对企图达到最理想交际境界的否定,就好比他们在批驳交际的基础是互知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人类交际的基础是互明,而不是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的互知,互知不过是人们假想的一种理想境界。(Sperber&Wilson 2001:49-66)那么,同一个道理在交际中至多能实现最佳关联,而不可能实现关联最大化。所谓实现关联最大化,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奢望罢了。
通过以上个例的展示和分析,可以明白为什么关联理论问世后至今,还有人会将最佳关联和最大关联混为一谈。应该说,这更多是由于作者本身出现的问题,而非读者的理解能力差所致。
5 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现象
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关联性》第三章中自问自答了一些问题,有些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例如,“问:关联原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交际吗?答:不:它只适用于明示交际,而并不适用于编码交际”(Sperber&Wilson 2001:159)。在《关联性》第一章中,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编码交际,同时他们在书中明确提出并论证了人类的交际模式就是明示-推理交际,那么他们的这个自问自答岂不是在说明示交际-推理只不过是人类众多交际模式中的一种吗(假如有的话)?另外,这个回答降低了关联原则对人类交际的解释力。他们提出关联原则的初衷是设计一个可以解释人类一切交际行为的原则,那么既然如此,关联原则怎么只限于解释多种交际模式中的一种呢,假如存在多种交际模式的话(根据关联理论,实际上不存在多种交际模式)?
又如,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的另一个自问自答:“问:你认为所有明示交际至少都在力图作到具有最佳关联性吗?答:我们从关联原则中得不出这个看法。在理论上,一个交际者可以不忠诚地表达其关联假设,正如她可以不忠诚地表达任何假设一样。不过,明示交际者一般都会尽力作到最佳关联”(Sperber&Wilson 2001:159)。但根据他们给出的关联原则定义:“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其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Sperber&Wilson 2001:158),现在他们的这个自问自答违反了自己给出的关联原则。尽管交际者在交际中言不由衷,但只要其发出的是明示行为,其交际意图后面必然传递着某种信息意图,在看似不关联的表层下面必然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我们就以他们随即给出的一个例子为例:“煽动者对一个集会作长篇大论,只是为了延迟集会的进程。言语交际的所有通常特征都被表现出来,甚至被表现得很突出,但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没有企图实现最佳关联性”(Sperber& Wilson 2001:159)。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要说明的是,在此,交际者是在进行一种虚假交际,因为其演讲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他们忽略了一点,虚假交际也是交际中的一种,更何况在这个虚假交际的演讲中,交际者在其交际意图后面存在着以拖延时间为目的的这样一个信息意图,那么这种演讲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十分清晰的明示行为。换言之,该明示行为就具备了最佳关联性。同时,这种最佳关联性在听众中也得以实现了,因为听众听来听去到后来变得兴趣索然,发现演讲者不过是在废话连篇,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因此听众的这种反应就是演讲者的明示行为所取得的语境效果。所以,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的这个自问自答实际上跟之前他们提出的明示行为概念和关联原则相矛盾,让《关联性》的读者不知所云。
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关联性》中违反自己给出的最佳关联性概念和关联原则的例子还有:“如果交际者所作出的关联假设是错误的,那情况会是怎样呢?这会使受话者在理解时要付出多一点的处理努力,也更加容易导致理解失败,但不会使理解过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且也不一定不会得出一个可行的理解。为了跟关联原则一致,所得出的一个意思实际上对受话者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最佳关联性,不过这个意思只是在交际者看来似乎一定如此。相反,第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意思在交际者不可能预见到的某一点上可能恰恰是具有关联性的。这样,该理解就跟关联原则不一致。在所有情况下,受话者所要作的就是找到跟关联原则一致的一个理解,即:交际者会明显期望具有最佳关联性的一个理解。如果受话者可以相信交际者并因此认为交际者意想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他想到的第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理解的话,受话者的理解过程当然就会变得容易些了,但并不会被完全改变”(Sperber&Wilson 2001:169)。我们看其中一句:“为了跟关联原则一致,所得出的一个意思实际上对受话者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最佳关联性,不过这个意思只是在交际者看来似乎一定如此”。显然,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此说的最佳关联性违背了他们自己给出的最佳关联性定义:“最佳关联性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处理努力之后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 processing effort)”(何自然 冉永平1998)。这句话中的“最佳”很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最好或最大”。我们再看这段话中的另一句:“相反,第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意思在交际者不可能预见到的某一点上可能恰恰是具有关联性的,这样该理解就跟关联原则不一致。在所有情况下,受话者所要作的就是找到跟关联原则一致的一个理解,即:交际者会明显期望具有最佳关联性的一个理解”。这句话显然是对作者自己给出的关联原则的违反。在《关联性》一书中,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彻底否定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具体批评的一点就是合作原则一方面要遵守,另一方面又可以违反,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何自然1995)在批评格莱斯合作原则时,他们说在交际中关联原则是不可能违反的,那么据此岂不是说在交际中听话者必须要实现交际者的信息意图才能不违反关联原则或才能实现最佳关联性吗?而在《关联性》一书中,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多次论证了关联原则并非只解释交际中的正确理解,同时也可解释诸如不完全理解、误解或错误理解之类。在谈到语境效果时,他们也论证了交际中的4种语境效果:(1)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2)现时语境假设的加强(strenght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3)现时语境假设的相互矛盾与否定(contradicition and elimination of existing assumptions);(4)现时语境效果的削弱(weak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何自然冉永平1998)类似的例子还有:“歧义消除和所指分配实现得越快,所需的处理成本就越小。在话语生成过程中,大脑所产生的不同理解越多,处理努力也就越大。如果说话人要实现最佳关联,他就应使其话语简练,以方便听话人尽早正确地消除歧义”(Sperber&Wilson 2001:204)。以上诸例都可以说明Dan Sperber和Deidre Wilson在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
6 结束语
自关联理论1986年问世后,其影响力超出至今任何一种语用学理论,但时至今日各种激烈的争议和批评之声也从未间断过。客观地说,关联理论本身存在着各种诸如自相矛盾、措辞不严谨等之类的“硬伤”。这些“硬伤”的严重性在于它们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关联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的论述中,因此引发诸多读者的误解和错误理解也就不足为奇。当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反批评之声(何自然2004)。但是,我们不能把读者的误解和错误理解都归咎于读者,那是对读者的不公。我们应该更多从关联理论本身存在的那些微观性缺陷去寻找原因。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并非彻底否定关联理论,而是本着进一步完善关联理论的意旨,将自己多年研究关联理论的心得和体会写出来跟大家交流,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笔者在本文中基本上在用《关联性》作者自己的言论对关联理论进行微观性批评。
②关联理论中的“交际者”泛指明示行为的发出者。
何自然.Grice认知学说与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何自然 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现代外语,1998(3).
何自然.关联理论是一种“因错而‘对’“的理论吗?——关联理论是非谈[J].现代外语,2004(1).
何奕娇.试论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外语学刊,2007(5).
胡旭辉.关联理论与乔姆斯基语言学共性初探及反思[J].外语学刊,2008(2).
姜望琪.关联理论质疑[J].外语研究,2001(4).
刘国辉.关联理论的回顾与思考[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2).
乔 娜.对“关联理论”的几点不同看法[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1).
曲卫国.也评“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2).
王建国.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局限性[J].语言与翻译,2003(1).
熊学亮.对关联理论中逻辑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0).
徐盛桓.关联原则与优化思维——关联理论的阐释与献疑[J].外国语,2002(3).
Hu,Xuhui.Relevance Theory:Reflection,Criticisms and Solutions[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Sperber,D.& 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