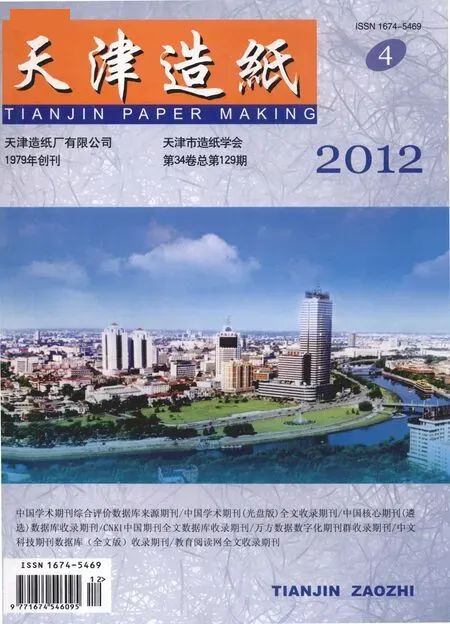我写文章
刘仁庆
我写文章
刘仁庆
(一)要从记日记开始
我从上初中二年级起,受到“国文”老师朱忱先生的影响开始记日记。可是,不知道到底该记些什么。篇篇都差不多,不外乎是早上几点起床,洗漱、出门、“过早”(湖北话,即吃早餐),上学校。上午上什么课、下午上什么课,晚上在教室上自习。天黑了,回家睡觉。每天记的都是一些芝麻事、豆腐账,如同“小和尚念经”,天天如此,十分乏味,不堪卒读。自己也觉得很伤脑筋,越写越不想再写了。
有一天,在路上我遇见了朱老师,便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怎么记日记?他说,找个“礼拜天”到我寒舍里来谈一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学的师生之间主要在课堂上见面,这种反“家访”的现象是极少见到的。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终于走进了他的“宿舍”。
进门后,我毕功毕敬地向朱老师行了一鞠躬。放眼小房间的四周: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摞了一些什么书刊、报纸之类,乱七八糟的。他好像早有准备,手里拿着一本书,嘴里轻声地说道:“来,来,来坐下,不客气”。朱老师指着一旁的小板凳说。这一幕,因为是第一次,过去60年了!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朱老师看了我写的日记,一边鼓励我说:你能开始写就不错了。一边指导我说:记日记要抓住要点,不是流水账。还说:你看一下这本书之后,就可以大致地明白记日记的一些写法了。原来朱老师借给我看的那本书,是我国三十年代在武汉扬名的、湖南女作家谢冰莹(与北京女作家谢冰心双双齐名)写的作品:《从军日记》。今天的青年读者,恐怕很少有人听说过这本书吧。
后来,我又慢慢地找了一些日记体的文章、书籍来阅读,自己也从其中学到一些写作技巧和方法。上大学之后,我痴心未改,因为当了学校“周报”(《华南工学院院刊》)的通讯员、记者等。出于工作需要,又记了许多本日记。遗憾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我害怕“惹祸”,暗地里把这些日记本统统处理掉,并内心“发誓”,以后再也不记日记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通过这么多年记日记的经历,其显著的收获是:锻炼了我的毅力,理清了我的思路,同时也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新近有媒体报道,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写日记能增强人的自尊心,让人变得更自信,甚至有利于减轻生活中的烦恼和焦虑感。青年朋友,如有兴趣不妨试一试?看看到底效果怎样?老同志呢,若是仍然“心有余悸”,那么就姑且“作罢”算了。
(二)文章、稿件有区别
我由记日记起,逐步地走向写文章到写稿件,似乎是沿着这样的轨道进行的:即从收集素材 (当原料)、打磨加工(发构思),直到完成作品(点主题)等“三步法”。在日记或备忘录里,把自己平时的所见、所听、所读、所想的点点滴滴,逐一记录下来。然后,再从中挑选一两个有思想、有意思、有意义的主题,再逐步写下去,最后初稿完成,放下手来。过一段时间以后,再仔细地推敲、修改,慢慢定稿。
有人说过,写文章是三分技巧七分“选材”。材料从何而来?来自生活,来自读书,来自观察,来自积累,这话很有道理。不过,我还要添一句:来自思考。因为我们日常接触的人和事,多如牛毛。是不是都值得去写?否!还要从所选的材料中提炼出有教育意义、感染人心的内容和主题。这就需要用脑子好好地想一想,从中抽出最重要的内容,再进行拟题、起草、修改、定稿等。在这一连串的写作过程中,思考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我认为:文章与稿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章是什么?我的体会是,文章不一定拿出来公开发表,可以自读、可供友人参考。其实,不论是写日记、书信,还是写请示报告、工作总结,都可以视着是写文章。通过写文章可以锻练自己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总结能力。文章涉及(或者说影响)的读者范围可能是有限的(非公开的)。但文章与稿件又是相通的,两者可以互变。难道说被编辑部头头“枪毙”(常以“缓用”二字搪塞)的稿件都不是文章了?有时,此刊不用的稿件,“改换门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之后又被彼刊发表,变来变去,十分有趣。只要不是“一稿多投”,则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不对?
稿件是著作,目的是向大众进行宣传,一旦公开发表便成为社会的公共财富(享有著作权)。写稿件的注意事项,一是明确对象(读者是谁);二是主题鲜明(宣传什么);三是文责自负(绝不能有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我还认为:口语与文稿也是有差别的。口语是说话,文稿是书写。一般而言,前者芜杂,拖泥带水;后者洗炼,干净利落。“出口成章”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话说出口就符合规范,意思表达清楚,形容“口才”好;也形容学问渊博,文思敏捷,堪称文化水平高。它的原文出自《淮南子?脩务训》:出言成章,这是一句夸奖别人的、好听的话。切切不可理解为一说“出口”就成文章,一字不动,就拿去当稿件发表(这是坊间传言,殊不可信)。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就寝后随意翻阅,调理思绪,莞尔—乐,安然成眠”,这句话只有19个字。若换成用口语说,那就是“当我上床准备休息的时候,将拿在手里的刊物随便翻翻看看,流览一下,清理自己脑子里的思维活动,偶然见到有趣的文章,便会开心一笑,不久就安稳地闭上眼睛睡着了”,共有69个字。瞧,两者字数相差3倍多,口语是不是显得特别啰嗦、没有文采了吗?
文章经过慎重地修改之后,若找报刊或媒体发表就变成稿件了。所以说写文章与写稿件是有细微区别的。我曾经做过编稿、审稿方面的工作,对此还有点不同的看法。一是关于编稿。因为杂志收到的稿件很多,作者的写作风格各异。同时,又因为受版面限制,刊登时要做一点调整、压缩和删节,这原本无可厚非。所以为了保证刊物的质量,对来稿需要做编辑处理(如订正来稿的笔误、错别字、标点符号等),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作者不明白这一点,声明我的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显然出于误会,不可取也。
二是关于审稿。因稿件有多种,如科学研究论文、工业技术报告、经济理论评析、文化艺术随笔等,作者的写法各异。故专业刊物的编辑部在约请审稿人员时,必须掌握由在某一方面具有特长、文化涵养较高的专家来担任。我国造纸业内的个别刊物,有唯“技术至上”、思想僵化的倾向。发表的硬性稿件较多,而软性稿件较少。据我猜想可能至今还受到“苏联情结”阴影的影响,其仿本就是以前的苏联《造纸工业》(
бумаж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杂志, 再加上一点“欧美味道”搅和而成。君不见,他们之间的栏目、格式岂不都是同出一辙乎?
关于审稿,再举一例:有一次,某刊收到一篇带有点软性的稿件,约请了“外审”。审稿者提出,该稿内容比较随意,有点“笔随意行,信马由缰”的感觉,部分内容与题目的关联性不高。而作者却认为:本文采用的是随笔体,从一开始由对“纸”的不认识,一直到今天希望“纸”发达兴旺,都是通过作者与纸的有关文字,相识、相知、相恋而联系起来的,这就是文章凝聚的主旨。因此,看似“天马行空”的描写,实际是经过“形象思维”后设计的。倘若不明白它与“抽象思维”的区别,那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以为我离题,我实际在联想;他不屑随意,我却在发挥。文艺的关联性是隐性的,如果什么都直白出来,哪里有含蓄、意趣可言?”当然,我们也反对胡写、呆写、乱写。“百花齐放”嘛,只要符合办刊的方针和要求,应该允许各种稿件在版面上出现,“文责自负”,是不是?
我想杂志上刊出的稿件,最好要“杂”一点,长短结合,硬软搭配,不要都登硬性文章(蹩脚的“论文”、“报告”,即使愿交版面费,也不要发表),软性文章就是以“事”或以“人”而发,以“情”感人,能够激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调动读者与作者、编者的互动积极性。这样的文章更能拉近编辑部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取得良好的共鸣效果,也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刊物的影响力。
(三)多想多改出华章
按照一般科研的套路,首先是选题。其后去找参考文献,摘抄主要内容。再后是拟出试验计划,做出添置设备、药品的经费预算,让公家或自行采购。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动手进行“攻关”了。
然而,写文章则不必如此,可以简化成我前边说的“三步法”。过去,一枝笔、几张稿纸就可以了。现在,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也成事实,写作工具更先进、更省力了。不过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思想、有激情才能迸发出灵感,有了灵感才能有源流、笔下才能写出好文章。当然,诚如胡适先生告诫他的学生唐德刚有一段话: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凭记忆是靠不住的,时间会使它变形“走样”,甚至消失,想修改也没有基础。何况丢三挪四,凑合写得干瘪瘪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应该在平常的日子里,遇到感兴趣的任何一件事,或者说历史上任何一件事,都要仔细地多想一下,勾起对过去积累的知识和资料的“反刍”,再加以判断选择:究竟哪些事值得去写?加以“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季羡林先生有一句名言:没有新意,莫写文章。有时,你写的东西,别人早就发表了。此时唯一的办法,只好忍痛割爱,另起炉灶。我记得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写稿件是一项社会劳动,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发表后它是要对历史负责的。因此,稿件写完之后,必须进行“冷处理”——最好放它几天。过一段时间重新审读,遣词造句,专挑毛病,不停地修改、补充,以臻于完美。
有的人扬言,自己写东西很快,“一遍就过”,从不修改。如果这真是事实,当然 “顶好”,是有本领、水平高的表现,令人佩服。但是,依老汉我个人的经历和认识,这仅仅是稀世“个案”,决不是普遍现象。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谨慎一点,勿求快,力求稳,更求好。从电脑上大段大段地“引用”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错误百出,这个教训还少吗?我审查过一些稿件,深感这种浮燥的作风,会带来“很差劲”的影响。作为一个普通的作者来说,决不应该沾染“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陈腐的旧观念,更不要藏有投机取巧、急于求成的心态。总之,既不要“唱戏转身拍屁股——自捧自”;也不必“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编辑当然也应该尊重作者,保持他人的写作风格,尽量少改动、甚至不改动。但是,见错不改,怕得罪人,还要你这个编辑干啥子嘛?
除了自行动手修改文章之外,拜师学艺、请教高手,又是一种力求上进的好方法。写作隶属人文科学,这门学科十分重视“师承”的作用。良师可以迅速把你带到专业学科的前沿;良师可以帮助你打掉浮躁的毛病;良师可以提高你具有探究、鉴别的能力;良师可以培养你宏阔深湛的学术意识。总之,有良师指导,就能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深入学问,还可以少走弯路,尽快地“入门”,比自己“瞎摸”强得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一旦听到或碰到某一件事,就会隐约地觉得文革中“打倒老师”、“打倒权威”的口号声,仍然还在我耳边“嘶叫”,可见要肃清这些“流毒”和“余患”,实在是非常之困难的。
1961年我这个科普门外汉,有幸结识了两位科普界的良师:一位是写出《算得快》的科普作家刘后一,这本书曾发行了几百万册以上,社会影响大;另一位是苏联伊林科普作品的翻译家符其珣,出版书籍多。这两位老师在写作上对我的帮助,使我终身难忘。他们从文题直到结尾,细致地指出应该如何安排、怎样修改,才能脱离俗套。他们让我慢慢懂得了什么是学术论文,什么是科普资料;什么是技术报告,什么是科普短文;什么是生产实践,什么是理论探讨;以及什么是科学小品,什么是科普创作,等等。更重要的是了解了怎样写文章、怎么改稿件。总而言之,归根到底,要写好文章(或稿件)有个“改字诀”,这就是:一改、二改、三还是改!
2012-9-15
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