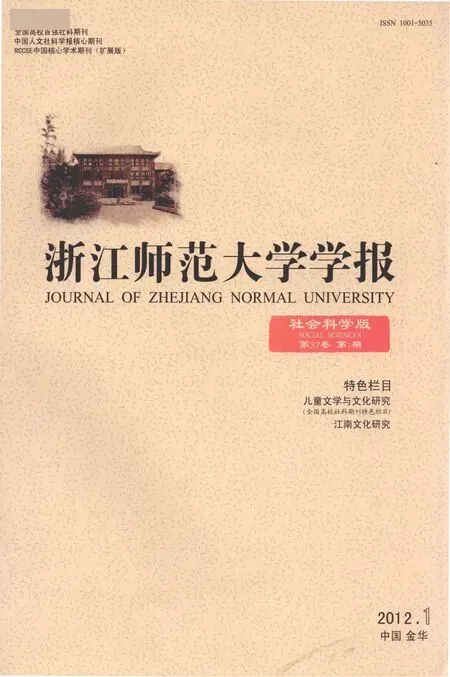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金滢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关于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学界关注不多,且多将目光集中在唐五代科举制度、私学和童蒙教育,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深入下去。目前所见,仅有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1]侯力《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教育》、[2]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3]马秀勇和王永平《论唐代童子科》[4]等少数文章涉及到科举考试与童蒙教育的问题;此外,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5]王炳照《配图蒙学十篇·序》、[6]1-16徐梓《中国传统蒙学述评》(《蒙学须知》序)、[7]乔卫平《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8]金滢坤《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9]等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由于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此,对本文选题的论述也就不够深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张新鹏《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等论著,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大大推动了学界对唐五代童蒙读物的了解和研究。本文试图将唐五代科举与童蒙教育结合起来,借以探讨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一)唐代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
唐代官学教育中对童蒙教育的缺失,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科举制度设立之初,就确立了官学教育与科举选士相结合的模式,官学教育的机构和课程设置也基本上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考试主要是为了选拔官员,因此它所面向的选拔对象是成年人。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其招收的对象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青少年,对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
唐代的学校教育分两个层次:一是官学,二是私学。官学,分中央馆监官学和地方州县学官学。中央官学由国子监、崇文馆、弘文馆及广文馆组成。国子监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和广文馆。国子学、太学和广文馆主要面向皇亲国戚、高官子弟;四门学和律学、算学、书学主要面向低级官员子弟和百姓中的俊秀者。六学和馆学的入学年龄大致为“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10]卷44,1154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律学为专门人才,年龄略高,限定在为18-25岁。显然,中央官学主要招收已经通过家学、私学、寺学、乡学等进行过童蒙教育的生员,也就是说官学系统基本上没有童蒙教育的功能,因此,唐代童蒙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广义上的私学来完成。
唐代的国子监、弘文馆、广文馆以及州县学等官学均以“九经”、《论语》、《孝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元以后随着道举的设立,天宝二载设崇玄馆,又增加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考试逐渐重文,进士科最受时人推崇,偏重经学的官学系统渐受轻视,举子渐轻两监出身而重“乡贡”出身。[11]卷1,5私学因受官方影响有限,能比较灵活地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承担了诗赋等文学方面的教育职责。
应该说,中晚唐私学的快速发展,是顺应科举考试重诗文变化的要求的结果,作为举子应试教育初级阶段的童蒙教育,无疑也受到了科举考试制度变化的影响。
科举在选举地位中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提升了唐人对童蒙教育的热诚。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出身仕宦特别迅捷,以至于十数年便拟迹庙堂,成为中晚唐选官的“第一出身”,卿相的后备人选。[12]不仅如此,有科举出身者还成了世人脔婿的最佳人选,一时间,“榜下择婿”、“榜前择婿”成为社会时尚。科举地位的提高带动了整个世风,世人不分士庶,穷经皓首,以科举为业,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举人群体。据韩愈估计,每年参加礼部省试的明经考生就有三千人,[13]卷4,249进士上千数。[13]卷4,259又据《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规定,每年乡贡举人、国子监贡送举人中,明经1340人,进士 633 人,总计为 1973 人 。[11]卷1,2总的来说,中晚唐时期每年参加省试的诸科举人在两三千人左右,若将逐年的落第举人和国子监、州府试的落第举人计算在内,全国每年从事科举考试的少说也有十万。①[14]362科举考试的低端,儿童和少年,即童蒙阶段,数目应当更大。
这种全民向学的庞大的应试需求,直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特别是开元、天宝之中,天下太平,“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成了人生的最佳选择。于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希望获取功名,光大门第,“资身奉家”,以至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14]358可以说,科举考试极大地促进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士庶之家往往将培养孩子读书获取功名作为第一要务。
(二)科举考试促进了私学的快速多样化发展
唐代私学,包括家学、乡学、巷学、社学、寺学、村学(小学)、书院等,比较庞杂。
1.家学
唐代私学中,首当家学。[2]家学——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门第教育[15]——在唐代童蒙教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唐前期,以明经科为主的经学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魏晋以来的经学世家在科举考试中仍然保持着优势。
唐前期以家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家学有父兄教授子弟、母亲与外族教诲子弟两种形式。唐五代家学主要由士大夫阶层所承担,他们文化程度高,是童蒙教育的重要力量。父兄教授子弟是唐五代家学教育最基本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说是魏晋以来士族充分发展的结果。唐代建立以后,家学在私学教育中仍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武则天当政以后,“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14]358科名渐趋代替了门第,士族不得不更加注重子弟的教育。
例如,刘知几十二岁时,其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其父得知后,便改授《左氏》。结果,刘知几“遂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最后擢进士第。[10]卷132,4519刘藏器精通经史,对刘氏兄弟从幼童时期就开始了严格的家学教育,为他们后来的登科考试打下了良好基础。又如贞元四年(788),胡珦被贬为献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以自给,教授子弟”。[13]卷7,467胡珦曾为工部员外郎,虽为县令,但文化程度却很高,他亲自教授子弟,教育质量自然不低。
唐代家学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且州清阳人宋庭芬,世为儒学,“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即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为赏叹”。[16]卷52,2198后来五女之一的若昭竟官至女学士。像宋庭芬这样世为儒学、兼通诗赋、教授子弟者,在唐代士大夫中较为常见。
在这种情况下,家学教育也不免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如柳子温家法非常严厉,“常合苦参、黄莲、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盗勤苦”。[17]足见士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和科举竞争的激烈,激励和鞭策子弟及早读书、日夜勤勉用功乃时代风气。
唐代家学教育秉承魏晋以来的风气,不仅给幼童编纂了很多童蒙读物,还制定了子弟培养计划。唐中宗时期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记载了子弟的培养方案:“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18]
母亲与外族是承担儿童教育的又一重要角色,往往在夫亡、家贫的情况下,母亲和外族便担当起了子弟童蒙教育的重任。《旧唐书·薛播传》云:“初,播伯父元暖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暖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搃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16]卷146,3956济南林氏之所以在夫丧之后训导诸子、从子,使其连中进士科,名扬天下,其重要原因是林氏出生于士族之家,“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具备了传授家学的良好条件。唐代不少政要和文化名人都是在父亡家贫的情况下因母训而登第者。重振门第者亦不乏人。如杨凭,“虢州弘农人。少孤,其母训道有方。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10]卷160,4967又如牛僧孺,父亡之后,“为母所训,遂习先业”,后登进士科,官至宰相;[19]元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16]卷166,4327李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元和初,登进士第,官至宰相;[16]卷173,5344杨收,“七岁丧父,居丧有如成人,而长孙夫人知书,亲自教授,十三略通诸经义,善于文咏,吴人呼为‘神童’”。此类情况史书记载甚多,不再一一例举。唐代士大夫子弟在父亡之后,随母依附于外族接受外家家学教育的情况也很常见。如李公素,河南士族,“七岁丧其父,贫不能家,母夫人提以归,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经选”;[13]卷6,369韦丹,少孤,“以甥孙从太师鲁公真卿学,太师爱之。举明经第”。[13]卷6,374
当然,家学教育也有其缺陷:一是宗族内的儿童数量有限,缺乏规模,儿童之间的竞争力不足,难以调动他们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望;二是术有专攻,宗族内承担教授任务的主要是父兄和母亲,很难做到通晓诸家经典以及诗文,往往以一家之言传授子弟,容易造成子弟视野不宽、学业封闭的状况。
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及中晚唐常举、制举和科目选的全面发展,科举对举子的学识、文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学已经不能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于是,家学开始向私塾转化,通过延聘师傅来补充其不足。中唐宋若莘的《女论语·训男女章第八》云:“大抵人家,皆有男女……男入书堂,请延师傅,习学礼义,吟诗作赋,尊敬师儒,束修洒脯。”[20]一部分家学开始招收亲友故吏子弟和社会子弟,使家学逐渐转换成私塾。如刘邺,其父三复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的从事,刘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16]卷177,4617另如柳宗元,少时就曾入学“乡闾家塾”。[21]
2.乡学
安史之乱以后,士族逐渐衰落,家学的地位也随之衰弱,代之以乡学、巷学、村学(小学)、书馆、寺学、社学、书院等社会性更强的私学,并逐渐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私学的发展在于其形式多样、招生范围扩大、层次差别大和内容丰富、教师学识各异,既满足了不同层次儿童的需要,也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求,是以往家学和官学所无法比及的。
乡学是唐代社会教育体制中对儿童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形式之一。乡学主要针对社会中下层子弟的初级教育,以乡村童子为对象。隋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每乡立学”的情况。武德七年(624),唐高祖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16]卷24,916明确地将立学的范围扩展到了乡一级。天宝三载,玄宗下诏,令“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22]卷310,3150七载,玄宗又下诏,“先置乡学,务令敦劝”。[23]卷59,94此后,在一些地方长官的推崇之下,乡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建中初,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颇嗜诱进后生”,[22]卷544,5514“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极大地推动了福建道乡学的发展和科举风气的兴盛。罗珦为庐州刺史后,“命乡塾党庠,缉其墙室,乡先生总童冠子弟”,以《周礼》、《易》等儒家经典及百王之言教之。[22]卷478,4885
贞元三年,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结果未能上报。[24]卷35,635但乡学似乎在元和年间得到了很大发展。正如白居易所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孀妇、处女之口”,常有咏其《秦中吟》、《长恨歌》等诗的。[16]卷166,4349唐人皮日休《伤严子重》序云:“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25]“乡校”即“乡学”,为乡村对儿童进行童蒙教育的重要场所。虽然目前还很难判定唐代乡学是否属于官学控制的范围,但乡学以乡村儿童为教育对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太公家教》由村落间的教师所作,唐代乡村乡学的数量和普遍性自然不可低估,也说明乡学教师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其教学素养也不低。作者自称:“才轻德薄,不堪人师”,“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注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用传于后”。②[26]《太公家教》的内容和影响力足以说明作者在学识和文采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诙谐所累》云:“刘岳与任赞偶语,见(冯)道行而复顾,赞曰:‘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园策》来。’道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授散骑常侍。北中村野多以《兔园策》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策》乃徐廋文体,非鄙朴之谈。”[27]349-350《兔园策府》与《太公家教》相似,亦为乡村教师所作,可见乡学在唐五代确为民间儿童教育的重教场所。敦煌文书北敦5819V题记云:“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武保会、判官武保瑞自手书记。”[28]此“悬泉学士”,即指悬泉乡学学士郎。该题记为唐代存在乡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里学、巷学、社学
乡学之外,还有里学、巷学、社学。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24]卷35,635关于里设学,仅有此一条记载。里是唐代最基层的单位,里是否真正设立过学校,还有待进一步证实。S.4307《新集严父教一本》卷末有题记:“丁亥年(987)三月九日定难坊巷学郎崔定兴自书手记之耳。”[29]说明城市中还存在巷学。关于唐代社学的情况,学界还不是很清楚,但P.2904《论语》卷第二文末有题记:“未年正月十九日社学写记了。”[30]说明社学的确存在,其具体形式史料阙如。
4.寺学
寺学是唐代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唐代佛教在中土鼎盛,实现了中国化,寺院也逐渐成为儒、佛、道三教汇融的中心。中唐以后,随着家学和官学教育的衰落,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渐兴。[31]严耕望先生在《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中列举了终南山、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区、泰山及其近区诸山,敦煌诸寺院等14个唐人读书的著名山林寺院,概括了唐人读书山林寺院的大致原由。[31]山林寺院不仅是中青年士大夫论学读书的地方,还是童蒙教育的重要场所。唐代佛教继魏晋南北朝以来日渐兴盛,寺院经济也不断发展,山林寺院逐渐成为士大夫学习论道之地,不仅集中了高僧大德,还因环境幽雅吸引了许多文人、举子隐居其中,潜心习业。因此,山林寺院也成了唐五代童蒙教育的重要场所。如裴休佛学修养很高,他在出任凤翔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期间便游历太原、凤翔附近名山、寺院,“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16]卷177,4594太原、凤翔诸山佛寺中义学僧造诣极高,他们常常吸引封疆大吏一起讨论佛理,这足以说明中晚唐寺学具有相当高的师资力量。当然,寺学比较注重对佛理的教育。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敦煌寺学的学郎读物、作业中,记有当时的学郎题记,这些题记为研究唐五代敦煌寺学提供了宝贵材料。唐五代敦煌地区共有寺院十六所,其中九所设有寺学,敦煌文书中的儿郎题记为此提供了可靠证据。如:P.2808《百行章跋尾》末题:净土寺(学)郎阴义进;P.609《俗务要名林残卷》背题:灵图寺学仕郎强盈润;P.2712《贰师泉赋》:龙兴寺学郎张安八;P.3189《开蒙要训》: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P.3381《秦妇吟》:金光明寺学仕(郎)张龟信;P.3569《太公家教》:莲台寺学士(郎)索威建;S.1386《孝经》:永安寺学士郎高清子;S.5463《开蒙要训》:大云寺学士郎;北盈76背《目连变文》:显德寺学士郎杨愿受。[32]寺院内设置的义学,传授儒家学说、诗赋的情况极为普遍。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大量寺学学仕郎题记的童蒙读物,如《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策府》、《百行章》、《孝经》等,[32]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寺学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儿童。
唐五代寺院经济强盛。由于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时常提供免费食宿,寺学便成了衰落士族子弟和贫寒子弟接受童蒙教育的重要场所,贫寒家庭的子弟随僧洗钵、论学读书而至通显者,时有所闻。例如: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相穆宗;[11]卷7,73刘轲少为僧,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11]卷11,120孔述睿,既孤,与弟俱隐于嵩山;[11]卷192,5130吕向,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10]卷202,5758徐彦伯,七岁能为文,结庐太行山。[10]卷114,4201此类情况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5.村学
村学或称小学,实际上就是私人讲学,也就是后来的私塾,是童蒙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唐代村学一部分由家学招收乡里子弟读书转变而来;一部分为个人造舍,以讲学为业,是靠教授乡村子弟为生的私学。如元和中,有田先生者,“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33]卷44,274此小学同书又称为“村学”,说明二者可以等同,“小学”主要说明教学的对象为孩童。又如窦相易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34]村学的规模似乎不小,不完全是自然村的孩童,还招收附近村庄的孩童。唐代甚至还有村学住宿的情况。《太平广记》载:开元二十九年,修武县有一村庄,“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33]卷494,4056大概因为村学教学质量通常比较差,卢仝在教诲子孙时曾让其“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35]卷387,4369把村学生当作反面的例子。显然,村学教育在私学体系中相对较为薄弱,大概多限于扫盲和文化普及,跟家学教育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唐五代私人讲学非常盛行,仅敦煌文书中记载的敦煌私学就有张求学、白侍郎学、范孔目学、孔目官学、安参谋学、就家学、郎羲君学、李家学等众多私学,[36]可见当时私学之普及。唐代私人讲学,应当包括了家塾、村学、巷学等形式,私人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增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
6.书院
晚唐五代社会大乱,大族之私庄、别业尽遭扫荡,加之科举制度的兴起,导致了士族的末落,家学随之衰落,为寺观学和私人讲学所代替。小姓、寒人接收教育的机会与需求比以前增大了,私人讲学与寺观学也随之日趋发达,并日趋合流,从而形成了以山林、寺院为中心的大规模的讲学组织——书院。书院不但有名师、图书、学舍,供诸生学习与居住,而且有仓廪以给诸生。比较有名的书院有白鹿、睢阳、嵩阳、岳麓四大书院。晚唐五代书院的发展,也为童蒙教育提供了新的学习环境。
中晚唐士族之家往往自建“学院”、“学舍”、“书堂”当作教授子弟的场所,这也是家学转变的一种形式。《唐语林·德行》载:“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33]卷148,1069牛希济也曾“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27]389晚唐学院,似乎已有学生寄宿,并且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元和中,王建有诗云:“初从学院别先生,便领偏师得战名。”[35]卷300,3408昭义军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33]卷366,2509学院一般供同宗和亲表兄弟学习。元和初,韩愈有疏从子侄投奔自己,便“令学院中伴子弟”学习。[37]后晋太常卿崔棁少年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33]卷467,3852在唐末后梁之际,窦禹钧“家尚俭,建书院四十间,藏书万卷,延文行师儒,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结果其五子并登第。[38]窦禹钧建书院四十间,学员自然不光是自家子弟,社会生员应该不少。此时的书院不仅将教学、读书和藏书的功能结合了起来,而且将生员扩展到了面向社会。
在唐末五代家学性质的私人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九江德安县的陈氏义门书院。大顺元年(890)订立的《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日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次弟抽一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39]显然,家学性质的学馆对培养和选拔家族内适龄儿童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承担着选拔“有能者”进入更高层次的“东佳馆”进行培养的责任。陈氏义门书院将子弟按年龄和才能分为童蒙教育和科举应试教育两个层次,充分体现了科举对家学和书院的影响。陈氏书院设先生一人,副手一人,也初步具备了书院由多人讲学的特点。晚唐五代的学院、学舍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逐渐向书院发展。[40]
唐五代童子科的产生和发展与同时代的家学、乡学、寺学、私人讲学、书院等不同形式的童蒙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唐五代社会教育体制的变迁与完善,特别是私学的兴起,为儿童教育提供了多样的教育环境,补充了国家官学教育体制中十四岁以下儿童教育的不足,成为唐五代童子接收早期教育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形势的变迁,尽管各种教学形式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一样,但应该说都对该时期童子科的发展与童蒙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童子科的设置促进了童蒙教育的发展
唐代科举考试为了及早培养合格的治国人才,专门设立童子科,鼓励和促进儿童从小立志从事举业,荣登显宦。[3,4,41]随着童子科的逐步完善及影响日渐扩大,童子科考试自然也就影响着童蒙教育的发展。
(一)童子科的设置
唐代童子科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童子郎”、“童子奉车郎”、“童子”等名号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东汉顺帝尚书令左雄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童子郎。”[42]自此,能通经的童子便以“童子郎”的名目征召入仕。汉魏两晋南北朝时,童子科正处于萌牙阶段,童子郎已经成为成人以外的又一种选举。然而,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仅见臧洪、公孙、司马伯达等数人得拜童子郎,真可谓凤毛麟角,但影响并不大。南朝梁天监七年九月,置“童子奉车郎”。岑之敬年十六拜为童子奉车郎,庾质八岁拜为奉车郎,此“童子奉车郎”、“奉车郎”,应系东汉童子郎发展而来,[43]与唐代科举制下的“童子科”有着质的差别。
唐代童子科的目的是通过考试选拔儿童中的天才入仕,是科举考试的一个常科科目。
唐初,高祖就曾下诏,引导百官重视儿童教育。武德七年七月诏曰:“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邱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宜普颁示,咸使知闻。如此之徒,并即申上,朕加亲览,时将褒异。”[44]高祖将此事普颁天下,目的是鼓励士大夫积极教导幼童早习儒家经典,从而尽快培养出新政权所需之官员。从文中云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就可以“并即申上,朕加亲览,时将褒异”,还可“故从优秩,赏以不次”,说明唐初童子仍由地方向皇帝荐举,童子科作为常科科目尚在形成之中。贞观年间,童子仍通过举荐而被征召、见用。如贾嘉隐年七岁时就“以神童召见”,终于在年十一二岁的时候,于贞观中被举为童子。[45]这说明贞观年间童子科尚未设立,③贾嘉隐是通过童子的名目,以举荐的形式入仕的。《旧唐书·杨炯传》云:“(杨炯)神童举,拜校书郎。”[16]卷190,5000徐松《登科记考》云,杨炯举神童在显庆六年(661),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言登神童举者。[46]又《裴耀卿传》载:“(裴耀卿)少聪敏,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俄补相王府典签。”[16]卷98,3079王维《裴仆射齐州遗爱碑》云:“(耀卿)八岁,神童举,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35]卷326,3305徐松以耀卿天宝二载年六十三岁推之,其登第年在垂拱四年(668)。以上两例说明,在唐前期已有“神童举”及第者,此“神童举”以童子为对象,在高宗朝似已发展为常科科目。[47]
唐代初期,童子科当与科举考试的其它科目一起进行,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高祖武德四年(621)科举考试由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考,“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11]卷15,159但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因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考生发生冲突,被考生反唇相讥,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11]卷1,11此后,科举考试归于礼部主持,童子科也不例外。大历三年(768)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24]卷76,1399开成三年(838)十二月敕:诸道应荐童子等,“有官者合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24]卷76,1399两道敕文均明确记载,童子科由礼部主持考试。
(二)童子科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
唐代童子科,及第便可授官。如前所述,杨炯神童举及第,便拜校书郎。随着中晚唐童子科及第人数的增加和选举员额的不足,即便是童子及第后不能马上授官,也可以到弱冠之后再参选授官。例如王丘,“年十一,童子举擢第”,“弱冠,又应制举,拜奉礼郎”。由于童子科及第使童子小小年纪就可以入仕,造成了童子伪滥、及第后不思进取的现象。如张童子九岁便童子科及第,十一岁“益通二经。有司复上其事,繇是拜卫兵曹之命”。张童子因此声名大噪,“人皆谓童子耳目明达,神气以灵”,张不免沉浸在赞美和应酬之中;韩愈则表示担忧,认为张童子应该“勤乎其未学者可也”。[13]卷4,251这种情况到了五代更加严重,往往是童子“及名成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22]卷855,9156童子科出身虽说是“滥蠲徭役,虚占官名”,负面作用不小,但也足以说明童子科及第对个人来讲可以获得诸多好处,这无疑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他们希望子弟及早成才的心理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为了鼓励聪颖的童子向学,从事举业,一些开明君王还通过赏赐的形式加以鼓励。玄宗曾下《赐蒲州童子敕》云:“蒲州童子吴豸之,薄缀小篇,兼记古事,不稍优异,无申奖劝。宜赐其父绢十匹,令更习学,便有成就。”[22]卷34,376在童子科的影响下,中晚唐世人应举往往自小从应童子科开始。童子科及第,或释褐为官,或继续参加进士等更高的科目;若不第,长大再应明经或进士等科。例如翁袭明,“早举童子”不第,便持之以恒,长大后再参加进士等科的考试。[22]卷824,8685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童子科对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促进了蒙书的发展
据《唐会要·童子》载,大历三年四月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24]卷76,1399唐代科举考试对所试经书规定:《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合起来称为“九经”。[10]卷44,1160前文所言“通一经”当指此九经中的任意一经。垂拱四年(668),裴耀卿八岁中神童举,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其中《毛诗》为九经中“通一经”之经,《论语》为兼习之经,正合相关记载。唐代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也在不断调整和加深难度。宣宗大中十年五月,中书门下省颁发的一条整顿童子科条令中,明令诸道荐送的童子,对所习经文要能“精熟”,并“经旨全通,兼自能进书写”。[24]卷77,1402由于童子年龄小,学识有限,难以做到“九经”“经旨全通”,因此许多蒙书都对《论语》、《孝经》以及“九经”大义、典故进行简明扼要的改编、注解,以便初学者使用。
(四)童子科的弊端与停废
唐代童子科因为所取对象以年幼、聪慧为特点,往往需贤者发现、举荐才能被皇帝和选举机构知晓,故而童子科取士,荐举占了上风。诸道荐送童子也容易产生岁数不实、鱼龙混杂等情况,使知贡举者不易甄别虚实。广德二年(764),礼部侍郎杨绾奏曰:乡贡童子岁数越众,有失其实,怕成侥幸之路,要求暂停童子科。是年,童子科停。[23]卷640,2103至大历三年,恢复童子科,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例考试。大历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停童子科。但此后童子科并未长期停废,[24]卷76,1399不久又恢复了。因童子科的伪滥、延引、请托之风仍在继续,文宗于开成三年(838)十二月下敕停童子科,[24]卷76,1399但不久又复置了。宣宗大中十年(856)五月,中书门下奏请将童子科暂停三年,一同停举的还有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明法、明算等科,暂停的原因是上述九科取人颇滥。[24]卷77,1401-1402奏章中还特别提到诸道荐送童子的种种弊端,如“其童子近日诸道所荐送者,多年齿已过,考其所业,又是常流”;因此,奏章要求:“起今已后,望令天下州府,荐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须精熟,经旨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违条例,本道长吏,亦宜议惩罚。”[24]卷77,1402明言若诸道长吏荐送童子不实,就要给予惩罚,这也正说明了中晚唐童子科请托、虚荐、延引等不正之风久禁不止。这种状况沿续到了五代。
当然,过早地进行童蒙教育,让儿童追逐科名,贪图名利,不仅违背了教育规律,也对儿童的教育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上《条陈贡举事例奏》就批驳了童子科中出现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童子科设置的初衷是“禀神异之性”选拔“精采英奇”,随其自然,不必强求;但现实截然相反,家长往往“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限隔而游思不容,仆抶而痛楚多及”,完全是拔苗助长,限制儿童娱乐,进行强化教育,甚至加以棍棒,违背“孩童之意”,以至于孩子自身都不知为啥这样;第二,童子参加省试之际,岁数难知,年貌难辨,很少有念诵精通者,结果造成知贡举者定去留时,“家人之诉讼”纠纷不断。因此,窦仪建议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23]卷642,2116从窦仪的建议来看,童子科的设置似乎过大于功,对童蒙教育和选拔官员都不是很好的办法,这大概也是童子科在唐五代时期屡遭革废的原因。
童子科的伪滥状况,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唐代童子科对广大童子参加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吸引力。童子科虽然出现了诸多伪滥情况,但童子仍积极应举,这无疑对童蒙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科举制度促进了蒙书的蓬勃发展
早在周秦之际,童蒙教育就有了初步的发展。幼儿出生后便接受“保傅之教”,七八岁之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这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蒙学教材《史籀篇》。两汉南北朝时期,童蒙教育趋于成熟,宫廷和达官、士族之家已经普遍存在,在蒙书教材的编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蔡邕的《劝学》、周兴嗣的《千字文》等,主要是一些有关识字、名物介绍和小百科全书性质的读物,其中以《千字文》的影响最大。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唐前期在官学教育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童蒙教学为科举服务的宗旨;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蒙书较之前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蒙学教材多由综合性读物向侧重某一方面的专精发展,蒙书的内容和性质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唐代之前比较有名的蒙书《急就篇》和《千字文》是典型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读物,极具代表性;唐代新出了很多有影响的蒙书,但综合性的减少了。流通较广的综合性识字类蒙书,除了之前的《千字文》外,仅有《开蒙要训》和《新合六字千文》。而后者只是对《千字文》进行重新组织,在内容上二者并不相悖,只是在形式上由四字变成了六字而已,《新合六字千文》本质上仍是《千字文》新版。[48]40-51综合性知识类蒙书也仅有《杂抄》和《孔子备问书》。[48]165-226与此同时,唐代蒙书在专精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识字类蒙书为例,综合性识字类蒙书之外,还出现了杂字类蒙书,如《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俗字类蒙书有《碎金》、《白家碎金》等;习字蒙书有《上大夫》等。[48]10-164从目前所知唐五代新出蒙书的性质来看,以识字、名物典章、历史故事、伦理道德、家教格言、劝学等特色、类型明显的蒙书居多。
(二)蒙书除了识字、知晓名物典章和历史知识,逐渐增加了立志、灌输儒家修生、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而达到规范儿童言行,培养其志趣,使其学会为人处事、侍奉尊长的目的
唐代出现的《蒙求》、《古贤集》、《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等庶民童蒙教材,大多通过讲述历史典故、人物事迹、格言要训来给孩童灌输历史知识,通过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用忠孝仁爱等观念来规范孩童的德行。杜正伦的《百行章》则为唐代官方颁布的启蒙教材,是童蒙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集大成者。[49-50]全书以“孝行章”开始,讫止于“劝行章”,共八十四章,以忠孝节义统摄全书,多摘录儒家经典中的警句、典故而成。警句多出自《论语》、《孝经》,典故多出自《史记》、《说苑》等书。作者在《百行章》开头即言:“至如世之所重,唯学为先,立身之道,莫过忠孝。”[48]326明确了编纂意图。足见唐初社会风气颓败,忠孝不行,作者期望以忠孝匡正世风,教化天下。[48]344-345作者还极力主张以孝治家,进而以孝治乡,从而实现以孝治国。
(三)唐代科举考试重文,童蒙教材中不仅出现了诗词类蒙书,而且在蒙书编纂中还普遍存在重音韵、对偶的现象
以往学者认为宋以后的童蒙诗歌是童蒙读物的特色,尤以《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最为著名;[6]4实际上,晚唐五代以诗歌形式编写的童蒙读物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其内容往往将格言融入诗歌,对儿童的立身处世加以训诫。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大量的《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都是诗词形式的童蒙读物,充分说明了晚唐五代童蒙读物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显然与晚唐五代进士科考试重诗赋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梵志诗》在敦煌地区颇为流行,往往与《太公家教》抄写在一起,二者内容相近,充满了教训、说理、处世格言等童蒙性质的诗篇,文辞浅近俚语,琅琅上口,通俗易懂。[48]423《夫子劝世词》敦煌文书中仅保存了一件(P.4094),为五言韵语,类似于后世的劝世诗,以劝世为宗,如“生死天曹注,衣食冥司判;祸福不由人,并是神官断”,充满了宿命论的观点。这种劝世诗歌,其思想与宋代《训蒙诗》、《神童诗》中的劝世思想颇为接近。[48]439
(四)唐代科举考试日渐成熟,出现了应试范文类型的蒙书
杜嗣先《兔园策府》针对唐代常科和制举试策的情况,以四六骈文纂古今事,设问对策,分四十八门,共十卷,作为童蒙习文的范文,以便童子学习对策之精要,也是备科考的基本教材。现存敦煌文书中仅保存了《兔园策府》序和卷一,内容为“变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五个门类。《兔园策府》在唐五代流传甚广,为乡村私塾童蒙教育的重要读物。据敦煌文献载,后唐宰相冯道携《兔园策府》上朝,不慎遗留朝堂,被同僚诮之。[51-53]此事恰好说明《兔园策府》深受世人喜爱,即便身居高位,也改变不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喜好。
(五)唐代科举考试常科因科目的不同,可以选择“九经”中不同的经书应考,直接催生了唐代的“九经”精粹类童蒙读物
唐代进士科、明经科、道举、三礼科、三传科、一史科、三史科、五经科、九经科、童子科等科目都要按照科目的不同,选取“九经”中不同的经书作为必考内容,因此“九经”便成了举子学习的必备教材。但对初学的孩童来讲,“九经”不仅艰涩难懂,而且瀚如烟海,很难掌握其要领,不知如何入门。随着私学的发展,民间儿童对“九经”的学习需求日益增大,从“九经”中辑录精粹言论的做法应运而生。简言之,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对九经进行删繁节要,并分门别类加以编纂,以供儿童学习和便览,使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九经”的精粹,激发孩童的学习兴趣。于是,出现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勤读书抄》、《励忠节抄》等摘要、略抄、摘抄“九经”的通俗读物。以《新集文词九经抄》为例,该书为“训俗安邦,号名家教”的一部通俗蒙书,具有“罗含内外”、“通禅内外”的三教融合的特点。该书引经据典非常丰富,共计 89 种之多,[48]303主要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及《论语》、《孝经》为主,兼及《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充分显示了此类童蒙读物为科举服务的宗旨。特别是对《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四书内容的大量摘抄,说明开元以后道举的设立,直接影响了童蒙读物在编纂上对道教文献的重视。[54-55]《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编纂结构、体例及援引内容与《文词教林》相比,存在明显的抄袭痕迹。郑阿财先生认为《新集文词九经抄》为《文词教林》之后新编纂的童蒙读物,故《新集文词九经抄》征引了《文词教林》中的很多内容。[48]320可见,《文词教林》在当时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才被不断地重新编辑,出现了《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文词教林》等童蒙读物,这无疑是与当时科举制度的推动分不开的。
(六)唐代社会重科举的风气浓烈,蒙书中劝学应举的内容也不断加重
敦煌文书P.2564《齖书》是唐五代在敦煌广为流行的民间童蒙读物,其中有劝学歌词《十二时·劝学》云: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未得贵,由自行歌自负薪。
日出卯。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56]
又P.2952《二十时·劝学》残卷亦云:
平旦寅。□□□□未安身。奉劝有男须入学,莫言推道我家贫。从小父娘□□□,到大偻猡必越人。纵然未得一官职,笔下安国养二亲。
……
正南午。读书便是仕(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幼时入学曾辛苦……[57]
同卷《十二时·求宦》云:
晡时申。劝君交(教)子胜留银,不见昔时勤学仕,意(衣)锦还乡朱买臣。
……
黄昏戌。官职比来从此出,文章争不尽心学,有智勿令生愧悔。
人定亥。先王典籍合敬爱,若能读得百家书,万劫千生名槚(价)在。
夜半子。春榜即写才文字,朝廷上下聘词章,万个之中无有二。
鸡鸣丑。权隐在尘非长久,一朝肥马意(衣)轻裘,富贵荣华万物有。[57]
这些通俗易懂的童蒙读物,集中体现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社会底层的深远影响。“丈夫学问”、“读书”便是“随身宝”的观念已被世人接受,成为世人劝夫教子专事举业的精神支柱。在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以“写才文字”、“词章”为取士原则的情况下,“官职比来从此出”的观念已经植根于世人心中;若能以“学问”、“读书”而登科、入仕清流,便可“一朝肥马衣轻裘,富贵荣华万物有”,这已经成为共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童蒙读物还激励家道贫寒者,莫辞家贫而不学诗书,“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打破了当时的士庶概念,增强了家道贫寒者勤奋读书,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及官位的信心,足见科举制度对当时社会影响之广泛及深远。[58]《太公家教》云:“明珠不莹,焉发其光;人生不学,言不成章”;[59]24“善男不教,为人养奴;养女不教,不如养猪”。[59]26《王梵志诗》亦云:“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珠珍。丈夫无伎艺,虚霑一世人。”[60]将读书与登科、仕宦联系在一起,敦劝孩童树立以“学问”、“读书”而登科、入仕清流的观念,明确了读书人的目的,反映了科举对童蒙教育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七)晚唐五代随着家学教育逐渐向私塾、学院、书院教育的转变,家学将童蒙教育的对象从魏晋以来讲究门第转向了面向天下、四海、百姓
具体言之,就是以乡村和地域为中心的私塾、学院和书院教育,蒙书的编纂也体现了这一转变。魏晋以来士族制度得到了充分发展,士族十分注重门风、家风、家学,家学教育集中体现了门第教育的特点。为了标榜自己的门第,士族都比较注重所谓自家的“家风”、“家教”、“家规”、“家训”方面的教育,其内容无非是劝学、劝孝、戒斗、戒淫等处世的准则和规范,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典范。到了唐代,此类蒙书得到了较大发展。颜之推之后颜真卿又作《家教》三卷,可惜已经失传。传世典籍中流传较广的唯有宋若莘《女论语》十卷。但是,敦煌文书中《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的发现,为学界了解唐代道德伦理类蒙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改变了学界对唐代此类蒙书的认识。唐代敦煌文献中《太公家教》为现存最早的格言、谚语类家训蒙书,在敦煌流传极广,现存达 42 件之多。[48]440《太公家教》从古代诗书、经史等典籍中择取先贤名言、警句,适当增减,多用四言韵语编辑而成,通过劝诫忠孝、修身、礼节、劝学、处世等,达到童蒙教育的目的。其取材主要来自《礼记》、《论语》、《孝经》、《荀子》、《庄子》、《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烈女传》、《抱朴子》、《颜氏家训》、《汉书》、《晋书》、《傅玄箴》、《千字文》等书中的格言警句。[48]360
唐代道德伦理类蒙书摆脱了魏晋时代“家训”“家教”以某一姓、一宗为童蒙教育的对象,重在标榜自家门风,培养和规范本宗子弟为人处事、入仕为宦的道德伦理的局限,将童蒙教育的对象扩展至天下、四海、百姓。这反映出唐代士族衰落,小姓和寒素兴起,天下百姓均有对童蒙教育的需求,童蒙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一姓、一宗的“家教”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因此《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的作者都不敢自称某姓、某宗的“家教”,而是借圣贤为名,目的就是教育百姓童蒙,这是童蒙教育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进步。《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也有意回避某姓“家教”的问题,道理是一样的。
四、小 结
唐代科举制度在设立之初就确立了官学教育与科举选士相结合的模式,官学教育的机构和课程设置也基本上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其招收的对象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青少年,童蒙教育处于缺失状态,这就为唐代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五代社会教育体制的变迁与完善,特别是私学的兴起,为儿童教育提供了多样的教育环境,补充了国家在官学教育体制中对十四岁以下儿童教育的不足,成为唐五代儿童接收早期教育的主要途径。
唐代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尽管童子科及第出现了“滥蠲徭役,虚占官名”等负面影响,但童子科及第对个人来讲的确可以获得诸多好处,这无疑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士大夫希望子弟及早成才的心理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在童子科的影响下,中晚唐世人应举往往从自小应童子科开始,童子科不第,长大再应明经或进士等科;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童子科对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童子科未能起到选拔“精采英奇”的作用,却使童子过早地接受教育,限制儿童娱乐,甚至加以棍棒,让其追逐科名,贪图名利,违背教育规律,完全是拔苗助长;参加省试的童子岁数难知,年貌难辨,很少有名实相符者,结果造成纠纷不断,舆论四起,对儿童的教育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因此,童子科在中晚唐五代一直受到世人的诟病,屡有停废。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唐前期在官学教育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这就决定了童蒙教学为科举服务的宗旨;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蒙书也较之前代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注释:
①唐前期诸官学学生2210人,州县学生60710人。
②见英藏敦煌文献S.1291+S.1291V。
③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认为贞观年间已有神童科,确切年代不详。
[1]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04-109.
[2]侯力.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教育[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19(1):39-43.
[3]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9(4):39-46.
[4]马秀勇,王永平.论唐代童子科[J].齐鲁学刊,2001(3):127-131.
[5]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J].国学研究,1995,3:27-60.
[6]王炳照.配图蒙学十篇·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徐梓,王雪梅.蒙学须知[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1-19.
[8]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7-264.
[9]金滢坤.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1):65-71.
[10]欧阳修,宋祁,范镇,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J].中国史研究,2003(1):81-87.
[1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杜佑.通典:卷15[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58-163.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钱易.南部新书:卷丁[M].北京:中华书局,2002:40.
[18]刘清之.戒子通录:卷3[M]//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23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86.
[19]龙衮.江南野史[M]//丛书集成新编:第1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230.
[20]宋若莘.女四书·女孝经女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90.
[2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3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38.
[22]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宋本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5]计有功.唐诗纪事:卷6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994.
[26]郝春文,金滢坤.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卷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07.
[27]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8]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78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04.
[2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英藏敦煌文献:卷6[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9.
[3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82.
[31]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C]//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271-316.
[32]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J].敦煌学辑刊,1987(1):26-40.
[33]李昉,吕文仲,赵邻几,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4]赵璘.因话录:卷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2.
[35]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6]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J].敦煌研究,1986(1):39-47.
[37]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01.
[38]李昌龄.乐善录:卷上[M]//丛书集成·初编:第268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2.
[39]费成康.中国的家族法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239-241.
[40]李才栋.唐代书院的创建与功能[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1):69-75.
[41]金滢坤.唐五代的童子科[J].光明日报,2001-01-16(3).
[4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5[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9.
[43]王應麟.玉海:卷115[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25.
[44]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册府元龟(明本):卷97[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53.
[45]刘餗,张鷟.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M].程毅中,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33.
[46]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50.
[47]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86.
[48]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49]福井康顺.百行章につこての诸问题[J].东方宗教,1958(13-14合刊):1-23.
[50]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J].文物,1984(9):65-66.
[51]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J].敦煌学辑刊,1994(2):17-29.
[52]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J].敦煌研究,1998(1):111-116.
[53]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J].敦煌研究,2001(3):126-129.
[54]魏明孔.唐代道举初探[J].甘肃社会科学,1993(6):142-143.
[55]林西朗.唐代道举制度述略[J].宗教学研究,2004(3):135-138.
[56]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4.
[57]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3.
[58]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J].历史研究,2003(4):49-67.
[59]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M].台北:渊明印刷股份公司,1986.
[60]项楚.王梵志诗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83.
——五常市实验小学校教育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