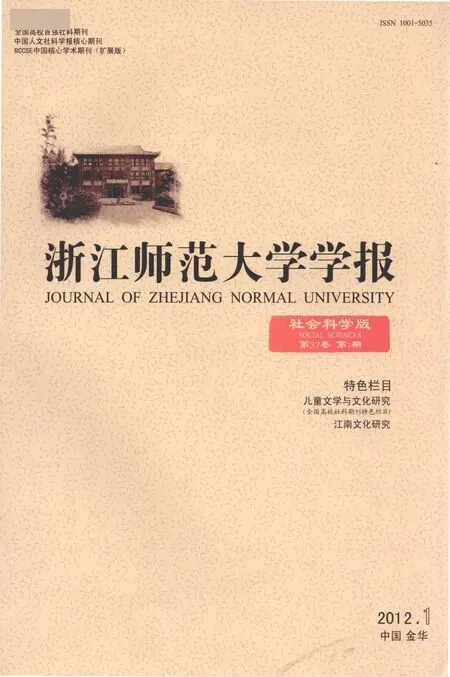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俞樟华, 娄欣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古代传记研究史上,方外传记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至于方外传记中的类传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所谓方外传记,即记录佛教徒或道教徒这一类人物的传记。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就是将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写在同一个传记里,并以类标题的一种传记形式。随着佛教、道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方外传记中的类传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方外类传作品进行分析,以此展示方外传记中类传这一形式的发展变化轨迹,从而丰富古代类传研究的成果。
一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道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相对独立的时期,崇信佛道、研读经书、学习道义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崇信与倡导,佛教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佛学也日益发达,“佛教和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关僧人和道士的传记正式开始出现”。[1]据陈士强先生统计,仅东晋时期就出现过数百种佛教撰述,其中“有关教史的记传志铭占1/3”,就是说有很多佛教著作都是为著名僧侣所立的传记。最初出现的佛教传记都是为西域来华高僧撰写的单传,如《安清别传》、《高座别传》、《佛图澄别传》等。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逐渐出现了以记载汉地僧人为主的单人传记或某一类僧人的类传,如《支遁传》、《竺法乘传》、《于法兰传》、《单道开传》、《安法师传》、《高逸沙门传》、《江东名德传》、《庐山僧传》、《东山僧传》、《游方沙门传》、《沙门传》、《法师传》、《名僧传》、《众僧传》,以及中国最早总括诸尼事迹的《比丘尼传》等等。它们有的直接以僧传命名,有的以记叙寺塔为主而附载僧人之行事活动,有的则是在记述世间的鬼怪神异故事中附见僧人的事迹,但这些著作所载僧人之事迹,或仅举一方,或只限一时,或偏重一行,或侧重赞颂褒奖,或记述简要,或繁琐杂芜,使得某一僧人之主要事迹既难完全呈现,更不能完整地反映各个时代佛教活动之概貌。在佛教传播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道教。宣扬长生不死、飞天成仙之说的道教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因此,在此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道教传记中的类传包括:葛洪的《神仙传》、刘向的《列仙传》、朱思祖的《说仙传》、鬼谷先生的《集仙传》和《洞仙传》等。
有鉴于之前佛教传记的不足,梁僧人慧皎首次总结整理编写出了能够比较全面反映自东汉至梁代高僧主要活动事迹的著作《高僧传》。此类传记载了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我国以来,至南朝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年间,二百五十余位高僧的传记,若加上旁出附见者,则约有五百人。其撰述时间之长,立传者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人类传,《高僧传》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在体例编排上,《高僧传》首次采用了类传体的形式,以科分类,计有十科,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和“唱导”等十类,根据每位僧人的特点,将他们分别归入相应的科类。如译经科,即记载从事翻译佛教经典的高僧事迹。在佛教东传之初,“法流东土,盖由传译之勋”,[2]524译经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作者将译经僧放于篇首,并且用三卷的篇幅记载了35位译经科僧人的事迹。义解科,所载都是通达佛法义理,弘化济众的高僧。本科用五卷的篇幅记载了101位义解僧的事迹。神异科,即记载那些借助于神通感应之力量,惩恶扬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扬的僧人事迹。卷九、十两卷共收此等神异高僧20人。习禅科,即记载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增长功德,还化众生的高僧。于卷十一前半部收习禅僧21人。明律科,收录明晓如来所制律法,防非止过,调练身、口、意三业的高僧。于卷十一后半部收律僧13人。亡身科,记载烧身供养佛陀,或慈心舍身护生,忘我利物,培植慈悲喜舍之心的高僧。于卷十二前半部收忘身僧11人。诵经科,所载为诵读经典有成的高僧。于卷十二后半部收诵经僧21人。兴福科,所载为行善积德,广种福田,造立塔像,树兴福善的高僧。于卷十三前部分收兴福僧14人。经师科,专指巧于转读经典和善于梵呗的僧人。于卷十三中间部分收经师11人。唱导科,专载善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高僧。于卷十三后部分收唱导师10人。《高僧传》十科序列不仅以科相从,而且以时代为序。这种序列安排和佛教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佛教的发展正是先由经典的翻译到义理的诠释和以神通传教,再到佛教徒自身修行法门习禅、戒律、亡身、诵经等的发展、完善,而转读和唱导本身就是在宋、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3]
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都有“太史公曰”,班固《汉书》每篇传记后面都有“赞曰”,这是史传作者直接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方法。以后历代相沿,形成惯例,一部二十四史,除《元史》外,皆有史传作者的评论。《高僧传》受史传的影响,也在每科之末,附有作者的论赞,称“论曰”或“赞曰”,“至于讨核源流,商榷取舍,都列于赞论之中,附于文后。而论之内容,虽各有小异,而体式大致相同:即始标大意,犹如前序;末辩时人,如同后跋。若穿插其中,嫌其繁杂,故列于一科之末,通称为论。”[2]525论赞结合,先叙大意,再辩时人,讨核源流,商榷取舍,概述本科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各科思想内涵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对僧传的总结和补充。这类评论文章,常常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当然,《高僧传》作为现存最早、最全的僧人类传,不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高僧传》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人类传,展现了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各个侧面,是了解中国初期佛教发展的基本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传中记载的五百多位高僧的事迹,他们或以传译经典、阐释义理而使慧灯长传;或以神通利物、遗身济众而使佛法深入人心;有的以精进修禅为四方禅林作则;有的则以戒律严谨而成为天下学僧之模范。这些传记使历史上高僧之德业能够得到表彰和弘扬,更为了使僧有所依仿,后人得到启迪,使佛法不断发扬光大,具有“明僧业而弘佛法”之宗教意义。梁代以后,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三十卷(一称《唐高僧传》),宋代赞宁等撰《宋高僧传》三十卷,明代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八卷,其体例大致都依据梁《高僧传》,合称《四朝高僧传》。
第二,《高僧传》是一部很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对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它记载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译经僧在佛经翻译文学方面的贡献,如卷二记载了作为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大师之一的鸠摩罗什翻译文字的方法:“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2]52主张更改以前佛经汉译的直译为意译,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其次,此书记载了许多文人和佛教僧侣的交往以及他们受佛教影响的情况,如“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2]221记载了谢灵运深受慧远佛法的影响。再次,此书在记述一些僧侣事迹时,也写到了他们的文学活动,如“唱导”部分的总论曰:“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2]521叙述南朝佛教徒利用讲唱形式宣扬教义的情形,这也经常被研究俗文学的学者引用。此外,书中的一些情节逐渐演变为志怪小说中的故事内容,例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宣验记》、颜之推的《冤魂志》中都有这种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怪之谈也杂处,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4]此时期的佛教典籍促使了后世志怪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正如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高僧传》之文化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僧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客观上为中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僧传》中涉及的佛经翻译之历史衍变及译经之规则,对于今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此时期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因佛教、道教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首要的任务在于传播佛教和道教,使更多的人接触了解佛教、道教,所以方外类传中所收入的人物都是在佛教、道教中具有较高声望、地位的僧人、道士、仙人,内容都是记载他们如何走上崇佛信道之路,如何研习教义,发展佛教理论,修炼仙丹,在佛教、道教领域作出了何种贡献。通过这些内容的描写,宣扬佛教、道教思想,普及佛教、道教教义,扩大佛教、道教的影响。
二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身变革与探索,佛教逐渐找到了在中国生根发芽的途径与适宜土壤,逐渐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佛教发展到隋唐,进入了鼎盛时期。唐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权的扶持,中国佛教之兴,始于统治者。隋唐统治者正是看到了佛教在缓和社会矛盾、稳固政权方面的重大作用才给予了佛教极大的支持。唐太宗曾说,佛教教义讲“慈悲为主”,这有利于“膏润群生”;讲“因果报应”,可以教人“积善”。主张“丧乱”之后,应令天下寺院“度人为僧尼”,在客观上保护了佛教的发展。同时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甚至出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5]的说法,可见当时佛门经济的雄厚。
此时期佛教事业的突出成就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而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中国佛教传播活动中的一项中心事业。唐代的译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据圆照撰写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所载,从唐初到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共有译者46人,共翻译了佛教典籍435部,著名的译经家以玄奘、义净、不空为代表,与东晋鸠摩罗什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西行求法,即“指汉地僧人通过丝绸之路到西域和天竺各国求取佛经、传播佛法的历史活动”。[6]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自佛法东渐以来,中国佛教教徒对教义理解不明,众说纷纭,为了解决此时期中国佛教存在的问题,有唐一代到印度求取“真经”的僧徒不绝于路,形成了一个高潮,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此时期不仅有大量的佛经从印度和中亚翻译、传播到中国,而且在中国出现了大批在译经、注经、传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僧。与此同时,方外传记也逐渐出现了专门以某一类僧侣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传记作品,重点是介绍某一类僧侣的活动事迹,总结他们的作用和影响,表彰他们为佛法的传播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其代表性的方外类传有: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唐高僧传》)。
唐义净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原题《沙门义净从西国还在南海室利佛逝撰寄归并那烂陀寺图》,共两卷,记载了唐初至义净访印期间到印度求法的46年间,中国、朝鲜、越南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卷末附有永昌元年随同前往的贞固等4人传,最后为义净本人的自传。每篇传记篇幅一般都是数十字乃至一千多字的短文,记述各人的籍贯乡里、西行所经的路线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等情况。篇中有些传后还附有四言或五、七言感叹或赞颂的诗偈。在记载求法僧西域求法的过程中,传记详细记载了求法僧在求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学和所感,其中不仅包含了众多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较高研究参考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南亚、东南亚等地的历史风俗提供了帮助。
第一,本书记载了求法僧在西行途中经过的著名寺院,如那烂陀寺作为当时印度最大的寺院以及印度第一大道场,以大乘之学为主,传中具体细致地描写了那烂陀寺的结构布局,虽然现今不能看到此寺庙的真面目,但其描写逼真地还原了那烂陀寺的内外建筑构造,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类传中还记载了大觉寺(佛陀成道处)、信者寺、新寺、大寺、般涅槃寺(佛陀涅槃处)、羯罗荼寺等著名佛教寺庙,为后代研究佛教寺庙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第二,通过这些僧人传记,我们可以整理出僧人西行求法陆海两条不同的路线,保存了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海陆交通的历史资料。在陆路方面,当时玄照、道希、玄恪、道方、慧轮等人是由长安贯通西藏地区经尼泊尔而往印度;而玄照第二次西行以及玄会、质多跋摩、隆法师、唐僧等人西行,则大概是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南道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入印巴次大陆,或者是由天山迤南的戈壁北道经帕米尔高原北面过阿富汗、巴基斯坦而入克什米尔的。由于当时海上交通已因航海术的进步而相当发达,传中诸僧泛海西行的比陆行的多。传中所载义净、明远、义朗、义玄、会宁、大乘灯、道琳等37人的西行,主要是走这条路线:由广州出发,经屯门山(香港迤北)、占不劳山、陵山、门毒国、古篁国、奔陀浪洲、军突弄山(以上均今越南沿岸)、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间海峡(今新加坡海峡)、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而到印度的航线。在记载求法僧西域求法经过古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时,作者同时也介绍了当地有关的历史、风俗等情况,这些都是求法僧真实的所见所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类传中对于各国频繁的西域求法的描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境内政权统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与邻近国家友好往来频繁的社会现实。传中所载诸僧求法的范围,除印度以外,还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以及南亚等国。如道琳、僧哲等人到过当时的乌苌、犍陀罗(均今巴基斯坦境内)、三摩呾吒(今孟加拉境内)等国,玄照、道琳等人到过当时的缚曷罗、迦毕试(均今阿富汗境内)等国,义朗、明远等人到过当时的师子国;常愍、义净等人到过当时的室利佛逝、诃陵、渤盆(均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等国。西域求法不仅增进了各国宗教界之间僧人的友好交流,而且对于增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具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传中所记唐朝遣使循陆海两道出国通好的史料,也可以补充正史之缺。
第四,类传中还记载了求法僧西行求法以因明、俱舍、戒律、瑜伽、中观等五科佛学为主要学习内容。比如玄照,即是“沉情《俱舍》,既解对法,清想《律仪》,两教斯明,后之那烂陀寺留住三年,就胜光法师学《中、百论》,复就宝师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7]10无行也是“向那烂陀听《瑜伽》,习《中观》,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复往羝罗荼寺……习陈那法称之作”。[7]182-183这些记载,对研究古代佛教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行求法是我国高僧大德为了探求佛教教义的完美,翻山越岭,横穿亚洲大陆,向外寻求新思想、新知识所展现的具体行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古代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国僧人留学海外的重要记录,不仅为研究唐代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印交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
两宋时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世俗化和平民化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总趋势,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新天地。由于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宋代佛教自身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促使了宋代佛教史籍的兴盛,无论在史籍数量,还是在内容、体裁的开拓上,都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基本奠定了中国佛教史籍的格局。[8]宋代佛教僧传,一方面在取材标准、撰述体例等方面继承了以往僧传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和佛教的发展,也在撰述方法、分类方法等方面产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僧传在两宋时期呈现出的新气象和新方向,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在古代传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众多的方外传记中,属于方外类传的作品包括:赞宁等的《宋高僧传》,集录由唐太宗至宋太宗三百余年间的高僧传记;不著撰人的《东林十八高贤传》,收录了晋宋时以慧远为首的僧人居士18人的事迹;惠洪的《禅林僧宝传》,记载了自五代到北宋政和末年81人的传记;庆老的《补禅林僧宝传》,记载了法演、悟新、怀志三人的传记;祖琇的《僧宝正续传》,记载了北宋仁宗至南宋孝宗初年约一百多年间,罗汉南至黄龙震28位禅师的事迹;士衡编的《天台九祖传》,记录了天台宗九世祖师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的传记;元敬、元复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收录了曾在杭州各寺居住的晋、南齐、隋、唐、五代、宋诸代高僧30人的事迹。
佛教发展到明清时期,居士佛教蓬勃涌起。所谓居士,即“受过‘三归’(又称三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宝)、‘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在家佛教徒”。[9]居士佛教,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运动”。[10]居士佛教自古就有,但在明清之后才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当时被誉为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祩宏就大力倡导居士佛教运动,对于在家信佛居士的研究更是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有关居士的传记也应运而生。这时期的方外类传,在明代有朱棣编的《神僧传》,采辑了中国历代佛教史传中所载的“神僧”传记;祩宏辑的《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记载了明僧慧朗、梵琦、景隆、本善、雪庭5人的小传;如惺撰的《大明高僧传》,集录南宋初至明神宗万历年中约五百年间高僧之事迹;夏树芳撰的《法喜志》,收录自西汉东方朔至元初杨维祯等历代208位名士之传记。在清代有自融撰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记载了南宋建炎元年到清顺治四年五百多年间禅僧97人的传记94篇;续法辑的《法界宗五祖略记》,记载了华严宗初祖法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5人的传记;彭际清编述的《居士传》,收录了从东汉至清乾隆年间归佛的居士事迹;彭际清的《善女人传》,则收录了自晋以来至清乾隆年间女性佛教世俗信徒138人的传记;悟开撰的《莲宗九祖传略》,摘录了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等人的传记。在这些方外类传中,《居士传》与《善女人传》代表了方外类传新的发展趋势。
清代彭际清编的《居士传》共56卷,收集了从后汉的牟融、安玄等开始到清康熙间男性佛教世俗信徒312人的传记,其收录之广,择取之严,记述之详,是记载历代居士事迹较为完备的一部书,可谓居士传记的集大成之作。彭际清认为过去专载佛门人文事迹的书,像《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以及兼带记载居士事迹的书,像《佛祖统纪》、《佛祖通载》、《传灯录》、《续传灯录》等,“所录事言,互有详略,或失之冗,或失之疏”,所以作者“节取诸书者十之五,别征史传、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视诸书倍之。裁别缀属,成列传五十余篇”。“非其真实有关慧命者,概弗列焉。”[11]428“非系于佛法,弗录其事迹。”[11]429以三公“庞居士之于宗,李长者之于教,刘遗民之于净土”[11]428为准绳,以各居士佛法的造诣以及影响为标准,详细叙述从后汉到清康熙年间在家俸佛的男性居士们入道的因缘,成道功候,期望“有志者各随根性,或宗或教或净土。观感愿乐,具足师资”。[11]428
《居士传》最大的特点,在于每篇传记后都附有作者的赞和其他编写者的按语。作者的赞,名为“知归子曰”,总结每卷列传收入居士的标准、原因、特点、评价以及影响等,表达作者对这一类人物或赞赏、或惋惜、或同情的思想感情。例如在评价白莲社123人中,认为只有7人可入选为居士。是为“诚慎所与哉”,[11]442予亦不得而称之也。在卷十六写到了将颜清臣与韦城武合传的原因时曰:“然予读公书,其于佛法信向久矣。若韦公者,其亦颜公之亚也,故合而论之。”[11]480在评价陶渊明时,认为其“志尚虽高,于道阔矣”,[11]439表达了惋惜之情。在评价昭明太子时,认为其“可谓了了见佛法者,非梁君臣之所及也”,赞赏其对佛法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天亦不能纯佑命于太子也”,[11]458表达了对昭明太子早逝的惋惜和悲痛。此外,书中部分传记之后还附有汪缙的“汪大绅云”、罗有高的“罗台山云”等按语,主要对每篇传记的观点、写法、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评价。如称赞卷一牟安支二竺阙孙谢传时“汪大绅云”:“为传中不可少之文。所记事言虽浅,然亦近实,千经万典流传。”[11]438评价卷七傅大士传时“汪大绅云”:“自家屋里人,说自家屋里话,读之通身毛孔皆笑。”[11]454评价卷十九王摩诘、柳子厚、白乐天传时汪缙认为:“三人同传而以白先生为指归,此传引人入胜处也。”[11]485这些按语,对于读者的阅读,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彭际清的《居士传》只载男性人物,但当时居家信佛的女性也大有人在。为了把这些信佛的女性事迹也记载下来,作者又另外编撰了《善女人传》一卷,共收录古今女性佛教世俗信徒138人。她们或是利用各种机缘传播佛教者;或是机锋善辩者;或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佛教,并幡然醒悟,皈依佛教;或是诚心修炼得遇灵验者;或往生净土者,大致按年代顺序排列。《善女人传》是中国佛教史上唯一一部专门搜集世俗女性信佛人士生平事迹的集子,也就是说,它是古代第一部关于女性佛教徒的类传。彭际清在《善女人传》的凡例中认为,入传的女性,其人其事真实与否,并不是他主要考虑的标准。这些女性的故事是否具有教育意义,或者说是否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是否有利于体现佛教所认可的价值观等等,才是作者主要考虑的问题。传记中的这些女性不仅是佛教徒,而且还是孝女,贤妻,良母。她们能够在很好地履行自己家庭责任的同时,又专心修行,最终得以悟道或者往生净土。佛教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可以激发人们向善,更能鼓励规范人们的德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居士传》和《善女人传》以普通在家信佛百姓的事迹为传记内容,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使方外传记有了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点。清代出现的这些以佛教居士为传主的方外类传,体现了人们对于佛教的关注已经从佛法高深的僧侣身上转移到了在家信佛的普通人身上,方外传记的中心也从如何通过高僧的事迹传播和发展佛教转移到了普通个人如何修行、如何传播佛教这一重点上来。佛教从开始进入中国到在中国普及的发展过程,也是方外传记中类传人物由重视高层僧侣到重视普通教徒的发展过程。
四
古代传记中的类传,始创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列传中,创立了单传、合传、类传和附传四种形式,以后这四种形式成了传记写作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不仅在历代史传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在杂传和方外传记中也经常使用。所以说,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就是在吸收了史传中类传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诸方面,与史传中的类传还是有明显的差异。
在记载内容上,史传中的类传不仅记载对于当时历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正面人物,例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列女传》、《忠义传》、《孝义传》等,而且记载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负面影响的反面人物,例如《酷吏列传》、《佞幸列传》、《宦者列传》、《外戚传》、《叛逆传》、《贼臣传》等。通过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记载,一方面留下某一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为后代统治提供治国的借鉴。而方外传记则侧重于记载作为传主的佛教徒或道教徒自身修行以及如何传播佛教、道教的事迹,都是对佛教和道教正面人物的描写。例如梁代、唐代和宋代的《高僧传》,都是为某一时期在佛教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著名僧人所立的传记,《东林十八高贤传》记载的是东林莲社中著名僧人居士的事迹,《天台九祖传》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是对特定地域著名僧人事迹的记载。几乎所有的方外类传都是为在佛教、道教中具有一定地位,或在某一特定地域具有较高声誉的著名僧人、道士所立的传,以此来传播佛教、宣扬道教,很少有为反面人物作传的情况。因为史传的创作目的是“善可以为师,恶亦可以为师”,所以传记创作以正面人物为主,兼及反面人物;方外传记不管是单传、合传,还是类传,都以正面表彰弘扬佛法、潜心修行的教徒为主,自然不会把创作的目光投向那些所谓的“恶徒”。此其一。
其二,在历朝史传创作中,人物类传的描写往往注重记载某一类人物在某一方面突出的特点和言行,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如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将能导民,能禁奸,能奉职循理的官吏称作循吏,传中列举了孙叔敖、子产、公孙仪、石奢、李离五人为官生涯中的一二轶事,歌颂一批修身正己、奉法循理的爱民官员,突出他们在营造一种宽缓不苛的社会政治局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班固《汉书·外戚传》记录了西汉25位后妃的生平事迹与外家状况,将涉及权力斗争的人物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传中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通过刻画后宫掌权人的频繁更换,后妃家族系统的频繁参政,以及权利角逐愈加激烈的复杂局面,清晰地呈现了后宫夺权和国家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展示了外戚登上舞台后,朝政混乱,破家伤国的悲痛结局。作者希望列此类传,使得后人通过观照西汉帝王后妃之权势起伏涨落以及王朝之兴亡变迁,得到一定的启示,为后代治国平天下提供参照与警示。而方外传记却很少涉及古人社会现实生活主题。类传中所记载的对象都是佛教、道教教徒以及世俗信佛人士,他们的生活都是围绕着佛教、道教展开,包括如何修行,如何学习佛教、道教教义,收到了何种益处,以及如何发展、传播佛教和道教。他们经历的事情都是与佛教、道教有关,所以传记中很少有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更不会大量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勾心斗角。传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姓名、籍贯、家庭情况,因何种机缘遁入佛教、道教,善学常修某一佛法理论,属于何种禅宗体系,修炼何种丹药,在某一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然后列举其人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修佛信道的事迹,粗线条勾勒出其作为佛教、道教徒这一身份的人生历程。这一模式从《梁高僧传》开始,之后的方外类传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一写作模式,并且从记载造诣较高的高僧领域延伸到了普通世俗信徒的传记中。传中佛教、道教理论以及信佛、修道的事迹记载虽然无关现实社会生活,但是这些人物却在中国佛教、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思想观念上,史传中的类传,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儒家的道德规范统筹分类记载了正反两方面各种类型的人物事迹。儒家“忠”、“孝”、“节”、“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信条影响了史传中不同类型人物事迹的分类。而方外传记的主导思想无疑是佛教、道教思想。通过佛教徒或道教徒自身修行以及传播佛教、道教的事迹,弘扬佛教、道教,促进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不管是得道的高僧、道士,还是世俗信佛的百姓,他们都相信佛教、道教拥有着无上的法力,虔诚修佛、修道,对于佛教、道教教义深信不疑。史传中的类传与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在标题的拟取、材料的选择以及评论上都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
第一,在标题的拟取上,二十四史中的类传,例如《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忠义传》、《贼臣传》、《孝行传》、《孝友传》等以儒家忠孝的观点为标准分类记载人物事迹,《列女传》、《节义传》、《一行传》、《死节传》、《死事传》等以儒家节义的思想标准区分不同的人物性质,每篇类传标题的定义上无不体现了儒家忠孝节义、仁信理智的思想观点。而在方外传记中,沙门、僧宝作为佛教术语,一些方外类传就以这些术语命名,例如《高逸沙门传》、《游方沙门传》、《沙门传》、《禅林僧宝传》、《补禅林僧宝传》、《僧宝正续传》等,此外大多数的方外类传标题都直接以记载的僧侣、道士类型为题,如记载高僧的《梁高僧传》、《续高僧传》、《明高僧传》、《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记载求法僧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神异僧的《神僧传》;记载道士神仙的《神仙传》、《集仙传》等。这些方外类传在标题的拟取上就已经鲜明体现了其崇拜、宣扬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观点。
第二,在内容取材上,史传中的类传,例如《酷吏传》主要记载那些依靠严刑峻法维护社会秩序的官吏的事迹,以儒家“仁”、“礼”等思想的标准来批评酷吏形象。《隐逸传》中对于隐逸人士的记载,体现了儒家“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隐逸思想的真谛。而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对于人物事迹的记载则主要选择与佛教、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材料。众多佛教高僧的传记,例如鸠摩罗什、慧远、玄奘、一行等大师的传记都从他们少时就具有佛法悟性的事迹写起,随后主要记载他们在遁入佛教之后修行佛法,研习佛教教义,对某一佛法理论产生的独特领悟,介绍他们在推动某一佛法理论发展上做出的突出贡献。选取的材料都紧紧围绕高僧如何修佛法,研教义,如何传播发展佛教这一中心,佛教思想贯穿传记的始终。对于世俗信佛、信教人士的记载,传记材料的选取同样与佛教、道教密切相关,他们虽然没有像高僧、道士那样精通佛教、道教教义,但他们坚信佛教、道教对他们人生命运的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与道教、佛教相关,遇到的人、物、事,或真实,或荒诞,都是佛教、道教对他们的指引、感化和改变。这些材料的择取表现出传主对于佛教的无比推崇。
第三,在对类传人物的评论上,史传中的类传以儒家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最高准则。班固《汉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依据儒家的思想,类传中所谓善恶的标准完全视对儒家道德规范实践的程度而定。[12]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3]为标准,将历史人物分为“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的上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的中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的下愚,将不同类型的人物限于九等之内,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后世史学评论家也以儒家正统的思想作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扬雄、班氏父子、谯周对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专据正经”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方外类传中对于僧人、道士以及世俗信徒的评价,当然是以他们在佛教或道教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做出的贡献作为标准,以佛教、道教思想来作为评价的宗旨,不管是地位高尚的僧人、道士,还是普通平民百姓,他们都是为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在叙事风格上,简要是史传叙事的基本要求。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4]这既是对史传作者的要求,也是评价史传叙事成就的基本标准。古代优秀的类传,都能做到叙事言简意赅。其方法,就是截取最能够反映某一类人物特点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典型性的人生片段,通过典型的事迹和个性化的言行刻画人物形象,使得类传中的人物既具有某一类型的共通性,也有各具特点的差异性。例如《史记·酷吏列传》共刻画了十名酷吏的形象,十位传主都具有共通性,即执法苛刻严峻。但是作者又通过各自的典型事件表现了他们的性格差异。如写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15]3135写酷吏宁成:“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15]3145写酷吏王温舒,杀人如麻,流血十里,感慨国家刑杀的时间太短,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15]3148司马迁对于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刻画入微,抓住了每个人的个性去塑造人物形象,在共性之中突出了个性。
与史传注重直书实录,言简意赅不同,方外传记以记载佛教、道教人物在传播和发展佛教、道家过程中遇到的神异、惊险、荒诞的事迹为主要内容,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不求确凿无疑,传记内容中夸大、虚构的故事较为普遍。例如玄奘西行求法路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奇异的事件,以及对于梦境的描写,都存在虚构、夸大的成分。在情感表达上,方外传记中的类传带有强烈的佛教、道教崇拜倾向,认为佛、道具有无边的法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都可以克服,对佛教、道教完全信服。在叙述过程中,唐代之前的方外类传平淡简约,情节缺乏波澜,以一种或轻松或幽默的口吻讲述佛教、道教故事,宣扬佛教、道教的崇高地位;唐之后,方外类传则更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传奇性,特别是西行求法的高僧传记,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口吻讲述在传播佛教、道教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传奇故事,展示佛教、道教无所不能的法力。在人物塑造上,高度的程式化和概括化让人物的共性大于个性,不同的人物给人以雷同的感觉。对于某一领域的高僧,他们都是精通佛理,历经艰难险阻之后终于修成佛法,得到了众人尊敬,例如慧远、释道、玄奘、鸠摩罗什等;对于世俗信佛、信教人士,都是通过普通生活中所遇到的奇异事件去表现佛教、道教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性,每个人物只有身份地位的不同,经历的事件却都是大同小异,对于佛教、道教也都是无比虔诚。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中国古代传记中一个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传记形式,一方面,作为中国佛教、道教史籍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刻画了众多在中国佛教、道教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高僧、道士形象,以及在传播佛教、道教思想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世俗教徒,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兴衰、官方的宗教政策、宗派发展、宗教人物、宗教建筑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描写和勾勒。这些方外类传作品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道教史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和道教发展、传播状况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文献本身,这些方外类传作品中对于一些史事的记载往往比正史更为详细,起到了补充正史文献的作用。此外,方外类传还保存了大量现在已经亡佚的诗文集、方志等史料,对于后代文献的辑佚、补遗、校勘、纠谬等工作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起到了“比事质疑与补充”的作用。同时方外类传中某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情节也成为了后代众多文学作品的写作素材,为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01.
[2]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方梅.《高僧传》艺术论[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3.
[4]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8.
[5]刘昫.旧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80.
[6]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9.
[7]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M].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9]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69.
[10]潘桂敏.中国居士佛教史(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
[11]彭绍升.续编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居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3.
[13]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5.
[14]刘知几.史通[M].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2.
[1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