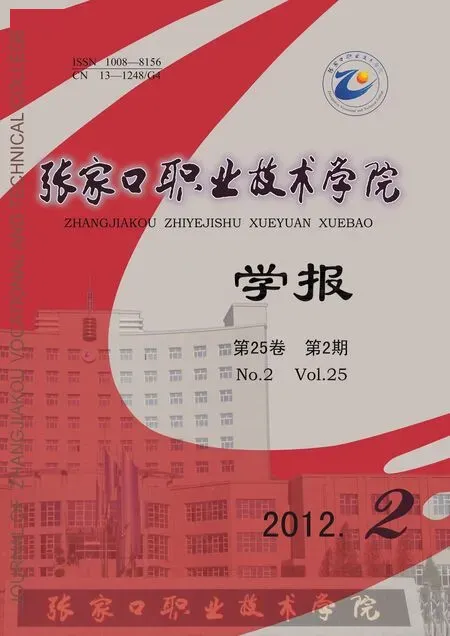“松”的文化意义初探
韩起英
(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天津 300387)
语言在发挥其重要的交际作用的同时,还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种种发展与变迁;其中以词汇这一要素反映最为鲜明。研究语言中的词汇系统,往往会发现,词语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迅捷反映使得其承载的意义异常丰富,这即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词语的文化意义。对此,苏宝荣曾明确论述:“词的文化意义和语言意义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词的语言意义,是指以概念为核心的词的基本意义及由语言本身因素所形成的派生义;词的文化意义,是指词在特定社会文化交际背景下所获得的意义。……词的文化意义,需要联系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解释清楚,光从语言本身去说明,是难以奏效的。”[1]汉语使用至今,诸多词语历经几千年的时间,在本身的语言意义之外,往往衍生出具有独特民族气息的文化意义。以“松”为例,《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中“松”字头下有关于“松”的若干条目:“松花酒”、“松明炬”、“松庭”、“松友”、“松心”、“松性”、“松契”、“松格”、“松鹤”、“松柏之志”、“松柏寒盟”、“松筠之节”、“松柏后凋”、“松乔之寿”等等。这些词语的形成反映出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进程中,“松”这种植物,由深入古人的日常生活到衍化出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流变,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时映射出古人独有的一种价值观念。
一
上古时代,“松”这个词语即已用来记录这种植物,它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可以找到“松”的身影。今天可见的古代典籍中也有对“松”的记载,如《诗经》中《卫风·竹竿》:“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大雅·皇矣》:“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鲁颂·閟宫》:“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商颂·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等。“松”是《诗经》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语,其功用已经不是对这种树木的简单记录,从中或可看出“松”的用途——制造小舟及椽子;或可作为“比兴”手法;或可看出古人对松的端直高大所进行的反复赞美。古代地理奇书《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也有记载,“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卷三《北山经》载“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卷五《中山经》载“荆山……其木多松柏。”其由于高大端直而成为海岛上承载日月的象征,也由于与古人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而逐渐产生文化上的审美意义。总之,“松”的意象很早就出现于古人的意识中,且因为“松”在古人生活中的功用及生在高山的物性,使古人自然产生了对“松”的情感与态度——褒扬。这在《小雅·天保》中表达得已很明确:“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郑玄笺:“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青青相承,无衰落也。”以至今天流传下来“松柏之茂”这样一个词语来比喻长青不衰。而《尚书·禹贡》中记载:“青州厥贡:岱、畎、丝、枲、铅、松、怪石。”[2]彼时,青州松木以树木的身份被古人列为贡品。抛开当时科技不发达导致古人认识上的局限不论,可以看出“松”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其后,至春秋时,古人对“松”的自然属性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如《国语》卷十四《晋语八》:“榣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卷十五《晋语九》:“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松”择地而生,生于高山,不惧干旱贫瘠,只怕水湿肥沃。因其自身这种自然物性呈现出一种坚韧,是以在古人看来这恰恰是一种个人情怀的言说,因而“松”逐渐地走进古人的认知视野。
二
孔子于《论语·子罕》中有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圣人率先旗帜鲜明地赋予“松”文化上的含义,以“松柏后凋”之意象征君子坚贞高洁之性。词语“松”的这种文化意义的形成与儒家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儒家思想提出格调极高的理想人格——“君子”。在这一做人的终极追求上,“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荀子》卷二十《法行》)这里,孔子明确提出“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这一衡量君子德行的重要标准,并以“玉”为喻,形象指出君子应具有“仁”、“知”、“义”、“行”、“勇”、“情”的品性。
“君子比德”观念一经提出,即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及先秦儒家以自然物譬喻寄兴、托物言志、感物兴怀,借以标榜“君子”应具备或追求“仁”、“义”、“礼”、“智”、“信”等美好道德品质与高尚精神人格。
“松”作为汉语植物词中的一个,其语言意义为“常绿乔木,叶针状,耐严寒,不畏干旱与贫瘠,适应性极强。”“松”的这种物性恰恰吻合了儒家学派的“君子比德”观念,于是“松”苍翠不凋、不畏严寒的特征很自然地被用来类比君子刚直不屈的人格,从而影响后世观念。比如《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松柏后凋”条下所引语料:南朝梁元帝《遗周弘直书》:“京师搢绅,无不附逆……唯有周生,确乎不拔。言及四军,潺湲掩泪,恒思吾志,如望岁焉,松柏后凋,一人而已。”南朝·梁·沈约《修竹弹甘蕉文》:“非有松柏后凋之心,盖阙葵藿倾阳之职。”《陈书·袁宪传》:“今日见卿,可谓岁寒知松柏后凋也。”皆以“松柏后凋”来比喻志士在艰危的境况中奋斗到最后。
以松比德的儒家观念下,“松柏”、“松筠”等词语出现在儒家的其它典籍中并延续下来。如《礼记·礼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松、柏、竹皆长青不凋,象征着儒家倡导的人格上的志操坚贞,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作比,提出人格上的高尚追求。而《荀子·大略》中的“松柏经隆冬而不调,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贞矣。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则进一步以“松柏”来比喻君子。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在“松”的“经冬不凋、蒙霜雪而不变”的自然属性上找到了共鸣。
先秦时期,儒道思想并行,但在“松”的自然物性与君子德行间的契合这一观念上是统一的。《庄子·让王》:“临难而不失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也是借助于“松柏”外在的不畏霜雪、四季常青之特点来赞美人的道德情操。《庄子·德充符》中有“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之语,因松柏之四季常青、高大端直得以与人君尧舜并称。这种对“松”的崇尚在封建社会有更为极端的表述,如《梦书》中更是直接以松为人君:“松为人君,梦见松者,见人君也。”[3]使得“松”在国人心目中获得了其它树木难以企及的地位。以至于李时珍说:“按王安石《字说》云‘松为百木之长’。”[4]
无名氏《爱松说》中,“大抵松之为物,极地气不能移,历岁寒不为改,大类有道君子。顾当其始生,困蓬蒿,阨牛羊,摧折于斧斤者,往往而是。惟托根深山大壑,苏之以风雨,照之以日月,笼之以轻烟薄雾,而又饱饮雪霜,延历岁时,然后翠蕤摩空,铁干拂汉。虬掀鳞射,夭矫扶疏为故国伟观。良亦不易矣,爱松者当何如珍护耶。”对“松”高洁正直的品性进行了放达快意的抒写。松的君子比德意蕴亦可见一斑,是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
松性比德,在这一观念影响下,有关“松”词汇上的文化意义逐渐丰富起来。后世典籍中零星记载了与“松”有关的一些典故。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即有记载:“(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另据宋范镇《东斋记事》(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后汉应劭作<汉官仪>……盖松柏在泰山之小天门……五大夫盖秦爵之第九级……”按:秦时定爵位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为大夫之尊。时至今日,泰山“五大夫松”依然挺立,诚为木之尊者也。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有记载:“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枯。”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朝真观九星院有三贤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阁老妓以丽水囊贮香游之,不数日松皆半枯。”“松”以君子之性超然于世,高洁正直可见一斑,不容凡俗淫秽亵渎玷污,否则毋宁死。
三
收入《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与“松”有关的还有“松性”、“松菊”、“松友”、“松竹”等词语,并引用了语料来源。南朝·梁·江淹《知己赋》:“我筠心而松性,君金采而玉相。”句中以“松竹”明志,抒发自己如松柏样的坚贞秉性。晋·陶潜《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松”与“菊”不畏严寒,诗人以其自喻坚贞节操。《南史·张冲传》:“房长渝谓孜曰:‘前使君忠实昊天,操愈松竹。’”文中以“松竹”为喻,品评节操坚贞的贤人。南朝·梁·陶弘景《解官表》:“今便灭影桂庭,神交松友。”表面看陶弘景以松为友,实指其隐居避世之念。从语料记载时间来看,这些词语大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漫长黑暗、战乱频仍的时代,社会现实异常残酷。这一时期,残酷的政治环境使得魏晋士大夫失去安身立命之所,无拘无束、出世阔达的庄老精神提供了乱世下魏晋士人重新审视与肯定自身价值的契机,人格境界由对“君子”的追求转而向个性风采与自然人格相融合的方向发展。在人生无奈中,士人趋向庄老自然任性的精神追求,以玩世不恭的士人心态对抗畸形的黑暗社会,自然山水不再是“比德”观念的投射,而是压抑的士人精神徜徉之所在。自然界中的“百木之长”——“松”卓尔不群,合乎魏晋士人蔑世的操守与心态,是以其以“松”明志,以“松”自比、自喻喻人。
同时,政治环境的黑暗与压迫使得士人迫不得已不问功名与时事,转求安身保命,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彼时,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道教形成,在其“自然天道观”的影响下,时人开始追求长生不老,进而祈望得道升仙。“松”因其四季常青,经冬不凋,所以成为当时人这种精神追求的首要寄托。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第一百九十七卷《松部》引《玉策记》:“千岁松树,枝叶四边披起,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又引《抱朴子》:“天陵偃盖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与天齐,其长地等其久。”“松”的寿命被魏晋士人夸张到了极限,由“松”的如天地般长久的寿命转而希冀个体生命的延续不老,其后认为服食松叶、松实、松脂等便能飞升成仙、长生不死。《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有“松术”条,释义:松实和术。古人认为食之可长生。所引语料:《南史·隐逸传上·宗测》:“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薛萝。”《北史·艺术传上·由吾道荣》:“道荣仍归本郡,隐于琅琊山中,辟谷饵松术茯苓,求长生之秘。”从记载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人开始食松以求长生。
《魏书·释老志》卷一百一十四:“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这里,对“饵松脂,不食五谷”的罗崇之“立坛祈请”,已经出现了“仙化”的苗头。
葛洪《抱朴子》(见《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第一百九十七卷《木部》)云:“上党赵瞿病癞。历年,垂死,其家弃之,送至山穴中。瞿怨泣。经日有仙人见而哀之,以一囊药与之。瞿服百余日,其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再过之,瞿谢活命之恩,乞求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山中便多此物。汝炼服之,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长服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涉险终日不困,年百余岁,齿不坠发不白。……后入抱犊山成地仙。”这里,借凡人故事言说一己情怀,宣扬了道家的“食松成仙”思想。
魏晋乱世,士人摆脱儒家思想束缚,转向求仙、成仙,仙道思想盛行。而“松”确实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皆可食,松叶、松皮、松节、松子、松脂等也确实有疗疾奇效,这就更加促成了当时人们希望通过“食松”而达到“成仙不死”的追求。关于“松”的这种词汇文化意义的形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或许是很好的注解:“凡物长久则灵,则贵。”
参考文献:
[1]苏宝荣.词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与辞书编纂[J].辞书研究,1996,(4):148.
[2][3][4](清)陈梦雷 编纂,蒋廷锡 校订.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松部[M].四川: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出版,1985.66743,66793,66745.
[5]四库全书·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六十八·木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47(1-7).
[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