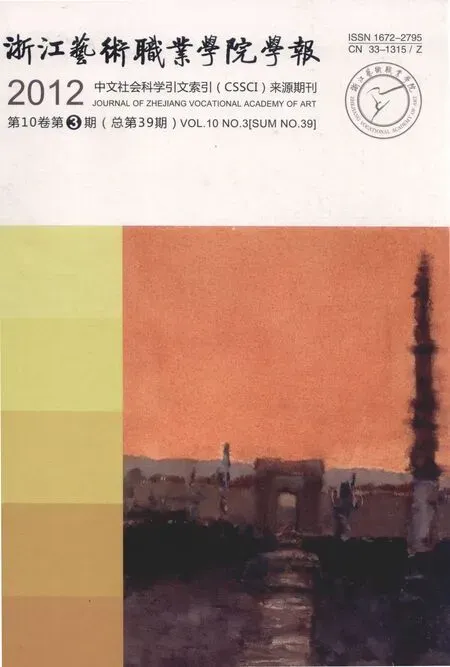中国古典舞基本范畴“变”与“韵”的审美分析
李 曼
对于中国古典舞而言,审美分析的基本范畴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由于舞蹈本身是动的艺术,是用肢体表述情感的艺术,又是经过舞者的表演、观众的欣赏才能够实现,因此,舞蹈具有时间性、流动性、明确性。中国古典舞有自身独特的审美形态,这种独特性使其区别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对中国古典舞进行范畴的研究,理论视角是基于叶朗先生的关于审美形态的相关论述。
叶朗先生认为,对于审美形态的研究,最好从文化学的角度,把不同的审美范畴看成是文化的“大风格”,……把审美范畴研究纳入文化形态之中,而将形而上的所谓美的本质问题“悬置”起来,回到文化的审美现象上去。[1]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中和、雅俗、气韵、意境等范畴,是中国人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在长期审美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基本审美形态。
中国古代的老庄思想对中国古典舞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庄的自然论影响到中国古典舞审美和创作上的自然化倾向;二是庄子“游”的思想影响到中国古典舞追求一种“逍遥”(庄子语)之境界。这种思想促成中国古典舞动作求“变”的内在驱动力,由“变”产生无法穷尽的丰富;佛教中的“空灵”观影响到中国古典舞身体对“韵”的强调与追求上,韵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境界,这种韵是中国古典舞身体表现中自然而然带动出来的,对韵的把握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作品的意境。在佛教影响下,中国古典舞在意境上追求一种“空灵”的玄妙之境。
从“变”与“韵”两个范畴入手对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形态进行研究探讨可见,中国古典舞的“变”与“韵”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在中国古典审美精神影响下舞蹈本体的反映,也是对古代人生境界的感性显现。
一、中国古典舞基本范畴“变”的审美分析
(一)“生生之谓易”
老子和庄子是智慧的,他们看到了万事万物必然变化的规律,对于这种规律人们无法回避,所以只有超脱,只有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使心“游”起来。老庄的精神超脱与精神自由,表现在艺术上就是与不变的永恒的道相对应的现实的变动不居。
艺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在变动中生存和发展,正所谓的“生生之谓易”。“变”是舞蹈得以发展的内驱力,因为舞蹈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人体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身体运动形式。舞蹈动态就是在不断变化中丰富和发展从而完成对心意的抒发。在所有艺术门类中,也只有舞蹈能够有这样的功能,能够让人们在此时此刻感受到变化,感受到透过表面变化之后深层次的底蕴。
早在老庄之前,《易经》中就记载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动”“变”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所谓“易”,就是“动”,就是“变”,“生生之谓易”。万事万物都在变,唯有“变”不变。“变动”是万物的基本属性之一,而显现这种“动”与“变”,就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旨趣。舞蹈本身就是依靠肢体的节奏动律变化来进行艺术的想象与创作,中国古典舞秉承着这样的哲学理念与艺术传统,自然也会在舞蹈的时空变化中展现出中国人对于生命、宇宙的变动之道的理解。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也就是一切都有可能![2]正如舞蹈理论家叶宁先生说:“在美的舞蹈中,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着另一个形象,每个形象都凭着它特有的个性而富有生命。”[3]正所谓“变”实现了舞蹈发展的本质。离开了“变”就无从谈起舞蹈动作,也就无法成就舞蹈作品的产生。
袁中道认为文学艺术是在不断变化中前进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皆不及知。”(卷一《花雪赋引》)袁中道在这里指出了艺术发展的规律,通过不断的发展变化使得艺术生命力得以延传。[4]382中国古典舞讲求形上的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瞬息万变,这一点恰与袁中道所说相同:“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4]385例如,在中国古典舞剑舞中,舞姿动势富于多变。它不是一味地追求均衡和对称,而常常是斜中寓直、奇中求正,在不平衡中求平衡,在多姿的变幻中求统一,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中产生多变,从而使动作呈现一种闪转腾挪、纵横往来、起伏跌宕之感,同时造成了生生不息的空间层次和方向位移。如今,中国古典舞创作在舞蹈语言、运动路线等方面已经开始打破此前固有的动作轨迹和模式,在传统的平圆、立圆、8 字圆的运行路线中发展变化,通过突破既定思维,实现顺势或逆势衔接、空间上的高低变化、动作衔接上的不断衍生等,这些方式方法的运用是从身体“变”的角度实现新的传情达意。
(二) 中国古典舞中“变”的前提——“势”
“势”体现了华夏民族对于人类社会和宇宙万物的一种理解: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势态格局中以某种节律进行着不得不然的运动,这种运动有不可穷尽的变化,似乎又向着对立面转化又周而复始的循环趋势。这“势”以动态的形为依据,体现着运动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兼有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内涵,或者说有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古人的意识中,势态的格局及其运动趋势、时机,事物的位置、力度、声威、倾向、控制范畴皆可称“势”,或者由“势”使然。[5]650
古代艺术的“势”以展开过程的疾徐、收放、开合、隐显、集散、奇偶等变化方式表现出特有的节奏,以此冲击和影响审美主体生理和心理的节律。比如,“起势不凡”可以先声夺人,立即吸引住欣赏者;“蓄势”不仅积累了力量,其引而未发、居高临下的势态强化了无形的威压;起伏贿选之势能形成感情、心理的推进层次;戛然而止常有“辞已尽而势有余”的效果;首尾呼应和“起、承、转、合”式的展开又给人一种意象完整的心理满足。[5]653“势”在舞蹈中体现在身体运动的重力方向性的控制上,也是中国古典舞“欲前先后”“欲左先右”从反向运动作为开始的基础。
势有顺有逆。顺指其运动的方式和取向与审美主体的心理倾向或思维习惯协调一致,使观照者有淋漓畅快、意气宏深的感受;逆则是其运动方式和取向与观照者的心理倾向或思维习惯相违背相抵触,于是产生紧张和冲突成为审美心理的主导方面。中国古典舞动作与动作的衔接也分为顺势衔接和逆势衔接,顺势衔接顾名思义是就势而发展动作,没有破坏动作游走的路线和动势,顺势而行在中国古典舞中最常见;逆势衔接是指动作的衔接出其不意地发生逆转,增加了动作的不可预知性,从而让观者感受到变化的奇特与巧妙,逆势衔接做得巧妙也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二、中国古典舞基本范畴“韵”的审美分析
(一) 中国古典舞之“韵”
“韵”字大致出现在汉魏之间,自晋人开始“舍声言韵”,在唐代非常通用,在宋代流行于口语之中。“韵”的本义是“同声相应”,即声音的合拍、和谐和有节奏感。但历史上人们对于“气韵”之“韵”的解释很少将它看做音韵、声韵、韵律。宋代范温在《范潜诗眼》里提出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他认为“韵者,美之极”,“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
《中国美学范畴词典》中对韵的解释是“一是指和谐、清雅的声音,即韵律之韵;二是指形象有超形象的意味,尤其是那种幽微淡远的意味,即韵为之韵。”[5]162
韵从本质来看,其一,美学形态上,它属于阳刚之美相对的阴柔之美;其二,在审美层次上,它属于同形式美相对的意蕴美,超越了悦目、悦情而达到了悦神的最高层次;其三,在与人生的关系上,它既是对外在人生的远离,又是向内在人生的深入;最后,在哲学基础上,它是庄学、玄学,尤其是禅学共同酝酿、层层积淀的美学结晶,而距传统儒学较远。中国古代艺术推崇“气韵生动”,主张虚实相生,力图建构静穆与飞动辩证统一的艺术时空,将空间导向无限,将时间引入无穷。[5]170由于这样一种审美倾向,中国艺术往往重视“超以象外”,即是指不被艺术作品表现本身束缚和局限,而是通过想象,把作品内在的思想内容发掘出来。因此,艺术作品的“韵”具有模糊性的特征,这种模糊性给予观者以极大的、自由的空间,观者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把握作品的韵味,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中国古典舞的“韵”表现为淡化舞蹈动作的形式内容,突出其包含的精神内容,把韵当做神来用。编导在创作中国古典舞的剧目时,内容题材是思考的前提,通过动作体现古典舞特有的神韵和要表现的人物性格气质才是编导,特别是古典舞编导把握的最核心的内容。古典舞不同于芭蕾、民间舞和现代舞,它除了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之外,更含有广博深刻的思想内涵,往往一部成功的古典舞作品,精神之韵的体现要大于舞蹈形式内容本身。所以,中国古典舞的美正是体现于精神之韵的外化。
宗白华认为在中国的绘画、戏剧及书法里,“都贯穿着舞蹈精神,由舞蹈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宗白华这里指出的“由舞蹈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就是指舞蹈的气韵。在舞蹈动作之间体现的是动作形象,但是形象背后却是情感的表达,因为情感无法用言语说出,正所谓的“言不尽意”,所以,用语言无法表达的那部分就是舞蹈展现给人们的深邃的“气韵”。
(二) 以情带“韵”
情在舞蹈表现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超越了人类普通的情绪,舞蹈外在的形式美都是由内在的情感带动而发的。在中国古典舞中除了情感自内而发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以情带韵。这种情含蓄蕴藉,浑然天成,完全符合“言有尽而意无穷”。
韵更多地偏向人的情感意味,指生命力中的那种内敛的柔韧。《乐记》将舞列为“本于心”的艺术,即是由诗、歌引申而来。舞蹈将歌、诗的情感灵魂附之以形体直观地呈现,因此产生了悦目娱心的特殊魅力。《乐记·乐象篇》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是在诗、歌、舞的三者对比中揭示舞蹈的独有审美特性的。这里的“动容”是舞蹈的表演主体在作品的表演中动其形容,也就是把处于真情使动的形容、英华发外,展现给观者,这是舞蹈的特性所在,是诗与歌都不能实现的审美表现。
黑格尔说:“因为心情、情感尽管都是精神性的和内在的,却和感性的肉体的东西永远有一种联系,所以它们可以从外表方面,通过肉体,通过眼光、神色或是较富于精神性的音调和语言,把精神的最内在的生活和存在揭露出来。”[6]舞蹈形象因为有准确、精练的舞蹈动作和舞蹈技巧,同时又有舞者内心的情感诉说,所以舞蹈形象可以说是具体生动的。中国古典舞以体现古典审美精神为己任,它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展现。很多优秀的作品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作品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能够唤起人们心灵中的美感。所以,中国古典舞可以说比中国其他艺术来说,更能够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气质。所以说,理之于舞,如盐溶于水,又味无痕,性存体匿。艺术作品作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产物,它的和谐既体现了造化的生命精神,又体现了主体情感的和谐。物我同一,才能使作品生气灌注。傅毅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激楚》《结凤》《阳阿》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确实,乐作为一种起于心源的东西,不管它在歌与舞的层面如何外化为身体性的表现,就其作为音乐存在本身而言,却无法像舞蹈一样直接诉诸感性形象。[7]
传神写照通过气韵贯穿在中国古典舞之中。“韵”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旷放之美,而这种美是留驻于人的形象之间,从形象中可以看得出来。以玄学为基础的作品,从超俗方面去加以把握,其风格当然是淡的,这正是此处所谓的韵了。气与韵,都是“神”的分解性说法,都是“神”的一面;所以气常称为“神气”,而韵亦常称为“神韵”。宗炳曾说过:“夫以应目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8]在观察的基础上,用主观感情、思想和情绪去融会大自然的山水,光凭视觉是不行的,还得依靠“心”的思考和体验。以意带韵的身体动态语言传神地营造了中国古典舞的雅致与格调。
三、结 语
受道家“游”的思想影响,中国古典舞讲求“变”,这种“变”是对自然的一种复归,也是作为舞者自身体“道”的一种方式。在变化之中寻找自由,在变化之中释放心灵,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追求。
在道家自然观和佛教“空灵”观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古典舞讲究通过外部动作表述内在的“韵”,这种韵有两种体现:一是来自于舞者自身的动作表现,就是动作传达的内在神韵;另一种是源自编导对整体韵味的把握与阐释上,往往表现在对舞蹈整部作品创造出空灵的意境,带给观者无尽的遐想,从而获得美的审美体验。
[1]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
[2]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1):76.
[3]叶宁.舞论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57.
[4]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成复旺.中国美学范畴词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6]黑格尔.美学 (第2 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01.
[7]刘成纪.汉代美学中的身体问题[D].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5.
[8]宗炳.画山水序[M].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