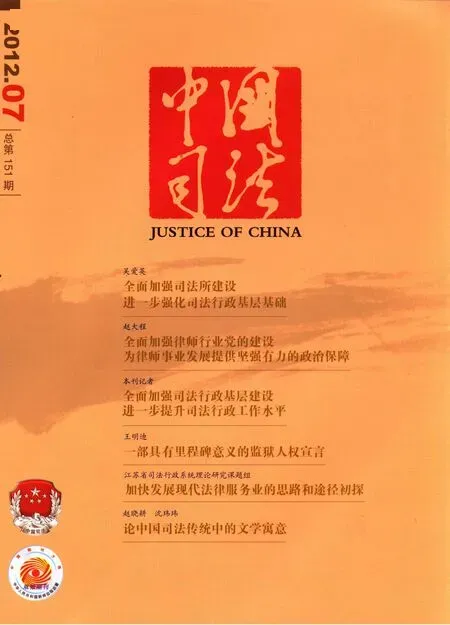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文
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2)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文
一、文人知识与诗性裁判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①转引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文官治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士人治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应然之道,经邦济世乃是文人士子的最大抱负,而通过文官进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文官的知识教育中, 《诗》位列第一。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也正是文人知识背景的变迁过程,这些文学样式都是具有诗性的。历来中国士子为官的资格,不在于是否接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练,而在于是否熟读经史,工于文章,科举取士也是首重文章的,因此士人文章大体上都是诗意盎然的。其结果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判决便具有了一种别样的风貌。虽然它们也像古今所有民族的法律判决一样叙述事实,适用法律,但同时又是文人作品,具体而言都是诗性作品。它们的式样一面受一个时代文风的影响,一面也反映出作者个人的文学趣味和修养。因此,这些判决被称之为“文人判”②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虽然有些判语十分注重文辞,近乎于文字游戏,诗赋的工拙有时也成为影响判决的一个因素,但无需置疑,诗是可以为治的。在古代的社会治理环境中,诗不但是文艺的一种,更兼有伦理的和政治的功能,“以诗刺恶”的经典也一直传承到了近代。而自先秦已降,礼从俗③《慎子·逸文》。,诗亦源自俗语,诗或许最初就是礼 (法)的表达载体。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文字被统治阶级所专有,统治阶级利用文字以教化百姓,因此,文字必须具有通俗易懂的优越性才会被用作传播的载体。于是,统治阶层将来自不同地域的诗歌,不同功用的诗歌组成一本诗集,很好地兼顾了官方文字和通俗之语的特点。《诗经》中的《国风》就是最为明显的体现。《国风》歌谣本身就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用来说明道德哲学的准则和政治学的准则,具有教化之意④[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因此,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⑤《论语·为政第二》。”《诗经》通俗简约,让人遐想的特点自然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但在教学传道的过程中,学习兼具内容和流露的《诗经》必须以礼和乐来约束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方可“思无邪”。只有对礼的探求才是对《诗经》文本的深究,乐又是根据礼仪而订定的,所以在掌握礼仪后才能学习相配的乐曲以巩固所学。因此,《诗经》本身可以被视一部修身齐家治国之作,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具有极大的延展性。治国之人希望从中得到明示,治学之人期望从中得到开通,进谏之人期盼从中得到证据,普通之人期待从中得到愉悦⑥葛兰言认为学习《诗经》不仅是在了解一个民族的过去,也是在了解它的王国政治史。从诗歌诞生,到被采集整理,然后加以意义的教化使其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最后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部分,这是《诗经》逐步象征化的过程。在《诗经》中,不仅仅是祭祀宫廷乐曲才具有象征化的解读。在田园诗、爱情诗和山川歌谣中同样如此。参见[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71页。。
历代读书人,平日饱览诗书,一朝服官任事,自然将平时所学用于政事。《诗经》之传统被发扬光大便是理所当然。虽然古之治道内容宏富,古人治国自有制度,但诗的特殊应用却也是这个政制安排中的一项⑦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第200页。。尽管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士人是仅受过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们接受俸禄,但没有任何行政与法律的知识,只能吟诗挥毫,诠释经典文献⑧[德]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第127页。。这一过分的评价很可能是韦伯文人相轻和西方中心的心态所致。不过,黄仁宇也认为,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恰恰是中华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一个困难。其结果将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⑨[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9页。”在黄仁宇看来,在古代中国文人是难以胜任治国重任的。由于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很难清晰界定,所以昂格尔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摆脱统治者顾问身份的可辨认的法律职业”⑩[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第92页。。由于长期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以及诗文写作技巧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从而极大地妨碍了人文知识与法律知识的分化。因此,入仕为官者并非法律家,他们对法律知识通常没有专门的研究⑪贺卫方:《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近代化》,载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第183页。。 “舞文”和“弄法”才会常被连在一起,担当司法职能的古代士人常被认为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则乃至精神,其司法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传统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实际上已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经学和礼学;而读经过程中对经典语句的考据辩析方法,在为官断案时对律条的引用解读与选择,其实从逻辑方法上并无多大的不同;以此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科举以外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诸如观政和候补,担任游幕,尤其是“官箴书”等——来弥补“技术”知识的不足。由于古代案件类型和法律条文比较简单,加之幕友的协助和审转程序的设计,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案件的审理工作⑫徐忠明、杜金:《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千余年来的超稳定性都是在文官的治理系统下维系的,通过文官的社会治理是有效的。
自隋唐确立科举取仕以来,诗文一项一直是入仕测试的重点。唐代铨选官吏讲求“身言书判”, 《古今图书集成》铨衡典卷二十二载: “唐吏部所试四者之中,以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皆可以此觇之。”所谓“文理优长”之“理”,主要体现在“通晓”事之理和“谙练”法之理两方面,事理和法理同属于“理”的范畴。但实际操作中,重“理”这一最初的设想却转向了重“文”这一面。唐代吏部考判从“理”到“文”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据《通典》卷十五所载: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以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寝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这三个阶段的难度是逐步加大的,其目的很明显,主要是为了在举子众多的情势下能够有效地选拔人才。这些要求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入仕者若想依法办案,则并非难事,难者在于深谙义理,融事理和法理一体。简言之,对熟读经书礼仪的士子来讲,读律识律用律并非难事,高境界者在于集情理法之大成。这是“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古训所在。而判决书的制作更应如此,因为“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既要“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还要说理深刻,即“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既要逻辑井然、论证缜密,即所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无隙可击”,“辞共心密,无机可乘”;还要以礼服人、以理服人,即所谓的“词深人天,至远方寸”,“阴阳莫贰,鬼神靡遁”⑬邱本:《法官的“身”“言”“书”“判”》,《人民法院报》,2004年6月2日。。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唐代判词中,张鷟的《龙筋凤髓判》明显属于第一阶段,白居易的判词基本属于第二阶段,但却保留了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张白二人均能通晓律文,所做判词也切合律意⑭霍存福:《张鷟〈龙筋风髓判〉与白居易〈甲乙判〉异同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2期。。这也正是二人判词流传至今的原因。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判词在唐代已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当时发展成熟的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⑮苗怀明:《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宋元时期“说话”的文学传统是书判体公案小说的渊源。“说公案”就是判词和“说话”结合而产生的新形式,它标志着“公案小说”正式诞生。到了明代,判词与公案小说进一步的结合,催生出了书判体公案小说。它在融法律文书于小说方面的努力更加自觉:不仅保留若干文牍,就连原、被告的诉状和主审官的判文在各篇中一一罗列,并且行文上也用标准的法律文书格式。书判体公案小说并非纯正的公案小说,倒有点像法律知识方面的通俗读物⑯杨绪容:《明书判体公案小说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体演变》,《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就此而言,书判体公案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通过诗化的判词“立言”的志趣。它本身具有文学样式,富有韵味,而且通俗明快,有口皆碑,因此,它对于法律知识的推广和普及十分重要。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法官使用与口头语言相距甚远的文言文来制作判决,又时常炫耀法官本人的文采,讲用典、对仗、节奏,甚至以骈文行之,美则美矣,但离逻辑的要求却愈来愈远。因此,正如中国的诗化语言曾经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它也是中国古代律学进步的绊脚石。在如此注重形式美的前提下,作为一篇司法判决,法官还有多少余地在其中进行法律概念和规则的阐述呢?再者,使用这种语言所制作的司法判决又怎样促使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民众通过司法了解法律呢⑰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这反倒成全了通俗易懂的书判体公案小说盛行繁荣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官方的书判导致了公案小说的发展,还是后者影响了官府的书判形式?仰或两者彼此影响?从对古代判词的研究方面看,是基于对诗性判词的批判,才成就了宋元已降的书判形式。而对这一问题的深究,至今仍是一桩公案,只能留待另文讨论了。
不过,文学化的叙述结构和修辞格式与逻辑在很多时候确实是相悖的。实际上,骈判大多古雅精致。文章纯然是一种形式,但宣判的结论是明确的:该罚该杀,准与不准……当事人应该都很清楚。古人在公文或官样文字中既要充分表达政治理想和政治见解,又要尽量表现文学才华,这就是古代“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⑱赵静:《司法判词的表达与实践——以古代判词为中心》,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9页~第120页。。有学者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主要特质归纳为五点⑲胡旭晟:《试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之特质》,《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其中诉讼的道德化、诉讼的人情化与艺术化以及司法的个别化和非逻辑化均与富有诗意的判词密切相关。在古代判词叙事中,司法官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即司法官并没有完全以旁观者的口吻讲故事说案情,相反他对这个故事明显含有情感。在判词的叙事中,叙述者往往热情洋溢地向受述者灌输他的道德评价结论,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撇开故事的进程,直接诉诸于读者,希望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如不时以“尔”“尔等”的称谓直接对受述者进行指点教育。在判词叙事中,这种叙述者干预表现为法官会一时偏离所讲述的故事,或者暂时切断故事的内在组织,而插入叙述者对案件人物与事件所做的价值、规范、信念等方面的评价与判断⑳赵静:《法律叙事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坛》,2008年第2期。。很明显,这些叙述手法会给人造成一种缺乏逻辑的感觉,但却无一不是判官带着诗意的情感饱含深情之所作,并且直达心灵深处,诉诸灵魂征服。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通过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然而现在人们发现理性和逻辑并不能解决一切法律问题,因为它不能诉诸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结构。中国古代判词虽然非逻辑化倾向比较严重,也没有对法言法语使用的严格要求。但古代判词却通过比较巧妙的修辞技巧,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以达到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为目的。这可以称得上为一种情感的诉求机制。这种判决与礼的精神是一致的,古代中国追求的伦理上的和谐是以司法中的反逻辑(也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反逻辑)为代价,使得司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总是处在一个维护礼治秩序工具的从属地位。然而若从“礼”的原始含义“仪式和典礼”讲,它也是富有诗意和美感的。礼为人们以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其情感开辟了渠道,而法律则缺少情感方面的内容㉑[美]D·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融礼于律,正是将情感内容增加到法律的条文和实践中。在判词中以诗意的形式说理释法,正是古人的追求。因此,反逻辑并非反法律,倒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通过法律解纷的境界。
总体而言,具有诗性的文艺语体对公文语体的渗透确实加强了古代判词的文学色彩。我们将这种判词不妨称为“诗性裁判”,即通过诗意的文学手法而制作的判词。而当文学语体进入司法判词时,通过公文语体的整合效应,其原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形象性以及历史的意蕴已被有限消解,仅仅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针对性的表意工具,仅成为增强说服力的修辞。这样,判词的诗化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其本质是反诗意的。因为文学语体进入公文语体之后,切断了同原有意象特定语境的联系,其语词原有的丰富的内涵、情调的线索、联想、暗示、呼应都被减弱,融入了使用者的声音,被赋予新的功能。诗意的文学已经消失㉒赵静:《语体的融合与转换——以古代判词为基本依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被呈现出来是一种说理判词。通过这种被称为妙判的判词的广为传唱,文学不仅成了普及法律的手段,而且被当做一种文人治理的有效手段加以推广。
二、文学方法与充分说理
判例以文学化的手法加以表现并传播,正说明中国司法传统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文学化的手段。无论古今,判例也是一种故事的形式,都是一种过去意义上的事实裁判。案件事实不是证据的建构,而是修辞的建构,司法审理便是一种修辞过程,一种通过将证据所提供的素材情节化、戏剧化来得出案件事实以及判决结果的活动㉓刘燕:“案件事实,还是叙事修辞?——崔英杰案的再认识”,《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6期。。当法律作为一种故事时,判决就成了讲故事。要想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更是需要好的叙述者,而好的叙述者定是颇富诗性的人。因此,司法的过程也将被展示为一种文学化的过程,一种诗性的过程。
讲故事即我们所谓的深描,尤其在事件史的叙述中,而司法的过程也即是对事件史的一种深描。深描更是一种文学手法。文学的叙述方式可以换来对理论的视觉呈现,文学化的司法过程也可能会唤起对真实情感的再现,同样可能唤起对公正判决的呈现。对法院和法官而言,总是希望全面充分地论证自己的裁定理由。然而,这样一种希望以及实施,由于运用自己认为不错的说理方式,反而徒增他者可以自然而然提出的疑问乃至质疑。重要的原因在于,法院所追求的“充分”说理是在希望运用法律规定、法律原则和形式逻辑之外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论证资源以期实现“很有道理”。而正是这种多重资源的使用造成了“说理方式”的“地方性”冲突㉔刘星:《司法中的法律论证资源辨析:在“充分”上追问——基于一份终审裁定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因此,试图“充分”说理却导致了“说不清理”的结果。在司法论证中,仅仅通过自认为完美全面的逻辑说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胜败皆服”的司法效果颇让人怀疑。从宋鱼水的经验来看,她在司法实践中所运用的“充分说理”既有可能不断地驯服对方的思考从而实现征服,也有可能不断地解放对方的思考,从而遭遇抵抗㉕刘星:《走向什么司法模型?—— “宋鱼水经验”的理论分析》,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这种朴素的抵抗情绪其实是大众对于“职业化”所导致的与“日常化”的疏离而产生的不满与不可理解。二者的和谐共存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理性职业化”回到“感性大众化”,而文学就是在这种感性策略中响应着日常化的情感呼唤和共鸣。
在新中国初期,司法是强调大众动员型的人民司法。在一个开放的广场化司法语境中,人们通过情感的碰撞、各自故事的讲演来诉说和维护着司法的正义,文学的感性激扬实现了广场化氛围中大众所需要的情感互动效应㉖陈文琼:《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河北法学》,2009年第7期。。同样,由于当时文法不分,政法相容,职业化的法律逻辑几乎不存在,只有日常化的生活逻辑支配着整个司法过程,司法过程同革命过程或日常生活无法区分。因此,广场化的司法并不存在说理性的难题。随着司法职业化的兴起,职业逻辑开始刻意同日常逻辑划清界限。在职业逻辑被不断强化的同时,法院也越来越不被信任。为了解决职业与日常的矛盾,故事文学或许可以利用。在具体案件中,具有故事文学机制的周边情况陈述,可以使被格式化后的法律意见争论悬置起来,较为有效地终止对诉讼争议或疑案的无穷追问,从而使司法受众包括司法者,从案件整体来理解司法意见的适恰与否,而非关注抽象的法律意见㉗刘星:《司法决疑与“故事文学”利用——以〈威尼斯商人〉为样本》,《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我们不妨向前推进一步,当代司法的过程或许更需要的是故事文学的支撑,尤其是通俗故事文学的推动。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衍生于陪审团审判的故事构造模式除了用于解释裁判者的心证形成过程外,还通过控辩双方的“故事比拼”来实现证明的说服力,以故事脉络设置举证顺序和庭审顺序,以故事的全面性、一致性、独特性作为证明标准,可以使证明过程更具有可操作性㉘葛琳:《证明如同讲故事?——故事构造模式对公诉证明的启示》,《法律科学》,2009年第1期。。这些都说明文学化的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变得越发有效。
古代中国判词的文学化倾向表明在司法文书中能够用文学语言来弥补法律语言的不足,构建一种适合阅读和表达的法律语言体系。并且,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书中的体现㉙蒋先福、彭中礼:《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法官进行说理的重要部分。正因为没有扎实的论据支持,才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是法官是否达到“胜败皆服”的司法公正的绝佳量标。古人引入诗意化的表述方式,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利用诗化的语言动之以情,无疑能达到良好的情感效果和说理效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指出“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而欲使法律文书成为生动的法制教材,无不是通过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而达到的。增强说理性的重点在于针对质证中有争议的证据,这些证据大多需要自由裁量,综合考虑法理、人情、社会条件等等。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对审判者的这些要求甚至更符合美国司法中理想法官的标准——法律人/政治家,能够适度地去“超越法律”㉚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反观人世,通过诗性化的思维更好地进行说理。总之,通过文学化的方式来进行“充分”说理未尝不是一条正途。
三、社会治理与诗性正义
由于司法与文学密不可分,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便日益兴盛。广义的“法律与文学”包括四个分支: “文学中的法律”“作为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有关文学的法律”。本文恰恰要关注的是“通过文学的法律”,即“用文学的手段来讲述、讨论和表达法律问题”㉛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它与“作为文学的法律”有相似之处,都是应用文学的感染力来达到作者的立意目的,延伸到法律上,就成为立法者进行法律传播与大众说服的一种策略。诗性裁判即是一种通过文学的法律进行社会治理的方式。
事实上,文学一直承载着重大的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整合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具有了某种社会控制的作用㉜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第28页。。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国家的财力、人力和信息都极其匮乏,国家法律因这些因素的限制无法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统治者单凭法律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必须借助意识形态来辅助国家的治理,儒家的“德主刑辅”大概就是在此意义上形成的一种政法制度和治理策略。通过文学的治理,或者是诗化 (礼)的治理,在普及正统意识观念的同时,也化解了司法纷争并传播普及了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化万民,使国泰而民安。这是一种在当时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模式。到现代讲法治的社会,因为法治的逻辑是无诗化的,所以无法公开认可文学的教化功能。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法治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法治一样,需要有与之配合的文艺表现形式,将抽象的法治话语 (公民权利、赏罚二柄之类)转化为人民愿意接受的社会正义和具体的政治操作。㉝冯象:《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因此,文学和法律开始合一,文学的教化功能被法治所吸收,文学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而存在。
努斯鲍姆提供和阐述了一种与文学和情感相关的诗性正义。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性”。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在这一中立旁观者的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媒介,能够让我们触摸到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能够让我们通过“移情”和远处的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文学和情感能够带来畅想,能够带来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文学对于普通大众的兴趣,情感对于那些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能够使得读者和旁观者尽量深入和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每个方面。在文学和情感的关注之下,旁观者的视角将变得更为公正和明智㉞[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这一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至少能够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性标准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古代中国司法中,文人判官无一不是将文学化的表现手法和抒发自我情感作为判词拟定的自发语境。这与努斯鲍姆所强调的文学和情感相当吻合。文学的阅读对社会公众,终究具有潜移默化的规训,进而也会左右其对现实法律实践的看法,最终“干预”法律实践。因此,左右文艺,左右思想传播,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中之重。
另外,文学和情感给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多的是经验边界(文学)和信息量 (情感)的扩展,尤其是关于人的知识和信息的扩展㉟丁晓东:《走向诗性正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9年第1期。。经验和信息量无疑是实现公正司法的必备要件。信息量同样也能被经验所涵盖,否则信息并不能被有效收集和理解。因此,努斯鲍姆同样重复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一至理名言。经验孕育着情感,贮藏着信息。而更多的经验则需要文学性的视角,尤其是诗性的视角来发现,这样才能更人性化地对待司法。因为人性与诗性是相通的。
四、政法合一与文学价值
“政法合一”一词可以用来很好地概括中国司法的传统和现实。古代中国司法也是行政司法合一, “法”既是“政”的基本内容,也是施政的具体措施,司法的终极目标是“必也使之无讼”。因此,法的存在最终是为了“不存在”,政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全部。在政治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对诗文的强调是理所当然的,诗文传达的是思想意识的控制,此谓“文以载道”。因此,通过文学的治理是政治的不二选择。在法治社会的标准下,党政对法的正面和背后的影响常用的方式便是宣传,尤其是文艺式的宣传。通过简短明快、通俗易懂的口语化的大众文学手法来表述,取得了广为人知的宣传效果。当然,在宣传时还将“党政民”三者捆绑在一起,就越发增强了“政法合一”正当性的渲染力。
在古代中国,正是“政法合一”才使得法官职位由并非受过法学专业知识训练的文人墨客担当,才使得诗性裁判成为了可能,使得司法同大众紧密联系,使得“天人合一”(天理国法人情)成为司法的最高追求。它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终极目的是在于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正是诗意的文学修为造就了士人和世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因文学而衍生出的诗性裁判也恰当满足了当时社会对自然与人世合一的追求。近代以来的“变法图强”,国家力图通过立法而实现宪政,进而迈向繁荣。于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媒体进行“国衰民弱”的诗意化描述,来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通过法律实现强国梦的观念。新中国以来的大众司法一直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也融入了文学与道德情感。文学通过其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来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物化载体而存在。改革开放至今,政法环境的转变也没能让文学完全失去主导社会教化的地位,当代司法实践现实依然无法离开文学的感性表达作用,“普法运动”“法制文艺”等都无法回避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因此,文学始终萦绕着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在不断推行司法改革的当下,司法的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成为学界共识,但随着司法专业化的纵深推进,司法的公信力却越来越弱化。中国司法似乎在高高在上的变革中,逐渐同民众拉大了距离。于是,近年来,为民司法的思想又被重新强调,群众路线的红色经验因司法的信任危机而重返政法舞台,司法判决书也推出了加强说理的改革方案,这或许是诗性的判词传统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重要契机。至于诗性的判词传统如何与当前不断专业化的法律术语进行衔接,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司法判例制度研究》之子课题《中国历史上司法判例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0JZD0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