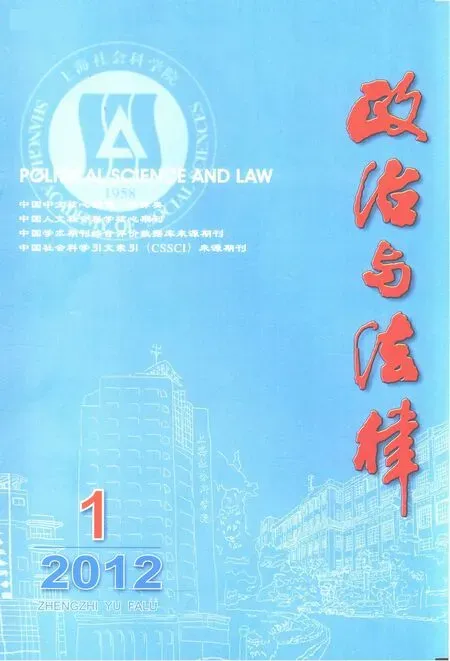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问题研究
张 建 俞小海
教唆犯又称造意犯,是指有意唆使他人,使其产生犯罪意图,进而实施所教唆之罪的人。与实行犯、帮助犯不同的是,教唆犯通过他人实施犯罪行为来实现其犯罪意图。这就决定了教唆犯须将其犯罪意图转达给被教唆人,并由被教唆人去完成犯罪行为。由于教唆犯主观意志表达和客观情况变化等原因,被教唆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会随时调整其主观思想和客观行为,从而出现其行为或行为导致的后果与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一致之情形,这便是教唆犯中的实行过限问题。对于该问题,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实务界也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出现了个案处理上的差异。被教唆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实行过限,对于教唆人的刑法评价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就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问题展开分析,对于准确定罪与量刑、做到罪刑相适应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案例及其反映的问题
实行过限的基本含义为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1因此,教唆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实行犯超出了教唆故意的行为。对于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的不同反映到个案上,则表现为案件定罪与量刑上的差异。下面列举三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以作说明。
案例1:2005年9月29日晚,余某因怀疑同宿舍工友王某窃取其洗涤用品而与王某发生纠纷,遂打电话给陈某,要陈某前来“教训”王某。次日晚上8时许,陈某携带尖刀伙同同乡吕某(另案处理)来到某公司门口与余某会合,此时王某与被害人胡某及武某正从门口经过,经余某指认,陈某即上前责问并殴打胡某,余某、吕某也上前分别与武某、王某对打。其间,陈某持尖刀朝胡某的胸部、大腿等处连刺三刀,致使胡某左肺破裂、左股动静脉离断,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陈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余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二审法院认为,陈某所实施的杀人行为系过限行为,不能令余某对该杀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对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刑事责任,故认定余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
案例2:2003年,王某与逄某各自承包了本村沙地售沙。王某因逄某卖沙价格较低影响自己沙地的经营,即预谋找人教训逄某。2003年10月8日16时许,王某得知逄某与妻子在地里干活,即纠集了韩某、王某某、崔某(在逃)、冯某(在逃)等人。王某将准备好的4根铁管分给韩某等人,并指认了逄某。韩某、王某某等人即冲入田地殴打逄某。其间,韩某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捅刺逄某腿部数刀,致其双下肢多处锐器创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雇佣纠集人员伤害他人,韩某、王某某积极实施伤害行为,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韩某的持刀捅刺行为并非实行过限的个人行为,被告人王某、韩某、王某某应共同对被害人逄某的死亡后果负责。3
案例3:被告人华某因琐事与周某发生纠纷,当晚周父与周某及周某的丈夫彭某找到华某,双方发生争执。华某遂打电话给谢某称被人找麻烦,需要帮忙。谢某随即转告谭某、王某、颜某、谢某某、封某,并要王某、颜某、谢某某三人先过去。王某和谢某某便各拿一把砍刀,与颜某先行赶到现场。后因彭某打了华某一个耳光,致使双方争吵升级。华某被打后要王某打电话叫谢某、谭某、封某也过来。随后,谭某、封某各带刀由谢某驾驶摩托车一同赶到。在华某指认了彭某后,谭某、王某、封某等人便持刀冲向彭某,周某见状拦住谭某,谭某便持刀朝周某的腹部捅了一刀,随即又向彭某的胸部刺了一刀。彭某和周某被捅刺后均流血倒地。彭某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周某经鉴定损伤程度为重伤,八级伤残。法院认为被告人谭某的行为属于超出同案人犯罪故意内容的过限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华某、王某、谢某、颜某的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4
上述案例的共同点在于:犯罪行为均系某人纠集而实施,各犯罪人之间是一种雇佣犯罪关系,属于教唆犯的一种;教唆人教唆他人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在实施伤害行为过程中都有行为人持刀捅刺被害人的行为,且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方面,上述三个案情相似的案例,却得到了不同的刑法评价。其中,司法机关认定案例1和案例3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为过限行为所致,而案例2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则并非实行过限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尽管认定案例1和案例3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为过限行为所致,按照实行过限之理论,“过限行为由于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所以应当由实施过限行为的人对过限行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其他共同犯罪人对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5,但是,案例1和案例3中作为教唆者的余某与华某却对由过限行为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之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显然,这种做法与实行过限的基本理论不符。
教唆犯的实行过限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种情形:第一,被教唆人实施了与教唆人教唆之罪性质完全不同的他种犯罪,如被教唆人在入室盗窃过程中另行对女主人强奸;第二,被教唆人实施了与教唆人教唆之罪性质相同或者部分相同的犯罪,但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结果,如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第三,被教唆人实施了与教唆人教唆之罪有某种联系但罪质发生转化,如在抢夺、盗窃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等。上述第一种情况,被教唆人的强奸行为显然超出了教唆犯的教唆范围,其构成实行过限并无异议。而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中,被教唆人之行为所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被教唆人的行为发生罪质上的转化,是否构成实行过限,不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刑事司法中经常遇到的实务问题(上述三个案例即属于这种情形)。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
二、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认定的现有理论
学界对教唆犯中的实行过限问题展开了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超出教唆故意说
德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主张该说。其认为:“教唆人只是在被教唆人实施的行为与他的故意相一致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行为人的行为过限不对他增加责任。”6换言之,只有当正犯行为与教唆者的故意相吻合的,教唆犯始承担责任。如果正犯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超出了教唆人所期望的范围(过剩),教唆人只对其教唆故意所涉及的犯罪部分负责。7也有学者表述为“正犯的行为超出了教唆者的愿望(过度)”,比如正犯盗窃时携带武器,而非如教唆的那样实施简单的盗窃,那么,教唆犯只应根据其故意的程度(当过失也受到刑罚处罚时,最多只为过失造成了其他后果时)承担责任。8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指出,教唆犯对于被教唆人超过其教唆故意范围的过剩部分,教唆犯对此不负故意犯的刑责,仅由被教唆之正犯单独负责。9
(二)未预见说
此说为意大利刑法学者在实行过限问题上的主张,也是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学者在教唆犯中结果加重犯的实行过限问题上坚持的观点。对于实行过限,意大利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该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当实施的犯罪不同于某个共同行为人所希望的犯罪时,如果结果是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他也得对该犯罪负责。”这被认为是一种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偏离”,即就某一具体的共同犯罪人来说,其他人和他一起共同“实现”的犯罪,并不是他“希望发生”的犯罪。但是,该条仅仅根据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的刑事责任,有客观责任之嫌。正如意大利刑法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按此逻辑,一个在外为盗窃犯放风的人,就可能为盗窃犯们在房内强奸女主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极端严厉的规定,实际上是滑向了要求主体为他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边缘。因为,这无疑是将他人起意实施、主观上与主体无关的行为,仅根据纯粹客观的联系,就当作主体“所希望的”的行为来处理。10因此,司法实践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一种较缓和的方式。他们认为,如果要共同行为人对某一个他所不希望的犯罪承担责任,该犯罪的结果就必须是行为人能够预见的结果。11反之,如果对结果未能预见,则不需要就结果承担责任。
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些学者在教唆犯中结果加重犯实行过限之认定上,也坚持了未预见说。比如德国刑法学者指出:“在结果加重犯情况下,只有当教唆人对加重结果的产生具有过失时,教唆人对此等结果才负责。”12日本刑法学者认为:“由于结果加重犯是基本犯罪中因为包含有发生一定重结果的危险而成为独立犯罪的情况,所以,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的共同实行人,通常对于发生重结果具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因此,各人具有避免发生重结果的共同注意义务。换句话说,在基本犯的共同实行人中,一部分人由于过失而引起了重结果发生的场合,原则上,对该重结果的发生具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各个人就是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13因此,“在正犯者所实现的犯罪是结果加重犯的场合下,共犯者对于严重结果的发生有过失的时候可以考虑结果加重犯的共犯的成立。例如,甲教唆乙对丙实施伤害,乙伤害了丙并将其致死的场合下,只要甲对于丙的死亡有过失,对甲就成立伤害致死罪的教唆犯”。1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指出:“教唆犯就其所认识之犯罪事实限度内,负其责任,但被教唆者所为之犯罪行为如发生应加重处罚之结果,且系能预见者,则教唆者对之亦应负责。”15还有学者认为:“唯有教唆人对于加重结果有预见可能性者,始就加重结果部分负责。”16
(三)共同行为意思说
此说为韩国学者的观点。该说站在行为共同说的立场,认为具有共同的基本行为或者具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就必须对行为或者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比较典型的便是结果加重犯的场合。只要具有共同实施暴力或其他侵害身体行为的意思,作为结果加重犯的伤害致人死亡罪与共同正犯即可成立,不需要共同致使结果发生的意思。因此,集群打架的人用刀刺死对方时,即使其他共犯人对结果没有认识,也必须承担伤害致人死亡罪的责任。17按此逻辑,教唆他人故意伤害的,由于具有了实施暴力或侵害身体行为的意思,即便对被教唆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一结果没有认识和预见,也应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四)构成要件异质说
此说为我国部分学者坚持的观点。其认为,并非任何行为都可构成过限犯罪。只有与共犯行为存在构成要件的本质性区别的行为,才是过限犯的客观外部表现行为。所谓构成要件上的本质性区别,是指刑法分则明确地将其规定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独立的犯罪,外部表现为构成要件上的独立性和不相融通性。如果一犯罪构成是另一犯罪构成的修正形态,或者一犯罪构成是另一种犯罪构成的派生情形,则二者之间就不存在本质性区别,应将前一构成行为作为后一构成行为的一部分来看待,它们统领于一个总的犯罪行为之下,不具有独立性。18在教唆犯实行过限问题上,有学者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与非重合性过限。19重合性过限,是指被教唆人所实行的犯罪行为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某种重合性而发生的实行过限。例如,甲教唆乙伤害丙,乙却杀害了丙。在这种情况下,甲只负教唆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乙则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20由于杀人行为也是伤害行为的一种,因此甲所教唆的故意伤害与乙所实行的故意杀人在故意伤害这一层面具有重合性。非重合性过限,是指实行过限行为与教唆犯罪行为不存在重合的情形。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实行犯既实施了约定的共同犯罪,又实施了过限行为;二是实行犯根本未实施约定的共同犯罪,而是实施了与约定共同犯罪性质完全不同的犯罪。21前者如,甲教唆乙盗窃,乙在实施盗窃的同时实施了强奸行为。后者如,甲教唆乙盗窃,乙并未实施盗窃,而是实施了抢劫行为。
(五)教唆类型区分说
此说也主要为我国学者所主张。在被教唆人接受教唆的内容而实施该内容的情况下,教唆内容对过限犯的认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在认定教唆犯中实行过限问题时,有学者将教唆的内容分为明确性教唆、概然性和选择性教唆三种情形,并分别讨论教唆犯实行过限之认定问题。在明确性教唆下,由于教唆犯对所教唆的犯罪类型、犯罪对象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指向,一般地说,当被教唆人在实施教唆之罪时实施了超出教唆内容之外的行为,即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之间不一致的时候,被教唆者构成过限犯,过限之刑事责任由被教唆者单独承担。在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时,即概然性教唆情况下,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教唆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并予以实施,不论其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犯共同承担。选择性教唆是指教唆内容相对确定的教唆。其所指向的犯罪不惟一,也不概然,而是让被教唆者实施可选择的犯罪中的一种或几种。被教唆人只要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实施任何一种或几种犯罪,都不会发生过限的问题。22
三、对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现有理论的评析
应该看到,学界关于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的现有理论丰富了共同犯罪研究的视域,对于司法实践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如果进一步推敲,则会发现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过于原则
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均未能提供进一步的判断标准,带有相当程度的抽象性,无法为司法个案提供实质性的指导。超出教唆故意说,概言之,就是指教唆犯对于超出其教唆故意的实行犯的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而未预见说则是指教唆人对实行犯的行为或后果有预见性或预见可能性时才对过限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如何判断实行犯的行为或行为导致的结果超出教唆犯的教唆故意?如何判断实行犯的行为或行为导致的结果在教唆犯的预见范围之内?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均未能给出回答。而事实上,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中的核心部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超出教唆故意说之表述其实是将实行过限的概念直接搬到了教唆犯实行过限当中,可以说是对实行过限概念的重复。23因此,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仅仅给出了一条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的思路,但是并未提供进一步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其无法为个案分析提供实质性的指导,也导致了在分析具体个案时各学者自说自话的倾向。比如,甲教唆乙实施盗窃或抢夺,乙在盗窃或夺取财物的过程中,因被害人的发现和反抗,遂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压制了被害人的反抗而顺利取得财物。对此,有人认为,乙转化的抢劫超出了甲教唆犯罪的范围,构成实行过限。24而有人认为,教唆犯在教唆他人实施盗窃等犯罪时对于被害人的反抗是应当有预见的。因此,教唆盗窃,被教唆人基于盗窃受阻而转化为抢劫的,不能认为是实行过限。25但是,对于乙的转化抢劫如何超出了甲的教唆范围,以及教唆犯对于罪质转化为什么应该有所预见、如何预见等,论者均未提及。又比如,针对“甲教唆乙伤害丙,乙在伤害丙的过程中致丙死亡”之情形,有人认为教唆者对于加重结果一般应当预见,并且,在结果加重犯的场合,由于基本犯罪本身就有造成结果加重的高度危险性,一旦发生了加重结果让教唆人承担这种加重结果的责任,也是应该的。26有人则基于同一理论认为其系一种过限情形。27
由此看来,对于教唆犯中实行行为导致加重结果或实行行为发生罪质转化等情形,同样是基于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也完全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抽象性的标准,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对于具体个案并无多大解释力,从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出发,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共同行为意思说有客观责任之虞
共同行为意思说强调具有共同的基本行为或者具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即可,既不需要共同致使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思,也不需要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预见,但是,危害结果一旦产生,就必须就结果承担责任。将该理论具体到教唆犯上,则会发现只要教唆人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就表明教唆人具有了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此时,被教唆人的行为无论是产生了加重结果,还是行为性质发生转化,该结果都应当归责于教唆人,而不问教唆人主观上是否对加重结果或行为性质转化具有认识和预见。诚然,由于教唆犯是犯意的制造者,因而共犯(如教唆犯)具有共同的基本行为或者具有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与正犯(实行犯)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并使得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了可能性。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即便因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可以推导出共犯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而直接推导出共犯对正犯结果也存在故意”。28而共犯对正犯行为和结果的故意(或过失),是共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共同行为意思说抛开共犯对正犯结果的主观因素,带有客观责任的残余,实不足取。
(三)构成要件异质说难以应对复杂问题
构成要件异质说坚持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在构成要件上的独立性和不相融通性过于绝对,也无法解决教唆犯中的一些复杂问题。比如甲教唆乙杀丙,乙在杀丙后发现丙的妻子丁也在现场,为避免事情败露,乙又将丁杀死。按照构成要件异质说,乙杀丁的行为与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是两种构成要件相同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行为),因而乙杀丁的行为不构成实行过限,甲应当对丁的死亡结果负责,但很显然这难以被人接受。又如,A教唆B伤害甲,但B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致使甲死亡,按照构成要件异质说,这种情形根本就不会存在实行过限问题,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虽然重合性过限与非重合性过限的划分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划分的实质是在已经得出实行过限结论的基础上对被教唆人所实行的犯罪行为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的描述,而其本身并不具有认定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与否的功能。比如,A教唆B伤害甲,但B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致使甲死亡,此时教唆犯A所教唆的犯罪行为和被教唆人B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有重合,但据此并不能得出实行过限的肯定性判断。29因此,构成要件异质说和重合性过限之理论,在面对复杂个案时要么存在一定缺陷,要么出现功能性缺位。
(四)教唆类型区分说的标准不统一
教唆类型区分说一般将教唆的内容分为明确性教唆、概然性教唆和选择性教唆三种情形,并分别讨论教唆犯实行过限之认定问题。但是,第一,关于明确性教唆、概然性教唆和选择性教唆的区分,尚未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标准。实际情况是,对于这一问题出现了仁者见仁的局面。第二,在概然性教唆的情况下,该说强调不论被教唆人行为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这无疑会极大压缩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存在空间,不符合相关事实和罪刑相适应之要求。第三,即便对于同一种教唆类型,不同的主体也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来看,教唆人的教唆内容一般都不是非常明确、具体,因而大致可划归概然性教唆的范畴。但是,对于概然性教唆下教唆人对被教唆人之行为及其导致的后果的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的判定也会出现重大差异。
以上文提到的三个案件为例。案例1和案例2均是教唆人教唆他人教训被害人,而案例3虽然没有“教训”二字,但结合事件背景和纠纷当时的情形,可以得出教唆人华某也是希望谭某等教训他人。由于三个案例中的教唆人均未就“教训”的手段、后果等作出明示,可以说,三个案例中的教唆均属于不明确的教唆。对于该概然性教唆,司法机关在案例1的裁判理由中解释到:“虽然‘教训’的具体含义有多种,但在没有证据证实余某有要求陈某杀害他人的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包括杀人。余某没有让陈某带凶器,更没有让陈某带尖刀这种容易致人伤亡的凶器,也没有证据证明余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知道陈某带着尖刀。虽然余某与陈某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概括的故意,但这一概括的故意却是有限度的,至少不包括杀人的故意。”30对于案例3中教唆人(华某)的主观故意,司法机关人员也分析到:“被告人谭某与华某等人虽成立共同犯罪,但共同犯罪故意却不甚明确,可以说是一个概括故意,但这一概括故意却是有限度的,至少不包括杀人的故意。”31但是,在案例2的裁判理由中司法机关却写到:“王某预谋找人教训一下被害人,至于怎么教训,教训到什么程度,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正面要求,同时,王某事前也没有明确禁止韩某、王某某等人用什么手段、禁止他们教训被害人达到什么程度的反面要求。所以,从被告人王某的教唆内容看属于概然性教唆。在这种情形下,虽然王某仅向实行犯韩某、王某某等提供了铁管,韩某系用自己所持的尖刀捅刺的被害人,且被害人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超乎王某等人意料,但因其对韩某的这种行为事前没有明确禁止,所以仍不能判定韩某的这种行为属于过限行为,教唆者王某仍应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32由此看来,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完全可以就同一个概括故意(比如“教训”)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结论(比如司法机关认为案例1和案例3中的概然性教唆内容不包括致人死亡,而同时认为案例2中的概然性教唆内容包括致人死亡),并进而影响到教唆犯实行过限的成立以及教唆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说明,仅仅从教唆类型区分说出发,也无法为教唆犯中实行过限问题提供独立、完整的解决路径。
四、对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理性认识
上文分析可知,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这一问题上的诸多观点,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或过于原则和抽象,或不足取,或难以应对复杂问题,或无法独立承担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之任务。由此也导致了该问题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亟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作出重新梳理。笔者认为,对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应该从两个层面进行:首先,坚持一定的原则;其次,在原则的指导之下进行具体因素的考量。
(一)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应坚持的原则
1.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的统一
对于实行过限的认定,我国有学者主张从主观上加以判断。该学者指出:“事实上,过限行为是否具有独立性,能否脱离共犯行为独立评价,不是取决于其在客观上与共犯行为有无异质性,而是取决于其在主观上有无违反共同故意。”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实行过限的本质特征,是行为超出共同犯罪的故意范围。因此,对实行过限的判定,应当从行为的主观方面入手。”33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综合评估这样一种态度,这无疑是当代刑法学中的一条公理。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其最终落脚于教唆犯和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而该刑事责任的承担离不开我们对行为人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的综合把握。当然,仅仅从主观判断对实行过限进行认识是片面的,仅从客观事实来认识实行过限也是不对的。
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指出,教唆犯乃出于教唆故意而唆使他人实行故意犯罪行为之人。是以,犹如其他故意犯,教唆犯亦仅在“主观知欲要素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之间具备对应关系”的范围内,始负故意犯的刑责。教唆犯的过剩或错误等问题,同样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对应法则来处理。34因而笔者认为,在对教唆犯实行过限进行认定时,一方面需要分析教唆犯之教唆故意等主观要素;另一方面,对实行犯之客观行为、证据或其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等客观事实加以认识。在此基础上,目光则需要不断地往返于教唆犯教唆故意和实行犯客观行为之间,从而找出教唆犯教唆故意与实行犯行为之间的对应点。
2.理论性与实用有效性的统一
应该承认,上文提到的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并无多大问题。35但理论需要为实践服务,从理论到理论,或者是过于理想化的理论,在面对复杂的司法实践时,必然会遭遇诸多瓶颈。笔者认为,前文列举的学界关于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的现有理论,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未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实际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脱离实践的理论。当然,笔者同时认为,学界关于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的现有理论,确实有一些论点可资借鉴。比如,当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案件并得出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肯定结论时,该实行犯的行为或其行为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超出了教唆犯的教唆故意、超出了教唆犯的预见可能性;当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案件并得出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否定结论时,该实行犯的行为或其行为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未超出教唆犯的教唆故意、未超出教唆犯的预见可能性。因而可以认为,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是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的上位规则,是抽象标准,也是检验教唆犯中实行过限成立与否的最终标准。但也应当看到,由于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本身的抽象性,无法为司法个案提供一个现成的、实质性的指导,因而在这个抽象标准下还需要关照到实用有效性。换言之,我们主张在借鉴学界关于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之现有理论中合理论点的同时建立一个实用有效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认定思路。这便是将抽象的规则与具体的个案相融合的过程。就教唆犯实行过限之个案来说,实行犯之实行行为是否过限,最终要落在司法判断上,这一过程显然无法简单地将规则与案件对号入座,而需要结合教唆故意产生的背景、行为人的行为习惯、案件发生的情境因素等综合考虑。
(二)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认定之具体把握
笔者认为,对于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认定的把握,应当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个案中多种主客观要素作出综合的、个别的、具体的和实质性的判断。具体而言,这种判断需要同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36
1.准确区分概然性教唆与确定性教唆37
一般认为,根据教唆内容的确定性程度不同可以将教唆犯中的教唆分为明确性教唆、概然性教唆和选择性教唆三种。明确性教唆是指教唆犯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对象、犯罪类型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教唆;概然性教唆是相对于明确性教唆而言的;选择性教唆是指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内容具有让被教唆人进行选择的性质和要求,如所教唆的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行为对象或者二者均具有选择性要求。38尽管前文已提及,仅从教唆类型出发,无法为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提供独立、完整的标准,但笔者同时也认为,教唆类型的不同,对于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范围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认定被教唆人是否构成实行过限的时候,首先需要对教唆人的教唆内容进行认真考察,只有对教唆人的教唆内容作出准确分析,才有可能进一步确定被教唆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教唆犯的教唆范围,从而认定被教唆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实行过限。在概然性教唆的情况下,由于教唆的内容不确定,教唆人往往只是告知了被教唆人其犯罪目的或其通过犯罪欲达到的后果,因此,一般情况下,被教唆人无论采取了何种行为方式,只要没有明显超出教唆范围,就为实行过限的认定提供了初步依据。
但值得注意的是,概然性教唆的内容在概然性程度上也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往往很难在理论层面事先划出一条清晰的标准,而需要结合教唆人具体使用的语言、教唆人对过限行为的认识程度等加以判断。比如,甲让乙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一笔钱,则无论乙是通过盗窃或是抢夺、抢劫,甚至是故意杀人之后搞到钱,都不违反甲“不惜一切代价”的本意,也未超出甲对过限行为的认识程度,不宜认为实行过限。又比如,甲让乙晚上去街上“找点钱来花”,此处的教唆内容也不确定,可能是盗窃,也可能是抢夺,还可能是抢劫。但由于此时甲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也没有默认乙实施一切行为找钱的客观语言或暗示,因此如果乙实施了杀人行为搞钱的,则宜认定为教唆故意之外的实行过限,由乙单独就实行过限行为负责。尽管这两种教唆都属于概然性教唆,但是其确定性程度是不同的,由此也导致了教唆犯中实行过限判断上的差异。
2.考虑教唆人犯罪目的所产生的背景
在对教唆类型进行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还需要就教唆人犯罪目的所产生的背景作出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教唆人之所以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种教唆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也是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同一个教唆他人盗窃获取财物的行为,既有可能是出于零花的目的,也有可能是用来满足自己挥霍、赌博、从事高风险活动或犯罪活动的目的,很显然,这种通过教唆他人犯罪所欲实现的目的的不同,对于被教唆人接下来所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教唆人的教唆故意之判断也是有影响的。如果教唆人教唆他人实施盗窃是为了零花或者日用,而被教唆人实施了盗窃金融机构或盗窃珍贵文物的行为则一般不符合教唆人的教唆故意,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如果教唆人因赌博欠下巨额高利贷,需要巨额资金来偿还,这种情况下教唆他人盗窃的,被教唆人实施了盗窃金融机构或者盗窃珍贵文物的行为就可能没有超出教唆人的教唆范围,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又比如在教唆故意伤害案件中,教唆人与被害人之间平时较为熟悉,因为嫉妒、邻里纠纷等原因想给被害人造成某些不便或者让被害人出丑等而教唆他人“教训”被害人的,这种情况下被教唆人在实施故意伤害过程中造成被害人死亡这种结果就难以认为是包含在教唆人的教唆故意之中,宜认定为实行过限;而如果教唆人与被害人之前有深仇大恨或者重大经济纠葛,此时同样是教唆他人“教训”被害人,被教唆人实施故意伤害从而造成被害人死亡这种结果或许就可以考虑并未超出教唆人之教唆故意,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可见,教唆人犯罪目的所产生的背景,对于准确认定教唆犯中的实行过限问题,是有意义的。
3.厘清教唆人犯罪目的与被教唆人犯罪手段之间的关系
在教唆人教唆他人犯罪的情况下,有时候教唆人并未就被教唆人实施行为的种类、行为方式以及所要达到或者避免的后果等事项作出说明,而仅仅就其所欲实现的犯罪目的简单告知。此时,大致可以认为,被教唆人无论采用了何种行为方式,只要没有明显超出教唆人的认识程度或者预见范围,就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但这一结论仅仅是初步意义上的,而并非带有终局性。实践中,还应进一步考察,被教唆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方式是否是实现教唆人犯罪目的的必要或通常手段。如果被教唆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方式是实现教唆人犯罪目的的必要的或通常的手段,则属于教唆人教唆之范围。比如甲教唆乙去盗窃,乙则实施了入户盗窃,且在被主人发现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从而构成转化型抢劫的,由于乙所采取的“入户”行为方式符合盗窃行为的一般手段,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也符合盗窃财物之后保护财物的通常手段,因此并未超出甲的教唆范围,甲对乙所实施的这些行为方式应当有所认识和预见,这种情形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相反,如果被教唆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方式并非实现教唆人犯罪目的的必要或者通常的手段,则不属于教唆人教唆之范围,有可能构成实行过限。比如,甲教唆乙杀丙,但是乙盗窃枪支后将丙杀害。这种情况下,甲对丙死亡结果负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宜对乙盗窃枪支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因为,虽然枪支经常被人用于杀人,但是盗窃枪支并不是杀人的通常手段,因此乙盗窃枪支的行为超出了甲的教唆范围,宜认定为实行过限。至于如何判断被教唆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方式是否为实现教唆人犯罪目的的必要或者通常手段,我们认为,应当结合社会上的一般观念来进行。
4.就过限行为与教唆犯罪行为之间的事实要素作出判断
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行为的认定标准,除了需要综合考虑上述方面之外,还应当就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之间的事实要素作出实质性的判断。比如甲教唆乙杀丙,乙在杀丙之后发现丙的妻子丁也在现场,为避免事情败露,乙又将丁杀死。应该承认,乙将丁杀死的行为与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是同质的(都是故意杀人),但是这种构成要件的相同仅仅是一种抽象层面的相同,而这种抽象的构成要件相同之下具体的事实要素则是不同的。从抽象性上看,乙杀丁的行为与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的行为,都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从具体性上看,这两个故意杀人犯罪构成之下的事实要素却是独立的,不能互相替代。这种事实要素包括:行为指向的对象、行为所侵害的对象的个数等等。具体而言,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丙,而乙杀丁的行为指向的对象则是丁;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侵害的是单个对象,而乙实际实施的行为则指向两个对象。笔者认为,被教唆人所实施的行为即使与教唆人所教唆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具有抽象的符合性,但如果在事实要素上不具有同一性,也可能成立过限行为。据此,就这一例子而言,乙杀害丁的行为由于与甲教唆乙杀丙的行为在事实要素上不具有同一性,因而应当构成实行过限。
回到前文提及的三个案例。首先,从教唆类型上说,案例1、案例2和案例3中教唆人均未就“教训”的手段、后果等作出明示,属于概然性教唆,其对被教唆犯所可能采取的“教训”手段及其通常后果是应当预见的;其次,案例1由怀疑同宿舍工友窃取其洗涤用品并发生纠纷而引起,案例2是因同村人的经营纠纷,案例3也是因琐事纠纷,从教唆人犯罪目的产生的背景上看,很难得出教唆人的犯罪目的中包含致纠纷对方死亡甚至杀害对方;再次,尽管三个案例中的教唆人事前均未就被教唆人的手段、教训被害人的程度有所明确,但是从社会一般观念上分析,用刀不计后果地捅刺显然超出了达到(因纠纷而起的)教训他人这一目的通常的、必要的手段;最后,就案例1而言,教唆人余某的教唆故意指向的是王某,而最终被教唆人陈某持刀捅刺并致其死亡的是胡某,显然,陈某的持刀捅刺并致胡某死亡的行为与余某的教唆犯罪行为之间的事实要素存在偏差。据此,笔者初步认为,案例1、案例2和案例3均宜认定为实行过限。
五、结语
实行过限是伴随着共同犯罪而出现的一类犯罪形态,它与共同犯罪有着紧密的关联,是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其中,教唆犯的实行过限问题又是非常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课题。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这一问题上的诸多观点,在面对具体案件时,或过于原则和抽象,或不足取,或难以应对复杂问题,或无法独立承担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之任务,由此也导致了该问题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对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认定,首先,应该坚持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统一、理论性与实用有效性的统一;其次,在坚持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的基础上,结合案件发生的情境因素等,作出综合的、个别的、具体的和实质性的判断。
应该看到,对教唆犯中实行过限之认定问题作出上述分析,是刑事司法的精确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刑法与其他法律相比,由于它的属性及所涉对象均有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决定着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否,或者讲决定着人的自由与否,故其法性作用是其他法律无法做到的,也正因为这样,其适用性必须要在极度理性的基础下进行”。39换言之,刑法学的适用必须要精确无误,不能随意和含混。40在教唆犯的实行过限问题上,行为导致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罪质发生转化,往往是刑法中法定刑升格之条件,41因此,这种情形下实行过限与否之判定,对于教唆人的罪刑评价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直接关系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落实。因而对于这一问题,应当在理性、审慎的基础上进行认识。
注:
1参见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典刑案例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8页。
2、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第347-348页。
4参见刘敏、陈菂:《聚众斗殴中实行过限及其刑事责任的认定》,《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9期。
5陈兴良:《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345页。
6[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7、12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34-835页,第836页。
8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荫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333页。
9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10、11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4页,第294页。
13[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380页。
14[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
15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4页。
16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17参见[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18参见夏强:《过限犯若干问题探析》,载吴振兴主编:《犯罪形态研究精要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页。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熊正:《开车接应实行过限同案犯之定性》,《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12期;冯英菊:《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判断——色诱抢劫案中女性帮助犯的定性》,《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2期;徐展豪、刘新锋:《共同故意伤害犯罪中的实行过限的认定》,《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8期。
19参见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20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册)》(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453页。
21参见阴建峰:《实行过限之本体探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1期。
22参见陈兴良:《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法学杂志》1989年第6期;夏强:《过限犯认定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赵丰琳、史宝伦:《共犯过限的司法认定》,《人民检察》2000年第8期;张玉娟、何大勇:《试论教唆犯的实行过限》,《山东审判》2010年第5期。
23因为按照通说,实行过限的基本含义为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而根据超出教唆故意说,教唆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实行犯的行为超出了教唆者的故意。显然,后者是对前者的概念重复。
24参见张伟、王春福:《实行过限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夏强:《过限犯认定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25参见宁汉林、魏克家、吴雪松:《定罪与处理罪刑关系常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26参见马松建、王立志:《实行过限问题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7有论者将结果加重犯的共犯过限作如下界定:即在实施某一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因故意或过失地产生了某一更为严重的犯罪结果,且该结果超出了共同犯罪的范围而形成的一种过限情形。参见肖本山:《共犯过限与共犯减少》,《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2期。
2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29至于非重合性过限,其对于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实际上也不具有意义。非重合性过限是指被教唆人除实行了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以外,还实施了其他不同性质的犯罪。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实行犯既实施了约定的共同犯罪,又实施了过限行为;二是实行犯根本未实施约定的共同犯罪,而是实施了与约定的共同犯罪性质完全不同的犯罪。显然,第一种情况构成实行过限没有疑义。在第二种情况下,实行犯根本未实施约定的犯罪,因而并不存在共同犯罪之前提,在这种情形下,要么是两个单独的犯罪,要么一个是犯罪行为而另一个不构成犯罪,本来就没有是否实行过限之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非重合性过限没有存在的必要。参见阴建峰:《实行过限之本体探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1期。
30、3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第349页。
31刘敏、陈菂:《聚众斗殴中实行过限及其刑事责任的认定》,《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9期。
33叶良芳:《实行过限之构成及其判定标准》,《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4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35当然,对于共同行为意思说和构成要件异质说,笔者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
36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规则或原则都无法独立承担教唆犯中实行过限认定标准的任务,在纷繁复杂的司法个案面前,务实的态度是,在一般规则的指导之下,不断探寻更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次级规则。本文接下来从四个方面展开的分析便是这种寻找次级规则的尝试。但同时也须指出的是,本文接下来提及的四个方面,均不具有独立认定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的功能,任何一个方面所得出的仅仅是实行过限成立与否的初步结论,教唆犯中实行过限终局结论的作出,还须综合考量这四个方面并结合教唆犯实行过限认定的一般规则(即超出教唆故意说和未预见说)。而且,本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是开放性的,换言之,由这四个方面推出的结论并不具有绝对性,完全有可能受到各种更为具体的事实的补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接下来提及的在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时考虑的四个方面,与其说是一种操作细则,毋宁说是一种判定的思路。
37从名称和讨论的内容而言,这里的“概然性教唆与确定性教唆”和教唆类型区分说所涉及到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同在于,教唆类型区分说将教唆的不同类型作为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的独立的标准,而笔者在此处提及的“概然性教唆与确定性教唆”,对于教唆犯实行过限之认定并不具有独立、完全的意义,而仅仅是作为认定教唆犯实行过限时需要具体考量的一种因素。其地位、作用与教唆类型区分说下的教唆类型并不相同。
38参见张玉娟、何大勇:《试论教唆犯的实行过限》,《山东审判》2010年第5期。
39张建:《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40参见王世洲:《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译者序)》,[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41比如,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政治与法律的其它文章
- 感恩读者·感怀时代·感想未来——创刊30周年、刊行第200期有感
- 我国刑法分则中空白罪状的解释规则探讨——兼以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为例分析
-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 德国法上的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及其反思*本文系德国洪堡基金会联邦德国总理奖学金项目“一般人格权研究”的成果之一。
- 论垄断国有企业监管法律制度框架的重构*本文系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有股权行使和监督法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8BFX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征收农民房屋和土地的宪法法律问题*本文为2011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1BFX009)和2011年度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H2K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