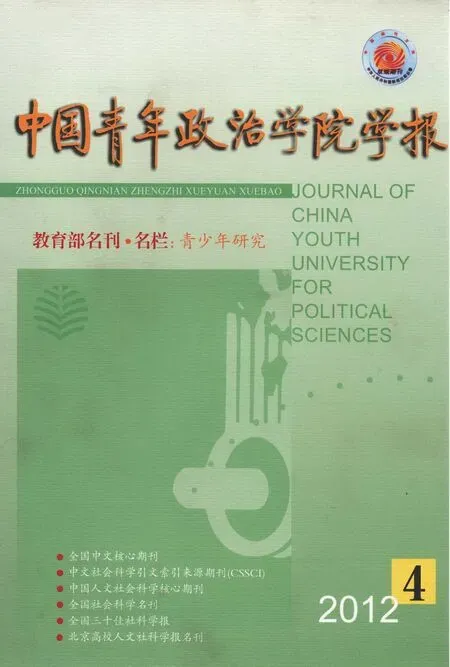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内部冲突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长期以来,众多国际法、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们在人道主义干涉的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问题上争论不休。基于人道主义因素的对外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是这些争论的焦点。现有研究表明,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具有正当性、支持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后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已经将人权保护明确列为国际义务,所以当一国不能履行此种义务时,由其他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涉是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相一致的,干涉行为不仅正当而且合法。而更多支持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者们则表示,尽管人道主义干涉与现行国际法的基础即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相冲突,但却继承了历史更加悠久、影响更为广泛的道德和正义传统,是一种“不合法但正当”(illegal but legitimate)的行为①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The Kosovo Report,http://www.reliefweb.int/library/documents/thekosovoreport.htm。以上论述构成了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基本框架。
本文选择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通常使用的“正义战争论”和国际法根据为研究对象,试图重新审视其对人道主义干涉正当性的支持情况,以期对全面理解相关理论问题有所助益。
一、人道主义干涉与正义战争论的内在矛盾
正义战争论是人道主义干涉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战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讨论可谓源远流长,东西方的古圣先贤们都曾或多或少地探讨过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13世纪的经院学者阿奎那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正义战争的条件,全面地分析了正义战争的两大组成部分:“开战正义”与“交战正义”。即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以及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当地进行。
“正义战争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战争是正当的(justifiable)?在宗教色彩浓厚的论述里,为信仰而战是战争的最佳理由。随着宗教势力从战争理论中的逐渐淡出,正义战争论经历了从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世俗学者以及天主教学者维多利亚(Victoria)将自然法看作战争正义性的来源。这一看法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奥古斯丁、阿奎那、苏亚雷斯(Suarez)和格老秀斯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
人道主义干涉倡导者们常常引用维多利亚和被称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的观点。维多利亚表示:如果不允许无辜者给恶人一个教训的话,那么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幸福康泰①参见 Mona Fixdal and Dan Smith,“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Just War”,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No.2,1998,p.283.。格老秀斯的观点则更为系统。他认为,如果一国对其国民和其他国家国民的待遇明显违反国际法,则另一国为保护其国民或其他国家国民所从事的所谓“正义战争”是有合法依据的②参见自迟德强:《从国际法看人道主义干涉》,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从这个角度来看,人道主义干涉与正义战争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人道主义干涉旨在保护人权、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以军事手段制裁虐待和迫害本国国民的政府或独裁者,因而此种干涉应当属于正义战争谱系之内。
然而,“强者总会寻找证明自身行动正当性的理由,他们也能够找到”。如果仔细回顾近代以来“正义战争”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正义战争论”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最早开始对外扩张的欧洲国家西班牙,需要为在南美大陆的殖民行为创造一种合理的解释,正义战争论首先出现在西班牙并不令人惊讶[1]。在维多利亚眼中,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特殊物种,“人人皆兄弟”,在“文明社会”中生活的基督徒有义务干涉“非文明社会”的内部事务,阻止如食人肉、活人献祭等“野蛮”行径。相应地,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干涉和教化行为就是“正义的征服”(just conquest)。建立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正义战争论实际上为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残酷屠戮当地土著提供了正当性支持。打着“文明传播者”旗号的殖民者对阿兹特克人等美洲土著实施了极为彻底的种族和文化灭绝,正义战争在这里只不过是强者实施镇压的借口而已。同样,格老秀斯的系统性论述也被后来欧洲各国积极引证,变成了在亚洲和非洲执行“文明使命”的理论基础。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倡导者经常引证的传统正义战争论在表述上是较为模糊的,如“善”、“恶”等价值判断在很多时候无法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衡量,这就为大国提供了按照自身需要进行选择和操纵的空间。相对而言,当代正义战争论在判定战争性质上的规定更为具体和严格。当代正义战争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正义战争论承认政治和权力现实。在各种讨论战争正义性的理论中,正义战争论对国际社会运行的现实表现了充分的接受。它认为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甚至是最重要的行为体③Leslie Burn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 and Just War:Legal,Moral,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Air University,Apr.2000.。(2)正义战争论认为,人类世界是不完美的,行为结果在道义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一般认为,正义战争论包含了三种道德传统,即义务论(deontology)、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和德行论(virtue ethics)。义务论强调行为者所肩负的法律义务(duty);结果论则根据行为的效果(effects)来判定行为的性质;而德行论则强调行为者本身的特征(character of the actor),如行为者是否为合法主体、是否具有良好意图等对行为的判定作用④Mona Fixdal and Dan Smith,“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Just War”,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2,No.2,1998.。(3)正义战争论承认世界并不完美,由于行为者意图和结果时常相互分离,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考虑战争或干涉的正当性。当代正义战争论提倡一种个案式的处理方法,即根据每一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其正当性进行评判,而不是按照某一类事件笼统地进行划分。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战争论同人道主义干涉是有内在矛盾的。
在当代,以沃尔泽为代表的“正义战争”理论家们具体地发展出了六项战争正义性的原则:(1)有正义的理由,正义的理由是正义战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必须由合法权威决定使用武力;(3)使用武力必须是最后手段;(4)战争可能造成的伤害与可能实现的正义相比,必须是相称的,即战争所实现的正义必须大于所造成的损失;(5)正当的意图,正当的意图是指行为者的意图必须是良好的,不能别有用心;(6)战争至少必须有成功的可能。
然而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使用正义战争思想为干涉行为背书时大都只借用了其最为空泛的概念,即为了正义事业可以使用武力。很少有研究者真正运用当代正义战争的标准衡量人道主义干涉的行为。以上六项原则包括了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两个部分,它不仅关注国家使用武力的目的和理由,也强调国家使用武力的过程。这避免了仅仅强调任何单一方面所造成的正当性的缺失。
如果严格按照当代正义战争的标准,即使完全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军事干涉也只能部分满足正义战争论的要求。这些内容包括:(1)行动目标是纯粹为了拯救人的生命,这一点构成了沃尔泽所说的“例外情况”;(2)行动选择是不可替代的,即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人的生命;(3)行动过程的无害性,即不造成与拯救人命无关的其他伤害。即便如此,人道主义干涉在正当性上仍有缺失,重点就在于对授权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权威是谁没有明确的表述。对于合法的权威,无论是新干涉主义还是“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论述都不能满足正义战争论的要求。新干涉主义认为,国家自身就有权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相当于认为国家不经授权就可以使用武力,自然不符合要求。“保护的责任”的论述则较为复杂,它首先认为联合国是一种当然的合法权威,具有授权行使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力①参见加拿大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中文版)》中关于授权的讨论。。在肯定联合国的地位之后,“保护的责任”却从这一立场退却,认为当联合国无法授权时,其他国际组织如北约也可以成为合法授权来源。这无疑也相当于解除了干涉者在授权问题上受到的限制。这种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的解读方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行为合法性的。理想化的人道主义干涉在授权问题上的缺失导致了正当性的先天不足,而在具体实践行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是造成冷战后几乎没有一次“人道主义干涉”可以称得上是正当的。
因此,当代正义战争论的代表人物沃尔泽对于人道主义干涉也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极端情况下,人道主义干涉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外”而获得行动的正当性。但由于可能导致国家滥用干涉的情况,因此必须对人道主义干涉加以控制。
二、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基础冲突
从法律意义上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以下将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探寻人道主义干涉的基础及其缺失。
部分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认为,国家具有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这种权利来自于国际人权法。国际人权法的产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纳粹的暴行,使得人权观念在战后获得一次飞跃式的进展。正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世界人权标准的确立是“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这是“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2]。尽管《世界人权宣言》还属于一种原则上的宣示,但它的确是人权发展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世界人权宣言》和在1966年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架构。
在此之后,国际法层面对人权设定了一系列的保护规则。根据1977年联合国大会《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规定,以下三种行为可以划入人权的国际保护范畴:一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及其他国家的民族自决权、自然资源主权、发展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权利的大规模严重侵害;二是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大规模制造和迫害难民、宣传战争、鼓吹法西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贩毒等;三是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恶意违反公约规定、不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而侵犯人权的行为[3]。
公允地讲,人权保护从国内层次上升到国际层次是一种进步。《世界人权宣言》也获得了当时与会各国的一致通过。然而,当深入到具体保护议题时,各国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在起草了十多年后才于1966年最终获得通过,后来又费时10年才正式生效。美国至今也没有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2年,根据《罗马规约》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依国际法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实施管辖权,这可以算作人权国际保护迈出的实质性一步。然而,冷战后将人权作为重要政策指导的美国却拒绝签署《罗马规约》。美国的消极态度使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大打折扣。美国不签署《罗马规约》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于自身主权的保护意识强烈,它不能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否则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和外交人员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追诉的对象。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美国在伊拉克虐囚丑闻爆发后百般阻挠相关调查,并将有明确证据指证犯下虐待罪行的士兵交由国内军事法院进行审理。
由于从条约法方面寻找的支持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基础十分薄弱,因此人道主义干涉提倡者们往往转而从国际习惯法中寻找支持,即希望从人道主义干涉与现行国际法的关系入手建立干涉的正当性。国际习惯法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其构成要素有两个:一是国家的实践;二是法律确信,二者分别代表了习惯法在物质和心理两方面的要素。国家的实践是指习惯规则的形成和存在需要有普遍的国家实践……国家实践应具有共同性和广泛性[4]。换言之,国际法中的习惯首先需要国家在实践中持续、反复地坚持一种行为模式,形成所谓的“通例”。而法律确信则是指国家认为其有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法定义务,即通例被“接受为法律者”[5]。他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不但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还包括普遍尊重和保护人权。在国际法体系中,二者没有层级之分。《宪章》序言中“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被认为暗含了国家有为保护人权而实施干涉的权利。从习惯法的角度看,人道主义干涉倡导者认为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大量存在的,多数国际法学家普遍支持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行动。方廷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只有少数学者坚持否定这种学说的有效性。虽然对于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诉诸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人道主义干涉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本身已被广泛地接受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①参见魏宗雷 邱桂荣孙 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对于人道主义干涉倡导者的观点,亨金提出了反驳。他认为《联合国宪章》将和平宣布为最高价值,不仅是为保障国家自治,而且是为所有人获取根本的秩序,它宣布了和平比国家间的正义更为迫切,甚至比人权或其他的价值更迫切[6]。尽管联合国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人权问题,联合国秘书长也多次发表谈话认为联合国需要改革以应对人道主义问题,但从《联合国宪章》的立法原意来说,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位居首位。有学者明确地表示:毫无疑问,1945年联合国的缔造者们将国际和平置于其他价值之上,这才是联合国创立之初的真实意思表达。国际习惯法是指经过长期实践和使用所形成的为历代民众所肯定的惯常做法,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效力,并以不成文的形式对人们产生拘束力,并且各国认识到行为中有法律的约束力[7]。而人道主义干涉历史已经表明,在冷战期间,带有较为明显的人道救援结果的干涉行为从来没有被承认为合法行为。冷战后,干涉实施者是极少数大国,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无力也无意进行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对“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保持着强烈的反对态度。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干涉”也大多是大国为帝国主义扩张寻找的借口而已,根本无法构成持续和稳定的反复实践。
综上所述,国际法上对跨越国界的人权保护尚未达成共识,更远没有达到赋予国家人道主义干涉权力的地步。人道主义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立法精神,也与国际习惯法相去甚远。因此,在现有国际法上缺少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发展的空间。
人道主义干涉的提倡者们从道义原则、政治伦理和国际法等基础出发建立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具有重大缺陷,其援引的主要思想渊源和法律根据并不能有效支持其正当性论述。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同当前主权国家体系秩序存在强烈冲突。由《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尽管在实践中主权国家内部可能存在种种问题,主权原则因此也饱受诟病,但作为一种政治权威,该原则本身仍是中小国家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抵御强权、维护秩序的最佳且唯一的选择。由人道主义干涉倡导者所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论述无疑都是对国家主权在法理上的削弱,将严重影响现行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行,其所导致的法律和政治后果都是极其严重的。
[1]Bhikhu Parekh,Rethink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1).
[2]《世界人权宣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udhr
[3]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Alternative Approaches and Ways and Means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UN Doc.A/Res./32/130/1977,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2/ares32r130.pdf
[4][5]蒂莫西·希利尔:《国际公法原理》,曲 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4页。
[6]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Dordrecht:Nijhoff Press.1995,p.102.
[7]杨泽伟:《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