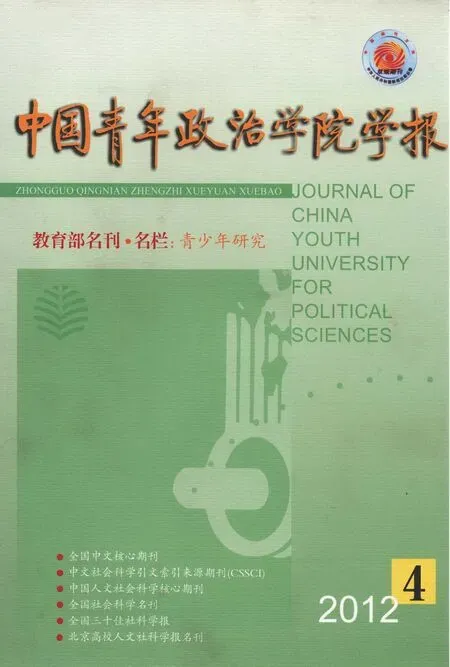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皇 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北京100089)
近年来中国公共危机频发,公共危机治理成为考验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危机状态下,政府需要迅速集中各种资源应对危机,因而危机的应对需要强有力的、迅速的动员。中国近年来若干次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都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政治动员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释放,资源得到整合,从而在短时间内形成解决危机的巨大社会合力。在中西方公共危机治理比较中,西方的危机治理强在制度,中国的危机治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这一工具就成为当前提高中国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议题之一。为此,需要首先分析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政治动员的具体方式以及其运行机理。
一、公共危机治理与政治动员
公共危机是与一般危机相对应,是指对社会公众具有巨大现实或潜在危险(危害或风险)的事件[1],(公共)危机是一种决策情境,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作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2]。公共危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科学的公共危机治理理念指导下,为了预防危机发生,减轻危机所造成的损害,尽早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所采取的治理行动。公共危机治理大体上包括(危机发生前的)事前治理、(危机发生后的)事中治理和(危机结束后的)事后治理。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政治动员是资源集中的一般过程。如汤森所界定的,政治动员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3]。具体来讲,政治动员是指政治动员主体通过宣传教育、利益激励和组织强制等各项活动获取资源,发动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得到社会成员的支持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这其中的资源包括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情感、认同)的资源。作为一个广义的资源汲取和控制的过程,动员的主体可以是官僚机构也可以是市民社会的团体或个人[4],而政治动员的主体只能是政治官僚机构,在中国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因而政治动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迫性、高度不确定性及处理的非程序性,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有效地应对危机,就需要动员整合和调动各种资源、促进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调适社会心理并维持政治稳定。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可以提供财力人力物力的支持,还能帮助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同时监督和约束政府,因而,政治动员对于公共危机治理非常重要。就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来说,由于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较为发达,在民主、自治、社会信任、平等开放以及法治的西方市民社会的文化语境下,面对公共危机,西方国家的民众会积极地以个人或者组织的形式参与并动员特定人群参与到公共危机的应对中。而中国在公共危机发生时,由于市民社会不发达,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动员相对西方国家较弱,面对公共危机严重的危害、紧迫的解决时间和有限的资源,运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动员民众,汲取一切资源以形成合力应对危机当然就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工具的首选。尽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逐渐兴起,社会动员出现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和现代化的特点,我国在近中期建立如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分立和竞争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较小。而政治动员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使用,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动员方式,是我国党和政府最为熟悉的治理工具之一,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和体制惯性。同时,政治动员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党和政府的组织体制和权力运作模式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相契合,在危机治理中常常取得较好的效果。因而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发生根本变化,政治动员就始终是我国危机治理的工具之一。
二、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从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来看,根据政治动员针对的对象和运行的机制,我国主要有两类政治动员方式:开放式政治动员和内控式政治动员。
开放式政治动员是一种针对全社会的政治动员,是一种社会性政治动员。开放式政治动员的客体包括党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军队官兵、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民众以及危机利益相关者,且动员是针对动员客体群体;从横向来说开放式政治动员的幅度较广,从纵向来说动员的层次较深,可至基层。同时动员的力度和强度较大,其动员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危机治理的事中阶段,根据危机治理情况可能持续到危机治理的事后阶段,但是在事后阶段其力度减弱。从政治动员的方式来看,开放式政治动员的具体形式主要包括:(1)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党和政府通过倡议、宣言、声明、标语口号等进行动员,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大力宣传,运用歌曲、晚会等文艺活动进行宣传等。(2)典型示范。通过树立典型,宣扬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号召向英雄模范学习来进行动员。
内控式政治动员是针对特定客体的动员,主要是针对危机发生地特定客体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内控式政治动员强调将动员控制在特定区域内,其动员对象主要包括相关党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军队官兵、公共危机发生当地的民众和危机利益相关者,对于这些动员客体,既有针对危机发生当地普通民众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针对利益相关者个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内控式政治动员的幅度大多局限于危机发生当地,对于公共危机发生地之外的民众仅仅是澄清事实,且报道宣传适度,以免引起反效果。但其动员的层次较深,动员的力度也较大,动员在危机治理的事中阶段,并主要持续到危机治理的事后阶段。动员的形式主要包括:(1)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培训、教育,做思想工作,或者与他们谈心,以了解他们的心理障碍,引导他们理性思考和分析,解决思想问题,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2)针对党政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军队官兵、公共危机发生当地的民众进行群体思想政治工作,其具体形式包括:学习文件、举办报告会和讲座、广泛宣传、典型示范等。
控制是两类政治动员的起点并且贯穿政治动员的全过程。首先,动员主体要控制危机事态的蔓延,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其次,当运用政治动员将人民动员起来,广泛参与到危机的应对中时,动员主体需要控制使得这种参与是在动员主体设定的规范的渠道之内,防止其“失范”、“失序”,不仅不利于危机的应对,反而引起新的危机。这两类政治动员在动员的具体形式方面可能相同,例如,在开放式政治动员和内控式政治动员中都可能出现宣传动员和树立典型各种形式,但其动员对象和动员幅度等存在差异。同时,政治动员要想取得效果,首先有赖于一个强大高效的政权机器。所以,从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实践来看,党和政府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集中的权力运作模式是两类政治动员得以有效推行的组织基础。并且这两类动员都需要“组织控制”这种动员方式,即政府依靠党政军内部的组织系统以及各种群众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动员,以充分动员发挥党政军各级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但是,两类政治动员方式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在其发生和运行机理上。
开放式政治动员主要是以情感激发为主,理性说服为辅,目的是通过激发动员客体个体的情感促使他们形成集体行动。开放式政治动员设定基本价值主题,如以人为本、不屈奋斗、互助、团结等人类基本价值,以这些价值主题为核心,结合动员客体的实际生活,以生动的形式进行大范围、高强度地政治动员,引发动员客体的情感共鸣,以得到动员客体的认同聚合。通过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公开和广泛的宣传,开放式政治动员力图在人们在对公共危机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唤起他们心中的同情心,爱心等等,进而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内控式政治动员主要是以理性说服为主,情感激发为辅,通过给动员客体讲事实,摆道理,清除他们的思想障碍,满足他们合理的利益,唤起他们的正面情感,获得他们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支持。内控式政治动员主要包括以下层次:一是通过坦诚沟通对利益相关者讲事实、摆道理,使利益相关者保持清醒、冷静,回归价值理性;二是对利益相关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尊重、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三是对所有动员客体进行教育和价值引导,使他们的价值需求朝着对党和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一动员过程是在尊重动员客体尤其是利益相关者自身利益前提下,在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和利益相关者的私人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可资引导的平衡点,形成理性互动的过程。
三、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政治动员方式的选择与运用
根据公共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将中国的公共危机分为两类:(1)突发性灾害。此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常常是人类不可控的,如疾病传播,各种自然突发事件,其表现形式如自然灾害、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2)社会性危机。此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常常是人为的,其根源是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的基本矛盾,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政府权能体系的失效,如腐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异化形成的冲突,如宗教、民族问题等。其表现形式如罢工、集体上访、静坐、示威游行、集会、暴力抗法、大规模群体冲突等。当然,公共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常常非常复杂,其中可能既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本文对于公共危机类型的确定主要是根据起主导作用的原因和其表现形式而定的。
(一)突发性灾害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针对突发性灾害,中国主要是采用开放式政治动员为主,内控式政治动员为辅的政治动员方式。在突发性灾害情境下,由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与政府、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可以说,突发性灾害的性质是“中性的”,所以,党和政府可以广泛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危机。在突发性灾害中,动员客体对于危机事实本身没有分歧,所以动员主体可以在主导价值的引导下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发起开放式政治动员,激发动员客体的同情心、爱心等,从而形成动员的回应。但是,突发性灾害中的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与危机的相关性,可能在危机治理中对于党和政府应对措施有更多的要求,甚至可能出现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对于这一类动员客体,动员主体主要运用内控式政治动员,以针对特定对象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明党和政府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以消除他们思想上的不满,从而形成认同聚合和参与。当然,同样是突发性灾害危机,不同危机治理中政治动员的具体方式和力度有所区别,影响其使用的因素主要包括:(1)危机的情境。危机越是严重,负外部性越强,危机的影响越大,政治动员的力度越大,其使用的方式越多。(2)制度。同一类型的危机,即使影响一样大,严重程度一样,也未必使用同样的政治动员方式,政治动员的力度也未必一样,这与有没有成熟的危机治理制度有关。通常,当危机首次发生,或是虽然以前发生过,但是尚未建立成熟的危机治理制度以应对的,党和政府需要较强的政治动员。
(二)社会性危机治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在社会性危机中,动员客体常常是理性的,指导他们行为的是事实和逻辑。当然他们在危机中可能表现得情绪高涨或者情绪失控。但是他们这种极端情绪的表现是基于他们对特定事实、特定的人,对政府的制度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其根源在于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在社会性危机中,动员客体外在的情绪下面是深层次的理性。针对这样的特点,政治动员就不能仅仅是激发他们的情感,空洞的情感激发不仅不能动员他们,反而可能引致反效果。
此外,社会性危机所以产生,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矛盾。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互为因果,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跟我国现代化的方式和进程有关。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齐头并进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社会性危机的产生还与民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有直接的关系。一些公民利益受损,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有利益诉求时不得不借由非常规的手段来向政治机构和决策者提出要求满足他们的利益。社会性危机反映了部分民众对于国家政权(至少是地方政权)的不信任,对当前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和对法律公正公平的质疑。因而,社会性危机的产生与政府、与制度有关,党和政府仅仅依靠法律或者是行政的手段去应对危机是不够的,因为正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政府的不作为或者是滥用权力,这些社会性危机才产生,而且引致社会性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矛盾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所以,党和政府应对危机就不能仅仅止于运用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控制住危机局势,还需要通过内控式政治动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对民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民众解决各种矛盾,满足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重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此外,社会性危机反映的深层次的矛盾并非只是危机发生地区存在,也并非只是危机发生地的民众感受到,只是因为没有导火线,其他地区才没有出现社会性危机。所以,政府在应对这类危机时就不能运用针对全国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样可能会导致其他地区的民众对社会性危机的参与者产生同情和认同,如果在行动上也予以支持的话,就会冲击社会稳定。即使是那些没有同样感受的民众,也会因为政府的宣传而对政府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所以,党和政府在应对社会性危机时,控制政治动员,对于危机发生地之外的民众仅仅是宣传事实真相,并且控制宣传的力度和强度,防止引起反效果。而对危机发生地的动员客体,党和政府就在价值引导下对政治动员客体群体和个人讲事实、摆道理,进行内控式政治动员。这种政治动员主要围绕着“理性说服”而展开。当然,情感和理性是很难分开的。这种理性说服也是与情感结合起来的。因而,内控式政治动员是在政治动员主体设定的价值目标下进行。这种价值目标一方面帮助动员客体厘清事实,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唤起动员客体的正面情感,让他们在理性和情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政治动员的认同聚合,最终形成集体行动。当然,根据社会性危机严重程度的不同,政治动员的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
随着转型的深入,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风险”时期,种种公共危机频发。公共危机特别是重大危机发生后,社会处于紧急状态,需要全社会广泛的动员,整合和调动各种资源来应对危机。动员因而是危机治理不可缺少的内容,危机治理需要高效的动员机制支撑。处于危机高发期的中国需要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而更为有效地应用政治动员这一公共危机治理工具正是提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政治动员今后将不断完善,配合逐渐发展的社会动员在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框架下,规范地引导社会多元力量与政府协同应对危机。
[1]李燕凌 陈冬林等:《农村公共危机的经济研究及管理机制建设》,载《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薛 澜张 强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詹姆斯·R.汤森 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 速 董 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4]Amitai Etzioni.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8,(19).